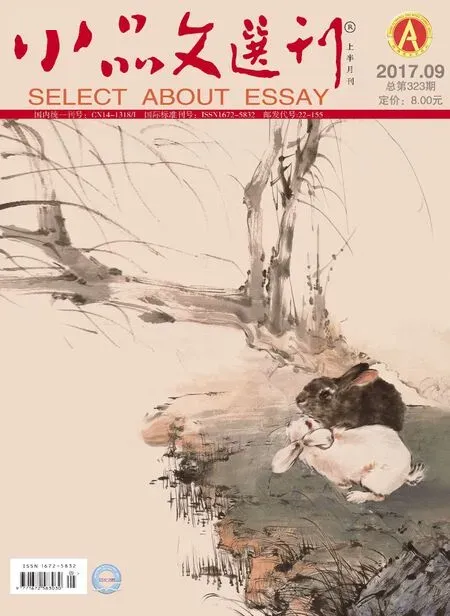共在人间
2017-09-03 10:59:15尤今
小品文选刊 2017年17期
□尤今
共在人间
□尤今

那一年,到土耳其去,住在一个仿佛与世隔绝的小农庄里。
我们下榻的农舍,住着一对年龄相加超越百岁的老夫妇。两张脸,像是皱缩成团的黑枣子,密密地布满纵横纹路。可是,他们腰不弯、背不驼,依然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生涯。
正是麦子播种的时候,还是停留在原始落后的“点播”方式,老叟走在前面,用锄头在土壤里打洞;老妪跟在后面,把麦种轻轻地撒进洞里。一行行、一亩亩地种,神情专注而满足,好似在从事一件无比庄严的事情。
傍晚,夫妻俩在厨房里烙饼而食。不起眼的古老灶子,烙出了溢着麦香的饼,大大圆圆的、热热烫烫的,含蓄的米黄色,淡淡的麦味儿。在幽幽的暮色里,两人坐在矮矮的木凳上,以枯瘦多皱但却坚实有力的手捧着饼,大口大口地吃,脸上浮现着快乐满足的笑意。
这一幕,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
活着,真好。
知足地活着,常乐。
许多人,活着而不快乐,只因不满足于他所拥有的,一心憬憧他所未知的,“共在人间说天上,不知天上忆人间”,往往坐这山,望那山、吃这碗、盼那碗;任由“欲望的树”在他心田里无止无尽地长着,长了一寸,他要一尺;长了一尺,他要一丈;眼看那“树”已经高入云霄了,可是,他还是满心焦灼地嫌那树“发育不良”。天天在欲望的“无底深潭”里浮浮沉沉,弹指间,短短数十寒暑已成过眼云烟;回首前尘,竟不知“快乐”一词如何诠释。
这个下午,和这一对萍水相逢的老夫妇共食大饼,共享快乐,是记忆里的永恒。
老夫妇教会了我,有一亩田,便诚诚恳恳地耕那一亩田;有一块饼,便快快乐乐地吃那一块饼。
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共在人间,话人间、爱人间。天上究竟有多少富贵、多少安逸,不必说,更不必盼。
选自《读者》
猜你喜欢
辽河(2023年11期)2023-12-30 10:19:06
今日农业(2022年14期)2022-09-15 01:43:58
东坡赤壁诗词(2022年1期)2022-02-25 16:31:13
金沙江文艺(2021年12期)2021-12-22 02:14:10
当代陕西(2021年13期)2021-08-06 09:24:10
青年歌声(2021年3期)2021-03-22 10:00:46
东坡赤壁诗词(2020年3期)2020-07-04 02:50:05
东坡赤壁诗词(2019年3期)2019-07-05 06:55:54
上海故事(2018年5期)2018-07-09 18:45:04
辽河(2014年10期)2014-11-05 11:2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