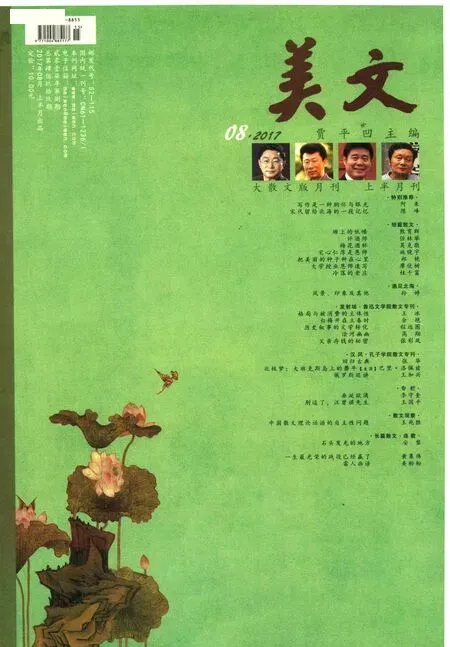历史叙事的文学转化
——评余艳《白梅开在立春时》
◎ 程远图
历史叙事的文学转化——评余艳《白梅开在立春时》
◎ 程远图

程远图 90后,就职于鲁迅文学院培训部。论文、评论、文学作品发表在《文艺争鸣》《美文》《诗探索》 等期刊杂志。
历史的痕迹,往往在沧桑荒凉之处显影。《白梅开在立春时》的作者余艳女士寻幽探密,在山林深处独自面对人迹罕至的向元姑之墓,发出深沉慨叹,回望近一个世纪前的时光,将一段哀婉绵长又满怀家国大义的故事娓娓道来。
如果说人们是被漫漫历史长河之流动所裹挟的,那么,这篇文章纪念的人物的悲欢沉浮则亦是历史在个人身上的体现。当鲜为人知的荒冢被寻访者意外发现,当那些已然被封存的过往岁月被重新唤醒,巨大的时间跨度在某个瞬间会被凝缩成点,历史上的悲喜沧桑,会与现实直接勾连。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能够获得与历史直接对话的契机。
这篇文章书写的是贺龙将军、向元姑、胡琴仙人生中的相守和相离,更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之下,个人悲喜与民族担当之间的复杂关系。余艳的叙述为夫君与向元姑之爱赋予了古典的气质,将传统乡土社会的生活与风俗、旧式姻缘与夫妻关系融入到古典审美的范畴中,而诗词意境的融入更使得故事弥漫着一层传统的美学色彩。当然,作者并没有单向度地将这种传统美学进行到底,而是以向元姑姐妹的视角引入了现代革命与觉醒的民族意识这个维度。一方面,文章中有着个人化的小叙事,讲述着夫妻之爱的真切与深挚;另一方面,也展现着时代革命的宏大图景,饱含着对历史流向的期冀与信念。
小叙事和大叙事的交错融合,小情感与大关怀的缠绕纠葛,是余艳这篇文章的一个显著特征,并且构成了叙事与美学的张力,塑造了文章厚重的历史感。文章主要从向元姑的角度切入,讲述姐妹俩对贺龙将军的爱慕,以及离别之后数十年间未能再相见的思念与苦楚。这作为个人化的小叙事,流露出悲凉哀婉的情感,向元姑不能与夫君长相厮守,只能任其在革命阵线浴血奋战、命悬一线,直到凄凉离世也没有再见上将军一面,不禁让人扼腕叹息;然而,向元姑姐妹虽是一介女流,却绝非狭隘简单的小女子,她们明辨大是大非,将对夫君之爱融入民族大义,将个人的小情感汇入波澜壮阔的革命时代;向元姑在身陷囹圄、备受折磨之时保持铮铮铁骨和凛然正气,成为坚贞不屈、具有革命气魄的女中豪杰——历史发展的大势正是在这样的千千万万的个体,在精神和实践的进取基础上凝聚而成。我们一方面认为个人是历史的产物,被历史的浪潮裹挟;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凝聚起来的千千万万的个体,则成了创造历史的主体。因此,由小叙事关联起的大叙事,由小情感汇聚起的大关怀,从文学的层面呈现出对历史、现实的深切认知,以及试图指出历史走向,为现实及未来提供可能性的使命感。
英雄主义和理想信念构成了大叙事的基调,但并非全部。文章中的贺龙将军并非仅仅指涉英雄和理想的符号,而是血肉丰满的立体形象,他心忧家国、深明大义,另外也有着日常的平凡有趣的一面,夫妻之间恩爱有加,他也会与夫人插科打诨。向元姑和胡琴仙的性格和关怀也具有丰富的面向,她们一定程度上是具有革命意识的女性,对革命的成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却不得不承认,她们身上仍然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普遍气质,她们缺乏现代的独立意识,不得不以夫君作为人生的精神依靠。实际上,中国在从传统旧社会步入现代转型的阶段,每个身在其中的个体都在历经着意识的觉醒和反复、价值观念的变革和撕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从根本上铲除传统旧观念在现实层面上是难以完成的。也正因此,新意识与旧观念在一个人的身上同时出现,才更为真实和丰满,才更有血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小叙事与大叙事之间存在着某种对立关系,两者之间的共融能使作品兼备结构的视野和个人性的丰沛情感,也更能呈现出微观历史的复杂性及其对于宏观历史走向的潜在作用。
这篇文章完成了对革命英雄大情怀与小生活的再书写,重新塑造了为民族大义舍弃个人小悲欢的英雄精神。作者把目光从当下投向深邃的过去,望向民族危难的生死关头,从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探索留给我们的民族精神遗产。在如今的繁荣年代里,那段艰苦岁月似乎早已退隐到人们记忆的角落,落满灰尘,无人问津。德国作家伯尔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一部进步史,就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当那些前辈的荣耀被后人贴上封条,送进故纸堆或博物馆,这个民族则可能会遭遇某些重要的缺失。单从文学的意义上说,在今天的文学语境中,余艳的写作具有某种特别的价值。当下文学中普遍面临历史感缺乏的困境,此外,个人主义写作趣味的盛行使文学越来越成为私人化的“亚文学”,对于世界的结构性以及总体性认知在文学中越发稀少,或者说,今天的文学越来越难以抵达使人们认清现实的目标。余艳写作的意义或许恰恰在于,她试图使我们知道,那些被逐渐淡忘的先辈的传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为今天文学面临的困境提供新的可能性,同时也引导我们思考:应当如何将作为文学资源的先辈光辉历程进行当代转化,或者说,我们如何从过去的岁月中探寻走向未来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