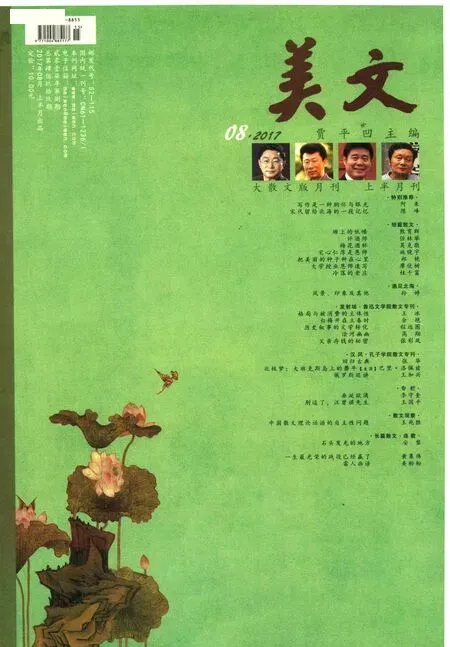冷落的老庄
◎ 桂千富
冷落的老庄
◎ 桂千富

桂千富 1965年生,先后在《美文》《延河》等发表散文、小说多篇。出版小说集《糖果》,长篇非虚构文学《你的孩子可以上清华》引起较大反响。
桂家老家在湖北省郧西县景阳乡一带的十万大山里。从漫川下高速一下子落入稠密的山峦沟壑,绕曲折的小溪行走,又爬上山,在崇山峻岭的肩上蜿蜒,忽而石头嶙峋,忽而壑渊险峻,惊情连连。弯曲的公路两旁不时有几栋参差的楼房掠过,仿佛是藤蔓上的小瓜,一个个似曾相识。这些稀拉、不同颜色的楼房组成村子,好像长在山顶的彩色大树。老家就坐落在这样的山脊上,感觉摇摇欲坠。盼望了很久,说到陡然到了,似乎少了铺垫和传奇,有点言犹未尽的意思,落入“看景不如听景”的俗套。这和许多事一样,挺高的期望,普通的结果。放眼望去,一条深沟在面前匍匐而去,两侧山峦温婉起伏,长满了桦栎、刺槐、桐子树和竹子,宛若静伏的苍龙,偶尔袅袅升起的炊烟和突然的呐喊打破寂静,感觉是龙的叹息和呼吸。我离开老家时五岁,记忆的深处摇曳着青葱的桦栎树和伸向天际的高大竹子。桦栎树爬连成一片浓荫,如同张开的无边无际的巨伞。我们在林子里爬树,捡拾树籽,躲避火焰般的太阳。桦栎树油性大,是最好的柴火。砍一捆桦栎树枝叶,一把把填进灶里,立刻听到火掠过时啪啪的快乐呻吟,叶子蜷曲由绿而红之后变成一块皱褶的锈铜,一股青葱的馨香悄然弥漫。
老家最好吃的莫过于板栗,成熟的季节,板栗啪啪坠落,砸到头上好疼,不少人爬上树打板栗,底下拾栗子的人就更受罪,不过为口福这点罪可以忽略不计。竹子高耸,冠在云里,到处萦绕着清新的竹香。孩子们搂住竹身,竹节虫似的一跃一跃爬向云端,从一个竹梢滑向另一个竹梢,行走在竹冠上,好像淘气的猴子。有一个人在竹林里拉屎,被突然冒出来的竹笋扎破了屁股,我们议论和嘲笑了好久。现在桐油树、竹子、栗子树都不多了,大部分成为桦栎树和刺槐的天下。刺槐,这个原产北美的客家树种,来到中国之后毫不羞怯,以主人的姿态和上帝的名义,迈着修长的双腿,登堂入室,攻城略地,占领了大片河山。不止如此,还一遍遍向本土树种说自己是耶稣的徒子,师傅受了魔鬼撒旦的诱惑,被犹大出卖,可怜地被钉在十字架上。要他复活,就要一点小小的迎接阳光和雨露的土地。心软的本土树种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忍受撕裂的疼痛退让。刺槐是树中的索托马约尔,总是比别的树蹿高那么一点点,先一步盛走雨水和阳光,于是乎许多地方都飘动着耶稣受难的单调黑色。
早春,万物复苏,送走了刺骨的寒风,刺槐才苏醒,照例要向上帝祷告,戴上祭奠耶稣受难时的硕大白花,摇曳耸动,祈祷,唱过落英缤纷的赞美歌之后,才褪去悲愁的黑色,着上与兄弟相似的绿色,开始新一轮的悲凄的布道。它要的根本不是星点土地,而是整个河。尽管如此,我不敢恨刺槐,它顽强的繁殖能力,它不挑不拣的居家能力,它营造的遮天蔽日的花海和绿荫,给贫瘠的陕北镀上油光锃亮的外表,让荒凉的黄土地也走起了优雅的猫步。还有,我们这些游子正是怀着刺槐一般的雄心壮志在异地生存,尽管没有它那落地生根、攻城略地的张扬效果,却实实在在吟唱着属于自己的歌谣。桦栎树是我对老家最生动的记忆,那是一个扣一扇门,每次见到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打开记忆的闸门。
洛川北部的相思川也有桦栎树,尤其是冬天,醒目而沉静,仿佛是一双温柔的小手在心里翻一本旧书:从湖北到陕西。春夏,这里的桦栎树与松柏组成了摇曳的绿色云团,随风晃动,整个大山似乎是缓慢移动的绿巨人。特别是深秋,桦栎树叶子由绿而黄最后变成深红色,与身边的松柏呼应,像龙凤在厮磨呢喃。树林里桦栎树叶子层层叠叠,像掉落的记忆碎片和生活的皲皮,走进去沙沙响,有回忆钩沉的想法。桦栎树叶子是恋家的孩子,即便是隆冬寒风的平行撕扯、大雪的垂直打击,仍然有些叶子会坚持到母亲苏醒的春天,眼见新的儿女诞生,母亲有人照顾才缓缓离去。松柏树的针叶更是不舍贫家,不做游子,一年四季都在衬托母亲的威仪。就是死了也会落在近处,手拉手织成一方厚厚的抵御严寒的棕色绵毯。
有一年我们带着干粮躺在树下,天空零碎而高远,阳光斑驳,如杜甫所言“日脚下平地”,投下来的光束温暖明亮,如光滑温柔的纤手摸抚得人痒痒的。身心倦怠,思维懒散,靡靡欲睡。偶尔清风低回,拂得小草晃动,衣襟翻飞,涛声阵阵,心也跟着晃动,完全是世外桃源的感觉。我们被世俗的东西羁绊太久,不是拼命地追求权利,就是暗暗与人攀比,浮躁、愤怒、脆弱,自然和森林才是平静的抚摸和深呼吸,如同妈妈的温暖怀抱。想必老家的林子里也是一片安逸,秋天的景色一定也很美。
桂家老庄在山腰下,沿公路往下走一公里的山路,在陡峭的桦栎树爬里穿行。过去老庄都在山腰坡和地的旁边,现在人们都往山顶路边聚集,老庄被忽视和冷落了。都说欧洲人不置房产,候鸟一样到处游弋栖息,但是他们的城市要古老得多,历史渐进的线索很明显。掩映在现代时光里的普罗旺斯和普罗夫迪夫,宛如踽踽而行的耄耋老人,一招一式都是超级慢镜头,显得沧桑恬静。那里古老的剧场至今仍琴声悠扬,演绎现代与传统剧目。反而,我们在不停地腾挪和拆迁,许多记忆遗落在荒芜之中,出现了不应该的断崖和空白。不住人自然就会被遗忘,何况我们已离别老庄这么久。小叔怕自己弄不清楚,专门叫了二爷家的老大桂龙财。
他70多岁,面庞黝黑清瘦,就像一棵古老的桦栎树,布满时光掠过的痕迹。开始我们还担心他的身体,没想到健步如飞,声音洪亮,让我好奇地不停端详。这些接地气的山中老者,比我们常坐办公室里的人强健,耐得住岁月的打磨。他一边走一边说,手指指点点,这是你们的地,那是你们的爬;你们走后,谁占了你们的地,谁住了你们的地方。俨然是这片山林的钟锤,捣得往夕和过去嗡嗡响。这里有遗憾和怨失的意思,觉得我们不该走。现在看来,走是对的,如果我们不走,依父亲的脾性和当时的处境,日子也不好过。
洛川人喜欢说,人没有前后眼也没有后悔药可吃。话说回来,有了就不是人生。人生的魅力也许就在突然的千转百回中。被动的决定不要问为什么。《日瓦戈医生》里有这么一句话,人是为生活而生,不是为准备生活而生。其实,现实中我们更多的表现是为准备应付生活的变故而手忙脚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有个著名的“费斯汀格法则”,生活中的10%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而另外的90%则是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所决定。并且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由手表的放置产生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结果。实际上,那10%往往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那一块砖,多数时候小头决定了大头。
桂家老庄盘桓在一个平缓的坳里,三面环山,一面朝沟。老家人都喜欢说是簸箕形状,背有靠山,前有流水,左右有山峁拱围,对面有山朝睹。哥哥懂点《易经》,也会看点面相和手相,经常说桂家老庄是个倒凹形,风水很好,就是朝向不好,旺财不旺人。石板房坐东面西一正九间,两厢是两层吊楼各一间,一共十一间。堂屋、卧房、客屋、灶屋、火屋、牛羊屋、柴屋、茅房,一应俱全,还有油坊。妈妈在世时常常念叨上茅房不湿脚,烧柴吃水近便。屋后有很粗的樱桃树、杏树,都会唱樱桃好吃树难栽的歌曲。记忆中我也会哼,隐隐的还有樱桃的甜香。门前有长青棕树、橘子树和高大的竹林,棕树好像一把伞架,挂满了张开的绿色雨伞;院子中央有一个莲花池,叶子宽大嫩绿,粉红花朵亭亭玉立,风雨袭来,一片窸窣。伯伯们和哥哥的描述极富画面感,我立刻想起了李商隐的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只是老家等得我们好辛苦,已经变了样了。
桂家老庄是仅次于汪家的大宅,在这一带也有名气。如画老家在我心里待了很久,原本零碎渺小,在天长日久的臆想中添砖加瓦砌得高大宏伟。被家人填得憋胀的脑子一一对号约分之后,由繁入简,空出来大片皱褶,可以修正差异和剪贴更多的东西。在陕西之所以动辄提及桂家老庄,是与我们当时的居住环境有关。记忆的重复往往与失意和得意联系。陕北人住窑洞,有石窑砖窑,最差的是土窑。我们上来时,多数人住进了石窑,我们一直蜗居在狭小危险的土窑洞里。因为是外来户,什么都慢半步,这以后成了我们无法克服的差距。就是后来有了工作与本地人的差距仍然存在,好像平行线之间的距离,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我们眼前的桂家老庄只有几间石板房,高大一点的三间,修建不久。隔开的一间低矮破旧,土墙窟窿眼睛,仿佛是时光箭镞的靶子风雨剥蚀的土丘,石板屋顶背风的地方积聚了不少桦栎树叶,有的叶子埋进尘土。房屋被岁月荒芜被人冷落,好似后妈的孩子,显现流浪者的破烂和恓惶,远没有传说的那么雄伟。
两个叔叔说这是豪华桂家老庄硕果仅存的一间,不要看现在低矮,当初可是好气派。人老回缩——洛川人说“旧”,不是名词形容词,是鲜活的动词——火焰爱抚之后慢慢萎缩。这里指人不易觉察的老去的过程。我的鞋号一年年往小里换,最终自动退出了高大上鞋店,不得不让皲裂油腻的小摊鞋匠干枯的手量脚的尺寸,告别了穿机械漂亮精致鞋的历史,也开启了生命的倒计时。皲裂的眼眶、干枯的指头,总是潜伏在真相的旁边,做出的并不豪华的鞋子却能严丝合缝地包裹着我的丝丝“旧”去的双脚。不知道房屋会不会在日月的爱抚下也“旧”。单从辉煌的唐长安城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可以断定,任何坚挺的东西都会“旧”,最终如日落一样徐徐沉到地平线下。这间石板房看上去比较谦虚,在晨光里安详恬淡,乜斜着失望和兴奋交错变化的主人。它不需要迈着觍觍的碎步迎接,完成了庇护、孵化的使命,蜕变成了一张照片或一个象征,具备了瞻仰和缅怀的崇高气质。它也知道,这次或若干次观瞻之后,就可以淡然地回到它的初始——尘埃之中。
俄罗斯作家果戈理说,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建筑是雕刻的文章和凝固的音乐。这个低矮的房屋就是孕育我们的皱缩的胎盘,它几乎不可能又十分确信地诞生了我们的生命,收藏了喜怒哀乐,然后又惜惜不舍放走了我们。内心对老庄心存向往,又带有淡淡的忧伤,不知是我们辜负了它,还是它遗弃了我们,总之有一股拧拧的劲,想中有不,不中还想。不过,它真的老了,佝偻了,“旧”得让我心里隐隐作痛,却确信无疑地释放遥远的幻境和隐约的熟悉的声音。我默默地观瞻和聆听老屋,昔日的生活情景在碘水里生动地析出来,陌生而又遥远,平静又带着浅浅的伤感,飘荡着一股若隐若现的死亡气息。房屋如此,人生也是如此,永恒是不存在的,不知道另一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相通的暗道在哪里。
英国作家克莱尔·麦克福尔写了一部小说《摆渡人》,年轻失意的女学生迪伦在去找父亲的途中遭遇火车爆炸死了,她的灵魂爬出洞,看到了山坡上眼睛冒着钴蓝色火焰的少年崔斯坦。原来他就是负责把死亡灵魂摆渡到天堂或另一个世界的灵魂摆渡人。一路上风声鹤唳,鬼影紧随,与摆渡人展开了对灵魂的血腥争夺。等到崔斯坦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把迪伦的灵魂摆渡到天堂的时候,她的心已经被他攫取,不想在这里静待父亲、母亲的到来,他们给予的全部温暖不抵这个忧郁少年钴蓝色眼睛温暖的一瞥。她独自返回,寻找去摆渡另一个灵魂的崔斯坦,他们相遇共同回到人间。小说构思奇妙,让我脆弱的心灵泡在水里久久无法打捞。这本小说被外国人写出来,不啻是一个遗憾,因为我们是那么信誓旦旦相信存在另一个世界,几千年前到现在一直有人在寻找那个秘密入口。而克莱尔·麦克福尔似乎给出了最接近的答案。我要是有幸被摆渡过去了,是不会回来的,如果不够做家人的资格,也要做父亲母亲的凳子和拐杖。因为离别得这么久,欠着铺天盖地的情感债务,让他们在重力挤压中和哒哒的远行中消磨我的生命。
老庄大部分房子拆倒重盖了,树也消失了,莲花池当然不在,当初高大的院落即使还在也不高大。记忆会长,不受岁月影响。如果不回去看,老家会长到故宫一样枝繁叶茂,鳞次栉比。院子西边是一栋两层楼房,整洁气派,显然是后来修的。或许是考虑到我们迟早要回来寻根,或许是老家桂氏人的干预,老庄正面中心没有大兴土木。人们都说汪家老庄最豪华,青砖墙,青瓦顶,盛瓦的底子都是薄砖片,屋里的地面用糯米水和黏土打成,磨得光亮,画着优美的图案,用桐油漆了一遍又一遍。老家人说走上去要绊跤子。老庄至今完好地矗立在墨绿的山坳里。金家的老庄不如我们,却有一棵远近闻名的桂花树王,直径有一米,树荫好大随阳光移动,金灿灿的小花开满枝条,如同蘸满蜂蜜香飘十里,老远都能看到蜂蝶飞舞。
“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文革”时有人要伐树,金家主人就抱住树,说要锯树先把我锯了,誓与桂花树共存亡。可能汪家也上演了舍命保老庄的一幕,不然不会毫发未损。去王家大院乔家大院游览过,可以说是家的顶峰,屋之造极,高宅深院,房间无数,雕梁画栋,生活繁剧,爱恨无边,巨起巨落。如此庞大连绵,不要说人嫉妒,连上帝都要皱眉。果然后人消失了,也还不如我们可以凭吊、念叨、叹息、回家,和另一个世界的家人发生着心灵上的对话和感应。出去的人回来都要去看看汪家老庄和桂花树王,我们也准备第二天去看。想起来叔叔怨失是有道理的,我们没有保护好老庄,能留下一点已经不错了。院子面前有一块土地,是挖了树、平掉莲花池开出来的,这是我回来看到的最平的一块地,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我对着面前的深沟和对面山峦大喊,将窝在心里的浊气换成林草清新的气息,难听的嚎叫像响箭穿过密林撞掉发黄的叶子。大家回头好奇地看我,我说不清此刻的心情,就是想呐喊。地里种的是黄豆,时值仲秋的早晨,叶子金黄,露珠在滚动,太阳普照,一地金光如同沸腾的金水热气腾腾的灼人眼睛。庄子、土地、黄豆、山林组成一幅厚实古朴的油画,特别是在对面山上眺望的时候真的有点诗情画意。龙财叔还在指指点点,庄的上面左右是你们的桦栎树爬——好大的爬,对面山坳是水田——好大一片。有水田是身份和富裕的象征,稻子和陕北的麦子一样金贵。叔叔很浓的湖北腔在山林里滚动,引发一片回应——那是的,可是个话,那比不了,都晓得的——叔叔说话喜欢带后缀,这个后缀是强调、加重,也是骄傲,一唱一和。如同口香糖,被我们贪婪地咀嚼,甜香盈口,也让我明白了爷爷不愿意上陕西和骂爸爸的原因,对老庄和爷爷有了不同的认识,增添了敬意。哥哥最得意,在叔叔们的声音里和手指间翻找着泛黄、扑满尘埃的记忆碎片,找到了当年玩游戏捉迷藏和放羊时避雨的石洞,藏在桦栎树林里,挂满了青藤和蛛网。
这个石洞如同锈迹斑斑的钥匙,勉强打开了昔日老家古旧铜锁,那些沉睡的记忆随着吱呀开门声音复活了:他说谁谁住我们的房子,和谁谁经常玩耍,人终究耐不过房子,许多人成了无法填充的空白;当然还要说到谁谁起劲地批斗爸爸,欺负我们放弃桂家老庄,他们迷失在因果报应的迷雾里。得意与叹息又在老庄回响。桂家老庄基本符合我模糊的记忆,爬里的树没有那么高大幽闭,它也没有躲过时世的风雨,已经很不错了。记忆中石头下面的泉池还在,离家很近,哥哥说是里沟——我们挑水的泉子,没见到水,落满了枯叶。我无数次重复的记忆,是妈妈上地把我放在水池旁,水清澈见底,水草嫩绿,灰色水马滑行,五彩蜻蜓低回——那是我年幼的心里挂了很久的画。可能受到诱惑,我掉进冰凉的水里,一条绿色的蛇甩着灵巧的身子逶迤而来,绕我转圈。我知道蛇,和死亡有关,因而吓得大哭,幼稚的心灵第一次面对残酷的死亡。怎么逃脱的已经忘了,这个画面陨石一样从此砸进我的梦里,温吞地撕扯着我脆弱的神经。
哥哥说,水泉不大,水浅,草蛇不咬人。这个泉子真的不大,几乎无法上演动魄的梦魇。人生总要面临许多入侵者,谜一般诡异,像讨厌的痦子、丢人的臭屁一样终生伴随。泉子也要掏,不然泉眼就会被堵住,被岁月的泥页一点点抹平。在陕西每隔几年就要掏泉子,而且是家家要参与的具有宗教仪式的活动。谁不参加就不好意思挑水。自来水到家了,这些潜伏在石缝里的泉水被忽视,在枯叶下默默流淌,遇到断崖和石头有了叮咚的声响。丝丝缕缕的泉水汇到沟底就有了气势和力量,舔舐得坚硬的石头沟壑深深,绳纹一样扭转,声音被一叠叠的水潭放大,蛇行在空气里。哥哥说沿沟底前行有个石门子,两面石山高耸,在天际几乎挨住,巨大的桦栎树枝叶交错,石崖嶙峋,仰望上去,一线天若隐若现。风在那里低回呜咽,树冠摇曳,碎石枯叶飞掠,热闹非凡又惊悚,如同在排练惊心动魄的神怪剧目。那里凉爽,队上经常召开会议。不幸的是当天下午就下雨了,原本第二天去石门子和汪家金家老庄的设想泡汤。世上没有完美的事,那怕是回老家这么简单。叔叔说好,留个念想再回来。我们都说可是个话。老家人说我们是稀客,带来了雨水。其实这是高抬我们。这里到处是树林,雾气蒸腾,雨水经常光顾。
雨中的桂家老庄模糊而妖娆,丝丝白雾从千沟万壑里升起,如同千万条倒流的溪水飞上天际,整个天空迷失在奔腾的浪涛里。雨时大时小,打在石板上树上发出忽起忽落的声响,像万物贪婪狂饮的吸溜。那片金贵的豆地,就像从天上坠落的明亮弦月,风雨在豆地里弄出一番动静,仿佛吴刚在轻啜桂花、美酒、嫦娥在翩翩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