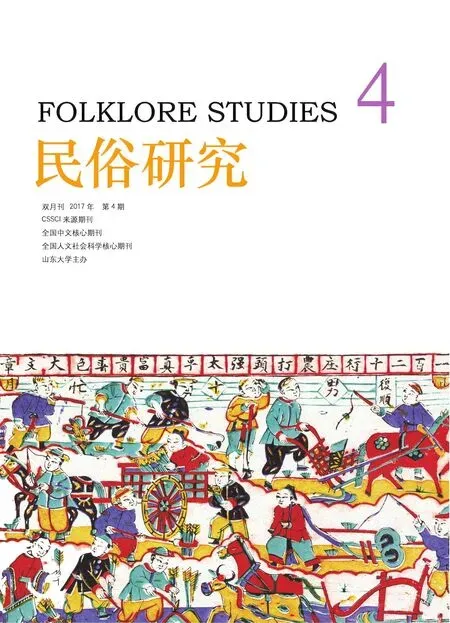一种传统武力陋习的考察及对当代的警示
郑国华
一种传统武力陋习的考察及对当代的警示
郑国华
中国农村通过选择武力的方式来解决民间纠纷问题,是中国乡土社会流传已久的陋习。旧中国乡土社会村民解决村际纠纷的方式会不约而同地选择民间调解的武力手段,从而建立了武力规制下的村落秩序,并形成了一种武力陋习。武力陋习形成的根源是政府的腐败、不作为导致的司法离场,以及村民对“江湖好汉”的推崇、行动的算计和话语权的争夺。在当今的乡土中国,这种武力陋习死灰复燃,以非常迅猛的速度在乡村蔓延并与司法共生,扰乱了社会秩序,危害了公共安全。要消解这种武力陋习,必须重新审视我们政府在农村治理上的粗暴行为,以及进一步规范民间体育社团,合理引导民间体育社团的良性竞争,以及通过法治和村民自治的有效融合,满足农民的公正性诉求。
武力;法治;乡土社会;权威;村落秩序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农村通过选择武力的方式来解决村际纠纷问题,是中国乡土社会流传已久的陋习。该陋习选择的武力手段较多,如“跳油锅捞铜钱”“穿铁靴量河面”“摆擂台比武械斗”等等,广大乡民都耳熟能详。在当今的中国乡土社会,仍留存着大量为纪念武力争执中的英雄而建的庙宇以及碑文遗迹等,这些庙宇和遗迹大多是乡民根据县志、史料或者旧时遗迹修复建造而成。每一座庙宇和碑文都与一个或几个英雄好汉的故事相关,虽故事的英雄人物不同,但武力内容相似。每年村民都有在庙宇烧香祭拜的习俗,这不但反映了中国乡土社会对武力英雄的崇敬,更反映了武力陋习确定的村际纠纷解决方式在地方社会所具有的权威。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影响社会安定和谐的祸根。
然而,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落后时代乡土中国在村际纠纷解决或分配公共资源时,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选择武力手段,或者以牺牲自己生命为代价的残酷手段呢?武力陋习对于乡土社会而言,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当今社会如何规避这种武力陋习死灰复燃?
中国学界在近几年来的研究中,对上述问题也有所关注,如赵世瑜就对山西汾水流域中的“油锅捞钱”分配水源的现象进行了解释,认为是“不同地位的村落、宗族势力获取水资源控制权的一种手段”,认为“水资源的公共物品特性及其随之而来的产权界定困难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赵世瑜:《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和象征》,《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但是,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乡民们会选择武力的手段来解决纠纷。张俊峰的研究也认为,“油锅捞钱和三七分水是本身不公平存在的根源,三七分水与民间水利纠纷之间存在必然关联”*张俊峰:《油锅捞钱与三七分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4期。,也只是论述了“油锅捞钱”与“三七分水”何者为因、何者为果的问题。与此类似的,还有胡其伟、华雯文、赵鹏飞、韩峙、贺海波、周磊等对乡土中国村际纠纷的解释,认为塑造英雄是个别村落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获取权利的心理,通过英雄事件来构建地方社会的空间秩序。*分别参见胡其伟:《民国以来沂沭泗流域环境变迁与水利纠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华雯文:《社会保障:规避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机制——基于J省的个案分析》,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赵鹏飞:《生产安全突发事件下个体与群体心理交互作用及对策研究》,中国矿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韩峙:《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群体性事件研究》,哈尔滨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贺海坡:《差序治理: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分层互动——以后税费时期花镇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周磊:《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群体行为演化机理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4。因此,既得利益者或利益丧失者又想将利益分配格局重新洗牌,这必然为武力陋习留有了生存的空间。与此不同,英国学者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在对中国山西村落纠纷问题的研究中指出,“油锅捞钱所体现的暴力手段,是民间社会争取水资源控制权的重要手段,它不同于官方出于维护儒家伦理道德而主张的公共资源必须公平分配的立场。油锅捞钱与乡村用水过程中其他使用武力的事件一样,构成了一套不同于儒家正统道德伦理的价值体系”*[英]沈艾娣:《道德、权力与晋水水利系统》,《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年第1期。。沈艾娣的认识,显示了可以从村民行动的策略和村落权威与秩序的维护角度思考武力陋习的民间存在根源,对该文的研究具有启发性。
总之,上述研究基本反映了当前学界对于本论文提出问题的研究进展。虽然前人的研究对解决本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却并未根本解决本文所关注三个问题,因此仍就存在深入研究的可能。为此,本文将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中国有代表性的村落为案例中心,探讨武力陋习在中国乡土社会中的缘起及如何消解。
二、案例分析:中国传统社会村际纠纷解决的武力陋习
(一)黄淮流域村际湖田产权之争
中国的黄淮流域,自古为鱼米之乡,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长期的战乱使这一区域的村民养成了尚武的风气,故此地民风彪悍,性格刚烈,偶遇纠纷便易冲动,一般诉诸武力解决。
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决口于河南省兰考县,山东、江苏部分县市均被淹,难民无数。洪水退后,冲出荒田无数。江苏、山东难民便争相前往开垦耕种。但灾难之年,土匪、流寇较多。于是,难民以若干村落或家族结为团体,打造兵器,修筑堡寨,成立“湖团”*湖团,是湖田产权范围内村民自发成立的民间自卫组织,其目的是保护自己村寨利益不受外人侵犯。湖团一般推选勇武之人为首领,农闲时节率年轻村民进行武术操练,以抵抗外侵。而自保。“江苏铜、沛两县,自黄河退涸,变为荒田,山东曹、济等属民陆续前往,创立湖团,相率垦种。”*《清史稿》卷一百二十《食货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3485页。咸丰九年(1859),黄淮流域“湖团”众多,仅在铜山县,从北至南就有“魏团、任团、北王团、唐团、北赵团、南王团、南赵团、于团、睢团、侯团等十余湖团”*民国《铜山县志》卷十五《田赋》。。而当时部分“湖团”人数众多,如唐团人数达数万之众。这些新开垦的湖田,有些是以前有主的良田,现在既已被外乡人霸占,原本地村民自是不服,便也建立新团与这些“湖团”抗衡,“铜、沛土民因客民占垦,日相控斗”*《清史稿》卷一百二十《食货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3485页。,也经常出现“新团”被“湖团”兼并的情况。清政府最初是想将外来人员驱逐回原籍,但后来看到“湖团”人员众多,势力越来越大,无法控制,便也不了了之。“湖团”成立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经常不惜损害别的村落利益,故“湖团”之间因作业范围之争,也经常械斗。武力强悍者,自然占得更多的利益。更甚者,每年洪水和枯水季节,各“湖团”为自保,不让自己的湖田被洪水淹没,以及使自己的湖田在枯水季节有水可用,在黄淮流域自建堤坝和水闸,在洪水季节堵住黄河之水不流经自己的村落,在枯水季节又开闸引水灌溉。对自己村落有利的事情,可能对别的村落就是有害的。黄淮流域在洪水季节将下游堵住,上游的村落必然受灾,于是经常发生黄淮上下游的“湖团”率村民械斗的事情。胜者挖开对方堤坝泄洪,以保自己村落和村民,而败者村落的村民只能四散离乡逃命。这类行为至光绪三十年(1904)更是得到官府暗中认同,“只要百姓出钱承领土地,官府便发土地红契,其它自保行为也被视为合理”*《清史稿》卷一百二十《食货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3485页。。自此,村际为产权之争的械斗更不可开交,村落“民团”组织得到更大的发展,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引发了大洪灾。“山东省甄城县一带民间堤坝决口,引发下游水位高涨,各地民堰决口,江苏、山东27个县,8700余个村庄被洪水淹没,淹死3065人。”*山东省水利史志编辑室编:《山东省志·水利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9页。
(二)赣江流域的村际纠纷
赣江流域村落间发生纠纷的类型,大体可分为水利纠纷、产业纠纷和姻亲纠纷等。村际间纠纷产生的原因主要和村民的性格特点有关:刚悍性急,又特别好面子,“喜争好讼”,故村际间的摩擦较多。
根据赣江流域村民的水田生产习惯,在7月份至12月份干旱季节,村民一般需要筑坝蓄水,引水入农田沟渠用于灌溉。上游筑坝,必然导致下游村民更为缺水,于是村际纠纷必将激化。如据江西档案馆案宗记载,民国二十五年(1936)新建县庵下熊村与石麓施村就为争水而发生纠纷。两村毗邻,熊村的水源必途经施村的沟渠分水而下。而施村分水到熊村的沟渠经过新修要比原来的沟渠高出少许,这样水流入施村的水量就大增,而流入熊村的水量却较往年少很多,稍遇天旱,流入熊村的沟渠更是基本断流。熊姓村民百余号人执锄头到施村的分水渠,将流往施村的水源堵住,提高水位,让水径直流入熊村沟渠。如此施姓村民自是不服,村民全部出动执器械争斗、抢水。结果施姓村民斗败,觉得很没有面子,便花重金从外地请来武师外援与熊村争斗,一来一往,两村人死伤无数。最后官府出面调解,令修建筑坝不高不矮,两村水量刚好合适为宜。*《呈为施姓新建筑坝口妨害水利恳请令县派员勘验秉公处置遵约履行而免命祸由》,江西省档案馆,全宗号:J023-01-06085。
据抚州府志记载,赣江的支流抚河区域村落基本以撒网捕鱼为生,而由于抚河是公共资源,捕鱼作业区域没有划分,村民经常为争夺河面范围而械斗。明清时期,村民呈文临川县衙,请求划分捕鱼水面。但是官府不管,导致村际间矛盾越来越大,异村的人,只要在河面上碰面,便相械斗,毁船撕网,死人的事常有发生。当时抚河流域文昌桥段几个较大的村子,如杨家村、付家村、赵家村等便派代表商议,既然官府不管,便自己管。最后商议的结果是效仿古人穿铁靴量地盘的方法,各村派代表穿上被碳火烧红的铁靴,自文昌桥上首的清风门城墙根沿着抚州堤往下跑,跑过的距离便为该村将来捕鱼的区域,它村不能越界。杨姓村民便穿起烧红的铁靴自起点一直往下游跑,当他坚持跑到自己村子的旁边时,倒下断了气。其他村民看到后,再不敢派代表出来穿铁靴。自此,杨姓村民跑过的这一段河面称为“杨打渔”,按约定仅限杨家村的人在此捕鱼,其他村子渔民也不再越界。
(三)渭水流域地区村际纠纷
中国渭水流域主要分布在陕西省的中部,历史上称为关中地区。渭水流域最早的村际纠纷源于何时,史料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根据各种材料分析,唐代以后该地区村际由于生产、生活资料权限的不明确或越权使用而导致的冲突是非常频繁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到清末民初时,关中地区的村际纠纷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都是以前不能比拟的,这在当时的史料中多有体现”*萧正洪:《历史时期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中的水权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另据张光廷关于《陕西省最近二十年农田水利纠纷之检讨》的统计,民国四年到民国二十三年(1916一1934年)这20年间,关中地区由于村际纠纷而引发大型械斗的事件多达41件。*张光廷:《陕西省最近二十年来农田水利纠纷之检讨》,《陕西水利季报》第1卷第1期,1936年9月。这种因村际纠纷引发的武力械斗,最常见的表现为生产资料使用权和公共资源占有的纠纷。
如陕西周至县大庄村与南堡村于民国十八年(1929)6月,因争水而引发的村际械斗。两村之间有一眼泉水流过村庄,村民历来依靠泉水灌溉农田。但该年天旱,水量稀少,两村村民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希望获得更多的水量,便组织村中年轻力壮的村民,手执器械守护泉水,引泉水流经自己的村庄农田,水量的分配便成了争执的焦点。大庄村认为自己村中农田数量多于南堡村,故分水量应该相对多一些,应四六分水;南淇堡村则认为水是公共资源,应该村际均分,仅赞成五五分水。于是,两村互不相让,各执器械大打出手,各村都有数十村民伤亡。政府在调解村际纠纷时也效果甚微,历来法不责众,不了了之。最终因大庄村人多势众,武力强悍,而达成三七分水之约。南堡村也仅暂时臣服于大庄村的武力威慑之下,很不服气,来年便重组武力进行争斗,乃至两村各成立村寨民团,委命村寨中勇武者或长于武术、搏斗之人负责日夜操练村民,以备来年分水之争。
同样的案例还有长安县水寨村与徐家寨村的农田产权之争和分水灌溉之争。这两村每年在春播来临之前都要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村际械斗,获胜者将有权决定当年农田产权的划分和灌溉分水量,械斗长达数十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方得政府合理解决。
而在清末民初之时,经查阅当时的碑刻资料*渭南地区水利志编纂办公室:《渭南地区水利碑褐集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3页。和民间族谱、村志资料*刘屏山:《清峪河各渠记事薄》,中华书局,2003年,第1-12页。,渭水流域中的径阳县、三原县、富平县农田产权和水利纠纷最为激烈。这三个县基本上是回民村寨和汉人村寨小聚居的地方,回汉农田产权、水利、生活习俗等都存在非常大的矛盾。同治元年(1862)四月,终引发大型械斗。各回民村和汉人村自组织民团相互厮杀,械斗从一个回民村开始引发,尔后多村参与械斗,最终发展成为三个县的回汉村民冲突,一直持续至十二月。此次械斗共死伤七万余人,各村房屋被大量烧毁。*赵鹏飞:《生产安全突发事件下个体与群体心理交互作用及对策研究》,中国矿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四)汾水流域的村际之争
汾水流域位于山西省西北,经山西宁武、太原,一路南下汇入黄河,是当地江河水的主要汇集带。晋水又是汾水的支流,流经30多个村落。晋水的源头位于晋祠的难老泉,而难老泉水流出的地方,则用一石坝阻拦。石坝下方凿有十个圆孔,用于分水。“北七孔,分水七分,所谓北渎是也;东流名北河,南三孔,分水三分,所谓南渎是也”,*刘大鹏:《晋祠志》卷三十《河例·石塘》,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70页。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七分水。据《晋祠志》记载:晋南和晋北村落的农民经常为分水灌溉而武力械斗,天越干旱,武力械斗就越厉害,经常命案不断。官府便以调解纠纷为由,在难老泉边架起一口大油锅,煮沸,然后放入十枚铜钱,要求南北各村派勇武之人跳入油锅中取出铜钱,并按各村代表取出铜钱的数量进行分水。晋南村落无人敢跳入油锅取铜钱,被吓跑了;晋北村落的张姓青年则奋勇跳入油锅,取出7枚铜钱,从而晋北获得七分水量。自此,晋南村落和晋北村落就分水问题再无争议。但是,张姓青年后来因为烫伤过重而死亡,后人感恩于他的英勇牺牲,便将他的骸骨埋于难老泉下,立碑纪念。后来,“跳油锅捞铜钱”的村际纠纷解决方式,便在汾水和晋水流域广泛传播和相互效仿起来。
清道光年间,晋北有两大产业,一是赤桥村的洗纸业,二是陆堡河村的磨碾业。水是两村产业发展必不可少的资源,而产业用水和农业用水也时常发生冲突。因此,争水便成了两村常年最大的纠纷。两村村民为了尽量获得更多的水源,分别在村中训练民团,执棍棒到上游抢水。今天赤桥村组织民团执棍棒器械打到陆堡河村,抢得水源尽流赤桥村;明天陆堡河村民又雇用更多民团、勇武之士打回赤桥村,抢回水源。这样一来一往常年不断,村民死伤无数。不得已,村中长老们效仿难老泉分水的方式,在当地源神庙架一口大油锅,里面盛满沸腾的菜油,扔进48枚铜钱,由各村好汉跳入油锅中捞钱。赤桥村民独捞得6枚,而陆堡河村民仅捞得少许,因而裁定赤桥村得水六分,而陆堡河村得水四分。*(清)叶汝芝:《介休县志》卷二《山川·水利》。
三、武力陋习的缘起
(一)武力陋习存在的传统文化基础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比武的方式来解决村际纠纷的传统,并且还往往是由官府来主持的。如据《韩非子·内储说上》所载,战国时期,魏国上地郡守李悝就曾经在当地发布“习射令”公文,强调“人之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要求那些因各类纠纷前来打官司的人,不管是谁,都必须先比试射箭,谁射箭的准确性高,官府就将裁决谁在纠纷争执中获胜,而那些射不中靶心的人,往往被官府裁决为败讼。官府的解释是只有心术正值的人,射箭的准确性才会高,才能命中靶心,而那些心生邪念和心术不正的人,射箭也一定会出现偏差。官府的这种纠纷裁决理念,地方百姓自然是群起响应,纷纷勤学苦练射箭技艺,以备将来自己发生诉讼之事时得到官府公平的裁决。当然,李悝的“习射令”有其军事战备的考虑,因为魏国地处中原,周边接邻强悍的秦国、齐国和楚国,边境村落常遭这些强邻的骚扰。只有提高地方后备兵力的防御能力,才能让老百姓过上安定的日子。故“习射令”一出,便产生了神奇的效果,上地郡的老百姓个个能征善战,射箭精准,多次击败强大秦军的入侵。而后,“习射令”也很快在各诸侯国中流传,各国的统治者几乎都认同了这一武力裁决的制度。在国家的积极推动下,以射箭为中心的武力运动迅速普及化,武力裁决也逐渐平民化。
另外,运用武力手段来解决村际纠纷还有另外两各原因。其一,中国古代社会虽然具备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但政府的行政管理并没有下达到广大的乡土社会,“皇权不下县”和“国法不下乡”是当时中国国家机构设置的现实。乡土社会的治理更多的是依靠村规民约和“自治”。其二,儒家“无讼”思想的传播。孔子是“无讼”思想的倡导者,如他在《论语·颜渊》中就指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另外,儒家典籍《无讼集·讼讼》中也大力宣扬尧舜之世的“无讼”“息讼止争”的治理,“两争者,必至之势也,圣人者其然,帮不责人之争,而但讼其曲直”*转引自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277、297页。。因此,古代中国人对诉讼是看不起的,他们认为“诉讼”本身就标注上了“道德败坏”的标签,是人性“恶”的表现。然而,任何时代,社会纠纷和争议事件都是避免不了的。既然,乡土社会“国法不下乡”,社会又不主张“诉讼”,那么当纠纷和争议发生时,社会必定会选择大家可以接受的裁决方法。因此,有传统社会文化基础的如“习射令”般的“射箭定讼”方式,必然会被大家所选择,甚至根据各民族自身特点加以发展。
(二)村际纠纷解决途径的便利性选择
中国传统社会关于村际纠纷的解决一般采用两种途径,即政府仲裁和民间调解,而采用民间调解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民间调解是指发生纠纷的双方,邀请第三者(某些地方也称为“和事佬”“中间人”“公证人”等)出面进行劝解,以达到协商解决纠纷的目的。民间调解的根源在于传统的惯例和受儒家传统“无讼”“以讼为耻”的思想,不主张向政府诉讼和寻求政府仲裁,而主张用民间调解的方式来解决村际纠纷。明朝时期,邀请第三者进行民间调解的纠纷解决方式得到官方认可。《大明律集解附例》裁:“凡民间应有词状,许耆老里长准受于本亭剖理。”清代更是把民间调解和“息讼”写入圣谕*清圣祖康熙撰:《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夏炘注释,清同治九年江苏书局刊本。,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村规乡约,由村中族长和乡绅来调解村际纠纷。光绪末年、宣统初年,清政府提倡乡村自治,村际纠纷更是全部交由民间自行调解。仅当村际纠纷升级,影响较大,或出现命案时,政府才会出面进行仲裁。
1.政府仲裁
在村际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往往是先启动民间调解。纠纷的双方,邀请第三方作中间人,进行协商调解纠纷。但是,在纠纷的民间调解中,往往会发现调解的中间人或多或少会偏向于“人多势众”“武力强悍”的村落,而“弱小村落”只能忍气吞声,或者诉讼于政府,寻求政府仲裁。
在黄淮河流域的湖田产权之争中,零散的“土民”组建的“新团”,在武力上自然赶不上强悍“客民”组建的“湖团”,于是只能寻求当时清政府的仲裁。然后,清政府也因“湖团”势大,难以控制,也只能不了了之;或者提出将湖田地契重新出售,谁出的钱多,谁就有归属权。这样的政府裁决是让“客民”占有湖田合法化,对于“土民”来说,没有半点利处。官府行为看似解决了纠纷,但是深层的村际矛盾便也滋生,村民不再相信政府能公正地解决纠纷,只能另寻其它途径。
在村际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弱势的村落族群往往会寻求国家的支持与保护,希望借用国家的权威以达到公平的目的。但事实有时并非如此,如民国二十五年(1936),江西省新建县政府和司法处接受熊村争水纠纷案的起诉,派员勘查。经勘查后,熊姓村民认为新建县政府“所派勘查人员,均无水利学识,既不依据证据,复不根据事实,以致司法处判决不公,属误判和黑幕判决”*江西省档案馆:《为妨害水利一案恳请派员查勘以明真相而免诉累由》,全宗号:J023-01-06057。。民国十七年(1928)九月,渭水流域上游寇家堡与下游铁李村因村际农田用水发生纠纷,诉讼到当地政府仲裁。政府拖延两月之久,却一直未勘查审判,村际农务实在是拖延不起,自愿息讼。政府却各收两村诉讼费200多元,并罚麦粮十石。*白尔恒、[法]蓝克利、魏丕信编著:《沟洫佚闻杂录》第一集《冶清诸渠册、薄及公牍》,中华书局,2003年,第78页。同年十月,渭水流域上游冯家堡与下游东李庄发生产业纠纷,诉讼于政府,政府多月不勘审,而收诉讼费冯家堡100元以上,东李庄200元以上。最后两村请人说和,情愿撤讼,自己私了。政府则批罚小麦二十石,方才了结此案。*白尔恒、[法]蓝克利、魏丕信编著:《沟洫佚闻杂录》第一集《冶清诸渠册、薄及公牍》,中华书局,2003年,第114页。
可见,弱势族群在求得政府仲裁来解决纠纷以维护自身利益时,往往不如预期。或者由于政府行政与司法对纠纷立案所采取的原则与民间习惯不同,即出现政府认为是合法、依法处理的案件,但是民间却认为不合情、不合理。若出现政府仲裁和民间调解两种的不同结果,双方当事人当然只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处理结果,从而加大了纠纷解决的难度。当然,官府权力的界入,确实对纠纷的解决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政府纠纷解决目的只是尽快结案,大多数时候并未能解决实质问题。另外,政府在解决村际纠纷时,一般要经历漫长的勘查过程,而根本不能立刻解决村落间棘手的问题。如农田用水问题,如不马上解决,必然影响农业耕种和村民的生活。所以,村际纠纷一般不到万不得已,村民都选择民间调解,较少走政府仲裁的途径。
2.民间调解
关于中国村际纠纷的民间调解历来盛行,原因在于在村际纠纷的解决过程中,虽然政府仲裁具有权威性,但政府断案却并不一定能使村民信服,所以其约束力的时效不长。另外,政府的繁琐仲裁程序走完,需要较长时间,而村际纠纷的解决有时是等不了那么长时间的。更别说中国传统社会官府腐败,诉讼费非常高,一般老百姓是打不起官司的,“倘有因水兴讼,则立刻倾家荡产”*白尔恒、[法]蓝克利、魏丕信编著:《沟洫佚闻杂录》第一集《冶清诸渠册、薄及公牍》,中华书局,2003年,第115页。。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是不提倡诉讼的,村民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会选择打官司。一旦发生村际纠纷,双方又都认为政府靠不住的情况下,村民更愿意选择自己的调解方式来解决。一般多由发生纠纷的双方邀请第三方中间人进行调解,而这位中间人一般是当地有相当威望的乡绅或氏族长,由他出面两方说和,各提出条件,最后协商妥善解决纠纷,并由其他乡民见证。而一旦当事人反悔,再起冲突,则会被当地人认为是无信而唾弃。自此,村际纠纷能较长时间平息。
一般来说,民间调解的方式大概分为两种:第一,比武力。在司法不健全的时期,农村基本还是靠拳头说话的。而凭借拳头的威力获胜,在农村是最具信服力的。因此,当村际发生纠纷时,两村的第一选择便是相互以武力震慑对方,让对方屈服。武力震慑一般选择的方式是在公证人的见证下,各村派代表若干参与比武,获胜者从而享有更多的资源。第二,比胆识。武力和胆识在生产力落后的农村是保家保寨、获取生存资本的重要手段。因此,被农村人看得比较重,也是最让农村人信服的两个元素。比胆识,在江南农村也叫“比量”。你想获得多少资源,就看你有多少“量”。因此,当村际纠纷发生时,双方在公证人的见证下,选择一项以命相搏的方式,来威慑对方,从而让对方自动放弃争取资源,常用的方法就是前面案例中提到的“跳油锅”“穿铁靴”“摆擂台比武”等。
四、武力陋习形成的根源
(一)“江湖好汉”精神的鼓动
通过对“跳油锅捞铜钱”“穿铁靴量河面”“村落武斗”等案例中涌现的民间英雄进行调查分析,我们发现这些案例中的民间英雄直至当前还为大多数村落人津津乐道,并建庙纪念和颂扬他们的义举,这反映了中国乡土社会武力陋习的根源是村民对于“江湖好汉”的崇尚。村落“江湖好汉”精神崇尚的结果,自然是武力陋习在乡土中国的蔓延,并深入人心。拳头即代表了村落的权威与秩序!哪个村落好汉多,武力强悍,哪个村落就具有话语权,就具有维护秩序的权威,并会得到其它村落的羡慕和尊重。因此,武力会成为解决村际纠纷的最有效方式。然而,武力解决纠纷的不公平性,却也埋下了更多村际纠纷发生的隐患。
在中国的乡土社会,历来就有崇尚“江湖好汉”的传统。这种传统与村落人价值取向和道德伦理是直接相关的。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村民接受的思想教化多来自于祖辈的口耳相授,或来自于对社会生活本身的感悟。其中,评书、戏曲、民间故事是在乡土中国传播传统文化进而进行思想启蒙和教化的主要方式。村民在听书、看戏、茶余饭后的闲谈评论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而评书、戏曲、民间故事等的内容,无不取材于古代武侠小说,如《水浒英雄传》《三国演义》《杨家将》《三侠五义》等。这些古代小说又都是以宣扬仁、义、礼、智、信、忠孝、善恶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精神为主要线索的。但由于村民自身知识的局限和理解偏差,他们往往选择性地记忆和宣扬《水浒》中108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江湖好汉”精神,《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的忠义精神,《杨家将》中杨家“七郎八虎”舍生忘死的忠勇精神等。这些曲艺故事的表演和宣扬,无不在潜移默化中向乡土中国的村民灌输一种行为标准、道德伦理和价值观。而一旦在村落人自己身边发生了类似的紧急事件时,这些深藏于乡土中国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便会直接转化为村民的实际行动,并得到充分的释放和张扬。这就是在乡土中国村际间发生纠纷时,村民们一般都会选择残酷武力的方式来解决的根源,其行为实质是村民不是更多地去关注纠纷解决的结果如何,而是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容易成为“江湖好汉”的机会。
(二)村民行动的算计
通过司法仲裁来解决纠纷是理性和公正的,而以武力来解决纠纷则是非理性和野蛮的行为,是非法的。但在乡土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一些村民的行动选择根本不会去考虑什么理性和非理性,他们只考虑这种行为是否适合他们争取生存空间,所以总是基于个人的生存境况做出符合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这种行为选择被民间称为生存“智慧”或行动的算计。在乡土中国村际纠纷的案例中,武力的使用带来了调解纠纷的“不公平”,但是,村民普遍认为“不公平是看本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鲁苏两省对于洙水赵王河决口筑堤修闸及黄河改道发生争执处理情形》,全宗号:(一);案卷号:3275。。张俊峰在对中国乡土社会秩序的研究中也认为,“本事是指个人或集体动用权力资源、社会关系网络、号召力甚至暴力手段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当乡民的意识中知道政府不可信或者靠不住时,相信别人还不如相信自己。所以村落‘惯例’‘武力’是乡村社会秩序的决定因素”*张俊峰:《明清介休水案与地方社会》,行龙、杨念群主编:《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90页。。显然,氏族和村落自组建民团、壮大械斗势力所代表的武力权威,在地方秩序的建构中无疑是破坏性的,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但是在制度公信力不足的乡土中国,无疑已然成为了一套村民自己的是非曲直、善恶好坏的道德评判体系。村民一方面肯定武力在乡村秩序建立中的决定因素,却也在不断衡量双方的力量对比,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行动算计。武力惯习的强化必然引发村际械斗的发生和村落秩序的破坏,从而使弱势的一方被迫放弃自己的权力,或者采取其它更极端的残酷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三)乡村精英话语权的争夺
在乡土中国,受农业生产、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乡村精英掌握了村落的实际权力,村落管理实质是由乡村精英主导的。*黄博、刘祖云:《精英话语与村民诉求》,《求实》2012年第3期。在落后的时代,乡村精英自然是由那些武力强悍的村落能人构成的。这些人,在农业生产中,是强劳动力,劳动效率比一般人高;在村际纠纷中,又能以武力威慑对方,从而为本村带来荣耀;在战乱的年代,又能使贼人胆颤心惊,保家寨平安。因此,他容易被村落人认可,甚至追捧。在那个“拳头”就代表了权威和话语权的时代,武力强悍者便成为了村落权力的中心。当然,大多数情况下,他也成了村落秩序的维护者。谁家有个纠纷、争执,便会请他前去解决,他的话语便是村落人认可的最合理的仲裁。在黄淮河流域村落纠纷案例中,“湖团”的头目便是各村落话语的主导者,如当时势力最大的唐团头目唐守忠便是典型的代表:
唐守忠,钜野人。咸丰初(1851),为平阳屯官。四年,粤贼陷钜野,土匪窃发,守忠闻警驰归,遭匪劫,仅以身免。与乡人生员张桂梯、职员姚鸿杰等议举团练,为守卫计。旬日集义勇五千馀人,分三队,捕斩土匪数十名,贼遂遁,嘉祥、钜野间悉平。土匪惧,以所劫物展转还守忠,并乞随团剿贼,誓不为乱,守忠察其诚,纳之。时年饥人乏食,守忠使子锡龄偕张桂梯各村劝捐助赈,富出赀,贫出丁,括计馀粮,计月分给,谓之均粮,而团练之势愈固。曹州、济宁两属乡团来附,贼不得逞,去。*《清史稿》卷四九三《列传·唐守忠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5884页。
可见,唐守忠以勇武之力获得众人认可,十里八村都依附于其民团之下,从而获得话语权,不仅村人听命于他,甚至贼人也信服于他。但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这种用武力争夺获取的话语权,自然又会在下一次武力争夺失败中丢失。强悍武力者可以驱逐贼人,但自己也更容易成为贼人。
(四)政府在乡村治理上的不作为
在乡土中国,武力陋习形成的另一根源是政府在解决乡村纠纷时的不作为。乡村纠纷的发生较多源于公共资源分配和占有的不均,如土地、道路、林地、湖田、水资源等。这些资源,都属于村际间的公共资源,在产权划分上是非常艰难的,它仅可以在使用权上给予暂时的规定,而不能私有化。因此,村际间要解决这些因资源使用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必然要引入一套规制。当然,政府有一套既定的仲裁程序,然而村民选择仲裁的程序费用太高,一般老百姓打不起官司;或者政府办事效率低,仲裁程序走完所要花费的时间非常长,老百姓耗不起。自然,由于村民对这套程序并不信任,从而使政府在村民心中失去了公信力。因此,民间调解成为村民选择村际间纠纷解决的主要手段。
由于政府的不作为,民间武力解决纠纷的方式便为村民所热衷,于是自然“跳油锅捞铜钱”“穿铁靴量河面”“比武裁决”等方式也就成为了旧社会村际纠纷解决的一种规制,而这种规制,随着农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共资源争夺的日益激烈而显得愈发重要。这种武力陋习形成的规制,很多内容是针对公共资源使用权属的确认和不同使用者边界的划分。政府为了省去管理的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竟也默许这种规制,从而助长了武力陋习的滋生。甚至,在武力规制明确了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属关系后,政府和地方便通过技术、制度等各种手段来加以维护。这进一步让村民误认了武力规制的正当性和公平性。如我们现在看到的难老泉“三七分水”的建筑遗迹,最初是通过建立分水石、限水石斗等来保证“三七分水”的,后来又建立木隔子进一步精确分水比例,再后来是在分水处先做分水天平,然后建立分水铁栅栏,种种措施都是为了保证“三七分水”的精确无误。对此,在洪洞的霍泉水神庙的石碑上就有这样一段记载:
其洪洞县见今水数不及三分,寻将两县见流水相并等量,得共深一尺九寸。依古旧碑文内各得水分数比附内,赵城县合得一尺,洪洞县合得九寸。若便依此分定,缘洪洞县陡门外地势低下水流缓急,减一寸只合得水深八寸。赵城县水只与深一尺,又缘陡门外地势高仰水流澄漫,以此更添深一寸,共合得一尺一寸。遂将两渠水堰塞,令别渠散流,两陡门内阔狭依古旧。将两渠陡门中用水斗量定,于洪洞县限口西壁向北,直添立石头阔二尺,拦水入南霍渠内,以此立定。赵城县合得水七分,洪洞县水三分。*孙焕仑纂:《洪洞县水利志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2页。
这种分水的方法,综合考虑了因地势等条件带来的不公平因素,并通过精密的丈量与计算,使洪洞县与赵城县“三七分水”的比例得到了准确划分。这种“严谨”的分水态度,正是政府和地方对“跳油锅捞铜钱”确定的分水规制的一种坚决维护,是政府管理无能、屈服民间恶势力或与恶势力沆瀣一气的明证。
不管是“跳油锅捞铜钱”“穿铁靴量河面”,还是“摆擂台比武”“群体械斗”,这种武力规制建立的民间纠纷解决的秩序,都是以某种巨大代价为基础的。事实上这些方法得出的秩序,面临通过下一次武力手段重新洗牌的危机,会在更大程度上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如武力规制得出的“三七分水”,事实上就是以不公平的资源划分来实现公平的竞争。这种不公平的资源划分便为后续村际纠纷的发生留下了隐患——后续的村际纠纷大多是村民为试图改变这种资源划分的不公平。但是,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碑记中,政府和民间强恶势力“都是想方设法来维护这个相对公平的既成事实,对那些挑战既成事实的行为,尽管可能是合理的,也不给予理睬”*赵世瑜:《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和象征》,《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武力陋习下的规制,使武力成为拥有强大势力的村落来强化这一规制合法化的工具,这也是旧社会乡土中国的公共资源基本上被强恶势力所独霸或瓜分为私有财产的原因。武力规制的出现,是政府无能,司法无效的无奈表现。
五、共生与紧张:新时期乡土中国的武力陋习和司法存在
中国传统社会武力参与解决村际纠纷的陋习,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缺少文化基础和社会空间,便逐渐消解。然而,在改革开放后旧的价值观被打破、新的价值观还没有形成之时,传统社会的武力陋习又出现死灰复燃的迹象。2007年以来,笔者带领课题组先后到江西、广西、广东、山东、云南、湖南、安徽等地区的农村,就关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失范的问题进行了田野调查。虽然,当时对若干村落的实证研究反映了村落武力陋习的存在,但却由于个案研究的特殊性无法充分反映武力陋习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影响。2015年,课题组在对前期调查对象进一步跟踪研究时,对当时选择“民族传统体育(武术)的动机”这一选项为“英雄崇拜”的受访群体,增设了“假如有人侵占了你的财产或者伤害了你的亲人,你会选择什么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同时,给出了“选择打官司解决”“带上一帮武力强悍的人找他算帐”“寻求村委会的帮助解决”“寻求村中的长辈帮助”“忍忍算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和“其它”5个选项,试图进一步考察受访者在村际纠纷发生时所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另外,就该项调查,布置为课题组老师和农村研究生的寒假社会调查作业。最后,共收上来3367份有效调查,其中调查对象的年龄范围在20-45岁之间。调查结果显示:17.4%的人选择了“带上一帮武力强悍的人找他算帐”,13.2%的人选择“寻求村委会的帮助解决”,仅有33.7%的人选择“打官司解决”(见表1)。而且,调查结果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和经济特征。如在西部偏僻的经济不发达地区,被调查的186个村民中,有75.3%的村民选择“寻求村委会的帮助解决”;在桂林市龙胜县和平村等经济条件好的区域,在被调查的68个村民中,有21.9%的人选择“带上一帮武力强悍的人找他算帐”,有12.1%的人选择“打官司解决”,没有一个人选择“寻求村委会的帮助解决”;在安徽省淮北市农村541名村民的调查中,有13.7%的村民选择“带上一帮武力强悍的人找他算帐”。同样的调查在江西省表现的最为突出。江西省南昌市郊131个访谈调查对象,26.9%的村民选择“带上一帮武力强悍的人找他算帐”,甚至在访谈时很多人都补充了一个观点,即“我找人卸掉他一条大腿”。在江西省抚州市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孝桥镇孝桥村、窑平村的308名村民调查中,29.3%的人选择“带上一帮武力强悍的人找他算帐”,并补充“找黑社会帮忙解决”;而在高平等一些落后、封闭的村落64位村民的调查中,却有70.3%的人选择“寻求村委会的帮助解决”。随后,相同的补充调查(走访调查)在浙江省宁波市汉塘村和上海市张江镇进行,在179位村民中,有73.3%的村民选择“打官司解决”,仅有5.1%的人选择武力解决。
这个调查结果让人非常震惊!在当今的法治社会中,为什么乡村在解决纠纷时每百人中仍有近18人选择武力的方式。这意味着我们身边随时可能发生武力或者暴力冲突。这一点,被近些年来我国公安机关受理的武力伤人或械斗案件数据的上升做了进一步补证(见表2)。近20年来,我国武力伤人和群体械斗案件从每年50万起,突增到每年500万起左右。特别是近5年,武力伤人和械斗事件更是居高不下。据对地方公安干警的进一步调查访谈,民间武力伤人和武力械斗的事件仅有5%左右会立案受理,大部分武力事件都是自己调解,很少报案,除非案件影响特别巨大。若按照这种情况重新进行预算的话,真实的数据应该是在此基础上再扩大20倍左右。再扣除农村和城市人口的比例,以及每起武力事件最少是在2个人以上发生的,可以预见表1调查得出的农村村民选择武力来解决纠纷所占17.4%的比例实际上是偏低的。

表1 中国部分农村村民纠纷解决方式调查情况(n=3367)

表2 我国公安机关受理的武力伤人或械斗案件数*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7至2015年所载相关数据。
进一步通过各地微信农村初中同学群的验证调查,也基本体现出以下几种现象。第一、经济发达的地区,如上海、宁波、广州等地的农村村民司法意识较高,一般很少使用武力来解决纠纷;第二,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如江西、山东、安徽、云南、湖南等地的一些农村,越是经济条件稍好的村落,村民的司法意识越低,武力陋习盛行;而越是偏僻的农村,村民虽然司法意识不高,但武力解决纠纷的情况却非常少,代之的是寻求村委会解决纠纷。
六、何以可能:乡村秩序的整合与武力陋习的消解
在对我国乡村武力陋习的历史考察和现实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发现武力陋习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旧社会乡村武力陋习的产生和发展源于国家和司法的离场,从而使民间传统文化的陋习得到过分地张扬;新时期武力陋习的死灰复燃更是在旧的思想根源上又融入了新社会的元素,从而使武力陋习的消解变得更为艰难。那么在现阶段,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这一问题呢?整体言之,在新时期的中国乡土社会,武力陋习的消解可以通过以下路径来实现:
第一,通过法治和村民自治的有效融合来消解武力陋习。中国传统社会的“村治”是指村民自治,传统的“村规民约”“习惯法”等是村民自治的基础。当然,传统“村规民约”和“习惯法”有很多非法的、暴力的内容,这与我们所讲的现代“村治”是不符的,是应该剔除的。“村治”的一套既定的方法,在管理村庄共同体中依靠乡村社会的道德评价体系来维持其正常运行,而乡村社会的道德评价体系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的,即我们常听到的“唾沫星子能淹死人”之类的表述!大家站在经验道德的至高点对其他人品头论足,其实质是宣扬一种行为约束,使那些行为越轨的人为乡村社会所不容,从而达到村庄秩序的维护。旧社会人们品评的是“好汉”的英勇和“本事”的高低,自然纵容了武力行为。因而,现代社会应该摈弃那些“江湖”习气,将法治思想融入到“村治”的经验道德评价中,替换那些不健康的如“江湖好汉”“哥们义气”等文化内容,将能很好地树立乡村人对司法的敬畏之心,从而消解乡村陋习。一个准备动用武力来解决纠纷的人,在同村人扑面而来的“你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你是要坐牢的”“你就是个法盲,是个蛮汉”“匹夫之勇”等道德评价中,就会丧失武力械斗的勇气。因为,武力在这种融入了法治精神的道德评价体系中不被人看重,自然也就没有了市场,便会自行消解。
第二,严厉惩治地方官员的贪政、懒政以及在农村治理上的粗暴行为,回应农民的合理性诉求。传统旧政府在处理乡村纠纷时,基本是离场的。他们秉持的观念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尽快息事宁人”,从而导致村民纠纷得不到政府的合理回应,助长了乡村武力陋习的盛行。而据我国公安部门统计的武力伤人和械斗事件,则有相当部分是发生于地方政府与村民的冲突之中。如2014年江西省孝桥村的政府征地事件,政府在未经村民同意的情况下,以6万元每亩的价格将村民100多亩水田出卖给商人,而且对讨要说法的村民进行了简单粗暴的驱赶,从而引发了村民集体围攻镇政府。更多的地方性武力冲突,则是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强拆民房、强占农民土地等粗暴行为引起的。因此,对这些地方“土皇帝”的恶劣行径,必须要严厉惩治,并通过多种官方途径为农民“说句公道话”,回应农民的合理性诉求,使农民在寻求纠纷的解决时,感觉到政府的关怀时刻在场,而不是漠不关心。当寻找政府的帮助是最便利的纠纷解决途径时,或政府能经常、主动地送司法下乡,自然能消解乡村武力陋习。
第三,合理引导地方体育社团的良性竞争。清代、民国时期,武力械斗多由“民团”引发。“民团”成立的目的就是“保家保寨”和不断扩张,从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旧社会“民团”的演变,部分成了我们现在的地方性体育社团。我国地方体育社团虽然已受到了新文化的改造,但也难完全剔除传统“江湖文化”的影响。一旦滋生“武力陋习”的条件和环境形成,则武力事件便会大规模爆发。我国公安机关受理的武力伤人案件在近5年成数十倍的增长,一者说明我们有些政府官员滋生了旧社会的官僚作风和习气,二者也反映了我国地方体育社团管理的极端功利主义倾向。我国的地方性体育竞赛期间,也是引发武力械斗的高发时期,如端午节前后的龙舟运动,就经常引发大型的武力械斗事件。武力械斗的原因,是地方体育社团为体育竞赛赋予了更多的非体育元素,使体育有了不可承载之重,如竞赛的巨额奖励、竞赛结果和政绩直接挂钩、竞赛结果代表了村落的荣誉等等。既承载了这些复杂的内涵,体育竞赛便过度地注重比赛的结果,因而出现“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情形。因此,合理引导地方体育社团的良性竞争,而不是秉承“不公平看本事”的理念,真正做到重竞赛过程、轻竞赛结果,也是消解武力陋习的必要途径。
第四,引导农村树立正确的体育健身观和文化价值观。在我国的江西、河南、山东等地的农村,仍有大量村民延传了习武的习俗。然而,当对他们习武的动机进行调研时,却发现仅仅为强身健体的并不多见。大部分农村人还是传承了旧社会的习武动机,即“防身”“保家护院”以及练武是为了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好汉”。甚至,有些人认为可以通过武力震慑他人,从而实现农村话语权的争夺。这种思想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武力陋习作用的结果,也为下一次武力的使用埋下了隐患。旧社会村民崇尚“英雄好汉”往往会助推两种行为的发生:一是见义勇为,二是武力械斗。“武力械斗”解决纠纷的行为是因为国家法制不健全,政府不作为,从而为村民默认。当今我国是文明、法治的社会,“武力械斗”解决纠纷根本不存在社会空间。因此,我们应该合理引导村民的习武动机,将“英雄好汉”传统文化的健康部分保留,强调见义勇为的道德价值,同时也强调“锻炼身体,增强体质,防病祛病,幸福生活”的体育文化价值观,但也要避免“除暴安良”这种传统文化陋习的出现。揭发恶势力、制止恶势力是应该的,然后应该把剩下的工作交给政府公检法部分去做。当然,这些理念的传播也是我国大众文化传媒的当代责任,乡村武力陋习的滋生,不能不说也与我们当下媒体的不恰当的武力、帮派文化价值传播相关。因此,我们在电影、电视剧等的武力传播和英雄塑造中,要注意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多树立一些礼教道德的英雄,少一些血腥杀戮、武力掠夺、除暴安良的英雄。
七、结 语
中国农村通过选择武力的方式来解决纠纷问题,缘起于制度上曾经出现“射箭定讼”“比武定讼”等文化传统,以及思想上曾经出现的儒家“无讼”“以讼为耻”等观念的传播,从而导致了武力裁决手段的普遍化和平民化。而又由于旧社会政府在村际管理层面上是软弱无力和退场,政府仲裁缺乏公信力,进而使民间调解的武力方式演变成为一种村际纠纷解决的陋习。个案的解析也发现,武力陋习形成的根源有村民对“江湖好汉”精神的崇尚,也有村民对自身行动的“算计”,还有乡村精英“话语权的争夺”而所有的这些根源都有一个共同的起点,即传统旧政府在乡村治理上的不作为。
通过抽样调查和我国公安机关受理的武力伤人和械斗案件数,我们也可以看到,近5年来武力陋习在我国以非常迅猛的速度死灰复燃,与司法共生。武力事件的大规模爆发,一定是社会滋生了形成“武力陋习”的条件和环境。因此,要消解武力陋习,则必须从传统形成根源和新情况、新问题上寻找解决途径,即可以通过法治和乡村治理的有效融合来消解武力陋习;严厉惩治地方官员的贪政、懒政以及在农村治理上的粗暴行为,回应农民的合理性诉求来消解武力陋习;合理引导地方体育社团的良性竞争,以及引导农村树立正确的体育健身观和文化价值观来消解武力陋习。
[责任编辑 王加华]
郑国华,上海体育学院体育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上海 200438)。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亚欧国家民族传统体育流变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0BTY00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