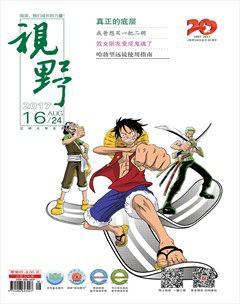曹操的宣言
王鼎钧
在京戏里,曹孟德冠带辉煌,站在舞台上高声宣示:“世人笑我好,我笑世人偏。为人少机变,富贵怎双全?”何等坦白!何等透彻!京戏不可不看。
这四句真言是宣言,也是预言,天下后世曹派传人,得曹丞相一体一貌一鳞一爪者皆不容轻视。
当年我不看京戏,无缘受曹丞相间接教诲,常指其人很“坏”。朋友问:他怎么个坏法?我能一五一十说出他一串罪状来。朋友听了,或点头微笑,或默然无语,或恍然有悟,没有任何异议。
不久,我发现这些朋友见了那个“坏人”两眼放光,用力跟他握手,寄精美的贺年卡,打电话和他谈论舞厅的装潢等等。我越是批评他,他的声望越高。
这是怎么了?是我的信用破产了吗?不,不,他们知道我是诚实的,正因为他们相信了我的话,这才断定那人“有用”,设法争取他做个好人——“对我好的人”。
(晴天摘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开放的人生》)
口味·耳音·兴趣
我有一次买牛肉。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中年妇女,看样子是个知识分子,南方人。轮到她了,她问卖牛肉的:“牛肉怎么做?”我很奇怪,问:“你没有做过牛肉?”——“没有。我们家不吃牛羊肉。”——“那您买牛肉——?”——“我的孩子大了,他们会到外地去。我让他们习惯习惯,出去了好适应。”这位做母亲的用心良苦。我于是尽了一趟义务,把她请到一边,讲了一通牛肉做法,从清炖、红烧、咖喱牛肉,直到广东的蚝油炒牛肉、四川的水煮牛肉、干煸牛肉丝……
有人不吃羊肉。我们到内蒙去体验生活。有一位女同志不吃羊肉——闻到羊肉味都恶心,这可苦了。她只好顿顿吃开水泡饭,吃咸菜。看见我吃手抓羊贝子(全羊)吃得那样香,直生气!
有人不吃辣椒。我们到重庆去体验生活。有几个女演员去吃汤圆,进门就嚷嚷:“不要辣椒!”卖汤圆的冷冷地说:“汤圆没有放辣椒的!”
许多东西不吃,“下去”,很不方便。到一个地方,听不懂那里的话,也很麻烦。
我们到湘鄂赣去体验生活。在长沙,有一个同志的鞋坏了去修鞋,鞋铺里不收,“为什么?”——“修鞋的不好过。”——“么?”——“修鞋的不好过!”我只得给他翻译一下,告诉他修鞋的今天病了,他不舒服。上了井冈山,更麻烦了:井冈山说的是客家话。我们听一位队长介绍情况,他说这里没有人肯当干部,他挺身而出,他老婆反对,说是“辣子毛补,两头秀腐”——“什么什么?”我又得给他翻译:“辣椒没有营养,吃下去两头受苦。”这样一翻译可就什么味道也没有了。
我去看昆曲,“打虎游街”“借茶活捉”……好戏。小丑的苏白尤其传神,我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发出笑声。邻座是一个唱花旦的京剧女演员,她听不懂,直着急,老问:“他说什么?说什么?”我又不能逐句翻译,她很遗憾。
我有一次到民族饭店去找人,身后有几个少女在叽叽呱呱地说很地道的苏州话。一边的电梯来了,一个少女大声招呼她的同伴:“乘面乘面(这边这边)!”
我回头一看:说苏州话的是几个美国人!
我们那位唱花旦的女演员在语言能力上比这几个美国少女可差多了。
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作家、一个演员的口味最好杂一点,从北京的豆汁到广东的龙虱都尝尝(有些吃的我也招架不了,比如贵州的鱼腥草);耳音要好一些,能多听懂几种方言,四川话、苏州话、扬州话(有些话我也一句不懂,比如温州话)。否则,是个损失。
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苦瓜是瓜吗?
昨天晚上,家里吃白兰瓜。我的一个小孙女,还不到三岁,一边吃,一边说:“白兰瓜、哈密瓜、黄金瓜、华莱士瓜、西瓜,这些都是瓜。”我很惊奇了:她已经能自己经过归纳,形成“瓜”的概念了(没有人教过她)。这表示她的智力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凭借概念,进行思维,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她奶奶问她;“黄瓜呢?”她点点头。“苦瓜呢?”她摇了摇头,并且说明她的理由:“苦瓜不像瓜。”我于是进一步想:我对她的概念的分析是不完全的。原来在她的“瓜”概念里除了好吃不好吃,还有一个像不像的问题(苦瓜的表皮疙里疙瘩的,也确实不大像瓜)。我翻了翻《辞海》,看到苦瓜属葫芦科。那么,我的孙女认为苦瓜不是瓜,是有道理的。我又翻了翻《辞海》的“黄瓜”条:黄瓜也是属葫芦科。苦瓜、黄瓜习惯上都叫作瓜;而另一种很“像”瓜的东西,在北方却称之为“西葫芦”。瓜乎?葫芦乎?苦瓜是不是瓜呢?我倒糊涂起来了。
“苦瓜”之名,我最初是从石涛的画上知道的。我家里有不少有正书局珂罗版印的画集,其中石涛的画不少。我从小喜石涛的画。石涛的别号甚多,除石涛外有释济、清湘道人、大涤子、瞎尊者和苦瓜和尚。但我不知道苦瓜为何物。到了昆明,一看:哦,原来就是癫葡萄!我的大伯父每年都要在后园里种几棵癞葡萄,不是为了吃,是为了成熟之后摘下来装在盘子里看着玩的。有时也剖开一两个,挖出籽儿来尝尝。有一点甜味,并不好吃。而且颜色鲜红,如同一个一个血饼子,看起来很刺激,也使人不敢吃它。当作菜,我没吃过。有一个西南联大的同学,是个诗人,他整了我一下子。我曾经吹牛,说没有我不吃的东西。他请我到一个小饭馆吃饭,要了三个菜:凉拌苦瓜、炒苦瓜、苦瓜湯!我咬咬牙,全吃了。从此,我就吃苦瓜了。
咸菜和文化
偶然和高晓声谈起“文化小说”,晓声说:“什么叫文化?——吃东西也是文化。”我同意他的看法。这两天自己在家里腌韭菜花,想起咸菜和文化。
咸菜可以算是一种中国文化。西方似乎没有咸菜。我吃过“洋泡菜”,那不能算咸菜。日本有咸菜,但不知道有没有中国这样盛行。“文革”前《福建日报》登过一则猴子腌咸菜的新闻,一个新华社归侨记者用此材料写了一篇
对外的特稿:“猴子会腌咸菜吗?”被批评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为什么这就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呢?猴子腌咸菜,大概是跟人学的。于此可以证明咸菜在中国是极为常见的东西。中国不出咸菜的地方大概不多。各地的咸菜各有特点,互不雷同。北京的水疙瘩、天津的津冬菜、保定的春不老。“保定有三宝,铁球、面酱、春不老。”我吃过苏州的春不老,是用带缨子的很小的萝卜腌制的,腌成后寸把长的小缨子还是碧绿的,极嫩,微甜,好吃,名字也起得好。保定的春不老我想也是这样的。周作人曾说他的家乡经常吃的是咸极了的咸鱼和咸极了的咸菜。鲁迅《风波》里写的蒸得乌黑的干菜很诱人。腌雪里蕻南北皆有。上海人爱吃咸菜肉丝面和雪笋汤。云南曲靖的韭菜花风味绝佳。曲靖韭菜花的主料其实是细切晾干的萝卜丝,与北京作为吃涮羊肉的调料的韭菜花不同。贵州有冰糖酸,乃以芥菜加醪糟、辣子腌成。四川咸菜种类极多,据说必以自贡井的粗盐腌制乃佳。行销全国,远至海外,堪称咸菜之王的,应数榨菜。朝鲜辣菜也可以算是咸菜。延边的腌蕨菜北京偶有卖的,人多不识。福建的黄萝卜很有名,可惜未曾吃过。我的家乡每到秋末冬初,多数人家都腌萝卜干。到店铺里学徒,要“吃三年萝卜干饭”,言其缺油水也。中国咸菜多矣,此不能备载。如果有人写一本《咸菜谱》,将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
和咸菜相伯仲的是酱菜。中国的酱菜大别起来,可分为北味的与南味的两类。北味的以北京为代表。六必居、天源、后门的“大葫芦”都很好——“大葫芦”门悬大葫芦为记,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保定酱菜有名,但与北京酱菜区别实不大。南味的以扬州酱菜为代表,商标为“三和”、“四美”。北方酱菜偏咸,南则偏甜。中国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酱。萝卜、瓜、莴苣、蒜苗、甘露、藕,乃至花生、核桃、杏仁,无不可酱。北京酱菜里有酱银苗,我到现在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只有荸荠不能酱。我的家乡不兴到酱油园里开口说买酱荸荠,那是骂人的话。
(李昭瑾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食事》)
“你爸,他想买一把二胡……”饭桌上,我妈用试探口气跟我说。我放下了筷子,沒说话。我妈猜不中我接下来想讲什么,便接着说:“我就说嘛,买来干吗,住在单元楼里面,哪能成天东拉西扯的,不吵到邻居才怪呢!”
我见她误会了我的意思,便打断了她的话头说:“他想买就买啊!”我妈见我迟疑的表情不是反对便笑了,接着说;“我的意思就是想让他出去找个僻静的地方去拉他的二胡去,别吵了我的清净……”
我妈其实并不知道我刚才那一瞬间的恍神是因为我忽然想起来,大概是一年前,不对,应该是一年半前,我爸他自己跟我提过他想买把二胡的事情。
我送女儿去学古筝有两年多时间了,因为课程都排在周四放学后,一般都是我爸负责接送,他总是在我耳边唠叨,孙女一节古筝课一百多块的学费有点不值,不是去得晚排在别的学员后面老师教得仓促,就是去得早别的学员等着老师教得草草。我总笑他那一百多块学费,得按停车场掐秒算才好。
有天回来,他提了句说问过店家有没有卖二胡的,店家答复他主营古筝和钢琴,若是想要可以进货的时候帮他带一把。他大概又跟店家讨论一下行情,最后决定买个玩票性质的二胡就好了。店家答复他,那怎么着也得五六百块钱吧。我当时也没有细想,随口回了他一句,你先别急着跟人家下订单,我有空帮你在网上看看,说不定两三百块就能买一把了。
可是我这话前脚说完,后脚我就给忘了,忘得彻彻底底,若不是我妈在饭桌上跟我提这件事情,我完全不记得我爸曾经跟我说过想买一把二胡。想到这里,我内心里涌出一股愧疚的情绪。长久以来,我一直自认在生活小节上还算是比较周全的人,可是为什么偏偏这件事情没有放在心上呢?难道真的是只有为人父母的才会永远惦记着孩子心里要的东西,而为人子女的却永远都不可能将心比心……
其实,我是知道我爸为什么想要买一把二胡的。他是一个大家庭的长子,身后还有一长串的弟弟妹妹,小时候赶上过饥荒,念初中的时候赶上了“文革”,为了撑起家中的生计早早就出社会工作,学业也就这么给荒废了。他跟我聊过他的学生生涯,最后几年几乎都在文宣队里度过的,学校里排样板戏,他被选出来学拉二胡,当时有个老师教他一段时间,可是还没有等到他完全学会,那个老师却被打倒了。后来,他不知道哪里来的神力,居然自己摸索着也就学会了,可是等到他学会了,文宣队也解散了,他终究没有上台拉上过一段,便一头扎进了讨生活的人生里。
当年,我并不喜欢他这个现如今听起来有点“鸡汤味”的故事,那是因为他买了把二胡给我,然后希望他自己手把手地教我拉会它。现如今重新回头来看,我还是得说二胡仍旧是个不太容易入门的乐器,它和小提琴一样没有明确的音阶,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太难了,我不能忍受学了几个月之后拉扯出来的声音仍旧如杀鸡一般。这份不好的经验直接影响了后来女儿面对学门乐器时我的判断和选择,我强烈推荐学习古筝,初衷很简单,即便是弹不出曲子,古筝这种乐器胡乱弹拨出来的声音也是悦耳的。
他买给我的那把二胡是把儿童二胡,几度搬家都还看得见它的身影,后来蛇皮闷了之后,我印象中我爸还修了一回,可是毕竟不是这方面的手艺人,修完之后的音色就全然不行了。再后来我也大了,拒绝再碰那把二胡,那把胡琴落到了什么地方就不得而知了。
饭桌上,我心里想事情,手上的筷子自然就慢了下来了。我妈见我这顿饭吃得不声不响的,便知道我心里面在想事情。她见我爸起身去了厨房便佯装跟我说悄悄话的样子,压低了嗓子对我讲:“你说这老头子贼不贼?我本来也不想跟你提这买二胡的事儿的。你猜他怎么跟我说?他今天一早跟我说,昨晚做了梦,梦见捡了一把二胡,本来挺高兴的,拿在手里仔细看一看,才发现二胡杆子断了……他这么跟我说什么意思啊?不就是想买嘛,太贼了,这老头子……”
我知道我妈的这番话我爸全能听见,心里面更觉得不是个滋味了,鼻头不由地发酸起来,为了怕场面尴尬我还是以当了多年任性孩子的口吻对他们说:“行了行了,不就是答应帮他在网上看看二胡的事情我给忘了嘛,至于演这么一大出的戏给我看吗?”我掏出手机,在购物APP里输入了二胡,哗啦啦出来一长串各式各样的二胡,从几千到几百的都有。
教古筝的店家说的也是靠谱的,这“低配入门级”的差不多也就是五六百的价位。我埋头刷手机,不知几时我爸已经站在我身后了,嘴里喃喃地说这二胡现在都这么贵了。我依旧强装任性地回答他:“那还用说啊,你也不想想你买二胡的时候,一个月工资多少钱,一斤猪肉多少钱。”我抬眼看了他一下,只见他苍老的额头上已布满了白发,于是又不忍地低下了头,却不肯改掉那任性的口气接着说:“这能看得上眼的差不多都要千把块的,你看看要哪一把,我就把订单下了,省得你老做捡二胡的梦。”
我爸的脸上流露出犯难的表情,这表情我太熟悉不过了,每每要给他买东西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表情,逢年过节领着他买衣服的时候有过,带着他出门去转转时要掏腰包破费的时候有过,带着他去看病体检要做CT的时候有过,虽然都是在花钱,可唯独他掏钱给我买什么的时候却不曾见过犯难的表情,送我读大学交学费的时候没有,买房凑首付的时候也没有……
最终,我还是拗不过他,也不想他将那把千元的二胡当作一种负累,以妥协的态度网购了一把五百多块价位的二胡。父亲从房间里拿了六张百元大钞放在我的手边。我脸上挂着笑,心里却流着泪说:“行了,这钱你收着,当我付给你的‘噪音污染防治费,你要是吵着我妈,我可要问你把这钱要回来的。”我爸仍不肯,僵在桌边。我妈看不过去了,冲着他说:“老头子,你行了吧,收好钱等着拉你的二胡去吧。我也不嫌你吵吵,你说说,你开开心心地多活一个月,领的退休工资能买多少把这样的二胡呢?……人上了年纪了,想买就买,想拉就拉吧!”
(云凡摘自“豆瓣”)
——六必居酱菜制作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