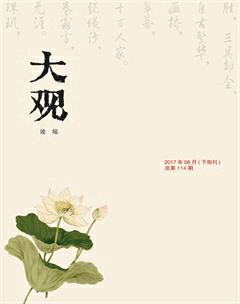论“山药蛋派”文学审美风格的成因及文学史地位
辛瑞涛
摘要: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山药蛋派”的出现是现当代文学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审美现象。其小说中对农村风土民情及农民精神风貌的如实叙写,及作家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景物与爱情描写中的求实,使得小说呈现出乡土化与崇实相结合的审美风格。而山西多山少平地的闭塞地域环境及在这种地域环境下所形成的重商、重实利的地域传统为其审美风格的形成提供了地域文化条件,文学大众化平民化的文学传统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其审美风格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山药蛋派”至今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在当代文学界我们依旧能看到它对文学创作手法以表现方式的影响。
关键词:山药蛋派;审美风格成因;文学史地位
“山药蛋派”小说注重对农村生活的平实叙写,努力将农村的生活风貌原原本本的展现出来,注重内容的真实并以语言和动作来写活人物,且小说中的爱情描写与景物描写因太过实用而缺少美感,以带有民间风味的叙事笔法叙写故事,重叙述轻描写,追求文学的大众化平民化,大多采用地方方言与乡间俚语,带有浓浓的地方气息,使得小说呈现出乡土化与崇实相结合的审美风格。
一、“山药蛋派”文学审美风格的成因
“山药蛋派”文学审美风格的形成,既有它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又有其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时代的召唤,革命斗争的需要,为“山药蛋派”审美风格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而抗战时期山西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以及作家们对山西的地域性物产、人情、风俗、民性的了解,为“山药蛋派”审美风格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地域文化基础。
(一)社会历史条件
五四时期白话文的提倡开创了文学大众化、平民化书写的先河,而周作人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平民文学》一文,更是从理论上总结和概括了中国现代文学平民化书写的任务与要求,反对贵族文学的雕琢与拗口,提出平民文学的两大特点即“普遍”与“真挚”。此时的文学平民化在某些意义上起到了启蒙大众作用。文学由“雅”入“俗”由此开启。可见文学的大众化平民化传统在五四时期已经开启,之后文学研究會对“民众文学”的倡导,到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大众文艺的出现,以及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口号,使得文学大众化平民化的进程进一步的加速,可见文学创作由“雅”入“俗”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大趋势,而“山药蛋派”文学的审美风格正是顺应这种潮流与趋势而生的。
尤其是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其审美风格的产生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抗战时期,延安是革命圣地,大量有识青年纷纷奔赴延安,希望为革命事业奉献终生,延安瞬间汇集了各路的文学名家,成为解放区的文化中心,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逐渐消减了青年们的革命热情,延安地区物资的缺乏使得他们怀念起了之前衣食无忧的生活,且由于知识分子骨子中的傲气使得他们不屑于与农民为伍。这就使得解放区内小资本主义思想盛行,且部分文学作品将本该作为解放区文学受众的工农兵作为对立面加以批判。“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赵树理在此期间所写的《小二黑结婚》,因太土、太俗而受到文学界的非议,直到《讲话》影响的逐渐扩大,才使得这一作品得到文学界的认同。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作家要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学习工农兵,了解工农兵的需要,并用工农兵乐于接受的方式来进行创作,且文学要从属与政治等等。《讲话》的发表为“山药蛋派”文学审美风格的产生提供了政治上的支持,随后,“山药蛋派”文学便在《讲话》的指导下大量出现,在文学界的影响也不断地扩大,甚至出现了所谓“赵树理方向”。
(二)地域文化条件
在上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山药蛋派”的审美风格应运而生,而为什么在同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及相同的艺术追求下,形成了绝无仅有的“山药蛋派”审美风格,这不得不归咎于山西的地域文化特征及作家自身的条件。
山西独特的地形,清代顾祖禹在《山西方舆纪要·序》中说:“山西之地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句注、雁门为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1]从顾祖禹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山西的地形相对封闭,且多山少平地。由于多山少平地使得山西耕地较少,为了生存不得不外出经商,进而导致重商、重实利的地域传统,如明《太原图册》中云:“士穷理学,兼习词章,敦厚不华,醇俭好学。工贾务实勤业。”而相对封闭的地形却易于形成本区域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这种地域文化特征在岁月变迁、政权更替及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可以相对完整的保留下来。这就使得山西拥有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地域文化。而“山药蛋派”的审美风格就是在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
在“山药蛋派”之前,文学界并不乏反映山西人与事的作品,如吴奚如的长篇小说《汾河上》、李健吾的《终条山的传说》、康濯的《水滴石穿》等等,但这些作品在表现山西地域文化特征上并不像“山药蛋派”那样自然而然,且表达方式上文人气息浓。尽管这些作家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山西地域文化的熏陶,但并没有形成乡土化与崇实相结合的审美风格,也没有产生像“山药蛋派”这样的影响。这是因为“山药蛋派”的作家都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从小便受到山西地域文化与传统的熏陶,形成了山西特有的关照问题的角度及艺术思维方式等等,而吴奚如、李健吾等作家,或原籍不是山西只是调任山西工作或虽原籍是山西但却搬离山西,山西的地域文化与传统并没有在其骨子里留下深深的烙印。且“山药蛋派”的作家除赵树理外在开始创作之前文化水平不高,大多是高小或高小以下的文化水准,西戎曾多次说过自己及他人的文化程度问题:“我文化程度不高,只上过高小,参加革命后,在宣传队里自学文化,也学其他”。[2]这为他们吸收民间文学的养分提供了便利,较少的正规教育使得他们较少受文人文学的影响,民间文化在其教育生涯中便占了主导地位,民间传说、民间戏剧、说唱文学等民间艺术成为其进行文学创作时汲取的首选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