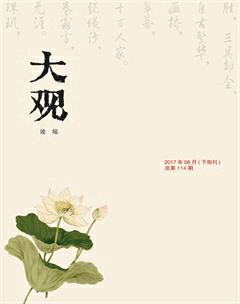评议李白《草书歌行》的真伪问题
摘要:自宋敏求将《草书歌行》一诗收入《李太白文集》中,北宋以来文人学者们颇多争议。本文大致列举历史上前人对此诗真伪的看法,并试从宗教、酒和二人的性情方面,探讨二人交游的可能性。
关键词:李白;怀素《草书歌行》真伪
“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笺麻素绢排数厢,宣州石砚墨色光。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如楚汉相攻战。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古来万事贵天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全唐诗》卷一六七)
这首《草书歌行》赞叹怀素的草书“天下称独步”,气势如万马奔腾,“字字飞动,圆转之妙,宛如有神”(《宣和书谱》)。但自从宋敏求将《草书歌行》一诗收入到《李太白文集》中,北宋以来文人学者们对此颇多争议。李白作为唐代著名的天才诗人,所作诗歌极多,有“李白一斗诗百篇” (杜甫《饮中八仙歌》) 之称。但由于李白长期处于漂泊流离的生活状况,加之其晚年经历战乱及牢狱之灾,造成其诗大量散佚,至北宋乐史编辑《李翰林集》、宋敏求编撰《李太白文集》,方广为搜集,但《李太白文集》一经面世,就不断受到人们质疑,其中就包括这首《草书歌行》。
历史上比较著名的论调基本如下:
苏轼最早提出李白的《草书歌行》是伪作这一观点。他在《东坡题跋》(丛书集成本)卷二“诸集伪谬”条中说:“近见曾子固编《太白集》,自谓颇获遗亡,而有《赠怀素草书歌》及《笑矣乎》数首,皆贯休以下词格。”但仔细追究就会发现,苏轼没有详细论证为何这些诗“皆贯休以下词格”,也没有说出让读者信服的理由,因此我们对苏轼是从哪个角度认为这首《草书歌行》是伪作的也并不清楚。
陆游在《入蜀记》中记载:“或日十咏及归来矣、笑矣乎、僧伽歌、怀素草书歌,太白旧集本无之。宋次道再编时,贪多务得之过也。”他们都因为旧集没有这首诗而提出疑问,可是我们又如何得知这里所言的“旧集”根据的是哪个集呢?
相比之下,朱谏从诗的风格分析此诗,颇为在理。他在《李诗辨疑》中说:“此诗格力虽不足,然辞气轻顺,颇有音节。较于李白,固所不逮,犹不失为唐人风调也。”
胡震亨在《唐音癸籤》卷三十二称:“太白集亦大有伪诗搀入。”所举例子就是苏轼曾指出的几首诗为例证,其中就包括《草书歌行》这首,并在其《李诗通》中将其视为伪作,置入附录。可见胡震亨并没有经过自己的考证,只是人云亦云,并无力证,就简单将这首诗纳入伪作行列。
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云:“笑矣乎,悲矣乎,怀素草书歌等,皆五代凡庸俗子所拟,后人无识,将此选入。”同样,沈德潜是从哪个角度指出这些诗“皆五代凡庸俗子所拟”的呢?我们不得而知。
北宋书法理论总集《墨池编》则称:“此诗本藏真(怀素字藏真)自作,驾名太白者。”认为这首诗是怀素所作,而非李白。此说法倒是颇有新意,可惜缺乏有力论证。
清人王琦按云:“以一少年上人而故贬王逸少、张伯英以推之,大失毁誉之实。至张旭与太白既同酒中八仙之游,而作诗称诩有‘胸藏风云世莫知之句,忽一旦而訾其‘老死不足数,太白决不没分别至此,断为伪作,信不疑矣。”王琦从诗的内容推论此诗不是李白所作,却并不能使人信服。众所周知,李白生性不羁,他在写诗的时候主要是抒发自己当下的内心情感,其诗常是即兴创作,随性而来,如《将进酒》等,如何要求他在创作时兼顾如此多的人情关系?即便李白在诗中借用张旭、公孙大娘二人之名,其目的也绝不是要贬低他们,而是希望借此突出怀素草书的精彩绝伦。
时人詹瑛则从诗中找实证,在《李白诗论丛》中云:“怀素生开元十三年,晚太白二十五岁。今诗中一则云:‘吾师醉后倚绳床,再则云:‘我师此义不师古,太白一生倨傲,断不至对一少年上人若是之崇也。”李白的倨傲是针对性的,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倨傲,更不用说是对和李白一样好美酒,藐成法,目空一切,充满强烈自信心的怀素了。尽管从年龄上说,二人的确相差过大,但从性格层面来说,二人却是同类人,李白欣赏怀素的率性,其实也就是欣赏他自己,更何况怀素还是佛门中人,李白将其称之为“师”又有何不可呢?
诗中又云:“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詹瑛据此作出批评:“湖南七郡,谓长沙郡、桂阳郡、零陵郡、连山郡、江华郡、邵華郡,此七郡皆在洞庭湖之南,故曰湖南。”他据此而论之曰:“按新唐书方镇表,广德二年置湖南节度使,共辖五州,湖南二字用作政治区划之名,当始于此。至宋太宗置湖南路,始统潭、衡、道、永、邵、郴、全七州,一桂阳监。太白卒于宝应元年,而此诗已有七郡之称,亦至可疑。”詹瑛从历史地理角度分析诗中的“湖南七郡”似有道理,但瞿蜕园、朱金城校本则针对这一论证反驳詹瑛:“至詹氏摭湖南七郡之语,谓广德二年始置湖南节度使,此又过泥。湖南犹江南、岭南,形之于诗者,非必作为行政区域,唐诗中如钱起之‘湖南远去有余情,比比也。”可见,詹瑛的解释并不能使人信服。
李白与怀素二人虽年龄相差较大,但却同在一个时代,并且在二人之间又有着诸多的因缘际会和性格、身世上的相似之处,那么从宗教和酒这两个方面着手,也许能看出二人交游的蛛丝马迹。
一、宗教联系
佛教东传之后,经过几千年的融合,在唐代与中国文化完全融合。怀素幼时好佛,出家为僧,一度客居京兆,与诸多文人交游。唐代诗人又多入于儒、出于道、游乎禅,李白亦如此。李白自号“青莲居士”,王琦在《李太白年谱》“长安元年”条写道:“青莲花出西竺, 梵语谓之优钵罗花,净香洁, 不染纤尘。太白自号, 疑取此义。”而李白也的确学过佛。他在《赠僧崖公》一诗中就曾回忆其学佛悟禅的那段经历:“昔在朗陵东,学禅白眉空。大地了镜彻,回旋寄轮风。揽彼造化力, 持为我神通。晚谒太山君, 亲见日没云。中夜卧山月, 拂衣逃人群。授余金仙道, 旷劫未始闻。”“镜彻”,瞿朱注曰:“《华严经》:观诸世间大地山河如镜鉴明,来无所粘,过无踪迹,”“轮风”,王琦注以“《法苑珠林》依《华严经》云: 三千大千世界,以无量因缘乃成,且如大地依水轮,水依风轮,风依空轮。空无所依,然众生业感,世界安住。”从诗的内容可见,先从白眉空受禅,后遇太山君学佛理的李白是深谙佛典的。
再看《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茫茫大梦中,惟我独先觉。腾转风火来,假合作容貌。灭除昏疑尽,领略入精要。澄虑观此身,因得通寂照。朗悟前后际,始知金仙妙。”此诗正是李白对佛教基本人生奥秘的参悟。首句说,觉醒者因为了悟了佛法真谛,感叹人生即如一场大梦;“腾转风火来”则是说,世间的一切都是地、水、火、风四大物质假合而成,并无实体。“灭除”句指出,只有灭尽种种无明的疑惑,才能了悟佛法;“澄虑”四句认为,贯通佛家顿悟之学,明心见性,才能领会金仙——佛之奥义。这首诗将佛法妙谛,娓娓道来,显露出李白的佛教思想。开元十三年( 725) 春三月, 李白出三峡。沿江舟行, 抵江夏。与僧行融“赋诗旃檀阁, 纵酒鹦鹉洲。”李白比拟行融与自己的关系为“梁有汤惠休, 常从鲍照游。峨眉史怀一, 独映陈公出。”将自己与行融的禅交深情表露无遗,同时我们亦可窥见历代文人与僧侣的交往对李白的影响。同期,李白还曾与“群公临流赋诗”赠别林上人,有《江夏送林公上人游衡岳亭》,称赞这位林上人“落发归道,专精律仪。白月在天,朗然独出。”秋抵金陵,曾往游城西南隅之瓦官寺,为作《瓦官阁》诗,有诗句“漫漫雨花落,嘈嘈天乐鸣。两廊振法鼓,四南吟风筝。”“雨花”“天乐”“法鼓”诸般佛教语汇中诗中自然嵌入,了无痕迹,足见李白对一般佛教典籍的熟悉程度。因此“游于禅”的李白与佛教徒怀素是拥有沟通的基本可能性的。
酒对于创作者的意义巨大,它是创作的催化剂,可以激发灵感,可以摆脱俗念。这点在怀素和李白的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
怀素喜饮酒,陆羽《僧怀素传》说怀素“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朱遥《草书歌》云:“连饮百杯神转工。”钱起诗也说:“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佩文斋书画谱》卷三十引《金壶记》说:“怀素嗜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凡一日九醉,时人谓之醉僧书”。由此知酒与怀素草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书画汇考》收怀素《酒狂帖》,帖中怀素以“酒狂”自称。宋代朱长文在《续书断》中称怀素的酒量很大,他“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已后始颠狂。”醉意朦胧的怀素“一颠一狂多意气,大叫一声起攘臂。挥毫倏忽千万字,有时一字两字长丈二。翕若长鲸泼剌动海岛,欻若长蛇戎律透深草,回环缭绕相拘连,千变万化在眼前。”极其生动地表现出酒后癫狂的怀素,借酒的神力挥洒出动人心魄的作品。
同样,李白也是“酒中仙”,他一生好酒未有稍懈。不仅如此,李白还在诗中比较完整地体现了自己饮酒的情态和对酒及饮酒的看法——《月下独酌四首》: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在酒精和狂歌劲舞的影响下,诗人想象着自己飘然成仙,和月和影相约在遥远的云汉相会。不仅狂饮、痛饮,李白还要为自己狂饮、痛饮找到理论上的依据: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晋书·天文志上》说:“轩辕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主宴飨饮食。”(卷十一)《神异经》说:“西北荒中有酒泉,人饮此酒,酒美如肉,清如镜,其上有玉樽,取一樽,复一樽出,与天地同休,无乾时,饮此酒人,不死长生。”(《艺文类聚》卷七十二)诗人说,不光是人喜欢酒,连天地都喜欢酒,否则,天上就不会有酒旗星,地上也不会有酒泉的存在了。天地既然同时爱酒,那么好酒好饮就自然不愧对天地了。在诗人看来,不饮酒既有悖于自然常理,也有悖于人性、人情。《三国志·徐邈传》说:“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诗人说清如“圣人”、浊如“贤人”的各种酒既已尝过,那又何必求什么神仙呢?饮三杯即通常理、正理(即“大道”),饮一斗越发顺合人事规律(即“自然”)了。既得“酒中趣”,又何必要告诉“醒者”呢?诗人在这里化用陶渊明“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饮酒二十首》其十三)诗意,意在说明悠然自得的“醉”和小心翼翼的“醒”是两个不相关的世界,不能沟通也没有必要沟通。但纵观怀素和李白二人的爱好及对酒的喜爱,我们可以想见这两个好醉且狂之人,则是不用沟通也能交流的了。原因便在于此二人所饮之“酒”是和追求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紧密联系的,体现在李白的诗文中就是其诗歌表现出的率性、自然和洒脱,不受理性觀念的约束,体现在怀素的书法中便是其狂草所散发出的大气磅礴、气象万千,这种人手合一、肆意驰骋的状态充满了解放精神和超越精神,为此二人所共有。
怀素和李白二人都有着自信、率真、狂放的性格特点,又都有着不如意的坎坷人生。怀素早岁家贫,“幼而事佛”,从小饱尝酸楚苦涩,即使在成名前后也备受士大夫阶层的凌辱和嘲笑。于是他借酒佯狂,见壁即书,为的是表达心中的愤懑和怨气,却体现出他的真性情。他的《藏真帖》《自叙帖》《律公帖》《苦笋帖》等风格多样,但都蕴含着一种超世拔俗、性灵豁畅的气质。而其代表作《自叙帖》的雄浑挚健、沉着豪迈,则完全是心灵自由奔放的象征,跃动着生命的激情和悲壮,显示出耿介傲世的独特气质。李白则常以管仲、乐毅的政治才能自许,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称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一心想要效法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李白却在实现人生抱负的道路上屡屡受挫,尽管如此,他依旧能做到“不屈己、不干人”笑傲权贵,平交诸侯的真实本色。面对李邕对年轻后辈矜持的态度,他在《上李邕》一诗中回敬道: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表现出李白的自信与傲岸。从这些方面来看,李白与怀素二人是大有可能通过佛家的牵线搭桥,发现并欣赏对方身上的种种个性特点,进而交游唱和,那么宋敏求将《草书歌行》收入《李太白文集》中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
【参考文献】
[1]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清]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作者简介:尚梦珣(1992-),女,汉族,安徽合肥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文学硕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