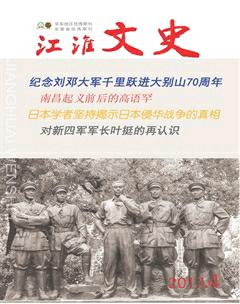在冀中军区的战斗岁月
[编者按] 白竟凡原名白桂荣,1918年12月生于黑龙江省安达县,系开国少将、原炮兵副司令员高存信夫人。她1936年7月参加革命,194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与高存信结婚后随抗大东北干部队挺进晋察冀敌后方。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供销总社教育局长,1982年离休。之后,一直从事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及东北军史的研究,曾编辑出版《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文集》《高崇民传》《高存信将军》等著作。2008年3月,在北京去世。本文是她生前回忆的关于1941年冀中反扫荡的亲身经历,由其女儿高劲松整理并提供给本刊刊发。
1940年9月我与高存信在延安结婚后,随抗大东北干部队(简称“东干队”)挺进晋察冀地区。一到晋察冀就遇到敌人大扫荡,我们就跟敌人转圈打埋伏。反扫荡之后,我们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转达的中央指示,东干队先到冀中军区分配工作。东干队队长张学思当即向全队作了宣布,并进行动员。大家一致拥护,愿意到平原上参加实际斗争。于是我们即准备过平汉路,到冀中军区去。平汉路虽处于平原地区,但敌人没有形成封锁面,仅仅是一条封锁线,有的地区连封锁线也没有形成,这就给我们带来便利。我们把宣传工作深入到了铁路两侧的村庄,带领我们过路的向导就是铁路两侧村庄的居民,他们虽然手中敲着锣,嘴里喊着“平安无事”,却是派来给我们带路的人。
七里沟的风雨夜
1940年12月底,我们胜利地越过了平汉线,抵达了冀中軍区所在地——定县甄村。我们到达后,冀中军区领导机关为我们举行了欢迎会。会上吕正操司令员、程子华政委、沙克参谋长都讲了话,欢迎东干队到冀中军区。
东干队到冀中军区的干部共有82人,分到司令部的有43人,高存信就被分到司令部作战科任科长。分到政治部的有35人,我和张学思的夫人谢雪萍以及郝力宁、李忠4位女同志被分到卫生部,还有两个女同志被分配到供给部。我任卫生部宣传处干事,谢雪萍任卫生部组织处干事。卫生部驻在冀西的唐县南清醒,所以我1941年3月到了冀西,和高存信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郝力宁被分配到冀中军区供给部。供给部驻在唐县北清醒,南北清醒相距有3里。当时我主要是负责编辑卫生部的一个报纸,搜集先进人物事迹,进行宣传报道,以增强人们抗日必胜的信心。
1941年6月,驻在保定、北平、太原、张家口的敌人向冀西根据地进行扫荡。因为我和谢雪萍怀孕,均将临产,军区卫生部即将我们俩安排在后方医院的休养五所。这是个干部休养所,所长是何权轩。五所驻地在易县娘娘宫东北的一条大沟里,名叫七里沟,那里只有几户人家。易县属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由于一分区5月袭击满城县东北角的石头村,俘敌30多人,并炸毁平汉路火车,敌人就在6月对一分区进行报复性的扫荡。
6月的一天,我腹部疼痛,由于是第一次生孩子,没有经验,肚子痛,我就满地走,结果羊水早流成了干产,所以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已经死了。产后3天的一个夜里,有消息说敌人要来扫荡,所里通知休养员们一律上山。夜里两点多钟,天空阴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谢雪萍即将生产,行动也很不方便,但仍然搀扶着十分虚弱的我,艰难地往山上爬。我们刚爬了一半,雷电交加,大雨来临,我们就地躲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下。我们两人坐在一个背包上,打开另一个背包,把被子取出盖在身上,以防备大雨的侵袭。谢雪萍让我坐在里面,她坐在外面,用自己的身体为我挡雨。我们同时还要用手牢牢抓住石崖,免得被洪水冲走。两个多钟头之后,雨渐渐停了,我们才舒了一口气,这时天已快要亮了,朝霞在云层中时隐时现。突然,从沟里传来一声枪响,这是所里发出的信号,让我们立即隐蔽,敌人开始搜山了。由于山里的荆条长得不高,我们便把被子盖好,伪装成一堆石头,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五所住的那边山顶上有部队的岗哨,他们急忙收起电话,翻过山转移了。不一会,敌人就来扫荡了,他们闯进五所住的村庄,这时村里已坚壁清野,大家早已上山了。敌人在村子里翻腾了半天,抓鸡、抓猪,到处搜查,一无所获。由于村中无人,敌人就从对面山坡上了山,进行搜山,一直折腾到太阳偏西,也没有任何收获,只抓了几个老百姓,就从另一个山梁撤走了。我们很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
之后我和谢雪萍就又回到卫生部,继续工作。
与扫荡的敌人周旋
1941年9月初,敌人调集了日伪军共7万多人,利用他们控制的交通线,从四面八方向北岳、西平区进行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晋察冀边区周围各县城的敌人都在增兵,军区估计敌人又要扫荡晋察冀边区,就布置了反扫荡的行动计划。卫生部为精简机关,同时加强后方医院各所的力量,便把部机关的大部分人员分到各所去帮助工作。谢雪萍是广东人,因口音不群众化,被留在卫生部机关,而我被分配到了二所。
9月上旬,我先到杨家台后方医院,院部给我写了介绍信,并派人把我送到二所。二所在冀西唐县和易县之间的白银坨道士观庄,位于白银坨主沟中一个叉沟清凉峪道士观沟的上端。我们从唐县的梯子沟出发去二所,梯子沟地势十分险要,出入口像梯子一样陡峭,故称为梯子沟。爬上去的时候像天梯一样难走,而下来的时候就更加困难,因为全是石头,没有树木和蒿草等借以攀扶的东西,只有用手攀着石头,一步一步地往下爬。虽有院部的通讯员送我,但在离底下还有两米多高的时候,我脚下突然踏空了,一下摔到了沟底,摔破了手腕和膝盖,扭伤了脚。休息了一会儿后,我又一瘸一拐地继续上路。
我们又走了1000多米河滩路,才到了仅有十几户人家的白银坨。我顺着上山的梯子路到了二所所在地道士观庄,见到了高洪江(原名高锡勤)所长和郭指导员,还有支部书记王敬同志。他们看我摔伤了,马上让人找来王蕴华医生。她看了我的手、膝盖和脚,问我是怎么摔的?我告诉她情况以后,她将划破的地方细心地用酒精棉擦洗,然后涂上药包扎好,接着又给我揉搓按摩扭伤的脚。经过她的精心治疗,没过多久我的脚就好了。
二所早就做好了反扫荡的准备,他们将伤员分成两组,一个是重伤员组,一个轻伤员组。重伤员组由郭指导员、王蕴华负责。因为重伤员病情较重,不能行走,就转移到隐蔽洞里。这些隐蔽洞早在几年前就已修成,是利用各种地形地貌修建的,大部分修在梯田中,先在田中挖一个深2米、宽2米、长短视地形而定的地窖,平好顶,培上土,种上庄稼,洞口多在地堰的石头里,洞口外地里长满了高粱、谷子和玉米,外面完全看不出痕迹。修在深山草丛中的洞口外则长满了野草和荆条子,也有的石洞上面完全是石头。因为这些隐蔽所是固定的,要求严格保密,那些住洞的伤员只知道自己的洞,对别的洞毫不知晓。
王蕴华医生负责附近大山上五六个洞里伤员的治疗。她与另外一个医生和几个看护员为一组,白天就藏在山间的野草中,天黑以后下山,到道士观去做饭。吃了饭后,担着饭和水到山洞里,送给伤病员,并进行治疗。因为不能让人发现,他们都是摸着黑走路。出入洞口,不能经常在同一个地方走,以免形成一条路的痕迹,暴露洞口,也不能留下脚印,有脚印时都要在走时用荆条扫一遍。伤病员闷在黑呼呼的地洞中,也不知道是黑夜还是白天。每次王医生来,他们都非常高兴,因为王医生不但给他们送来饭菜,还给他们带来外面的敌情和我们反扫荡胜利的消息,又对他们病体给予治疗,给他们试体温、发药、包扎伤口。这些工作做完后,王医生他们告别伤病员,又到另一个洞去。这另外一个洞,有的在三五里之外,有的还要翻越一两个山梁。没有月亮的夜里,伸手不见五指,路是漆黑的,走不惯黑路的人不时被石头绊倒,可他们不畏艰难、不辞辛苦,爬山越岭,总要在一夜之间把他们负责的五六个洞跑完,赶在拂晓前离洞上山。
轻伤员组由高所长、王敬书记和我带领,在磨鼻子山和玉皇坨一带跟敌人转来转去。一开始我们带有六七十个轻伤员,反扫荡进行一个多月后,我们这个队伍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原来在洞中不能行走的伤员,经过诊治有不少恢复了健康,可以行走了就不愿意呆在洞里。洞中天天不见天日,一旦被敌人发现就无法躲藏,非是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呆在洞里。所以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已经达到100多人。队伍庞大,隐蔽的地方就不好找,之前我们也遇到过敌人,但都由于我们警惕性高而脱险了。我们从不留恋村庄,一般都是晚间八九点钟下山,到老乡的地里掰来玉米,留个借条给老乡。老乡们也都愿意,因为这等于他们收了庄稼交了公粮。我们把玉米粒搓下来,放在碾子上碾几遍,即下锅煮粥。粥刚煮好,就听见瓷碗和小勺叮当乱响,随即一片吃饭的嘶嘶声,锅中的稀饭很快一扫而光。没有油也吃不上菜,在稀饭中放少许很宝贵的盐,就算不错了。为了节约盐,每餐只放一点点,大家吃起来还感到挺香甜。吃过饭差不多也就夜里12点钟了,我们就上山,今天上这个山,明天上那个山,总是躲着敌人所搜的山走。我们是没有战斗力的队伍,每人只有两颗手榴弹,主要任务就是与敌人周旋,不受损失就是胜利。
悲壮的道士观突围
之前敌人每次扫荡都是一个多月就结束了,我们队伍壮大之后,敌人的扫荡持续了一个多月,仍毫无结束的迹象,大家都感到很疲倦。因为敌人对晋察冀山区的扫荡,采用的是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所有的村庄都采取了“坚壁清野”,所有的老百姓也都藏在山中,村庄已经是空无一人,敌人到过的村庄则被烧得一片废墟。
一天晚上,我们在道士观吃完晚饭,午夜12点集合上了道士观东南的大山。山上长满了一人高的荆条,人们分散在荆条中睡觉。拂晓,我们隐隐绰绰看到西面的山上有一队轻装行进的人,他们穿白色衣服、蓝色裤子,没有牲口,没有背包,一个紧跟一个鱼贯似地上上下下,攀登着前进。一会儿,沟中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合着山谷的回响,像爆豆子一样。从枪声判断一定是敌人进山了。我们趴在荆条丛中,一动不动,静观动静。天大亮了,枪声依然不停。不一会儿,司务长带来一个陌生人,瘦瘦的身材,高高的个子,脸上的肌肉微微搐动,警惕的目光不时向四周张望。经介绍,他是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姜同志,刚才和敌人遭遇了。原来,他们是白求恩卫生学校的一个大队,200多人,由政委俞忠良带领,昨天夜里两点来到道士观,在村中吃饭时听到了枪声。敌人已经占领了村南的高地,地形对他们十分不利,他们没什么战斗力,更没什么战斗经验,便四面八方向外突围。姜同志顺着沟向南飞跑,可南山上的敌人已经追下山来,有两个敌人追着他不放。因沟中陡弯很多,敌人的火力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他迅速爬上陡坡,弯弯曲曲地向前爬,敌人放枪未打中他,但与敌人的距离却越来越近,在这紧要关头,他向敌人投了一颗手榴弹,趁手榴弹爆炸,他跑上了山,翻过两道山梁,甩掉了敌人。
下午四五点钟,敌人撤走了。村中的韩老伯来报告:敌人扫荡时,他正躲在沟南面山中的石缝中,看见不少同志都顺着沟向东跑,不料山上的敌人追了下来,他们跑到沟口向上攀登,敌人在后面边追边打枪,爬上去的人有的被击中掉了下来。在敌人追到距沟口30米左右,突然两个敌人被打倒了,于是后面的敌人急忙停了下来,架起机关枪疯狂地向沟里扫射,然后又向上冲,又被打倒了几个。敌人冲了几次,才发现沟口北崖的石壁上有一个小石洞,八路军正藏在那里阻击敌人。敌人用机枪疯狂地扫射,因洞口很小,没有奏效,敌人又向洞口投了许多手雷,都在洞口周围爆炸了,再加山路很窄,敌人又不能一拥而上,气得没有办法,哇哇直叫。直到太阳偏西,洞里的同志子弹打光了,敌人才冲上去,洞中的几个同志惨遭敌人杀害。第二天,二所的同志和村武委会主任到沟里去查看,看到山上有不少我们同志的尸体,山洞里阻击敌人的那几个八路军战士已血肉模糊。这些英勇牺牲的烈士是中华英雄儿女的代表,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
玉皇坨遇险
由于二所住在当地,我们和村干部都比较熟悉,每天都由民兵带路,找那些蒿草、荆条多的地方隐蔽。这些地方都比较潮湿,日子久了,大家身上都长了虱子,有的还长了疥疮。
有一天,我们问村长,明天我们这100多人到哪里去隐蔽?村长想了想说,玉皇坨南边有个石隩(指河岸弯曲的地方),你们可以去。我们以为石隩是个洞,就问村长能容下我们这些人吗?村长说:“能,可大咧!”我们一想有这么个好地方,今晚可以找个阳面山坡睡觉了。那时能在山阳面睡觉就算是改善了生活。
我们早早吃完饭,于夜里12点多钟向玉皇坨方向赶去。中途到了一个阳面山坡,由于山阳面被太阳晒得热呼呼的,大家很快都睡熟了。当我睡醒睁眼一看,“啊呀,不好!”都快拂晓了。这时王敬和高洪江也醒了,大家一看,真槽糕,的确晚了。高所长命令大家赶紧打上背包赶路。
从我们睡觉的地方到石隩还有七八里地,同志们用急行军的速度赶到了石隩,天已经大亮。我们一看石隩的地形都惊呆了!这哪里是大河,而是一条干河沟,河底不是小石头,全是大石板,地势很险峻。当时没有雨,河里也没有水,如果有水,就会形成许多条瀑布。每一个台阶都是立陡立陡的,有的十六七米高,有的20多米高,石头底一株草也不长,就是河两岸的草也不多,荆条也很稀少。我们一看这种地形都傻了眼,这地势虽险要但没有荆条和野草,无法藏身,马上转移也不知道哪里有好地方可去,加上100多人目标相当大,不能无目地的转移。当时二所所部只有一个警卫班。高所长说:“先叫大家采荆条子掩护自己,警卫班布置在山头上,我去看看山那边有没有可隐藏的地方。”他带着警卫班爬上了山头,我们这些人都在河岸两边采荆条子,还没有采到一把,一架配合敌人搜山的日军飞机就飞到了我们头上盘旋。我们下令所有的人都卧倒在原地不许动,只要不动,高空中看到的就是石头和杂草。这时候有8点多钟,敌机在玉皇坨上空盘旋了一个多钟头,扫射了一阵子就走了。我们又继续采荆条子。这时,听对面山上有幾个老百姓问从半山腰跑上来的几个百姓:“敌人到哪儿了?”下面的人回答:“到了黑猪沟上口了!”按说黑猪沟口离我们这儿还有20来里地。可是这个老百姓的话音还没落,一声枪响,敌人就上来了,老百姓往我们对面的高山上跑去,敌人也追到了我们对面的山上。我们和他们的直线距离只有二三百米。这时,王敬同志命令所有人员就地卧倒,绝对不许动,以免暴露目标。伤员们大多在河的西面,他们与敌人还隔着一些小山头,我和王敬,还有一个小通讯员,坐在河东岸的山坡上,面对敌人,监视敌人的动静。我们每个人都有两颗手榴弹,手中举着一把荆条子,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扮作石头,监视对面山上的敌人。敌人追到半山腰,有一片萝卜地,敌人就冲到地里拔萝卜,坐下来用刀削萝卜吃。敌人都穿着便衣,蓝裤子白褂子,大多数拿着盒子枪,也有的背着三八枪,这一切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忽然,有一个伤员看到敌人,惊慌得站起来,想要逃路。我和王敬同时厉声喝道:“不许动,卧倒!”那个伤员冷静了一下,立即乖乖地卧倒在地。
敌人在玉皇坨上来下去搜山,抓了一些老百姓,一直折腾到下午2点多钟,才下山去。我们趴着的、坐着的手脚都麻木了。敌人走后,高所长带的一个班也从山上下来。所幸敌人没有到我们所在的石隩。
血染葡萄沟
这次行动给了我们很大教训,由于所带队伍人太多,目标太大,活动不方便,当天夜里回到村里,我们便商量要把队伍分出去一小股。我们把郭指导员也找来,一起研究,最后决定分出30多人,抽调王蕴华医生和田管理员共同负责带这30多人的队伍,让他们在葡萄沟的附近打游击。王蕴华是保定清苑县张登镇人,幼时丧母,在继母的教育下长大,继母待她如亲生女。她爱国意识很强,1937年在保定女师上学时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七七事变后,说服了继母,通过地下党到了晋察冀,考入了白求恩卫生学校三期,她与支部书记王敬是同学也是老乡。这次所里把这个任务交给她,她毫无畏惧,欣然接受,表示一定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把他们分出去10多天,都安然无事。一天晚饭后,我对王敬说:“咱们该到王医生那里看看,他们那个组刚成立不久,不知有没有什么问题?”王敬说:“对,他们单独活动没有经验,那咱们今天就去吧。”我说:“今天我发疟疾严重,全身无力,明天去吧。”王支书说:“好吧,正好我还有几份鉴定没写完,今天写完,明天就去。”那天,我们照样上了山。在荆条丛中,我发着疟疾,哆哆嗦嗦,王敬在写鉴定。天黑后我们下了山,刚回到屋里,就看见田管理员脸色苍白,由一个看护人员搀扶着一瘸一拐地进来,她满面泪痕,看样子情况不妙。所长急忙问:“出什么事了?”田管理员说:“今天拂晓我们与敌人遭遇了,现在出来的就我们两个,别人恐怕都遇难了。”接着她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昨天夜里,他们吃完饭就上山了,选择在梯田的玉米地里隐蔽。天亮时,他们听到沟口有枪声,觉得这里地形不好,就立即向山上转移。他们顺着梯田往上走,结果被敌人发现,敌人尾随其后追了上来。他们绝大部分是伤病员,行军速度不快,管理员在前面领路,王医生在后面断后。他们用尽力气爬山,快到山顶时,遇到两条路,一条大路,一条小路。管理员想避开大路走小路,刚绕着山头转过弯来,敌人已从大路上赶了上来。枪声一响,管理员迅速就地卧倒,等敌人冲上来,她扔了一颗手榴弹,随即一个箭步转了一个弯,跳出了敌人的包围,一口气翻过两个山头,躲进草丛里。敌人从前后两面包围了他们,他们和敌人拼手榴弹。一片喊杀声,看护员看自己旁边是悬崖,就甩出了手榴弹,乘着黑烟顺势跳下悬崖。幸亏悬崖不高,下面又是篙草丛,她跳下来后没有受伤,连滚带爬,滑到山下,藏在荆条丛中,直到夜里才出来找所部,和田管理员相遇。她是跳山涧逃出来的,其他同志恐怕都遇难了。噩耗像铁锤一样,沉重地敲打着我的心,那30多位同志可能凶多吉少,我很后悔,若是昨晚去看了他们,就不会让他们在玉米地里隐蔽,发现敌情后也不会集体行动,可后悔也无济于事了。我们决定派通讯员连夜到清榆沟北山把郭指导员找回来,一起到现场去查看情况。就在这时,王医生那个组又逃回来一个轻伤员,他也是和看护员一样跳崖脱身的。他的回来给大家带来了希望,我们盼着其他同志也能一个个都回来。可等到夜里两点,再没有同志回来。
郭指导员闻讯赶来,高所长、郭指导员、王支书、田管理员和我,连同通讯员一共6人,夜里2点钟出发,在黑暗中爬山越岭,摸索前进。拂晓前,我们到了出事的那个山坳,趴下来仔细观察,看是否还有敌人的动静。周围寂静无声。根据敌人的活动规律,总是拂晓前包围目标,天亮即可看到敌人。我们一直等到天亮,看无敌人活动,也没听到枪声,便爬上山顶。原来那里并列着南北两个山头,一个北山,一个南山,西面是大路,从小路这边一直到与大路相接的小路尽头遍地都是遇难同志们的尸体。有的是被刺刀刺死的,血迹斑斑,有的是被枪打死的,还有的尸体不全,血肉横飞,说明当时是一场血战,同志们拉响了手中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还有一个伤员蹲在石缝里被敌人刺杀了。王蕴华医生躺在队伍的最后,她紧攥着的右手小指上,还有一个手榴弹的拉环。我们摘下帽子,走到王医生的跟前,向她默哀,眼泪不住地往外流。王敬猛地扑在她的遗体上嚎啕大哭。这时候,郭指导员大声说:“同志们,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敌人的残暴不能摧毁我们的反抗意志,只能在我们的心中种下一颗颗复仇的种子,我们要争取反扫荡的胜利,为死难的烈士报仇!”当时敌情变化莫测,我们必须抓紧善后工作。同志们擦干了泪,清理战场,把死难同志们背包中的遗物清理出来。在清理王医生的背包时,发现里面装有一本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一本白求恩卫校印的《内科学》教材。
无限的怀念
清理完战场,我们下山来到了只有几户人家的葡萄沟小村。晚上,我们找到葡萄沟的村长、支部书记和武委会主任研究善后工作。请他们帮助动员一些民兵,掩埋遇難的同志们。这个夜间,他们爬东山上西山,找来了10多个人,商量如何掩埋,商量好时已经快到拂晓了,他们拿着镐头、铁锨往山上出发了。我们还在小村子里统计被害者的名单,并注意收集敌情。这时已经八点多钟,太阳已经出来了。民兵们来报告说40里地内无敌情,我们就在屋内大胆地工作。然而民兵刚走不一会儿,突然听见沟口方向有枪响,我们揣测说:“敌人不会来得这么快吧?可能是自己人发生误会了?”高所长说:“不行,咱们还是提高警惕,上山!以防万一。”大家都同意,立刻收拾手中的东西,迅速爬上对面的东山。这个山不高,但地形复杂。我们也只爬了二三百米高,山下出现了部队。我们就藏在梯田中,向下观看,看见他们都穿的是八路军的棉灰军装,有部队、有牲口,有走着的,还有骑骡子的。这引起了我们怀疑:这是我们的人吗?队伍怎么这么大?自反扫荡开始后,我们的部队大都化整为零,没有这么大的队伍,而且我们的队伍大都是夜行军,这种白天行军的大队伍根本没有见过,值得怀疑。
队伍从沟口进来了,已经绕过我们的山脚走向小村。骡子颈上的铃铛有节奏地叮当响着,我们听得十分清楚。郭指导员转到山前高喊:“你们是哪部分的?”山下的队伍没有回答。在我们同志遇难的北山上,住着一个战斗连队,他们在北山顶上布置了哨兵,架着电线。只听哨兵也高声问:“你们是哪部分的?”下边的人仍是没有声响。队伍进了村庄,我们看到有的人端着枪在搜索房屋,有的在捉鸡抓猪,把鸡猪都抓得叫起来。这一下真相大白了,是敌人伪装成我们的人。北山上的队伍急速拆卷电话线,立即撤走。郭指导员也迅速从前山回来。敌人大概因为地形对他们不利,所以始终没有答话,当他们到了山顶坳部的路口,立即把机枪架起来,掩护他们的大部队继续行进。
我们趴在谷子地里,静静地等待敌人通过。敌人在山下走了两个钟头才过完,直到在北山坳部架设机枪的敌人也撤走了,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但是我们还是担心北山那些负责掩埋工作的老乡们的安全,因为敌人的机枪不仅架在路南的山坡上,而且敌人的队伍也路过那个山的路口。到了晚间有几个民兵告诉我们,白天他们正在那里做掩埋工作,听到枪声,看到伪装的队伍,有几个同志隐藏起来,而没有隐藏的几个老乡都被敌人抓去了。第二天,村干部又帮我们动员了几个民兵,才完成了掩埋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