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黑胶时代
宁夏/王西平
河北/田志军
我的黑胶时代
宁夏/王西平


我爱你黑铁一样的孤独,你孤独如同一个冰冷的怪物,你宠爱的怪物如流放的 “自我”,仿佛宠爱的钻石与铁锈,从一个男人黑黑的腋下划过。
哦,是那个叫黑夜的男人,和你一样丑陋,胡子拉碴,有一头白发蓬刺般爆炸,发出火石的电光。而另一个男人,送你一些细碎的纽扣,和一支香烟,你倾倒在他的臂弯内,他用热辣的体汗和玫瑰口水喂送迷幻的药丸。
嘿,精神的圣女,骤然出现在我面前的你,刺耳的、并特意讨人喜欢的你,站在镜子那遥远的内部,和一切闪光的物,像树桩一样跳上舞台,像漫画家那样为声音填色,像咆哮的孩子释放廉价的诗句,像怒放的磁铁石扬翻整个世界。
现在,所有的人手里拎着彩色的收音机,经过那条大裤衩的街,“哇卡卡嘿,哇卡卡嘿,哇卡卡嘿,哇卡嘿,哇卡嘿……”,突然你在每一个赫兹的高点,抛出黑云凝血的块,像一代传奇卡在水泥杆子上,又像十万吨羽毛飘向一群智障的列队。
我依然爱你,像裸体游泳者那样喘着热气爱你,像大象那样爱你,或像大象那样踩过枯枝烂叶嚎叫着爱你。像困兽那样爱你,爱你用包罗一切的布鲁斯困住所有的浑蛋男人般爱你。爱你冰冷刺骨的疼,和一把血斧劈开的狂言乱语。
是的,放纵是一种摩擦,27年,正如你的死亡,在正负两极之间的太平洋上游动,然而当浪花碎裂时,啊浑蛋,大马力的妖女,贾尼斯·乔普林,我们追逐着高巅上的蝴蝶,被雄鹰写入“捕猎的情景”,或在世界至高的火花中,获得重生……
注:贾尼斯·乔普林,被视为摇滚乐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歌手之一。她的演唱无与伦比,即使历史中,她只出了一张专辑,但也足够了。作为上世纪60年代最引人瞩目的摇滚女歌手,她27岁就死了。她唱歌的生涯也没几年,但她却仿佛积蓄了一辈子的力量,在短暂的时间里,尽全力爆发。

我们和虚晃一枪的黑趟过清晨之河。
吉他之声渐渐隆起,露珠准备剧烈进化,可能会,像一道烟的蓬乱主义那样,将他们赶回昨日。我们看见一群猫搬弄着一个山羊皮制的计划,它们或挽着手(爪),渡过英国乡下的无鼠之河。
不同温度的冷水,和被阻止的泪迟迟未能落下,即使有人暗中吹起了口哨,或者,两种夏日的混音再度响起,他们,仍然相爱,并且为和平而卧床不起。
他们相拥如蝶翅的情形,轻启玫瑰双唇刺向绒毛丰腴的床笫,亦如小野,活着,就是切片,不断切片。抑或不食烟火地相觑,只需一种裸姿,即可泅过终生的愤怒和不安。
魔鬼鼓起勇气,冲过了罗马大街,亮出藏在下腹的手形枪管,瞬间弹雨磅礴。那一刻,所谓为你迷者癫者是魔鬼,和刺耳的调调一番厮杀之后,三头六臂助长为八头八臂,他丧心病狂,如云烟氤氲,在日光下带着胜利。
死神终于来了,复制着你落满灰尘的地毯,复制着你蹒跚的拖鞋,复制着你绿毛的药片……戴圆眼镜的长头兄弟,正处于蓝色的想象之后,如病态的法师,穿越凌波不乱的枪眼。
世界为之幽闭,又为此而震颤。如此,只剩痛心,人们用同一句歌词不停地谈论,“首相,小人,楼梯扶栏,筒筒罐罐”。人们都问,“樱桃好吃吗?螃蟹好吃吗?橡皮色的溜溜圈好吃吗?《幻想》这首歌好听吗?”他们聚集在曲张的静脉间,放牧红油焖虾,然后在镭射的低噪音中蘸取黑色的胶汁。
列侬走了,他却说,“没有人会被杀或为此死亡”。他,带着鼻翼的油光,打碎了所有的碗,不慎带走了给和平一个和平的机会。我们在他的墓前用烟嗓炸响一串焦糖,因为我们聆听这纯酿的甜音,放弃了听其它一切可能的苦。
注:约翰·温斯顿·列侬,英国摇滚乐队“披头士”成员,摇滚音乐家,诗人,社会活动家。1980年12月8日晚上10点49分,列侬在纽约自己的寓所前被一名歌迷枪杀。1994年,约翰·列侬入选摇滚名人堂,2004年约翰·列侬入选《滚石》杂志评出的“历史上最伟大的50位流行音乐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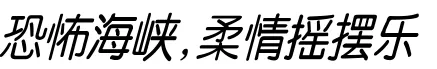
此刻,透过枝叶的缝隙,看见每条晃荡的大街上,有人光着膀子行走。
公园里正下着大雨,万物啊生长,我们吹响了的喇叭抛向高地。顷刻,如此浓郁的小镇风味缓缓下坠,看着它吧,多像家乡的马铃薯之花,这一切,绝非来自那贫困的洞洞村。
现在,有请摇摆之王,马克诺弗勒出场。灯光一路追逐,仿佛只是看了一眼,我们就被迫滋生出了“事迹”,仿佛回到了秋天,收获着无用的金钱。
是的,爱情胜过黄金,神也说过:情比金坚。我们相恋,携手,走在晃荡在大街上,成为了斑马的斑,也成了斑马的马。
呼吸击打着单薄的身子,花衬衣吹了又吹,蓝裤子的少年,越过星期五的晚上,又等同于过了一年。
请快速穿过咬定的时光之箭,收集所有的“角落”,隐藏来自夏日的一面镜子。于是,我们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在黑暗的阴影里,点燃火把,用松枝挂起斑子麻黄编织的鞋子。哦,洞洞村,这里是地球上神居的村,音乐里的小飞侠,你是村长,是爱人,是战士,是渔夫,是囚犯,是戏子,是小偷,是政客,唯独不是乐手,你站在泰恩河畔的赌场,和矿工的尸体分捡清冷,你唱纽约的电器商店,唱营销员,用静谧的弱拍对他们说三道四。
哦,我听恐怖海峡,柔情摇摆。
让我们手擎鲜花,或用白色的枯刺缠绕着天鹅与天鹅的颈与颈,那里有碧绿的池,有粉红的唇,那里,我们拥有每一个夜晚,和滚烫的金心。

哦,夜半恐怖海峡,翻江倒海,烟水茫茫。他们啊,四个人,歌声击打,纷纷如雪,仿佛马蒂斯的纸屑计划亦纷纷。
他们重回英伦,风正劲,天空的声名鹊起,大地,摇晃着胸脯,溢出深草里的忧郁。
蓝色的海峡王子,摆动着裙角和枝叶,拉起小提琴。听众纷纷起皱,紫色的拳头漫过额头,在空中变异,交织,奔跑,酷似金豹释放体内的简笔。
伟大的朋克组合,挽救起的死亡之鼓。
今晚,在每条大街上,茶不足,酒不足,我们是柴火的小分泌,
女人无痛,水波漾起。一声大钹搓起,喉咙里的裸女轻轻开启香唇,蝉影里的小拨片,触动了鸣叫。
雷闪阵阵,被劈成恐怖海峡的琴瑟演奏家,他说,“爱情胜过黄金”。我们整日浸泡在泪水里,没有光景,只有在音乐里,口含快乐的小铃铛。
今晚,纸币翻滚,我们高喊着:凤凰,凤凰。
然而蝴蝶翩翩数只,昏暗的汽油灯下,人人奉马圈里的天使猫为自由之神。
“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
听吧,时代的摇滚制造着金句,我们骑着黑白的泡泡收听王国的赫兹。
注:恐怖海峡(Dire Straits),伦敦乐队名,1976年创建。 他们的成功主要应归于吉他演奏大师、乐队的核心人物马克诺弗勒(Mark Knopfler生于1949年8月12日)。我的南方:云行风中
河北/田志军
1 我的南方是水打湿的,它在诗人陈东东的诗歌里表达了弄堂;对于南方我是陌生的,就像北方的田野——它不会打湿衣裳,他可能是北方的庄稼,是一蹴而就的简朴和健康。那时候,我很小。一直生活在母亲的怀抱,即使现在大了,母亲,依然是我最伟大的称呼,就像小时候,玩泥巴的孩子表达的——美学。
2 南方是水做的,它一点都不粗糙。即使是弄堂也曲曲折折,像水的波纹。但我一直纳闷,南方为何以加速度的节奏,将弄堂演变成了钢铁的森林,其实,即便这样,南方也依然丢不掉一身的水气,甚至是关于弄堂的味道。我在那份小资情调中,品味了——南方。有时候,我更多的觉得南方——像一阕宋词,但里面有人生百态,也有历史纷扰。
3 走进南方,也就走进了《长恨歌》。一个旧得发黄,甚至有些枯萎的故事。或许这是一个世纪的蹒跚,但我总是将北方的雪与南方的雨混为一体。因为我生活的地方,有一汪水,它滋润了四季,也丰富了我的想象。我相信:在我的人生履历中,肯定与南方交织,即使将雪朗诵成——雨,以及弯曲的水波。这一次,我要到南方去,聆听它的濡湿,看一下久违了——爱。
4 在北方长期呆久了,向往南方或者对南方的憧憬——是很自然的事件,只不过我的惦念,表达的更多是对炊烟之上的理解,那既是缥缈的天堂,也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百般惆怅。是的,当青春褪去青涩,当时间不再旋转,美丽的南方也只能是一个归途,至于天空的云岚多么邈远,那也是一声萧萧的嘶鸣。我,我的南方啊......
5 对于我而言,南方是一个温暖的词,它表述了一章可以叫做“华贵”的音乐,有如《前奏曲》,在我的印象中是这样的,没有华美,却有美丽,也可能是施特劳斯的某个短片,打动了曲曲折折的水乡。事实上,南方是突出的,就像北方——一直在呼唤一曲弯曲,这是南方带来的曲曲折折,也是北方的屋檐上的点点滴滴。
6 对南方的期待是少年时代,那时在诸多名家的美文中读出一种意蕴,比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鲁迅先生的乌镇系列及从文先生的湘西等等,他们的故国情怀、乡土情结、人生情爱,是一种剪不断的忧伤,就像弯曲的水泊动千年的——乡愁。南方,的确应该是一种期待;它在风雨如磐的时代,坚守了清洁的精神。
7 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雪铺天盖地般涌来,席卷邯郸大地,它让我在宁静的期待中聆听来自天空的巨响,更使我带着一种张望的情结——眺望南方。雪是雨的精魂,雨是水的上升。那无边的大雪接连了大地和天空,也将南方的妩媚和北方的粗壮融为一体。化作天籁之音,变为羽化之蝶,与奔驰的群山起舞,和通幽的弄堂清唱。我也在这流淌之中,渐渐抵达了春天,慢慢打开了命运之门——又一次返回了心灵之乡。
8 当暴雪覆盖了北方大地后,它悄然将目光伸向南方,在我清理40厘米厚的大雪时,南方迎来了一场大雪,此刻,大雪将南方和北方接连成一个崎岖的平面。也就在这个寒气逼人的时刻,我的南方和北方融为一体,它于无语中强调:世界是小的,也是横亘着的。这场轰轰烈烈的雪,也在颠覆之中压榨了我的屋宇,让我再次眺望“挽歌”,敲开了一个世纪的命运之门。并在野性的夜晚,冥想一个人的心灵史和一个地域的变迁史,这一切——源自于一个叫做“南方”的宽泛的词。
9 在大雪的舞蹈中,南方又一次召唤了我的灵魂,就像我赖以生存的北方的炊烟,它在轻柔的音乐里——抵达了我头顶上的天堂。但是,这一次我决计忘记,包括夏娃和亚当;包括雨、荷、雪。天堂——那是我的南方,也是大雪惦念的故乡。
10 我不知道南方是否有枫叶,那层林尽染的红——表达了刻骨的乡愁,但我对一幅唯美的图片写下:一幅印象的油画,一支漂流的雅歌,一对隐形的翅膀,一段散步的青春。任何微小的世界都孕育着天宇的风暴,它在一个瞬间进入永恒的雷电。就像南方——包含了太多的思想,在弯曲里浏览了千年的诗意的——乡村,但我依然仰视了“莱卡之城”,它连接了喧嚣的工业,在技术的程序里挥发人性的“风情”。因此,在南方的私语中,我遗忘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在 “葡萄牙的风”中——将南方——缠绵。
11 当我从《失乐园》中醒来,又一次对天才的17世纪瞭望,在踯躅中聆听一个辉煌的百年。这也像南方带来的一种澄明的憧憬,它在携带着风暴的宁静中,渐渐到达“康德之桥”。但是,却不是旋转的“幻象”,既不是指向“朝圣者的灵魂”,也不是《复乐园》中的基督,更不是力士参孙的轰鸣。它是一种诗意的栖居,是我依恋的里尔克的哀歌——一个空中的花园,只是没有天使,没有我的时代和南方。南方,你的弯曲打动了——嘹亮。
12 当我打开盛开的雪,也就展开了南方的画卷,她从雨巷中婉约而出,淋湿了年轻的戴望舒。她结着丁香一样的幽怨,撑起了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般的忧愁,这种怀旧的情结在大雪的舞动中——绽放。南方,是印象者的油彩,它的自恋使之变得高贵。即使是自虐也有一种华丽的风情,与美学保持着天然的渊源。
13 因为南方是远的,它翻腾在我的依稀的私语里;或许如冰山的异域,珍存着万千意象。就像陶渊明的几句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因此,南方是修饰的园林,它在自然的滋润中,汇聚了人文的烟火气味。我在对南方的想象中,扩大了她的容量,比如悠闲、平实、辛辣、承担等等,但是,我总以为南方有些许的水粉胭脂气,犹如古典的笔墨纸砚,它打开了缠绵的人性,不过,其中也有暴怒与狂躁,但它是隐喻的描述和表达,因为在“意”和“象”上,南方——更多地倾向了——象征。
14 南方是从天空徐徐落下的,也是从音乐的疏影中抖擞而出的。它总是在不经意间遗失来自隐秘的异域的符号,就像青春的明丽——依附于唯美而激越的乐章。它是一个春天的季节,将“他”打扮为“累人的明天”,将“她”扮演成“赛珍珠”,只有它依偎在传统的木船上,高歌,或低吟。怀揣着崇高的乡愁,把一轮明月唱醒,化为一波明亮的碎影。
15 南方是唯美的画卷,它舒展了古典的雨巷,但是,南方是楚楚动人的青春,虽然历尽文化中国的千年洗礼,它依旧是一卷《楚辞》。不管三闾大夫如何赋予“天问”绵远超然的意象,其清澈的“激愤”清明昭然。每当端午节来临,屈原便成为一个象征。也许距离产生美,阿赫玛托娃对这一天的“诗人节”情有独钟。我已不能铭记俄罗斯的“月亮之神”的悄吟,但我知道诗意的乡村和遥远的事物——必然携带着一个古老帝国的年轻的梦想。南方是美的,它不是如歌的行板,也不是《天鹅湖》;它是一个具备美丽、简朴、飘逸、功利、健康、勇毅、谦卑、怯然等多彩人格的复合体,简单说——它是一个乡下少女对爱情的第一次——呼唤。
16 在与南方的对话中,我领略了它的 “低音”,这像天蓝的叶赛宁的忧郁,携带着大自然的器官和乡土的绽放的气息。没有神明可以替代南方的青春时期的乐调,就像黄梅戏和河北梆子、大葱卷饼和龙抄手、南拳和北腿等,它有自己的领地。因此,其迂回婉转之情趣,犹如李煜之吟叹:“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但是,南方——肯定孕育着韬光养晦和刀枪剑戟,只是,云山之雾缠绵了它的内心的灰暗,变得豁达开朗起来,在青海湖的滋润中,一波激起了千层浪。
17 转身醒来,觉得清凉。不由怅想起南方的“千树万树梨花开”的万般妩媚,这种不期之约仿佛席慕容对内蒙古故乡之河的梦影的缠绕。在一个地方待久了,自然对另一个地域存在某种惦念,而且这种透明的向往——会随着生命的不断流逝变得越发的绵远。那么,这就像侗族大歌神秘的合音,那来自天堂的远古乡音,就在一个瞬间洞穿和照亮了任何卑微的灵魂,并以其温暖的手掬起神圣的痛苦,与奔腾的暴雪交织,和旋转的木桥汇融,在每一朵掉落的碎瓣里,阐释生命不断演变的主题。
18在我的“散步”中,大约有十个词——独唱,悬浮,停留,挽歌,低音,时间,雪豹,经典,诗意,忧伤。我把沉思交给了帕斯卡尔,把神圣的痛苦邮递给荷尔德林,把悲怆奉送给贝多芬,把精确呈现给修拉,把哀愁献予叶赛宁,把结构的城市描绘赋予斯蒂文斯……因此,我是不道德的——我没有提供有道德的诗歌。但是,我相信头顶上的三尺神明,就像圣母玛利亚凝视耶稣年轻的脚,在某一个瞬间,打通了隐秘的隧道,与我的南方——汇合。
19 在一个小镇上眺望南方,难免带有一个小镇与生俱来的自恋和哀愁,而这是一个拒绝忧伤的时代,或者说根本没有时间去——忧伤。但,南方是不同的,它在河流和大海的交织的舞蹈里,接连了——内陆的金黄。那黄土蜿蜒着的黄,就像曲折的水乡,它在悄吟的私语里,还原了一个词根:南方。
20 在我的“经过”中,总与南方失之交臂,因此,南方是我打通“命运之门”的金钥匙。人类的尊严在于思想,我也希望我的写作像一条河流,它横亘或摆渡在一个“湿婆之舞”的律动中,或者,潜伏在“美人鱼”的深海里,踏上“天路历程”,掬起“荒漠甘泉”,交合“南方北方”,将人性的生活——举起——并指向心愿之乡。那时,我远离了“乌托邦”,集解了萨福的“合唱队”,将荒谬写成荒谬,将真理写成真理。我相信屋檐之上即是天堂,也坚信在乌鸦的隐喻里,肯定隐蔽着一个——鲜活而高贵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