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见字如面说起
朱艳坤
古人讲见字如面,其实多是违心之言,见面哪里比得了见字。文字是有欺骗性的,深谙此道的人自然懂得扬长避短。写信之前,有充分的时间得以深思熟虑,何言当讲,何言不当讲,想得明明白白,落到纸上的文字自然万分妥帖。见面一个不慎,话一出口悔已迟,辛苦经营的好印象不免断送。

古人写信另有一桩妙处,便是信笺的运用,于今已少有人能够领会。好的信笺,如同美人的妆容。“十分美人七分妆”,漂亮的信笺即使不着一字寄过去,也是一种风流蕴藉。如此美妙的事曾经出现在日本,《源氏物语》中的风流浪子,遗一卷笺纸于草露相逢的美人,便是相思半生的情谊。
文川先生是个慢性子,放在如今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于古人却是解人。早些年他集火花而成大家,近些时候玩藏书票,也留下名家手笔满壁。在邮局门前冷落车马稀的今日,他把家安在了邮局楼上。去他那里喝茶,常见到远方寄来的包裹,有时还有刚拆出的书信,全是隐在历史角落的老先生以蝇头小楷写就,墨痕新成,余香犹在,雅人深致,羡煞晚辈。有一日闲坐在他的书坊翻书,门外走进来一位穿绿色制服的中年女人。他這里往来的文人居多,如此打扮的还真没见过,我还没问,文川先生已笑脸相迎,显见是熟人。后来才知竟是邮政的阿姨来问他要不要买近日发行的邮票,这玩意在我看来就是弃置已久的“古董”,还有专人来问他要不要购买,此君的“不合时宜”足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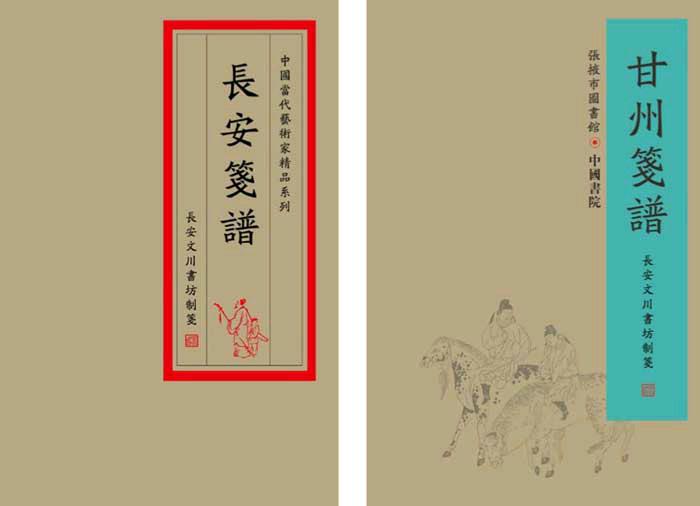
中国著名出版家范用曾说:“一张藏书票包含如许内容、思想、情操、追求,令人神驰,堪可玩味。”文川先生的藏书票很接地气,也通古代文化的气息,得到了国内许多藏书票艺术家的认可。他制作的藏书气象万千,每一款创作都别具匠心,花费了心思,融合了自己和书票主人的风格。
文川先生的雅兴最近集中到了笺纸上。周围朋友多笑他痴愚,如今互联网何等方便,字不拘多少,图不拘大小,鼠标一点,瞬息可达。更有甚者,开个视频,实时对话,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做信笺何用?且不说少有人写信,便是写信,又何须用纸?如此一想,旁人笑他痴愚,不是没有道理。但我与此君相交已久,他做的不合时宜的事又岂止这一桩,见得多了,也就不觉奇怪,反而期待他弄出个名堂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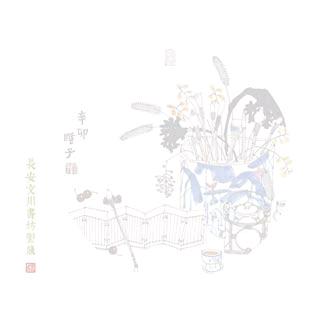

他从小爱读书,文川书坊里的书有万本以上,很多都是大部头的珍藏版:古籍、文史哲、书画散文、古今中外的版画图册,还有毛边本、台湾版的书、作家的签名本以及伊朗、尼泊尔等国的电影和唱碟。除了为作家、收藏家、画家、书法家和出版界人士定制藏书票,文川先生还为他们制作笺纸,如上海的陈子善、北京的邵燕祥和成都的流沙河,他们之间来往的书信全都写在充满古意的信笺上,缀满怀古情思。
清人项鸿祚有言,“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文川先生深得此言之旨。他整理手中的名家手迹,辛苦集字,描花写鸟,印出一叠叠笺纸供人涂鸦,用意之深,甚至让人觉得可惜。那么漂亮的笺纸,字写得丑的,但觉自惭形秽,又怎舍得沾染?一番辛苦之后,文川先生的长安笺纸倒是做出来了。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在《小引》中大致能看个究竟。它如是说,“文川本晋人,半生隐于长安,几间陋室,名之曰文川书坊,来鸿去雁,酬交天下相知,以为乐事。因与丹青妙手相得,集画满屋,夜思日览,遂起意效法先贤,以现代工艺,制谱以笺,引之斋号,配以图画,作笺纸百札,因地称名,号为长安笺谱。笺纸兼得书画之妙,取义高雅,又入时眸,为众所喜,风评甚佳。此不啻为今长安一桩风雅事,实可喜哉。”说到底,终究还是在叙说缘起、胸怀、情调还有担当。
诸君不妨取他的几页笺纸,不着一字,寄与心头可意之人,效仿无言浪子的风流,不也是一种意味深长的韵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