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的隐痛
□ 葛取兵
草木的隐痛
□ 葛取兵
我相信,草木像人一样,有灵魂,也有喜怒哀乐。
芒草
芒草是一种遍生江南极为普通的野草,俗名芭茅。与荻、芦苇、白茅极为相似,芦苇以水为邻,而芒草却是深根于丘陵山峦,沟坎坡梁,悬崖石缝,随处可见。春也罢,秋也罢,它奔走于山地,张扬喧哗。尤到秋日,芒花如雪,秋风拂动,满目苍茫。可声势再盛大,也改变不了卑微的命运。有时,卑微也是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
看到芒草,常让我想起舅爷爷,似乎谈不上怀念,但念想总冷不丁地把他拉在芒的背后,向着原野张望。张望,是乡村一种最好的坚守。应该是我十来岁的时候,也就是七十年代末期,离我家二十多里路程的舅爷爷每年会来我家一两次。双目失明的他全靠一根细小的竹杆探路前行,至今我无法理喻,他是如何一步一步摸索前行抵达他选择的终点。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有沟壑有泥泞,有乡村嫌贫爱富的恶狗,有酷暑的暴雨寒冬的冰雪,更有人情冷漠世态炎凉。
舅爷爷来时总会抖抖索索地摸出一小包山上的野果,最多的是秋天的毛栗子、饭泡子、山梨等等。当然还有几小节清甜的芒草根。母亲说,您老人家眼睛不利索,上山怕踩到蛇,又怕踩空跌下山。舅爷爷不动声色,“我看得见,这些东西就在眼前,一清二楚,让娃娃图个新鲜”。我有时调皮地用手在他眼前晃了几下,试探他的反映,很明显他浑浊的眼平静如水。我的举动却惹了母亲,她立马落下脸,高高举起手,似乎立马会呼啸而来。我如兔子般接过舅爷爷的礼物,蹦到院子里与小伙伴分享果实了。
舅爷爷的每次来临,不仅仅带来了山果,让我惊喜,更让我喜的是,舅爷爷总会带来三、五把用芒草花穗扎的扫帚,斜绑在背上,仿佛演老戏的武生背后高插的旌旗,手中的竹杆就是那根穿越历史的长矛,在人间挥舞金铁马。这是我的想象,很有趣,常常在梦中一遍遍地把舅爷爷演绎成武艺高超的侠客,抑或是神秘的丐帮帮主。传奇总是无法穿越梦境,现实的铁面却是如此苍茫。
一把芒草编织的扫帚又隐藏什么让我动心呢。
那时农村的扫帚不外乎几种,一种用竹枝丫做成的竹扫帚,大而笨重,主要是父亲用来打扫晒坪、院落;第二种是棕扫把,乡下的农舍前后都会长一两株棕树,大大的棕叶像张牙舞爪的魔掌,棕树,在我的童年边缘找不到位置,因为它除了扎成棕扫把,似乎毫无用处,用棕叶扎成的扫帚,笨重,不受我们欢喜。第三种铁扫帚,是农家来园子边生长的一种植物,应该是野生的,学名叫地肤,到秋天,枝条硬扎了,父亲会把它们砍下来扎成扫帚,一般用来室内扫地,轻便,但不容易清扫地面的尘土。最受我们欢迎的是舅爷爷带来的扫帚,用芒草扬花的穗扎成的,又软又轻,扫地时寂然无声,扫完的地面洁净,很容易得到父母亲的表扬。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会帮着父母亲承担一些家务活,哥哥主要是负责挑水,农忙时也会帮父亲挑谷搬草垛,姐姐会帮母亲洗洗衣服、煮饭、洗碗。我与妹妹的艰巨任务就是扫地。
其实,喜欢芒草扫帚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此扫地,还有一个小小的秘密。我小时虽不顽皮淘气,但少不更事,一不小心做错了事,自然免不了要挨父母的呵斥,甚至动用“家法”。父母的家法手段不异,母亲常常会用言语来表达对我们的不满。但母亲生性善良,对子女的骂也是单调乏一,不像村里的泼妇,骂起街来,词汇丰富多彩,言语尖酸刻薄,如一颗颗锐利的子弹呼叫着射向她的敌人。而母亲唯一的一句是“短命鬼仔哩”,气急了,会连骂几声,有时,母亲也会打屁股,惩罚我们。而父亲的家法则不同,不善言辞的父亲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我们领略生活带来的后果,父亲的家法一是敲叮当,我们背后叫“吃豌豆”,一般来得出其不意,父亲随手一扔,一记响亮的叮当敲在额头上,如吃炒脆的达锅豌豆,但品尝不到豌豆的香味。另一种打法是用荆条或竹枝打屁股或手板,这是最严厉的家法,轻易不会用,在我的印象中好像仅领教过一回。第三种家法就与芒草有关了。跪扫帚,面壁思过,自我反省,直到自认为已反思彻底,表示认错。竹扫帚,铁扫帚,棕扫帚,枝条硬,膝盖跪在上边,烙得生疼,唯有芒草柔软。所以我们犯错,首先要找的就是芒草扫帚。可芒草扫把有限,每年舅爷爷才背三五把过来,而芒草扫帚最大的弱点,不耐用,个把月,就体无完肤,只余一节手柄了,成为母亲灶膛里的柴火。正因为如此,我们舍不得用芒草扫地,也时时盼望舅爷爷到来。肩背扫帚,挥动竹杖,如得胜的武将策马而来……
人就是这么奇怪,一个小小的细节却成就一生的记忆。其实我至今不知晓舅爷爷的身世,我也无心去打听他的今生前世,我甚至记不起他的名字,也不知他的年龄,唯一知晓的是他无儿无女,一生未娶,孤独成为他最好的伴侣,寂寂地陪伴他屈指可数的岁月。最终,老了,无依无靠,全靠村子和亲人救济,那个年代穷啊,乡亲们都吃不饱肚子,何况一个老人呢?听父亲说,舅爷爷每年夏天,漫山遍野的芒草开花扬穗,舅爷爷总会在山上采芒花,扎扫帚,送给村里的乡亲,有时也会送到供销社,换一点酱醋盐之类的生活用品。但是卑微的芒草无法丰实舅爷爷的肚皮,手无缚鸡之力的他选择了乞讨,虽然不体面,这对于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又几乎是他最佳的选择。在我的印象,舅爷爷言语极少,有点吐词不清,裹舌头的味道抑或是孤独。一个人的生活让他沉默寡言。如今的盲人可以搞按摩,可以上街算命,当假神仙,可惜舅爷爷没有赶上这个时代,我有时想,如果舅爷爷当街一坐,挚起了算命的杏黄旗,真的如一位下凡人间的活神仙,为人间凡人指点迷津,道破仙机。无奈,舅爷爷选择了乞讨,而且总是在秋天出门。秋天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农村或多或少收了几担粮食入仓,总会施舍。至今,我十分诧异舅爷爷凭一根竹棍,如何外出乞讨,出村,回家,一个标点符号的距离,对于一个盲人又是怎样的遥远。我后来明白,每年秋季,舅爷爷来我家小歇一晚,只是他沿途乞讨的一个小小驿站。
其实,舅爷爷只是我家的远方亲戚。他的到来,母亲从未把他当做一个乞丐,在她的心目中,再远的亲人,也是亲人,这就是亲情,亲情无价啊。母亲总是想方设法弄两个菜,割几两肉,斩细,搓成肉丸子,做一个粉丝肉丸汤。又从鸡窝里掏两个蛋,还是温热的,放点紫苏,抑或从菜园子摘几个青椒,炒蛋。再煎几片豆腐,炒两个秋茄子,煮一碗南瓜,还有园子的萝卜菜。满满一桌子菜,舅爷爷看不到,但能闻其香,我能观察到舅爷爷的鼻翼有些颤动。舅爷爷总会吃两小碗米饭,细细地咀嚼肉丸子,吃粉丝时慢慢地吸,不像我们“哧溜”一下,粉丝吸进了喉。吃完饭,舅爷爷的山羊须上总会沾上几粒米饭,甚至会挂上一两滴肉汤,母亲掏出手帕,帮舅爷爷擦拭干净。饭后,舅爷爷眯着眼,坐在院子里,很满足的样子,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间泻下,落在他的脸上,梦一样飘忽。一脸的沧桑,像是解不开的心结。
苦难并没有压倒舅爷爷生存的信念,他总是以一种纤弱的努力来对抗生活的多难和命运的不公,譬如用芒草扎扫帚,譬如外出乞讨。一根竹竿,一个斜挂身上的布袋,支撑着他孤独的岁月。
终于,在一个喧闹的秋天,舅爷爷又执着拐杖外出乞讨,这一次远行他再也没能从秋天的深处抽身回来。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某种暗合,他出生也是在在一个秋意萧条的季节。丰硕时光的背后,是寒流逼人的冬季。那一次的离开,他的背影一定随着村口的雾气消融,随着飘逝的芒絮,遁入大地无处寻觅。尘世的漏洞就是这样叫人防不胜防呀。
我依稀记得那一年的秋雨下得十分绵密。一场秋雨一场寒。舅爷爷这一出杳无音信。家人急了,于是分头寻找,沿洞庭湖、长江水路寻觅,湖北的洪湖、监利、赤壁、通城,还有临近的华容、汨罗、湘阴、平江。寻找和失踪交织成一种蛛网密闭的网。找了一个多月,杳无音信,眼看着冬来了,一场雪披头盖脑地落下来,把这个季节凝固了。但时光凝固不住,再厚的冰雪也要消融,再寒冷的冬天也要走远,春来了,花会开。季节依旧轮换,如一茌茌的芒草。
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幸福,因为它能让人从此获得安详。后来亲人无从寻觅,断定他已客死他乡,便在家乡向阳的山坡上给他做了衣冠冢。从此,舅爷爷永远从我的视野消失,归于永恒的黑暗和沉寂。正如满山的芒草,在秋天枯萎消融。
那天从墓地归来,我回望了一下,满山疯长的芒草高过夕阳。高高的叶片和蓬蓬的穗状花,白茫茫地萋萋绵延,在斜阳的照耀下一片迷离。正是秋季,秋风下的芒草,残叶正在悄悄瘦去,当叶子消尽,一个植物的一生,也最后消去。若干年后,城市的喧嚣掩蔽了乡村风景,但在我的记忆里,还晃动着芒草。萎了,枯了,凝固了,但芒的落寞、怅惘,却永远被贮存。深秋,芒的那种情状,永远成为我内心一种残败、荒冷的风景。
人生一世,草木一春。春天总是如约而至,芒草在春风春雨中一定会发芽、生长、扬花,那如雪的芒花是否会守望这个失明的老人-----我熟悉却又陌生的舅爷爷,与我有着一脉血缘的亲人,能再回来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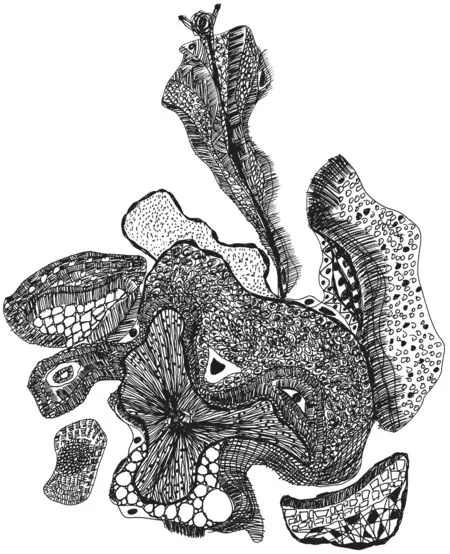
苦楝
人间四月,已是暮春。黄昏, 鸽子归家的弧影消失在错乱的屋顶上,大街上行色匆匆的归人或左右或东西, 向着家的方向前行。此刻,我突然想起,家乡的苦楝树正是花开灿烂的时候。
在乡下,树很多,村前村后,山上山上,树无处不在,有梧桐、樟树、桉树、杉树,更多的是枣、桔、桃、李,随处可见,它们大多三三两两,甚至毗连成林,唯独那树干斑驳,叶子细碎的苦楝树,在房前屋后,田头阡陌,或者沟壑的某个角落,总是孤独地生长着。苦楝树不成林,一切皆自由生长,有风也潇潇,无风也潇潇。自有一种树中隐士的风范。村人说,苦楝树苦,连花的味道也是苦的,弥漫开来,整个村子的空气也是苦的。我却喜欢苦楝花。初夏时节,桃花谢了春红,苦楝树浅紫的小花静悄悄地萌动。因为花小,树又高,如果路过不是闻到一阵又一阵浮动的暗香,促使你蓦然抬首,你是不会发现那一株寂寞的苦楝树。这时春天已经走远,只剩下一片模糊的背影,它没有赶上繁华似锦的盛世,却在春的末尾独自芬芳。开一树花,有风,落花一地,零落成泥。
这样想着,心里陡地生出了几许失落。心里似有某种记忆在渐渐地被唤醒。这种情绪中,接到乡下母亲打来的电话。母亲并没有像往常一样,零碎地说着见闻,而是直接告诉我一个悲悯的消息。
隔壁的君姐死了,死得很突然,一场不大不小的病竟然扼走了她蓬勃的生命,因为她还不到40岁。
母亲长叹一声:多好的姑娘哟,怎么这么早就走了呢?我恍若看到了一大滴晶莹的泪水从母亲的眼角涌出,那么义不容辞,是想告诉我什么?悲哀,或是怜悯。
会剪一手窗花的她,怎么就走了呢?我觉着她就是一株苦楝树,她的生命开着酸楚的美丽,像碎花飘零在脚下的土地,使我心震动漫溢。
我隐约记得君姐嫁到镇上来的情景。正是五月初,是花都已开过,是叶都已深绿。唯独苦楝,此时正开得浓烈。繁密的树叶间紫白相间的小花,一簇簇,一串串,挤挤挨挨,密密匝匝,满树可观。依旧记得她光鲜的脸庞在热热闹闹的鞭炮声中亮丽,新婚的她像一只美丽的百灵鸟在生活的每一个日子幸福地鸣唱着,她憧憬着未来。
记忆是湿润、清涩的。一张红纸,一把剪刀,眨眼功夫就从她的手中吐出鸡、鱼、莲等之类美央美仑的图案,一股喜庆味就弥漫开来。剪窗花是她的拿手戏。树有阴凉、草有灵气、花有香味,牛会吃草、鱼会游水、鸟会飞翔,剪什么像什么,我新婚时她剪出的窗纸还在老屋的窗玻璃上炫耀,只是褪却了光泽,消浅了喜气。纳鞋垫更是她拿手的好戏哩,左邻右舍谁没有穿过她纳的鞋垫,我至今都会感到那股柔柔的乡情。弄农家味极浓的小吃,都是她的绝活,紫苏姜梅、西瓜皮蜜饯……。正是心灵手巧的她,十多年来,硬是把拮据的生活,剪辑得有了些许生机。
其实,也不应走得那么匆忙。据我所知,那种病是不足以剥夺她的生命。然而贫困和劳累,使得病魔如阴雨连绵的细菌,在阴暗的角落地生长得蓬蓬勃勃。其实她的幸福生活尚未开始啊。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此刻是不是长跪在她母亲的坟茔旁痛哭呢,她们生命如此的灿烂,不正是她们母亲沉重的付出吗?挥之不绝的泪水拉不回君姐柔弱的身躯,可永恒的记忆又怎么能抹去君姐一生的辛勤与操劳。我不知道为什么故乡一些女人的命运如此多舛,而且我所知道的最朴素最善良的女人,成了记忆中青涩而潮湿的一部分。
其实她的幸福早就应该开始。可是当站在幸福与痛苦交叉口时,她选择了后者。依旧记得尚为人母的她,光洁的脸庞竟夹杂一丝凝重。年幼的我从母亲的言谈中悟出了些什么。那个哇哇叫喊着的女娃没有为她带来幸福。丈夫的指责,公婆的冷漠,如呼啸的北风,冰冷了她初为人母的笑容。或许是为了追求幸福的源头,或许是为了化解封建世俗的冰霜。她又选择生育。然而第二个幼小的生命来到人世时,带给她的不仅仅是身体的痛楚,还是心灵的痛苦。第二朵鲜花般的女儿又怎么知道自己的降临,给母亲带来的是痛苦呢?第三个女儿终于彻底断送了她的幸福前程,丈夫被开除公职迁怒于她,公婆指桑骂槐的谩骂。或许这就是她悲剧的开始。
一次回乡,我看到寂寞的她,带着小女儿若有所思地坐在村口的楝树下纳鞋垫,无言无语,或抬头仰望,目光里满是哀怨,或又低了头,若有所思。此时,我怎么能读懂她的心事。孩子就在身旁,小一点已睡着了,大一点的在萝卜开花的地头,瞅准卧在花丛中的蜜蜂,脱下鞋子,用力一扣,就捂住了,然后把这小小的精灵放飞;有时她赤脚站在渠边,耐心地将被水冲跑的蚂蚁捞起来,放在长满清草的田埂。
她们是一粒苦楝子吗?
苦楝树到了秋天,结满一串串的果子,椭圆,指头蛋儿大,自然叫苦楝子。果把儿很老,一兜一兜的在风里摇曳。苦楝子的确苦,小时候曾试着偷尝了一口苦楝子,结果眉头半天舒不开。难怪人们常说再苦不过苦楝子。但在孩子的眼中苦楝子是童年最好的玩具,年少的我们几乎每人都有一把自制弹弓,就用苦楝子作子弹,打麻雀,练靶子,玩的不亦乐乎。少年不知苦滋味。
我记得奶奶那时唱过一首关于苦楝树的歌。唱的大概是一个出嫁后的女子,婚后忙碌没法回娘家,将这女子比作苦楝树,一生皆苦。用的是我们家乡话,调子很容易记住。
苦楝子再苦,有女人的心苦么?
君姐真的就是乡下的一株苦楝树。
我想,假设当初她生育的是一个男孩,她的命运就不至如此悲哀。假如她生育第一个女孩后,坚决与封建世俗观念挑战,勇敢地闯出自已的一片新天地,她的幸福生活也会一天天走过来。但是生活中没有假设,没有退路,发生的事情又怎么能够更改呢?其实我只是期望用假设来为她的悲哀中掺杂一些幸福的气氛而已。我只是不愿意让她成为苦楝的隐喻。

其实她渴求幸福。她把一生的寄托注入三个女儿的身上,二十年的岁月眨眼就过去了,女儿一个个如花似玉,幸福的日子正在向她温柔地笑。我听到过她一次次地说,“女儿大了,就好啦!”可她等到这一天时,却又慷慨地把生命交给泥土,难道泥土中的生活是幸福的生活吗?是呀,泥土中有酽酽的稻香,有典雅的宁静,有从容的平凡,不然,她怎么会选择泥土?
生命有时竟然这般凝重,生命有时又是这么轻灵,我乡下的君姐在黝黑的泥土中是否真的很幸福地长眠呢?
故乡就是一棵苦楝树,微毒,让几多在异乡里守望的人寝食难安,不知能否想到苦楝树忧郁的身影。
已是深夜,无意读到一首诗:雨过溪头鸟篆沙,溪山深处野人家。门前桃李都飞尽,又见春光到楝花。想不到诗人笔下苦楝树纤弱而淡雅,自有一种朴素清新,温婉脱俗之美。苦楝原本也有它的另一幅面容。
其实草木并无高贵与卑微之分,苦楝树也不例外。
葛
葛,一种绿色藤本豆科植物。
在乡下,山林沟壑之中,不管是荒山秃地,还是石骨子地、砾石地,只要有一丝细小的缝隙,有一点点可趴窝的泥土,葛即可扎下根去. 有风有雨,再加上阳光的浸润,春天一到,葛藤就泥土里钻出来,开始匍匐蔓延,一路攀爬,渐渐舒展开来,热热闹闹地分枝,散叶,吐须,不经意间就爬满了山坡,可以说有一种霸气,强悍。等到农历六、七月,葛藤更像个任性的山里娃,以不可阻挡之势,在空旷的山谷间疯长,逶迤漫延,繁枝碎叶茂密得一塌糊涂,茎蔓更是张扬妖娆,长长的藤,一伸一展,就是几十米,有的长达百米开外,甚至可覆盖上百平方米的晒谷场。有一次回乡,闲逛到少年时就读的小学校园,因为撤校,已荒芜衰败,杂草丛生,那个曾经让我们汗水飞奔的大操场,如今却成了葛的领地。阳光下,透过葛的背影,旧时光的情景仍历历可寻,但年少时的那种情怀却无从寻觅了。
葛没有挺拔的树干,它唯一能展现自己的生机与活力,就是漫山遍野地圈地盘抢位置。 葛藤所到之处攀岩爬树,所向披靡。万顷土地,狂野不羁。 唯有秋天,葛终于可展示它娇羞的一面,红灿灿的葛花开得酣畅,仿佛烛台上跳动着无数紫色的火焰,有淡淡香气弥漫。
在乡村,葛再霸气,再张扬,也是卑微的,仿佛是丢在路边的半截草绳,只能用来做系系绑绑的事。譬如,我的父亲从深秋的菜园子里来,总会剁几根葛条系几棵饱满瓷实的大白菜,带回母亲的厨房。还有把那些翠绿肥嫩的萝卜缨切下,也是用葛条编成串,一串一串,挂在房前屋后的果树上风干,留着过冬。但埋在泥土中的葛根,却是另外一种待遇。
打葛粉就是年少时的我最喜欢的活之一。秋天的日子很是惬意,阳光暖暖的,透过树叶筛在地上的斑影,如白白的馒头。但白馒头只是一种奢望,葛粉才是摆在现实的美味。白天大人们上工去了,我们兄弟几个便到山坡上挖葛根。挖出葛根后又搬到河里去清洗刨皮。捶葛粉是个体力活,必须要等到大人们晚上下工后才干,捶的捶,洗的洗,磨得磨,淘的淘,十分忙碌也十分热闹。葛粉加工也是个细活,那时没有粉碎机,全凭人工加工,先把大的葛根用斧头剁成小块。放在青石板上用木榔头把它捶的很烂,然后用布袋装起来,放在装满清水的水缸里摆袋。刚打出的葛粉要漂洗好几道水,不漂水的葛粉很黑,吃起来又苦又涩,必须换3-4遍水,当水色由褐色变白色后才能取粉。摆袋就是过滤,细细的,白白的葛粉透过布袋的缝隙渗漏到水缸里沉淀,最后布袋里剩下的就是葛渣,葛渣再用石磨磨细后加上碎米面拌和后用蒸笼蒸成“葛巴”,在当时也是一种很不错的食品,虽然有点糙,但还是吃得津津有味。
“冬日霓裘,夏日葛布。”事实上,在久远的朝代,女子采葛藤,纺葛线,织葛布,做葛衣让后人怀想。 史料上说,粤地增城的女儿葛薄如蝉翼,为天工之物,未嫁女子终岁才能织出一匹,重约三四两,这样的葛布,是织给她未来夫婿的,市集上没得买卖。 年代已远,这样的女子也只是留在《诗经》里,但她的背影这样的装扮,搁在今天,算得上潮人了吧。
葛取兵,1972年生,湖南临湘人,曾在《人民日报》《散文海外版》《湖南文学》《时代文学》等报刊发表作品,系湖南省作协会员,湖南省散文学会理事,岳阳市作协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