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切特:图像小说使我感到自由
沈童睿
不久前,中法“圖像小说节”举办,一位名叫罗切特的画家桌前排起了长龙。原来曾轰动一时的电影《雪国列车》竟改编自一部经典的法国图像小说,而这位白胡子帅大叔正是它的作者之一。
罗切特是安古兰漫画节大奖得主,喜欢中国画,曾梦想做高山向导,也曾为环保投身反核运动。
他眼神深邃,爱说笑。只要两分钟,他就能为请求签名的读者画一幅漫画像,诙谐搞怪的画风和《雪国列车》迥然不同。
“图像小说”的说法对不少人来说陌生又怪异。什么是图像小说呢?它与漫画到底有什么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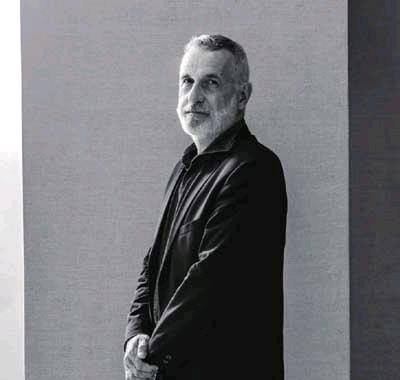
一部经典的重新发现
不少经典都要经历“再发现”的过程,《基督山伯爵》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起初都属于流行文化的范畴,风行一时。它们在时代的更替中一度沉寂,最后人们却能从中挖掘出恒久不变的内涵,各种阐释和研究由此而生,经典的地位就此确立起来。《雪国列车》也有类似的命运。
许多人是在奉俊昊的电影《雪国列车》上映之后,才知道三十多年前有这么一部同名图像小说的。其实,《雪国列车》由三卷组成。第一卷“逃出者”本是一部独立作品,在1982年问世,由法国漫画大家雅克·罗布(Jacques Lob)创作脚本,让-马克·罗切特(Jean-Marc Rochette)执笔绘制。1986年这部作品斩获了安古兰国际漫画节大奖,安古兰奖是欧洲最负盛名的漫画奖项,是出版商和艺术家都备极重视的殊荣。
这卷书说的是,人类滥用气象武器,致使大地被寒冰覆盖,暴露在野外的人,会被立即冻死。为了保命,人类被迫躲进一列一千零一节车厢的雪国列车。这辆车由永动机驱动,以极低的能量损耗在雪地上作漫无目的的长途旅行。没有人知道终点在哪里,只知道停车等于死亡。
主人公普罗洛夫是为了逃避饥荒,从末节车厢逃出来的,那里挤满了赤贫居民。列车的权势人物为防车速减慢,打算抛弃末节车厢,正好可以从普罗洛夫口中套取情报。这样,普罗洛夫就在士兵的押送下,从车尾到车头走了一遭。读者借助他的视角,看清楚了这列火车的全貌。
列车仿佛一个微缩的人类社会。上层阶级住在豪华的黄金车厢,夜夜笙歌麻痹自己。中层车厢发展出了对永动机的崇拜,希望“神圣的列车头”能带着他们永远前进。末节车厢的居民缺衣少食,也没有私密空间,对黄金车厢的奢华生活有强烈、夸张的向往……
后两卷的创作,则在1998和1999年间,绘画仍由罗切特负责,而脚本撰写的任务交给了本杰明·勒格朗。《勘测队》介绍了另一列行驶在相同轨道上的火车,车上居民知晓雪国列车的存在,上层人士利用他们对火车相撞的恐惧施行统治。《相交》说的是这趟火车的居民接收到音乐信号,以为野外还有人类幸存者,苦苦寻觅之后发现是一场徒劳。
第二、三部创作的时候,罗布已经故去多年。罗切特的打算是用两部续集纪念他敬重的罗布,并唤醒人们对第一卷《雪国列车》的回忆:“第一卷几乎已被遗忘,这本书失去了它的读者,我很清楚这一点,也为此感到遗憾。”2004年,这部三卷本的《雪国列车》被引入韩国。第二年,奉俊昊在一家小书店发现了它,他说:“那个瞬间我意识到,这将吞噬掉我一整段时期的生命。”2013年电影版《雪国列车》驶入影院。
有趣的是,这部出生在法国的杰作,经由韩国导演带到了好莱坞,才产生了国际影响力。图像小说属于漫画产业,法国漫画产业并非疲软无力,如漫画杂志《ZOO》的主编皮埃尔·伊维斯说,法国漫画受众遍及各种阶层、各年龄段,出版节奏极快。假如你在书店被一部漫画打动,但打算迟些再买,可能下周它就被新书取代了。法国是文艺大国,《奥德赛》、《追忆逝水年华》这样的文学经典,经常被改编成图像小说。还有一路图解派画家,从古物志传统中学习环境、物品的细节描绘,雅克·马丁的《阿利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此外,各种风格的作品如安德雷·朱亚的《蓝色笔记》,弗朗索瓦·布克的《保镖》……在法语世界都是响当当的作品。
但跨出国门,这些精致的作品,却不如《蝙蝠侠》、《超人》这般耳熟能详。罗切特说:“在市场运作方面,法国人还要做很多工作。”美日漫画产业,其实有一套有效的商业运作模式,漫威如果不是靠着游戏、影视、周边玩具一条龙的改编策略,很难说它能征服那么多国际受众。用时下流行的说法,美国人和日本人并不是在漫画品质上战胜了法国人,他们的优势是懂得运用大IP。
是命运让我参与《雪国列车》
罗切特1956年出生在德国边境的巴登-巴登,而他一生的学习、创作是在法国。其实,法国人对待漫画态度十分郑重,视之为“第九艺术”,漫画是一种长幼皆宜的读物,经常触碰政治、社会这样的严肃题材。在法国,漫画不仅是一种消遣的方式,也是人表达态度、参与抗争的武器。
罗切特小时候喜欢在博物馆观看绘画和雕塑,他尤其喜爱插画家古斯塔夫·多雷。尽管法国的社会风尚是如此有利于他这样喜爱美术的青年投身漫画,但他主要的心愿,还是四处爬山,成为一名高山向导。可是二十岁的时候,一场严重的登山事故终结了他这个梦想。罗切特得找些别的事干了。这个时候,在法国极为流行的“地下漫画”吸引了罗切特的注意。地下漫画起源于美国,六十年代的黑人运动和反战思潮,催生了一大批左翼青年,他们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挑战权威,漫画自然也是其中一件趁手兵器。这些作品大多古怪、暴力。
那时的罗切特也是“天生反骨”的青年,无法抗拒这种逆反的地下文化。在这时,他发现了理查德·寇本等艺术家,从他们的作品中,罗切特感受到一种“自由的感觉”,决定开始创作自己的漫画。1976年,他在一本地下刊物《当下》发表了处女作,从此开始了漫画生涯,并因《猪人爱德蒙》而在漫画圈子里获得了名气。《猪人爱德蒙》是一部黑白两色的幽默漫画,主人公最大的担忧是自己被做成香肠。从这部荒诞、搞笑的风格的作品中,还看不到《雪国列车》中惨淡阴森的笔触。
这时的羅切特还是初出茅庐的新人,雅克·罗布却早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漫画家和脚本作者。罗布在找到罗切特之前,正与画家阿莱克西斯合作《雪国列车》。阿莱克西斯是滑稽画家,他笔下的《雪国列车》更少悲观色彩,像是一个童话故事。没到31岁,阿莱克西斯因病去世,但作品还需要继续下去,罗布开始物色下一个合适人选。
罗布找了四年,1981年,他来到了罗切特这里,向他介绍了故事的要点。罗切特是个环保主义者,曾经是反核运动的积极分子。他觉得罗布的故事中蕴含了对环境的关切,尽管他不知道故事朝什么方向发展,还是与罗布一起,一个绘图,一个编剧,开始了《雪国列车》的创作。“我当时没有写实绘画的经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我,有时候我会觉得这就是命运。”
漫画家让-皮埃尔·迪昂奈说,罗切特是那种不断前进和质疑自己的艺术家。罗切特在《雪国列车》中第一次尝试用写实的、冷厉的画风讲述故事,就获得了成功,但他并没有止步于此。本书后两卷与第一卷画风相差很大,对人物的勾勒更简洁、富有动感。读者难免会觉得前后风格跳跃过于明显,不像是出自同一人之手。罗切特解释说,找到一种特定的风格并不是他的追求:“我的工作是为故事服务,我在各种风格中做选择,用最合适的那一种来表述小说中的情感。1981年的《雪国列车》和1998年的续作有巨大的差别。因为近二十年里,我研究了很多中国画,这让我的线条更有活力,创作也更加自由。”
罗切特现在已经不是那个三十年前的新手,在《白色安魂曲》、《拿破仑与波拿巴》等后续创作中,罗切特不断在写实主义和讽刺漫画之间转换,以服务每个故事的叙事需求,而不被禁锢于某种特定的风格。他已经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成熟画家了。
现在的他看来,自己二十五岁时画出来的《雪国列车》还有不少问题,但他拒绝作任何改动。罗切特希望这部作品的魅力和缺陷都能保持原样,这样一翻开书,他就仿佛重新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Q=《北京青年》周刊A=罗切特
Q:图像小说和漫画在哪一点吸引你?
A:我十八岁的时候开始接触图像小说,它最吸引我的是这个行业的自由度。当然,就算是任何创作都不可能绝对自由。但是所有艺术形式之中,漫画是相对自由的。很多创作需要市场的支持,但漫画相比影视,它的开支少很多,前期投入也会少很多。我们跟出版社会有很融洽的关系,出版社也会允许我们画自己想画的东西。
Q:尼尔·波兹曼说文字比图像更能承担深刻主题。你认同吗?
A: 我觉得能否表达思想,并非是由表达形式决定的。要知道漫画是比较新的艺术,它的出现比传统的文学形式晚很多,目前来看,确实还没有某部图像小说达到经典文学的高度,但我认为这只是因为它还没有爬升到其发展的巅峰。但这一天总归会来的。
Q:《雪国列车》是个反乌托邦的故事,它在现实中有所影射吗?
A:我和雅克·罗布在第一卷《雪国列车》中的关切主要不是政治性的,那个时候我们更关心的是生态环境。我参加过反核运动,而罗布关心污染问题。而在创作第二卷的时候,冷战结束,我们能感到一种新型统治方式出现了,那就是不断重复某些消息,以挑动人们的恐惧,而恐惧使人们服从。第二卷的主题,就是权力利用谎言和恐惧施行统治。
Q:当初从罗布手中接下《雪国列车》的绘制工作,你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A:那时我只有二十五岁,一个新手,而这个故事很难处理。所有人物行为都发生在一个非常狭窄的空间里,对我来说要让那么多读者满意,是个巨大的压力。
Q:在你看来,《雪国列车》的魅力在哪里,为什么能受到欢迎?
A:我觉得《雪国列车》讲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科幻故事,它是永远与当下相关的。比如现在,穷人和富人生活条件的差距达到了空前的地步。《雪国列车》受到欢迎,尤其在韩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是因为那里的民众能够理解这个故事,因为他们中不少人就处在书中所描绘的情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