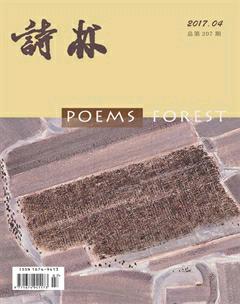张存己诗选
张存己 本名成棣,1992年生于北京。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14级硕士研究生。曾获第三届复旦大学“光华诗歌奖”、第三十二届“樱花诗赛”一等奖、2015年全球华语大学生短诗大赛一等奖,参加第七届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诗作散见于《诗刊》《天涯》《诗林》《星星》《诗歌风赏》《诗江南》等刊。
诗观 我把我的诗艺联系视为对音调的校正,像一个人每天在正午对表,驱除时间中的阴影。过去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吗?我希望保留变化的可能,我希望自己还可以再做些什么。
论童年
我是在一间小教室里发现他的
瘦小而弯曲的身影
稳稳地安置在墙角的座位里
每当气压回升的初秋降临
玻璃窗中的风物都会渐渐变得透明
让人可以轻易望见远处的铁塔
和树顶上的云
而孩子们则纷纷变成果实落向大地
在蓝色九月的第二个星期一
他们被送进这个闭合的教育世界
并和黑板上那些象形符号一起
成为彼此视线中不易觉察的异客
而那时唯有他悄悄靠在书桌旁
似一只临水的鹳鸟
棲息在课本上喧嚣的插画里
等着纸页上的光斑慢慢扩大,慢慢
把它也擦亮,然后
将他的目光引向窗框中明净的图景
当这个小小的奇迹发生时,当他
望见浮上塔尖的好天气
所有事物便呈现出自己的样子(就连
一点点隐藏在空气里的衰朽,也
毫无遮掩)这样地,一个人就能看到
他看不到的那些东西了吗?而这
永不落幕的第一课仍将留住他
使他反复地回忆起当天的日光
游荡在教室里,细小的光斑
在食用铅笔屑的沙沙声中变得白胖
变成一场空无一人的绵长午睡
几乎挡住了迎接孩子们回家的黑夜
论老年
一阵风,轻轻吹了进来,又轻轻掀起
那些纱质的幕帘,使它们看起来更像
一道道摇曳生姿的烛火。但他明知道
这所房子里的所有门窗都已被他亲手
关上。他安坐,在铺满马赛克的地板
中央,镜厅中的奔马也认出了它们的
王。此刻,若他伸出手,抓住壁橱里
晃动的灯绳,像从金色的沙丘上摘下
一朵低悬的云,也许就能画出他一生中
最后一次小小的巅峰吧。而他只是
将自己的身体靠进灰墙一角,垂下手
臂,把黑暗中唯一一处发亮的动作也
轻轻熄灭了。
“我要在门背后等你”,他听见一个
声音这样对他说。他站起身,把一颗
铁钉丢进壁炉,如同将一个词语抛入
蓝色的河流深处。他又闻到了那阵风,
卷着枯枝燃烧的气味,神不知鬼不觉
地从他的身旁穿过,把他的屋子慢慢
掏空了。他只能捡起脚边的一张报纸,
将当天的日期剪下,像给快要散架的
时间幽闭所凿一扇窗。他还需要再做
什么吗?他的影子,和他往日的许多
朋友们抱在一起,像一窝熟睡的兔子,
在冬天。是谁帮助他独自逃脱了情欲
的枷锁?而那从一开始就使他免于死
亡的,又是什么呢?
他已经不再能看清那些漂浮在空中的
名字了,因而他宁愿将漏进屋里的光
想象成一条隧道,可以把他带向一片
写满遗忘的海滩。他宁愿想象,走廊
尽头的另一个房间里,藏着一只黄色
的雾灯,若将它身上的灰尘擦拭干净,
他就能窥测到这座房子里每件物什的
过去。风声愈发紧凑,而他确信挂在
墙上的每一幅肖像画的音量,都已经
调至最低。他披起外衣,竟发觉自己
也变成了一张喑哑的旧胶片。无数未
来的日子像磷火,从他身体的空白处
悄然窜出,教他用生命的语言去述说
黑夜,命他把覆盖在人群头顶上的光
偷到他的暗室内,使他不得不永远地
活下去,并且做一个活跃在国境线上
走私知识的人。
海上花
——代S作
你在我对面的会议桌边坐下
点燃手中的香烟
你漫不经心地朝打火机凑过头去
像一架蓝色的鹅颈灯
不作声。我在速记本最后一页
写下:“亲爱的诗人来自远方。”
当你出现,峻峭的两颊下面
藏着一些坚硬的话
我认得你。在四月的长沙
你说:“风暴后,要去旅行。”
要穿过一些低微的雨天
逐一探望曾爱你的人
你手中的黑皮箱
正轻轻泄露着海潮的声音
甚至使我对大海的恐惧
也随之稍稍减轻
在上海度过了十四个夏天之后
我乘着电梯,来看你
我们隔着不知情的人群
身上落满细腻的滑石粉
我用手指悄悄抚过桌布上的縠纹
使它尽快隐没于触感的愉悦
你却向我投下红树林的影子
几乎高如天穹
我知道我就要和你去看一次大海
昏聩的大海,吞吐躯壳的海
它在这座东部城市边缘将自己
压制成一张黑白录像带
并不厌烦地向我们播放一种恒久
兴奋的形式,静穆的欢乐。世间
唯一真实的欢乐。躁动又虚空
丝 丝
丝丝,如她的名字一般
轻。
使人想起一株在细雨里颤抖的稠李树
在时间小河流的对岸,静静生长。
丝丝是从那边过来的人。
她来,也带来了一个漫长的雨天。
丝丝在我们初见的傍晚拈起一个词
起身,细密的步点敲过走廊,
整片湿热的暮云便散发出柔和而
虚弱的光芒。我在雨声里摊开一本书,
一本没有什么用的书,悄悄听着。
书里的小镇蒙着一圈温顺的茸毛。
我在那里见过一些人。
那些居民站在雨里,和我们相似,头上
顶着昏黄的光晕。“雨丝落向孩子和狗”
也落向他们对家庭与婚姻的期许。
那真是一个不属于我们时代的雨天,
它一度让我以为爱情、友谊,
干戈缭绕的私生活,都并不一定
只是古代才有的事情。
但雨丝兀自在稀疏的街道上碎银般跳跃。
一只黑猫窜到桌子上。
它白色的趾爪压上书页,那狐疑的姿态
像要打开一扇门。然后它就消失了。
而丝丝正在门的另一边朝我们微笑,
一种美丽的语言在她的铜镜中变得破旧,
仿佛一位退役的舞者,谦卑地微垂着头。
丝丝的雨天令每个人心怀歉意。
这柔软的歉意,应该是缪斯赐予我们的
最好的礼物了。
白嘴鸦
在每个轻得透明的好天气里
都会有位陌生的客人来访
比如锁门时突然想起的某个日期
什么人挟着伞站在湖边
听见泥土松动的声音
伞就从身上滑落
四四方方的云团不断涌进衣领
还有那些反复发生的新闻
也像村庄上的炊烟互相吹动
平原上的白杨闪闪发亮
彩色的鱼群游回天空
继续一场看不见玻璃窗的梦。梦中
长久的大雪已经在天亮前
干干净净地停了下来
合 欢
那天下午大风刚刚过去
街道上四处都是滚落的银杏
沙尘和秋天是同样的金色
我的父亲从唱片盒里翻出一封信
让我替他拿到邮局去寄
父亲说:你可以一路跑到邮局去,或者
只是上街散散步也好
父亲要我穿上厚毛衣再出门
父亲的脸上跳跃着快活的神气
我好像并不知道那封信要寄给谁
秋天深處的行人像一对对逗号
被落在地上的光反复拨动着、区隔着
这场景每每令我感到深深的讶异和遗憾
那一年我该是十二岁
我的屋子里摆着一面金色的镜子,还有
父亲那摞被时光烫金过的唱片
我有一个下午可以在那里安静地坐着
可是为什么,我真的想知道
为什么那时我依然
会觉得
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