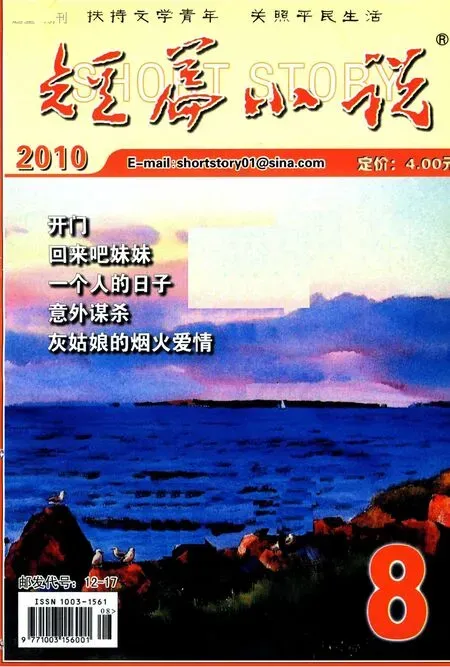晓看红湿处
◎魏 鹏
晓看红湿处
◎魏 鹏
上个星期天,诗人卷土(卷土喜欢我写到卷土时,在卷土前加上诗人二字)拿着他的几首诗稿向我请教。说真心话,我已好多年不写诗了。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长时间不写诗不看诗,有些诗我已看不明白了,不是诗人向我请教,应该请教的倒是我了。
诗人卷土的诗稿中有一首 《我理解你》,诗不长,是这样写的——
在我最尴尬的时候
你转过身去
我理解你
此刻,你同我一样尴尬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
你转过身去
我理解你
不愿我看到你眼里滚动的泪花
在我最孤单的时候
你转过身去
我理解你
你比我孤单千百倍
我理解你
如同理解我自己
我问诗人卷土:“这首诗是啥意思?”
诗人卷土嘿嘿一笑(是笑我的浅薄,更是笑我诗歌观的落伍。也是的,如今谁还会问这样的问题呢?太小儿科了吧),并不回答我,而是给我讲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年春天,我每天都在坚持晨跑。我不是在云河公园里跑,云河公园里遛狗的人太多,不安全;也不是在九月广场上跑,九月广场上跳舞的人多,太吵了。我是沿着幸福路直跑,一直跑到城乡结合部,然后再迎着朝阳,原路返回。天天如此,乐此不疲。
有一回,我跑到一个村庄的村东口,突然觉得肚子叽里咕噜的,像是钓鱼的人下了窝子,引来了几条鲤鱼在不停地吹着气泡。我双手捧着肚子,边小步慢跑,边向村口张望,看看附近有没有茅厕。
远远地,我看到村东口有一户人家,家后边有一个用旧水泥砖砌起来的有一人多高的茅厕。我像求神的见了菩萨,急急地向那个茅厕跑去。茅厕很简陋,没有封顶,也没有粘缝,门口既没有“男”字,也没有“女”字。城乡结合部的茅厕几乎都是男女不分男女共用的,哪怕是两三家共用一个茅厕,也是不写“男”字和“女”字的。
在茅厕上写上“男”字或“女”字,并不费事,也没人会因字写得丑而笑话,问题是这儿的人,认为这是精腚勒裤带,纯属多此一举的事。谁先进了茅厕,谁就抢到了蹲位,而且蹲位只有一个;后去的,只要在茅厕前听到里边的咳嗽声(仿佛地下党对暗号似的),不管咳嗽声是男是女,后去的都会止步不前。他们要么在外边等待,等里边的人出来了再进去;要么就装作无事人似的,悄悄地拐向不远处的另一家茅厕了。
我下了幸福路,沿着村头一条南北小道,向南边的茅厕疾步奔去,走了不到百米就进了茅厕。茅厕的墙砌成了圆形,墙外靠门处还有一棵拳头粗的冬青,门神似的站立着。茅厕里边很宽敞,够垒三个蹲位的,但只垒了一个。墙砌得很粗糙,有的砖缝里透亮,透过砖缝,里边蹲着的人能看到外边的一切,不管是人、是狗、是鸡,都看得一清二楚。但外边的人透过砖缝向里边看,就看得不清不楚了,有时能看到一条裤腿,有时能看到一块白肉,有时什么都看不到。有的砖缝太大,就用手纸塞上,仿佛那砖缝是特意留塞手纸似的。手纸用旧报纸的居多,褪色的居多,也有雪白雪白的卫生纸。忘记带手纸的,就蹲着(不用起身)伸手到砖缝里取来用,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似的,总会有人向砖缝里塞纸,就像总会有人从砖缝里取纸一样。我知道,城乡结合部的茅厕大多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一蹲下,就把手伸向砖缝,从砖缝里取出一团旧报纸。我边蹲边看报纸上的旧新闻,还从一半(另一半不知被谁给撕去了)的副刊上读到一首小诗,诗里写的是一只没有翅膀的鸟,在没有人烟的地方飞跑,跑着跑着就飞起来了。
我把旧报纸看得一字都不剩了,才把它当手纸用。
从茅厕里出来,我感到浑身轻松,通体舒泰,仿佛把一天的工作都做完了似的。当我迎着朝阳往回跑时,双脚就像踩着弹簧似的,两步并作一步走,五步的距离,两步就跑过啦。路两边绿岛上的花朵,都在夹道欢迎我,仿佛我是捧了奖杯凯旋归来的运动员。抬头看看太阳,太阳也给我一给甜甜的笑脸。
从那天以后,我每天晨跑都要到那个茅厕去一趟。有时去大便,有时去小便,有时到茅厕里只是放一个屁就出来了,有时去了连一个屁都不放。与此同时,我对家里的卫生间越来越看不上眼了,不是嫌瓷砖白得刺眼,就是嫌空间逼仄、压抑、气闷,也越来越不爱用家里的卫生间了。每天一起来,我就趁晨跑时去那个茅厕。
有人总结,说人生有三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我把山水替换为茅厕,仿佛每一个早晨都经历了这三种境界,仿佛一个早晨就替换了漫长的一生。
有人说,把弯路走直是聪明的,因为找到了捷径;把直路走弯是豁达的,因为看到了直路上看不到的风景。对我来说,幸福路就是一条直路,从幸福路拐进茅厕就是一条弯路,弯路尽头的茅厕,不亚于一处风景。仅用一个早晨,我就把直路和弯路都走了,把不易看到的风景也看了。
我对那个茅厕有点偏爱。爱是什么?正像一首歌中唱的那样:说也说不清楚。偏爱又是什么,更让我说不清道不明了,难道只是因为它在我拉肚子时,及时给我提供了方便?仿佛是,又仿佛不是,想到这些,我就在心里笑我自己。
每天晨跑,我都要跑进那个茅厕,这已成了我的习惯。有时,我对自己说:“这是一个坏习惯!”记得一个外国的作家说过:“改掉好习惯比改掉坏习惯容易得多。”这也就是说,改掉坏习惯是多么的不易!事实上,那时,我虽然知道自己每天晨跑都要跑进那个茅厕,是我的坏习惯,但我压根儿就没有改掉这坏习惯的想法。
日久成习惯,习惯成自然,而顺其自然,又是多么的聪明和豁达啊!
有一天早晨,当我拐进茅厕时,一下子愣住了——
茅厕里一片狼藉,血腥弥漫,浸透女人经血的卫生纸被鸡刨狗抓得满地都是,但白的依旧圣洁,红的依旧鲜艳。那是年轻女人的经血,不像绝经前女人的经血那样暗红、黑红,而是红得像火,红得像霞,红得让人看了想入非非。如果说绝经前女人的经血是残荷败柳,那少女的经血就是鲜花嫩草。大文豪鲁迅先生曾深刻地解剖中国人的想象:“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我是中国人,而且我还写诗,想象力是可想而知的,也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一层上,我的想象力比鲁迅先生列举的还要跃进,我想,这是谁的经血?谁的经血这样火红?谁的经血这样鲜艳?这充满活力和生命力的经血,让我想到了这女子的年龄,也许十八,也许二十,也许二十一,但决不会超过二十五。我不仅想到了这女子的年龄,还想到了这女子的容貌,说是花容月貌怕都俗了吧,但不这样说,又上哪里寻觅更恰当的字眼来形容她呢?也许只有见了她,她才能把那些更加贴切,更加鲜艳的字眼带给我吧!
我就这样蹲在茅厕里,犹如蹲在万花丛中。看着满眼的白的和红的,我诗意大发,张口吟出一句:“落红不是无情物!”但反反复复,只是吟出这么一句,就再也没有下文了。后来我觉得就这么一句,也仿佛不是自己的,仿佛是在哪一首古诗里见过的。
“落红不是无情物!”我边吟着这句诗,边从茅厕里出来。那天早晨,我是一步三回头离开那个茅厕的。
整整一个星期,茅厕里都是那样的红;整整一个星期,我的心都是那样的乱。不,自从见了那红之后,我的心就没有安宁过。每天一起床,就想到茅厕,就想到茅厕里的万花红遍。跑在幸福路上,那茅厕就成了我的标志性建筑,成了我的路标,我的希望,我的终点。一路跑来,我面带微笑,我手舞足蹈,谁也不知道我心底的动力,谁也不知道我心头的甜蜜。
那些日子,是我晨跑以来,没有一天间断的日子,阴雨无阻,一路欢笑。那些日子,是我晨跑以来,最不守时的日子,虽然每天坚持晨跑,但时早时晚,有时天还没亮,我就顶着星星上路了;有时晨跑的人都回来了,我才刚刚起床上路。但有一点是雷打不动的,起早起晚都要跑。每每跑到视线能抵达那个茅厕时,我的血压就会自然升高,我的心跳就会自然加快。
为什么我的血压会升高?为什么我的心跳会加快?我的心里像打鼓一样,比鲤鱼吹泡泡还要响。我无法解释,大概只有大科学家巴甫洛夫用他的条件反射学说,才能解释我这种生理现象。记得我在东方精神病院住院时,有几个病人蹲在卫生间里说自己很冷,快要冻死啦。有个医生拿来了一支粉笔,在卫生间南墙的上方画了一轮白炙的太阳,几分钟后,就有病人中暑啦!我大概也是如此,一见到那个茅厕就脸红心跳汗流浃背。
按理说,既有这样的条件反射,我就该远远地避开那个茅厕才对。是的,我也一次次这样想过,可想归想,双腿还是不听使唤似的,每天还非要向那个茅厕迈进不可。英国有个诗人叫劳伦斯的说过:“血和肉比才智更高明。”难道我的理智竟战胜不了我的双腿?每每想到这里,我就抬起双拳,狠命地捶打环跳 (在股外侧部的穴位),可越捶血肉越活,越捶经络越畅通,越捶步伐越稳健。
我知道,我一次次地光顾那个茅厕,只是想遇见一个人,一个能把茅厕打扮得如此花枝招展的人。可我一次次又迅速地从那个茅厕离开,我怕遇见一个人,一个只有她,才能让茅厕万花开遍的人。想见她又怕见她,这也许是人人都会经历过的,就像歌德说的那样:“哪个少男不钟情?那个少女不怀春?”
若是真的遇见了她,我是会心一笑还是吃惊地大叫呢?
那天早晨,我从茅厕里出来,依旧是一步三回头地回到幸福路上,但刚到幸福路,一回头,我突然看到茅厕边站着一个仙女,身材又苗条又笔直,就像那棵冬青一样。她长裙及地,墨发及肩,婷婷玉立,背影如喜欢拍背影的摄影家拍的艺术照。我不由地转过身,又向茅厕走去,脚步时快时慢,时而站立不前。当我犹犹豫豫地来到茅厕跟前时,我突然变得像个小流氓似的,一瞬间蹿了上去,从背后把仙女抱了起来,嘴里还不停地说:“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让我彻夜难眠!就是你让我夜不能寐!”声音虽小虽轻,但还是惊醒了我的春梦。我睁开眼睛,天已大亮。窗外的脚步声告诉我,晨跑的人们有的已经回来了。
春梦惊醒之后,也就是一个多月之后吧,炎热的夏季就跟着春天的脚步悄悄地来临了。天虽然热了起来,但我的晨跑仍没有间断,只是不再奢望与美人相遇了。心想,能再次看到茅厕里的遍地鲜花,已是心满意足了。然而就是这点可怜的欲望,也迟迟得不到满足。每次进那茅厕,总是看到我不想看的,而看不到我想看的。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件让我做梦都不曾梦到的事发生了。
那天,我正蹲在茅厕里,裤子还没有提起来,就听到茅厕外边一个男人喊道:“你,你,你,是你吗?”不知他是由于激动,还是本来就结巴。他把牛眼向我瞪着。
“是我。怎么啦?”我微笑着向他看去,只见他光着头,贼亮贼亮的,只穿一条短裤,趿拉着一双旧鞋,一脚抬起一脚放下,一脚放下一脚抬起,两只脚不停地倒腾着,仿佛急着上茅厕似的。他的上身虽然一丝不挂,但全部纹上了精美的图案,有龙,有鹰,有喜鹊,有知了,有青蛙……胸前,背后,胳膊上,全都是这些动物和图腾。说心里话,我对这些图腾和动物都十分喜欢,只是不喜欢他这个人。
“这,这,这个,是,是,是你的吗? ”他拿出一个纸团——被揉得像包饺子的面团。当他把纸团摊开在手掌上,我看到那半张皱巴巴的白纸上有我写的一行字:“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我想起来了,两个星期前的一天晚上,我想写一首诗,诗里想引用泰戈尔的这句话,但当我把泰戈尔的这句话写到纸上时,自己的诗兴却跑到爪哇国去了,再也写不出一行诗来,气得我在本子上撕下了这张纸,握了握就塞进了口袋。第二天晨跑时,我来到茅厕,想用它作手纸,但看到上边有泰戈尔的话,挺有哲理的,就没舍得,再说用它作手纸也小了点,就随手塞进了砖缝,又从砖缝里抽出半张旧报纸作手纸了。
我看着他手上半张皱巴巴的白纸,依旧微笑着,点了点头。不料这个结巴又拿出两张电影票在我眼前晃了晃,说:“这,这,这个,也,也,也是你,你的吧!”
“是的!”我又点了点头。这是一个星期前,单位里组织看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我和同事因为酒喝高了,错过了电影放映的钟点,两人都没有看成电影,电影票就作废了。第二天晨跑,我在茅厕里掏手纸时,掏出了我和同事作废了的两张电影票,痛惜不已,又舍不得扔,就随手把它塞进砖缝里边了。想不到又被这个结巴给挖了出来。
结巴见我点头说是,就一个箭步跨到我跟前,从我的上衣口袋里抢过一支派克金笔,然后又飞身踹了我一脚。这一脚踹到了我的胸口,把我踹得一个踉跄,后退两步,险些四肢朝天仰面倒下。结巴乘势又是一脚,这一脚没有踹到我,而结巴的鞋子却不翼而飞,落下时撞到了冬青的主干,而后又从主干斜落下去。我看到那只鞋子时,鞋子已在冬青下的稀粪池里出没了,就像稀粪池里突然冒出一只屎壳郎似的。
我被结巴给踹蒙了。稳住脚跟后还愣愣地站着,一直到一个女人的出现,我才醒悟过来——结巴把我当成他的情敌了。也许在他的心里,那半张白纸上的字,就是我写给他情人的诗;那两张电影票,就是我勾引他情人的证据。我和他的情人,在茅厕的砖缝里传递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这时,我突然想起手里还握着一张纸条——这是我刚才在砖缝里取旧报纸时带出来的一张纸条,我拿到手里还没有来得及看,就被结巴给叫了出来。
这个结巴踹了一脚之后,又像想起什么似的,在我的身上搜了起来,但除了他拿去的那支派克金笔之外,什么都没有搜到。“你!你!你!你凭什么搜身?”我举起的双拳,眼看就要砸到结巴的光头上了,但一个女人的到来像点了我的穴位似的,让我举起的双拳停在了空中,像缴了械的敌人似的举手投降。
那个女人,看打架看热闹一般突然来到结巴和我跟前,然后站着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她满头黑发又长又乱,像刚被一百个男人蹂躏过似的。有一缕乱发飘垂下来,而后又粘到了她的嘴角上。见到她,我就想起了人们常说的那两句话:“自古好女无好男,娇妻常伴拙夫眠。”
她把脸转向我,又转向结巴,转向结巴,又转向我。透过她光洁的额头飘下的乱发,我看到她的脸色一会儿白,白得像一张白纸;一会儿红,红得像天上的红霞。她的眼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双眼皮里藏着几分疲倦。我用期待的眼神看着她,我期待她能为我说一句公道话,再从结巴手里把我的派克金笔拿来,还给我。然而她哑巴似的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没有做,只是木雕泥塑般地站着,用无助、无奈、无可名状的眼神望着我。
后来,她不再看我,也不再看结巴,而是把脸转向了幸福路……
我又气又恨,真想把手里的纸条交给结巴,让结巴看看到底是谁在勾引谁,以洗刷我的清白。可我没有那样做。我自问,我真的像一张白纸那样清白吗?那个女人,面对屠夫般的结巴,又能为我做些什么?又能为我说些什么?何况我手里虽然握着一张纸条,可我并不知道这张纸条是谁的?也不知道纸条上写的是什么?
结巴拿着我的派克金笔,凯旋般地离去了。那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离去时看了我一眼,这一眼深得像井,掉下去就再也上不来了。披头散发的女人就这样地看了我一眼,似感激不是感激,似理解不是理解,似怨恨不是怨恨,似柔情不是柔情……好多天之后,我仍是不明不白不知何意。
那天,我从那个茅厕边离开时,天昏地暗,双腿像绑了沙袋似的沉重。看太阳也是黑色的,黑得像一团浓墨;听知了也是呻吟的,呻吟得像女人的抽泣。
到了幸福路上,我才把手里的纸条打开。纸条上只有一行字:“星期天晚上十点,幸福路(十字路口)上见,不见不散。”落款是“想见你的人。”字迹拙稚,像是女人写的,又像是屠夫写的。
我掰着指头,像病人期待着黎明,像囚徒期待着自由,像婴儿期待着乳房一样,我期待着星期天的到来。星期天晚上,皎洁的天空升起了一轮圆圆的月亮。月光照着云河公园和九月广场上的一对对情侣,然而在幸福路上却照不到我的身影。
那天晚上,我把那张纸条撕得粉碎。我想:这是结巴和那个女人的恶作剧?还是那个女人单独给我传递的信息?我不得而知。半夜里,我又从床上爬起来,就写了《我理解你》这首小诗。
“你这首小诗,远远不如你刚才讲的故事有趣。我看你还是和我一道,改行写小说吧!”我对诗人卷土说。
诗人卷土鄙夷地对我笑了笑,就拿回了他的诗稿,什么都不再对我说了。
责任编辑/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