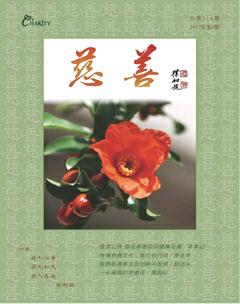慈心善语
东晋时期的高僧、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在《大智度论》中言简意赅地阐明了慈悲之善,不仅仅给人快乐,还要把人从苦难中拔救出来。他说:
“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苦。”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出台后,中华慈善总会会长李本公谈及中华慈善总会在《慈善法》出台后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时说:
“《慈善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慈善事业将进入法治时代,即依法运行、依法管理、依法监督,这是我们企盼已久的大事,会大大有利于慈善环境的改善和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对慈善组织来说,《慈善法》既是约束又是保护,更是督促。”
创作出版过《乔厂长上任记》《蛇神》《农民帝国》等著作的著名作家蒋子龙,一次在总结、分析国际上富豪慈善家的共同特点后说:
“节约是一种精神,一种态度。反过来,一个自信,一个奋发的民族,必然是勤俭节约的。奢侈是颓废,今朝有酒今朝醉,原因和腐败有关,跟社会的风气有关,跟引导有关,跟媒体在追求豪华有关,现在再不谈节约,就我们这点资源,我们这点钱,要是再这样下去,实际上不是经济损失多少,关键是我们丢了一种精神。看一个民族是不是奋发有为的,是不是有希望,有追求的,看他对物质的态度。”
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早在1919年来到中国,他认为中国人提倡的礼让、和气、智能、乐观的人生之道远非西方文化所能及,因此西方文化要学习中国的《道德经》哲学。他说,
中国的“立国之本在于比我们更宽厚、更慈善。”
美國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林罕·马斯洛研究总结不少优秀人物的人生轨迹,看到这些人基本上都喜欢幸福的结局,都希望看到好心有好报,看到残酷的剥削和丑恶受到惩罚。他认为,相信善恶因果报应进而止恶扬善,应该是人类相信永恒和神圣的东西。他说:
“最理想的社会就是善有善报的社会。”
《了凡四训》是明朝袁了凡先生教训儿子的有关“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篇文章。文章的重点是改过、修善,帮助人们辨别善恶,辨别正邪,辨别利害;处事、待人、接物要真心,舍去自私自利,起心动念都是利益大众。了凡在文章中说:
“至诚合天,福之将至,观其善而必先知之矣;祸之将至,观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今欲获福而远祸,未论行善,先须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