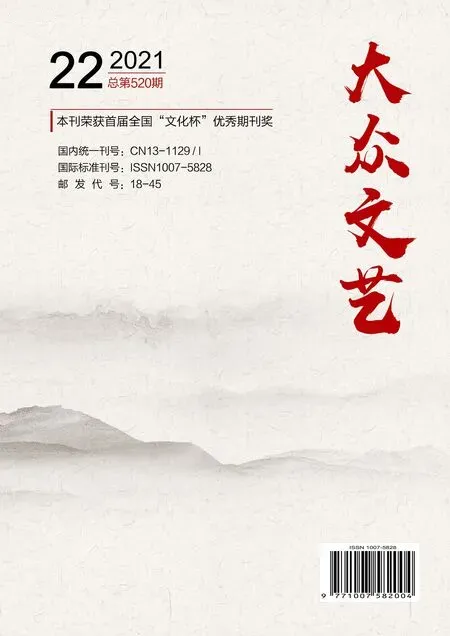从“分裂”到“和谐”
——论《处女与吉普赛人》中的伊维特的心理发展过程
李珊珊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315211)
从“分裂”到“和谐”
——论《处女与吉普赛人》中的伊维特的心理发展过程
李珊珊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315211)
D•H•劳伦斯创作的短篇小说《处女与吉普赛人》讲述生活在守旧沉闷家庭中的少女伊维特在与吉普赛男人相识相知后她的内心世界发展过程。本文从心理分析的视角,结合弗洛伊德学说,总结出:伊维特的内心变化呈现为从分裂到和谐,这一过程是伊维特对于欲望与精神相结合的自我平衡状态的追求,即劳伦斯式重生。
处女与吉普赛人;分裂;和谐;心理分析;弗洛伊德学说
一、引言
《处女与吉普赛人》是D•H•劳伦斯写于1926年的短篇小说作品,在中国,The Virgin and the Gipsy的翻译版本众多,本文一律采用《处女与吉普赛人》这一译名。会对母亲大打出手的父亲让劳伦斯从小对父亲就有抵触心理,该种心理使得他在小说中塑造的男性人物形象与其父亲粗鲁蛮横的矿工身份大相径庭,《处女与吉普赛人》中的吉普赛男人充满激情、神秘、有男子气概。而母亲对劳伦斯的掌控式的、扭曲的爱使得劳伦斯生性敏感,因此对于女性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在《处女与吉普赛人》中对女主人公伊维特的形象深入刻画,小说中大量对于伊维特反抗行为及心理活动的细节描写都体现了劳伦斯对女性的了解程度。
然而,《处女与吉普赛人》只引起了少数评论家的关注。在评论家Leavis(1956)看来,该小说是劳伦斯中篇小说中的佳作,更是一篇被低估的作品,他重点研究了劳伦斯在《处女与吉普赛人》中对女性内心情感的刻画;David Craig(1973)则把这部作品视为仅次于《一报还一报》的研究性问题的著作;Younghoon(2015)注意到了小说里关于文学的表演性以及它的道德研究。
女主人公伊维特的心理变化过程是人在不愿被社会掌控又不得完全脱离它时,开始融入、参与到其中的体现。因此,本文将从伊维特内心分裂到最终的和谐这一角度出发分析伊维特对于欲望与精神相结合的自我平衡状态的追求和。
二、《处女与吉普赛人》概述
小说讲述的是维多利亚时期,发生在一个充满宗教氛围和保守封建思想的三代同堂的牧师家庭中的故事。伊维特在法度鲜明的世俗社会中成长,从小被父亲溺爱,在设备良好的学校结业,与生俱来的一股傲慢气质,足以表明她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伊维特的母亲跟一位年轻人私奔后成为家中不可触及的话题,年少的伊维特姐妹俩认为是自己不讨母亲喜欢才使得母亲离开。她的父亲却由于这不幸得到了升迁之喜,成了牧区长,搬到了新的住宅,从此伊维特与奶奶、姑妈和叔叔一同居住。迂腐老迈的奶奶成了家里的主宰,伊维特厌恶阴冷死寂的家,反感狡黠贪婪的奶奶。成长的伊维特与她的母亲越来越相似,不甘于被现有生活束缚,竭力寻求积极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是伊维特却总会被自己的家庭地位带来的特权所诱惑而享受在一些高端会所带来的快感中。伊维特不敢公然反抗来自长辈的压迫,不愿轻易放弃特权的同时其精神世界缺乏活力而郁郁寡欢。
在与伙伴出游的路途中,伊维特遇到了吉普赛人。此前她一直觉得围在自己身边的男性都是死气沉沉、思想腐朽,无法与她有深层次的沟通,与他们在一起时她会被压抑控制。而第一次与吉普赛人相见时,她就感受到了他身上与众不同的气势。伊维特羡慕吉普赛人的生活,渴望他们拥有的自由,每次与吉普赛人男人见面以后再回到家里时,她内心都会有一番大动静,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去对抗家庭势力。小说的高潮就在于吉普赛男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洪水之中解救了伊维特,逃过一劫的俩人由于害怕和寒冷剧烈颤抖,吉普赛男人在伊维特的恳求下搂抱着赤身裸体的她相互取暖,等到身子暖和时双双入睡。等伊维特醒来,世界已经平静,吉普赛男人也已经逃离。伊维特的奶奶在这场洪水中去世,当伊维特离开残留的教区公馆回到父亲的怀抱时,新的生活正在向她展开。
原有生活的秩序给了伊维特安全感;但内心又驱使她去寻找自由。吉普赛男人带给了她追求精神世界自由的勇气和动力,伊维特从中寻找和谐与平衡——肉体在精神中实现的一种血液和心灵的平衡。
三、伊维特内心的分裂与和谐
导致伊维特内心从分裂到和谐这一过程的,有内因也有外因。她心里有着对自由的渴望却因为家庭而不敢轻举妄动,但吉普赛男人的出现和洪水的冲击给她的生命带来了变化。
1.伊维特内心的分裂
首先,伊维特的分裂来源于家庭地位,她喜欢舒适以及一定的特权,即使只是个教区长的女儿,也能享受一定的权力,而她喜欢这种特权。伊维特在抱怨着帕普尔维克冷漠、腐朽、无趣的生活的同时,墨守成规,不敢轻易打破生活的规律。她也是教区长公馆乏味生活的一个部分,同样呼吸着“中产阶级那种阴湿空气”。伊维特享受她这个阶级所能拥有的权力:常常出席宴请,参加舞会,出入大旅馆或高档舞厅。她在玩乐的过程中非常愉快,只是始终处于昏然迷茫的状态,内心深处藏匿着难以压抑的恼怒。她没有勇气打破原有生活的秩序,因为这种一成不变的秩序能带来安全感。在安全感的庇护下,伊维特的肉体是得到满足,但灵魂是空虚的。
其次,吉普赛人的出现使得伊维特的生命开始发生翻转,她内心渴望自由的灵被吉普赛男人唤醒。吉普赛人没有遭受文明力量的束缚与压制,他们的生活成为处处受约束和限制的现代生活的对照物。吉普赛男人浑身透露着宁静安详、神秘的忍耐力的光芒,他充满热情的眼神赤裸裸地直视伊维特时,她意识到自己四肢沐浴在他那朦胧、奇异的闪光中,直到最终变得纯真无暇。在与吉普赛男人一次又一次的接触后,伊维特逐渐明白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小伙子们的一味献媚求爱以及家里奶奶和锡西姑妈的压制让她对于吉普赛人的生活愈加向往。与他在一起的时候的伊维特内心是被充满的,不再是孤独凄凉,甚至感到自己能跟男人走,去做一个四处流浪的吉普赛女人。然而流浪的生活状态与她现有的安稳生活大相径庭,使得伊维特踌躇不前。伊维特依旧陷在对家庭的憎恨与敌意之中,但她始终没有勇气撇下自己的所处环境带来的安全感,跟着吉普赛男人流浪去未知的世界。
再次,青春期特有的叛逆让伊维特对于奶奶试图掌控整个家庭的行为感到愤怒与不满,但她却不敢有任何违背家人意愿的动作,只会暗自恼羞成怒、在背地里埋怨奶奶。实际上,她的行动是相对自由的,她生命的钥匙掌握在她自己的手里,只是她听之任之,未曾深入思考过自己真正的需求。来自家庭势力的约束和自己不敢公然反抗让伊维特的内心世界更加陷入分裂的状态,对自身的需求感到迷惘。
由此可知,女主人公深受文明的教化和理智的约束,虽然对于家庭环境极度鄙夷,却也没有被激情完全操控,放下现有的一切去跟随吉普赛人。从本能控制观和道德观来看,本我完全是非道德的,自我则力争成为道德的,而超我则可能是超道德的。可以说,劳伦斯塑造的伊维特受到了超我的辖制,超我代表了“道德化了的自我”,以指导自我去限制本我活动为主要职责。伊维特依恋社会及家庭带来的安全感而不敢对家庭束缚做出任何正面的抗争是超我的体现,内心想不顾一切跟随吉普赛男人过流浪的生活是本我的体现。她迷恋现有的秩序和权力带来的安稳的同时,内心对于自由生活、热切恋爱的欲望被强烈地激起。伊维特是典型的内心人格冲突和分裂,劳伦斯试图表现弗洛伊德学说中“现实原则”与“欢乐原则”的抗衡,即人的本能欲望在受到压抑时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剧烈冲突。
2.伊维特内心的和谐
伊维特内心趋于和谐的最明显的体现在于她回归原始家庭,但不再完全被家庭所掌控。奶奶在洪水中死去意味着专横腐朽的恶势力在赛韦尔一家中的倒塌,伊维特之前索然无味生活的结束。当她离开随时都会坍塌的房子,回到父亲的怀抱时,她与父亲之间的矛盾在死里逃生后化解。存留在洪水之上的教区长公馆代表着伊维特往后生活的基础和保障,自此以后,她在享受家庭带来的安全感的同时不用再付上被奶奶全权掌控的代价。
另外,当伊维特处在内心世界的分裂,与吉普赛男人的关系无法进一步发展时,一场洪水将他们再一次捆绑在一起。吉普赛男人在洪水来临之际,救伊维特脱离险境,在洪水退去伊维特还在熟睡时,悄悄离开继续他的流浪之旅。吉普赛人的出现和离去表面上看对女主人公的生活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但伊维特的内心深处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给伊维特带来了光明,唤醒她对原始生命力的激情以及对生活的勇气,促使她明白内心真正的需求,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
最后,“水”在该小说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意象,劳伦斯借助吉普赛老人通灵的本事,让伊维特留心听水的声音。老人的预言与洪水将小说推向“神秘主义与神话的境界”。一方面,永恒流动的水象征着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存留在公馆内的伊维特醒来后的世界犹如刚从造物主手中诞生一样,她结束了浑浑噩噩内心缺乏活力的旧生命,渴求自由独立的新生命苏醒过来。另一方面,帕普尔维克水坝的决堤,让人联想到了《圣经》旧约创世记的毁灭天下的洪水之灾。水在两者中都有净化和救赎的作用:创世纪里的洪水是为了除灭终日思想恶的人,小说中的洪水带走了教区长公馆的污秽和死寂,意味着被吉普赛男人一步一步打开的生命之水将会在伊维特心中流动不息。
吉普赛男人激起了伊维特的新生命,洪水带走了伊维特生活中的束缚使得她的新生命得以流淌。伊维特默认了吉普赛男人已失踪的事实,她那年轻的心灵明白,这样做是理智的,她清楚地知道了自己是不可能抛下现有的一切跟随吉普赛人去流浪的。她依然生活在原生家庭中,但摆脱了来自奶奶的压迫,在吉普赛男子的呼唤指引和洪水的冲击下获得了重生,精神和肉体的同步再生。整个过程中,伊维特的本我、自我和超我在彼此交互调节,和谐运作,最终达到平衡的状态,洪水过后,她在家庭带来的的安全感的基础上,以新生命继续生活。正如劳伦斯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自序中写到“如果要生命变得可以忍受,就得让心灵与肉体和谐,就得让心灵与肉体平衡,自然地相互尊重才行”。
四、结语
19世纪后20世纪前,英国的工业革命对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开始疯狂追求物质上的满足,忽略精神世界的需求。不仅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个体自身也变得矛盾与分裂。劳伦斯本人竭力追求欲望与精神的相互平衡,《处女与吉普赛人》倾向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和谐。劳伦斯看到了愈合人心分裂的希望,倡导人类对于生活和精神的积极态度。
[1]Alvarez A. Review: Lawrence, Leavis, and Eliot[J].The Kenyon Review,1956,18(3):478-485.
[2]David Craig. The Real Foundation: Literature and Social Change[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1973:318.
[3]Kim Younghoon. The Performativity of Literature and Its Ethical Engagements in D.H.Lawrence’s The Virgin and the Gipsy[J].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2015,7(01):148-162.
[4]戴维•赫伯特•劳伦斯.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选[M].主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5]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未婚少女与吉普赛人》[M].宋兆霖,等译.广西:漓江出版,1988.
[6]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6:自我与本我》[M].车文博主编.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7]李晓丽,李利.两极对照下《少女与吉普赛人》[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7,35(02).
[8]单敏.劳伦斯与弗洛伊德主义[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3,4(04).
[9]宋时磊.吉普赛人无根的双重流浪[J].世界文,2010(08):41-43.
[10]邵玉丽.从“无意识”到“血性意识”——论劳伦斯对弗洛伊德学说的继承与超越[J].河南广播大学学报,2009,22(02).
[11]汪志勤.《少女与吉普赛人》——劳伦斯后殖民文学的书写[M].上海:东方出版社,2010.
[12]祝昊.关于生存理想的言说——论D•H•劳伦斯的神话书写[D]. 天津:南开大学,2014.
———摄影大师艾略特·厄维特拍的一组情侣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