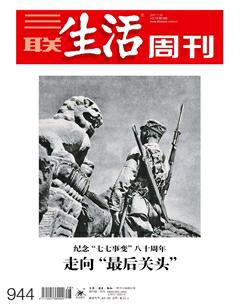在夏天,读懂普鲁斯特
马凌
“假若在漫漫长夏阅读普鲁斯特,这些回旋往复的主题定如溽暑、蝉鸣、微风,缭绕不去。”
巨著的中译本

好友要去医院探病,对方刚刚动完一场大手术,她觉得带一束花去过于平凡,莫若送一套《追忆逝水年华》,因此问我哪个版本好。这一问,真是令我百感交集。一则,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弟弟罗贝尔·普鲁斯特、著名外科医生,也是哥哥的遗嘱执行人,曾经感喟说:“可惜的是,要身患重病或腿部骨折,才有时间去看《追忆逝水年华》。”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从心境的角度,这部大书都更适合病人、闲人、有阅历的人,拿来探病也算不俗的礼物。二则,目前国内的普鲁斯特全译本,还是只有上世纪90年代集合了15位译者的七卷本译林版。此后,翻译家周克希先生独立翻译了第1、2、5卷(周译书名为《追寻逝去的时光》),于2014年宣布弃译。又一名翻译家徐和瑾先生,则在独立翻译了第1、2、3、4卷后,于2015年病逝。细论起来,多人译本风格不太统一,周译有繁花似锦之趣,徐译有清和简明之美,但正如法郎士所说:“人生太短,普鲁斯特太长。”后两种未成全璧,恨何如之。
一天早晨,普鲁斯特夜里睡了没多久刚醒来,还躺在床上,就对他忠实的女管家说:“我写下了‘完这个字,现在可以死了。”《追忆逝水年华》的法文全本将近3000页,500个人物,200余万字,皇皇巨著,令人“望长生畏”,令人敬而远之。如果说,名著就是那些我们急于购买却懒于翻开的书,《追忆》一定是在榜单前三甲。即便是在小众读者群里,它也是被谈论得多、被阅读得少——坚持读到最后一页的更少。反过来说亦正确:有相当一部分读者不想精读它、却想谈论它。在这个意义上,“缩写”和“导读”都大有可为。前一个工作,周克希做了,他在2016年夏天推出《〈追寻逝去的时光〉读本》,选译了七卷中的精彩部分,又用尽可能简洁的文字连缀成篇。后一个工作,徐和瑾做了,他在2014年翻译了同年法国出版的《与普鲁斯特共度假日》,那是法国最资深的八位普鲁斯特研究专家为普通读者做的导读,一本“最好的入门书”。
徐和瑾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在俄语、德语、捷克语和匈牙利语中转了一圈,后在复旦大学法语系任教多年。我与徐先生有一面之缘,某年上海书展,为了推介《追忆》,充作嘉宾与他对谈。那次,他穿一件白色短袖衬衣,风度儒雅,言谈简淡,有谦谦君子气度。目前网络上最常能看到的他的照片,就是那次活动的产物。记得攀谈中他说起,一直住在复旦凉城新村那边的老宿舍区,除了书别无所有,亦别无所求。徐先生用11年时间翻译《追忆》,完全是因为喜爱;同样,他翻译《与普鲁斯特共度假日》,也是缘于一见倾心。为了译它,他甚至停下了《追忆》第五卷的翻译。最令我动容的是,或许是因为清寒吧,他在治疗期间还预支了本书的翻译稿酬。知其人再观其书,这本粉绿色封面的清新小书,蓦然显出“遗作”的沉重。
《与普鲁斯特共度假日》囊括了一众法国顶尖的普鲁斯特研究者和编辑者。2013年,受法国公共电台的邀请,他们就各自有心得的题目,讲述作品中印象最深的一页。于是诞生了八个主题,分别是时间、人物、社交、爱情、想象、地方、哲学、艺术。读过《追忆》的读者知道,这八个主题,恰恰是交织在书中的深层脉络,每个主题大都包括五篇文章,每篇后附有小说最能表现主题的精彩片段——有趣的是,常常是普鲁斯特本人的表述为每一篇的点睛之笔。在普鲁斯特研究领域,庞德的教诲众所周知:“对这本书的最完美的批评应该只写一段,这一段必须有七页长,而且只能用分号。”可是八位作者并未如此矫情,既属厚积薄发,又能深入浅出,几乎可以算作知识分子服务公众的范本。
徐和瑾先生的译本照法文原本多了两个附录,一是参考三个法国权威版本,编出了长达39页的《追忆似水年华》梗概。二是将正文中提及而囿于篇幅未能录入的精彩片段,一并翻译收入。他体恤地解释说:“这样一来,这本书就可以有两种读法。一是按书中页码的次序一页页读下去,二是先读《追忆似水年华》的梗概,并按其中注出的书中页码依次阅读小说的精彩片段,读完后对这部小说就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再去读八位学者的分析,也许印象更为深刻。读完这本小书之后,想必会对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产生兴趣,那就去阅读七卷本的全书。”
如何了解一个人?
据说有这样一个规律,购买《在斯万家这边》的读者中,只有一半人買了第二卷《在花季少女倩影下》;购买《在花季少女倩影下》的读者中,只有一半人买了第三卷《盖尔芒特那边》。但读者阅读了《所多玛和蛾摩拉》之后,却不再拒购《女囚》《阿尔贝蒂娜失踪》和《重现的时光》。我想这是因为《所多玛和蛾摩拉》一卷勇敢描写同性恋,同时也是全书的转折卷,那些马塞尔自认为已经熟悉的人物,现出“陌生的另一面”,映照着普鲁斯特津津乐道的主题之一:“我们永远无法了解别人。”普鲁斯特研究权威让-伊夫·塔迪埃撰写“人物”部分,他为夏吕斯男爵设了专节,夏吕斯男爵出身极其高贵又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令人入迷,也令人不安,塔迪埃指出:“叙述者——以及普鲁斯特——特别感兴趣的,是表象和心灵深处之间、表象和现实之间的戏耍。夏吕斯从外表看极其阳刚,但内心却是女人。描写这种双重性,对一个热衷于寻求本质的小说家来说,是一件十分诱人的事情。”最神乎其技的是,塔迪埃只引用了《所多玛和蛾摩拉》开卷的一段19行的描写,就让读者领略了普鲁斯特文笔的精妙、思想的深邃。
相对而言,《追忆》中的爱情主题最能引起普通读者的共鸣。书中人物一旦恋爱,就会依次体验热情、不安、嫉妒、不幸,有时还会绝望,没有人最终能享受自己的情感。“爱情,”普鲁斯特说,“是一种相互折磨。”书中负责撰写“爱情”部分的是尼古拉·格里马尔蒂,他是哲学家,认为“等待”“失望”以及“想象的事物的魔力”,是理解普鲁斯特式爱情的关键词。
“爱情的这种痛苦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只想要我们没有占有的东西。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只要占有所爱的东西,就不再知道为什么我们想要这东西了。总之,正如我们从斯万和叙述者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是嫉妒的痛苦向我们揭示我们的爱情,同时把我们所爱的女人在场和我们痛苦的结束联系在一起。因为她不在我就痛苦,是这种痛苦使我知道我爱她。因此可以说,爱情和痛苦不可分离,只有痛苦才能向我们揭示爱情。”
在小说里,无论是斯万对奥黛特,还是马塞尔对阿尔贝蒂娜,皆处于这种强烈而又不幸的爱情中。相形之下,还是夏吕斯聪慧,他是书中少数认为“爱是幸福”的人:“在生活中,重要的不是喜爱什么,而是喜爱本身。”
如何留住流逝的时光?为什么爱情使人痛苦?是否能真正了解一个人?假若在漫漫长夏阅读普鲁斯特,这些回旋往复的主题定如溽暑、蝉鸣、微风,缭绕不去。要在某一个霹雳电闪的瞬间,读者会在字里行间看到自己,以及普鲁斯特所照亮的所有人的痛苦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