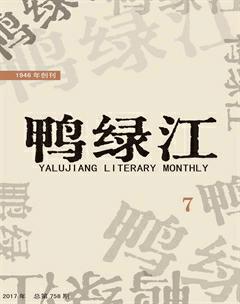诗歌是我的心灵史
問:很多人认为,诗歌是年轻人的事情,您从60年代开始写诗,写了四十多年,还在继续写,为什么您的诗歌创作能保持这么久的生命力?你如何理解诗人的成熟?
赵:我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是诗人的成熟。真正的诗人也许一生都纯真如孩童,不知成熟为何物。我最初的诗作,是写在“插队落户”的岁月中,还不到二十岁。那些在飘摇昏暗的油灯下写的诗行,现在读,还能带我进入当时的情境,油灯下身影孤独,窗外寒风呼啸,然而心中却有诗意荡漾,有梦想之翼拍动。可以说,诗歌不仅丰富了我的生活,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诗歌之于我,恰如那盏在黑暗中燃烧着的小油灯,伴我度过长夜,为我驱散孤独。人人心中都会有一盏灯,尽管人世间的风向来去不定,时起时伏,只要你心里还存着爱,存着对未来的希冀,这灯就不会熄灭。和诗歌结缘,是我的幸运。我写诗的数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这并非说明我对诗歌的热爱在消退。诗是激情的产物,诗的激情确实更多和青春相连,所以诗人的特征常常是年轻。然而这种年轻应该是精神的,而非生理的。只要精神不老,诗心便不会衰亡。
问:《火光——冬夜的断想》是青春年少的你在崇明岛的黑夜里写下的第一首诗吗?在这首诗中,感觉是用诗歌的光亮驱散黑暗和迷茫。写诗四十多年,在对诗歌形式和技巧的把握上一定有了变化和发展,能否谈谈这些变化和发展。哪些诗作是你诗歌之路上的标志性作品,代表着你在诗意、诗域和诗歌形式上的拓展?
赵:《火光》是我到崇明岛插队初期在日记本上写的一首诗,不是第一首,那时还写了不少别的诗,如《哑巴》《梦境》《友谊》等。那时写诗,不是为了发表,是一种心情的表达,一种情绪的宣泄,“用诗歌的光亮驱散黑暗和迷茫”,是评论家的说法,那时心里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念头,只是觉得在油灯下用分行的文字抒写自己的心情,描绘当时的生存状态,赞美大自然,是一种愉悦,有时沉浸在自己编织的文字幻境中,甚至会忘记肉体的疲惫。那时写诗,确实是一种在孤独困顿中的自慰和自救,是一个落水绝望的人在波涛和旋涡中抓到的一根救命稻草。从最初在日记本上写诗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五十年,可以说,诗歌陪伴了我的青春,陪伴了我的人生。对诗歌艺术的追求,对我来说也是一辈子的追求吧。这四五十年中,其实也一直在求新求变,对诗歌的形式、题材,对诗意的寻找和思考,对意象的发现和处理,对文字修辞的提炼,这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三言两语无法说清。但我认为诗歌应该是有灵魂的,这灵魂,取决于写作者真诚的态度,坦荡的心襟,自由的思想,浪漫不羁的想象,缺乏这些,形式再新奇绚烂,也不会有力量,不会有感染力和生命力。就像一具僵尸,即便身披华袍,总归了无生趣,没有生命。
问:200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沧桑之城》,是上海诗人创作的关于上海的第一首长诗。隔着十二年的岁月之河,你现在对《沧桑之城》有着怎样的评价?你书写《沧桑之城》的初衷是什么?上海是一座变化发展着的现代都市,上海有着丰富的前世今生,上海也有着一以贯之的个性,上海对你的文化个性和文学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
赵:《沧桑之城》是我献给故乡的一部长诗。我在这本诗集的扉页上有这样的题词:“谨以此诗献给我亲爱的父母之城”。父母之城,也就是生我养我的故乡之城。中国几千年历史,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基本是农耕社会,传世的文学作品,大多以山林自然为描写对象,若写到故乡,也多是乡村,是和大自然相关联的。在诗人的作品中,故乡就是一间草屋,一缕炊烟,一条河,一棵树,一弯荷塘,一片竹林,一群牛羊,一行归雁。所谓“乡关”,“乡梦”“乡情”“乡愁”,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诗人对童年时代所相处的大自然和乡村的依恋、向往和怀念。羁旅途中,眼帘中所见也多是乡野山林,触景生情,引发乡愁,是很自然的事情,譬如宋人王禹偁的怀乡妙句“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就是由此而生。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白话诗,也是延续了这个传统,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诗人,大多也来自乡间。但是时代发生了变化,现在的很多诗人,出生在城市,成长在城市,他们的童年和故乡,就是城市。这和古代诗人完全不同。如果还要在诗中学古人,学出自乡村的前辈,那就不合情理了。譬如我,我的故乡就是上海,我在这个城市城市出生,在这个城市长大,所有童年的记忆,都发生在这个城市中,羁旅在外,思乡之情都是和这个城市发生关联。我想,和我同时代的或者比我小的诗人,大致也是这个情况。写城市的诗篇中,出现了很多古诗中没有的意象,楼房,街道,工厂,商店,人山人海,也许很多人认为这些意象与诗无关,其实不然。所谓诗意,未必只和特定的对象发生关系,只要心中有诗意,有对美的追求和向往,有灵动的想象之翼在心头扇动,天地间的一切皆可入诗。故乡到底是什么?其实不仅仅是具体的地域,更是感情的寄托,父母亲情,手足之情,儿时的伙伴,一段往事,一缕乡音,都可能是记忆中故乡的形象,这些无关乡村还是城市。所以在《沧桑之城》中,我写了亲情,写了记忆中印象深刻的往事。虽然没有想过把这首长诗写成史诗,但也在诗中追述了我所了解的上海近现代历史,并将我在这个城市中所经历的悲欢离合诉诸文字,化为诗情。所谓史诗,其实未必是摆开架势叙述评价历史,如果能将历史的画面和思考以个人独特的视角呈现,哪怕是滴水之光,一孔之见,或者是大时代的一两个真实的回声,能让读者从中窥见历史的真相,也不失为史诗的一部分。有些微观的描述,因其真实细腻,因其独特真切,也许比那些试图以宏观浩瀚的姿态书写的史书更让人感觉亲近。
上海这座城市,这大半个世纪来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城市的形态,到市民的心态,都有大变化。我亲眼目睹感受了这种变化。这座城市对我的影响,如同水之于鱼,泥土之于草木,树林之于鸟雀。这种影响,是千丝万缕难以摆脱的。可以说,我写作的源头和动力,都藏在这座城市中。也许身在其中,感觉不到这座城市变化的巨大,“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是在这座城市性格中,有一些恒定不变的元素,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品格,虽然历尽沧桑,依然被坚守,成为支撑这座城市的风骨。我在《沧桑之城》写了几个人物,有的是从传闻中所知,有的是我认识的前辈。如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在市区武装游行时,从大世界顶楼高喊着“中国万岁”跳下来以死抗议的殉国者;如抗战期间蓄须明志、誓死不为侵略者唱戏的梅兰芳。我也在长诗中写了晚年的巴金,他的真诚和坦白,为天下的文人指出一条朴素之路,通向真和善的境界,他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良心。写这首长诗时,巴金正住在医院里,但他已经无法和人交流。我去医院里看望他时,曾在心里默默地吟诵那些为他而写的诗句。
问:2013年10月你获得塞尔维亚斯梅德雷沃金钥匙国际诗歌奖,给世界诗坛留下中国当代诗人的形象。一年一度的塞尔维亚诗歌最高奖在世界范围内遴选诗人有什么样的要求?你的哪一本诗集被翻译成了塞尔维亚文?你的诗歌最打动评委的是什么,他们做出了怎样的评价?你获奖的感受是什么?
赵:斯梅德雷沃城堡金钥匙国际诗歌奖是塞尔维亚最高规格的诗歌奖,起始于1970年,每年从全世界范围内评选出一位有影响的诗人颁授此奖,是欧洲著名的国际诗歌奖。能获得这个奖项,当然有一个前提,获奖者的诗歌在塞尔维亚文有翻译介绍,否则不可能进入评委视野。获奖其实也是运气吧,你的诗被翻译了,被评奖者关注并器重了,一顶桂冠突然就从天而降。文学评奖总是挂一漏万的事情,有多少优秀的作家一生和奖无缘,这并不影响读者对他们的喜爱。这个诗歌奖的获奖者大多是欧美诗人,除我之外,还有两位亚洲诗人曾获得此奖,1992年,中国诗人邹荻帆获奖,2010年,日本女诗人白石嘉寿子获奖。2013年的金钥匙诗歌奖颁奖典礼上,塞尔维亚作家协会主席安德里奇宣读了很长的颁奖词,其中有这样的话:“赵丽宏的诗歌让我们想起诗歌的自由本质,它是令一切梦想和爱得以成真的必要条件。”他还当场吟诵了我年轻时代的诗歌《梦境》。我的诗集《天上的船》的塞尔维亚语译者德拉格耶洛维奇是著名塞语诗人,他在颁奖会上介绍了我的诗歌,他在致辞中这样说:“赵丽宏是一位自我反思型的诗人,他的诗歌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最宝贵的艺术价值,同时又兼容了时代的敏感话题。从他的这本诗集中,读者能够很直接地感受到赵丽宏的个人经历和生活的时代,了解他的生活,他的为人。”“中国的诗歌传统和他们的文化一样悠久而丰富,往往在平淡中见真知,在不经意间透出新意。人类几千年的诗歌体验已经证实:简练的语言、丰富的想象、深远的寓意是诗歌的理想境界,永远不会过时。赵丽宏诗集《天上的船》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我在颁奖典礼上发表了简短的获奖感言,且摘录如下:
能用中国的方块字写诗,我一直引以为骄傲。我的诗歌,被翻译成塞尔维亚语,并被这里的读者接受,引起共鸣,我深感欣慰。
诗歌是什么?诗歌是文字的宝石,是心灵的花朵,是从灵魂的泉眼中涌出的汩汩清泉。很多年前,我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把语言变成音乐,用你独特的旋律和感受,真诚地倾吐一颗敏感的心对大自然和生命的爱——这便是诗。诗中的爱心是博大的,它可以涵盖人类感情中的一切声音:痛苦、欢乐、悲伤、忧愁、愤怒,甚至迷惘……唯一无法容纳的,是虚伪。好诗的标准,最重要的一条,应该是能够拨动读者的心弦。在浩瀚的心灵海洋中引不起一星半滴共鸣的自我激动,恐怕不会有生命力。”年轻时代的思索,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可以重申。
感谢斯梅德雷沃诗歌节评委,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这是对我的诗歌创作的褒奖,也是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肯定。感谢德拉根·德拉格耶洛维奇先生,把我的诗歌翻译成塞尔维亚语,没有他创造性的劳动,我在塞尔维亚永远只是一个遥远的陌生人。
中国有五千年的诗歌传统,我们的祖先创造的诗词,是人类文学的瑰宝。中国当代诗歌,是中国诗歌传统在新时代的延续。在中国,写诗的人不计其数,有众多优秀的诗人,很多人比我更出色。我的诗只是中国诗歌长河中的一滴水,一朵浪花。希望将来有更多的翻译家把中国的诗歌翻译介绍给世界。
问:你最新诗集是2016年出版的《疼痛》,从内容到形式,从书的装帧设计到诗集的内容,都给读者以鲜明视觉体验和心理冲击,一种现代性和先锋性油然而生。你为什么会在人生的这个阶段集中书写疼痛?是经历了人生坎坷后,对疼痛有了切身体验和深刻认识?还是你的诗学观念发生了重要转变,或者时代的变幻、现实的生活对你写作产生的影响?这是一次主动选择的重要改变吗?是什么促成了这次重要的转变?你對此书别致的装帧设计满意吗?
赵:《疼痛》出版后,有评论家和同行认为这是我的变法之作,和我年轻时代的诗风有很大改变。一位评论家说我“以一个完全陌生的诗人形象重新站立在读者面前”,说得有些夸张,但确实是很多读者的看法。其实我还是原来的我,只是写诗时改变了原来的一些习惯。年轻时写诗追求构思的奇特,形式的完整,语言的精美,诗作吟咏的对象,大多为我观察到的外在天地,写我对世界对人生的实在的感受,每写一首诗,都要力求清晰地表达一种观点,完成一个构思。而这几年写的诗,更多是对人生的一种反思,也是对我精神世界的一种梳理。经历了大半个世纪动荡复杂的时事,追溯以往,来路曲折,并非一目了然。这本诗集中的作品,不求讲明白什么道理,只是通过各种意象片断地袒示自己的心路历程,也许不是明晰的表达,但是对内心世界的真实开掘。我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如果说,年轻时写诗是对外开放,现在的诗,更多的是向内,向着自己内心深处的灵魂所在。每一首诗的孕育和诞生,都有不一样的过程,有灵光乍现瞬间完成,也有煎熬数年几经打磨。一首诗的完成,也许源于一个词汇,一句话,一个念头,也许源于一个表情,一个事件,一场梦。但是一定还有更深远幽邃的源头,那就是自己人生和精神成长的经历。
《疼痛》的装帧设计是别出心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美编确实是下了功夫。封面用纱布包裹,使人联想起包扎伤口的绷带,与书名的含义是契合的。内页的设计也非同一般。这本诗集,我不是用电脑写的,每一首都有手稿,而且改得密密麻麻,我的老习惯,喜欢随手在手稿上涂鸦,画一些和文字相关或无关的图像。其实也是写作心路历程的一部分。诗集的设计者将我的手稿处理成黑底金字,每一页的呈现方式都不一样。我感谢设计者为这本诗集的装帧进行的创造,他们为此耗费了心思,诗集出版后,读者对这本书的装帧设计有很多好的评价。
问:诗人杨炼认为,赵丽宏诗集《疼痛》的出现“再次证明,诗须臾不会离开真正的诗人,只会冶炼他挣脱虚丽浮华之词,裸出带血的灵魂”。真正的诗歌是挣脱虚丽浮华之词,真正的诗人应该是裸出带血的灵魂,这是你的追求吗?
赵:杨炼读了《疼痛》之后,从国外寄来了他的评论。他评论中那些话,让我感动,也使我心有共鸣。他在评论中这样说:“我们这一代的短短人生,已见证了数度生死沧桑。谁亲历过那些,不曾伤痕累累?但,又有几人甘愿直面自己的伤痕,甚或撕裂假装的愈合,读懂深处暗红淤积的血迹?”“当代中文诗不缺小聪明,唯缺真诚的‘笨拙——大巧若拙。真人生这首‘原诗,拼的不是词藻,而是人生深度和厚度。一种‘无声胜有声‘功夫在诗外,严厉裁判着我们写下的每个词句。”这是知音的评语。最近即将在塞尔维亚出版的《疼痛》塞语译本,已将杨炼的这篇评论翻译成塞尔维亚语并作为序文。
问:疼痛是人最直接的生理反应和心理体验,身体的创伤,心灵的创伤,都会让人感觉疼痛。你将诗集命名为《疼痛》,是一种坦诚,是一种勇敢,还是思想的重新出发?
赵:在写这本诗集时,并没有想过以《疼痛》作为书名,最后整理编辑时,对书名斟酌再三,曾经想过几个不同的书名,最后还是觉得《疼痛》似乎可以对集子中的诗作做一个情绪和思绪上的概括。这大概无所谓坦诚和勇敢,只是觉得《疼痛》是个合适的书名,尽管不新鲜,也没有什么独特,但对这本诗集而言,对我这些年写诗的心绪而言,这两个字恰如其分。
问:《疼痛》是从疼痛的角度,深入观察自我和内心,探究自我生命的状态。强烈的痛苦正是一个人生命力的反应,在疼痛中思索,人在麻木和混沌中是不可能思索的。你为何疼痛?是自我坚守的代价,是对不合理的现实的对峙?是因为善良被摧残,是非被颠倒,弱者被欺凌而疼痛?
赵:其实,你提这些问题,已经对何为“疼痛”做了一些解读,也是作了一些猜测。我不想揭谜底似的回答这些问题,觉得没有必要回答,也难以回答。所有的想法,都在我的詩中,有的已经明白道出,有的或许隐藏在文字中,隐藏在意象里,甚至隐藏在诗句的阴影和回声中。不同的读者,也许可以读出不同的情绪和意境。从评论家们的解读中,我已经感觉到,这使我欣慰。
问:写于1982年的《痛苦是基石》,是你刚出港的文学之舟的压舱之作吧,三十四年后依然让你印象深刻,将它收入《疼痛》诗集,它是你书写疼痛的起点吗?你还记得三十四年前你写《痛苦是基石》的缘起吗?那时你就认识到痛苦是人生的基石吗?
赵:每一首诗的构思和写作,都有起因,也许是生活中的一段际遇,也许是思考很久的问题有了一点眉目,也许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困惑,也许就是心灵一颤,是灵光乍现。写作《痛苦是基石》的年代,是思想活跃却也颇多纠结的年代,在一些人实现抱负的时候,更多的人在现实中遭遇挫折甚至头破血流,而人群中爱情的喜剧和悲剧永远在同时上演,后者往往给人更深刻的印象。诗人应该是思想者,对人性对人生有自己的思考。这首诗,当然是有感而发,当时写在笔记本上,是一个草稿,没有收入诗集。诗集《疼痛》的作品序列,以新作为先,诗集中只有这首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旧作,所以便排在了最后。评论家称之为“压舱石”,也引起我会心一笑。
问:《疼痛》中有好几首诗写到了梦,写到了梦境。据说您有几首诗完全是梦中出现的。诗和梦,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赵:《疼痛》中确实有多首诗写到梦,展现了梦境。我是一个多梦的人,从小就喜欢做梦,常常有非常奇特的梦境。有时候现实的生活会在梦境中以异常的方式延续,有时候会在梦中走进天方夜谭般的奇境。梦境一般醒来就会模糊,会忘记。但如果一醒来就赶紧写几个字记下来,梦境便会围绕着这几个字留存在记忆中。有时写作思路不畅,睡梦中会继续构想。譬如《重叠》这首诗,就是梦中所得,混沌的梦境中,有一个清晰的声音,一句一句在我耳畔吟诵回萦,吟毕梦醒,我用笔记下了还能记起的这些诗句。逝去的亲人,有时会走进我的梦境,《访问梦境的故人》,便是写梦境中遇见故人,有我对生和死的思索。《迷路》也是写一场梦,是写在梦中遇到去世多年的父亲,整首诗,是对一场奇异梦境的回顾,梦中有梦,梦醒之后,依然在梦中,当然,所有一切,都围绕着对父亲的思念。梦入诗境,当然是几个偶然的特例,可遇不可求。写诗不能靠做梦,但是诗的灵感如果在梦中降临,那也无法拒绝。
问:《疼痛》出版后,海外很快翻译出版了不同的译本,这在当下的诗歌创作中很少见,有何契机吗,现在已经有了几个译本?
赵:谈不上什么契机,是因为这本诗集中的部分作品,包括英译,陆续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引起一点关注。或许也是因为前几年在国际上获奖,有多种不同文字的诗集译本在国外出版。《疼痛》的英译近日已由美国Better Link出版社出版。翻译者是年轻而有才华的加拿大华裔女诗人Karmia Chao Olutade,哈佛大学著名的汉诗翻译家Canaan Morse是这本诗集的特约编辑。《疼痛》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语的翻译已经完成,马上会在两个国家分别出版。法语和西班牙语的翻译出版也在进行中。塞尔维亚翻译这本诗集,是因为我曾在那里获诗歌奖,有不少同行关注我。保加利亚前几年曾翻译出版过我的诗集和散文集,那里有我的读者。
问:“新诗百年”已成为近两年诗坛关注的热词,一百年来,中国经历了无数时代的动荡和变革,历史的潮流中涌动着无数诗人的身影。你从他们的身上汲取过精神和诗艺的滋养吗,思索过诗人诗歌创作和时代风云之间的关系吗?
赵:新诗百年,风云变幻,走过曲折的长路。这也是文学评论家的话题。每个时代的优秀诗人都值得尊重,我也曾从他们的文字中汲取营养,也获得教训。百年以来,不少诗人风云一时却逐渐被人淡忘,有些诗人曾经被批判嘲讽却重回当代人的阅读视野并地位日升。其中有政治对文艺的干扰原因,也有各种各样的媚俗的结果,很多人自以为清醒,却迷失在追风趋时的喧闹之中。而那些真正的诗人,即便孤独,即便曾经被忽略被嘲笑,却用自己不朽的文字告诉世界,什么样的诗才真正具备生生不息的灵魂。每一个现代诗歌写作者的经历中,都可以发现此类轨迹,包括我们这一代人。
问:你以散文和诗歌、小说三种形式,画出你的文学坐标,有评论家指出,赵丽宏的散文是站在他的诗歌的肩膀上的,他的散文和诗,是互相生发、互为补充的。你如何看你的诗歌创作和你的散文创作的关系?你的诗歌创作对散文写作有着怎样的影响?
赵:我的诗歌和散文确实互相生发,互为补充。诗歌是我的心灵史,是我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履历;散文是我的生命史,是我的人生经历和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的表达。这两者,有时候交织在一起,诗中有散文,散文中有诗,所以还有散文诗。有评论家专门评述过我散文中的诗意,这样的评论,大概也反映了我写作的一种习以为常的状态吧。写散文,犹如和朋友交谈,写诗,是和自己的心灵交谈,而且常常是扪心自问。
问:在一篇题为《诗意》的散文中,你曾引述一位西方哲人的如下话语:“我愿把未来的名望寄托在一首抒情诗上,而不是十部巨著上。十部巨著可能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被人忘记得干干净净,一首优美而真挚的小诗却可能长久地拨动人们的心弦。”在所有的创作中,你觉得诗歌创作是最重要的吗?
赵:我当然看重诗歌。那位西方哲人的话,引起我的共鸣。文学家的写作,其实都是灵魂的袒呈,是生命的感悟,是人性的思索,是对自己所处的自然和时代的评论。诗歌尤其是这样。如果有真挚睿智优雅的文字能留存下来,被一代又一代读者记住,那你就没有白写。我读唐诗宋词时经常这么想,这些写于千百年前的诗词,现在还在被人诵读,使人共鸣,这真是文学的奇妙魅力和伟大力量。有些诗人,他的一两句诗歌被读者记住并且世代流传,他就进入不朽的行列。当然,没有一个诗人在写作时想著自己会不朽,这是读者和历史的选择,也是文学真谛的选择。如果你的文字所呈现的是狭隘的偏见,是平庸的陈词滥调,那么,被遗弃被淡忘是必然的。有多少著作等身的文人,在历史长河中留不下一点回声。
问:互联网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也对当代诗歌的传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网络,加速了诗歌“草根性”的发展,大量草根诗人的诞生,就是诗歌大众化的一种注解,你读过草根诗人的作品吗?如何评价草根诗人的诗歌创作?
赵:我不太认同“草根诗人”的说法。那些挣扎在生活底层,却依然在寻找诗意,追求文学的理想,并把他们的追寻诉诸文字,其中有一些有才华的作者,写出了让很多人感动共鸣的诗歌。将这些人称为“草根诗人”时,发明这种称谓的人是居高临下的,为什么要俯瞰他们?你俯瞰着他们就可以自称为“鲜花诗人”或者“大树诗人”了吗?很荒唐。如果让“草根诗人”这个名字存在,我认为它可以涵盖所有写诗的人。在浩瀚自然中,我们人人都是一棵小草。当然,草和草是不同的,有自生自灭的野草,有生长期很短的杂草,也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生命草,也有珍奇仙草,如虫草灵芝。那些生活在底层的写作者,如果真有才华,超群出众,不是没有成为虫草灵芝的可能。套用《史记》中陈胜的名言,“诗人才子宁有种乎?”纯文学意义的诗歌创作,一定是小众的写作,任何时代都是如此,即便是盛唐,留名青史的诗人也只能是写诗者中很少一部分人。诗歌读者和作者因互联网的繁衍而壮大,这对诗歌创作当然是好事,关注参与者多,对诗的挑剔和要求也会随之增多增高,诗歌审美的眼光也会愈加丰富犀利。那些真正的好诗一定能遇到真正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