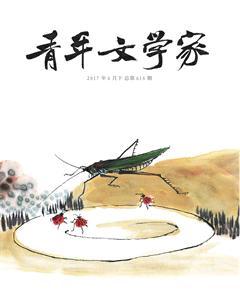从白山黑水到江畔山城
基金项目:陪都时期重庆文化生态对抗战文学创作的影响,项目编号:2011YBWX082。
摘 要:从1938年辗转来渝到1940年飞往香港,这一时期萧红的写作呈现出与前期不同的特征。本文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入手,通过对萧红前后期作品文本的对比分析,研究其创作中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从而探究地域文化对于萧红创作的影响,并进一步剖析抗战文学中的重庆形象。
关键词:萧红;地域文化;重庆形象
作者简介:刘瑜(1969-),女,重庆人,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作品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8-0-02
作为体验型的现代作家,萧红以自己悲剧性的生命体验,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存境遇,从而使其作品获得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和丰厚的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纵观萧红的创作经历,1938年之前写成的作品多体现出东北地域文化气息,而1938年之后的作品中则出现了大量巴渝地区特有的地理环境特征与民俗意象。生活环境的变迁在萧红的作品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萧红前后两期的文学创作,促使萧红的文学生命走向成熟。
一、呼兰的女儿——白山黑水育精魂
萧红的故乡小城呼兰位于黑龙江省南部,地域文化特征对萧红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在环境与人物描写这两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萧红在其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中,以细致的笔触描摹了东北故乡的风物:
“草叶和菜叶都蒙盖上灰白色的霜。山上黄了叶子的树,在等候太阳。……雾气象云烟一样蒙蔽了野花、小河、草屋;蒙蔽了一切声息,蒙蔽了远近的山岗。”
秋色、山岚、雾气等充满东北特色的景物于叙述中恰到好处地穿插,透露出十足萧红式的凄清动人,正是这些带有萧红主体情感的抒情语句镶嵌于作品中,使这个着意表现阶级对立的故事焕发出动人的诗意。
与此同时,除开独具特色的萧红式环境描写,萧红作品中各色人物塑造也是其文学价值的重要方面。萧红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东北人所特有的。《生死场》中的王婆,其承受人生苦难时超乎常人的顽强正是东北人强悍韧劲的体现,她身上有一种令人讶异的顽强到近于冷酷的个性。王婆这样向村妇描述女儿的死:
“偏偏孩子跌在铁犁一起,我以为她还活着呀!等我抱起来的时候……啊呀!一条闪光裂开来,看得清王婆是一个兴奋的幽灵……啊呀!……我把她丢到草堆上,血尽是向草堆上流呀!她的小手颤颤着,血在冒着气从鼻子流出,从嘴也流出,好像喉管被切断了。”萧红将雷雨、闪电与悲剧本身交织在一起,从个体挣扎的撕裂中显出形象的鲜活透出生命的残酷。
王婆述说女儿惨死的悲剧,“一点都不后悔,一滴眼泪都没淌下”,村中妇人难产,她也是“拿着钩子,也许用那个掘菜的刀子,把那孩子从娘的肚子里硬搅出来”,这种近乎野蛮的豪强气概,或许正是作为北方妇人的王婆能够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的一种先决条件,是北方人民“生的坚强,死的挣扎”。而王婆这样的强健的庄户农妇形象只有在开阔、严寒、艰苦的环境中才能产出。
可以说,在对故乡反复的书写中,萧红将关注点多放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人民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但在1938年的创作中,萧红对于底层人生活状态的描摹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盡管还是萧红式的对于苦难的感伤与悲悯,但是其中却大量出现了对南方江城景致与山城人物品格的描写,其写于抗战爆发初期的《山下》这样描写江景:
“清早起,嘉陵江边上的风是凉爽的,带着甜味的朝阳的光辉,凉爽得可以摸到的微黄的纸片似的,混着朝露向这个四围都是山而中间这三个小镇蒙下来……”
与前期作品《王阿嫂的死》中的景物描写相对比,《山下》显然是另一种话语书写。极寒、凋敝的冬景与气温适宜的江城风光形成强烈对比,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物形象也有很大差异,《王阿嫂的死》与《山下》就是一个很好的对比例证。王阿嫂与林家母女都生活困窘,但王阿嫂是蚁子般地活着,狗一般地死亡;林家母女却活得有滋有味, 纯朴而恬谧。同是青春少女,小环姑娘和林姑娘的生命状态反差巨大,小环姑娘的生存状态是:“……会忧愁,会思量。她听着秋虫吵叫的声音,只是用她的小嘴在学着大人叹气。”;林姑娘则是:“她有意把衣裳按到水底去,满衣都擦满了黄宁宁的沙子,她觉得这很好玩,这多有意思呵。”在实际生活境遇上,小环、林姑娘之间并无本质区别,然而一个悲哀、死寂,毫无生气,一个灵动富有生命的灵气,这种巨大的形象差别说明萧红对同一类创作对象的关注方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除了《山下》,萧红1938年之后所写的多篇作品中,都出现了大量的江城山水描写与巴渝意象,如《旷野的呼喊》《长安寺》《莲花池》等,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则在于萧红的生命场域发生了彻底改变。
山城风物在萧红1938年之后的作品中大量出现,而这一时期也是其创作日趋成熟,呈现出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萧红之美的关键期。综观萧红的创作道路,1938年来到重庆后的转变是明显的。这种转变是前期思想情感的自然发展,更是变动中战争的影响和个人对流寓经验的反省体验。
二、客寓巴渝——江畔山城中的流浪人
萧红1938年以后的作品中出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即不论是在小说还是散文中,都将重庆这座城市作为了描写对象。
重庆独特的山水地域环境,塑造了其别具一格的民俗民风。自然地理环境塑造了重庆粗粝朴拙,坚韧强悍的人文风格,地处长江水路要道赋予了重庆有别于上海等沿海码头城市的码头文化。重庆的码头文化是带有三峡地域特色平民市井文化,码头文化不仅是江湖气味浓重的豪侠气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多元化的融合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多重文化元素沉淀汇集,帮助城市形成自己的文化特征。
20世纪40年代文学重心由北京、上海转入重庆,带来重庆文学的繁荣,而重庆气质刚健活泼的码头文化,也影响了当时的文学;这种影响体现在萧红的作品中,则在于《山下》《长安寺》《滑竿》等作品对于巴山渝水中的风土人情的描绘。萧红散文《滑竿》描写了“滑竿”这一带有明显巴渝地区特色的物件以及以抬轿子为生的轿夫们的形象:“下坡路,他们的腿,轻捷得连他们自己也不能够止住,蹒跚地他们控制了这狭小的山路。他们的血液骄傲的跳动着,好像他们停止了呼吸,只听到草鞋触着石级的声音。在山涧中,在流泉中,在烟雾中,在凄惨的飞着细雨的斜坡上,他们喊着:左手!……”山城的多雾及道路的错杂崎岖跃然纸上。同时,《滑竿》一文的几组对话中还出现了“晓得”、“啥子”等川渝地区特有的方言词语。
长安寺是解放前重庆最大的寺庙,萧红在《长安寺》中细致地描绘了这座巴渝地区寺庙的风貌,文中冲茶卖的老头言行举止均体现出重庆人特有的活泼而俚俗的闲散气质:
“他总是高高兴兴的。走路时喜欢把身子向两边摆着,好像他故意把重心一会放在左腿上,一会放在右腿上。每当他掀起茶盅的盖子时,他的话就来了,一串一串的,他说:‘我们这四川没有啥好的,若不是打日本,先生们请也请不到这地方。”富于山城地理特点的景物风貌以及山区清新的民风,与萧红前期作品中寒冷豪阔的东北风物及粗犷凶悍的东北人性格形成了鲜明对比。
抗日全面爆发后,大量来自日寇占领区的人涌入重庆,重庆人习惯把这些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称为“下江人”,称自己为“上江人”。随着大量“下江人”涌入重庆,“下江人”成为了当时获得广泛认同且有明显文化特征的社会群体。“下江人”所带来的现代文化与本土的码头文化相互交流融汇,成为重庆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萧红在创作中深入思考了两种人群之间的隔阂和冲突、融合与理解。《山下》以细腻笔触勾画小女孩“林姑娘”在下江人家里帮佣时的心理成长过程,进而折射出下江人对本地人所造成的文化冲击。在去下江人家里做工之前,林姑娘家尽管生活艰难,但也怡然自得,但林姑娘和她母亲原本闲适、宁静的生活因为下江人的到来而改变了。满载着下江人的汽船,不仅带来了下江人的财富和货物,还带来了他们的文化和社会习俗,预示着下江人文化的介入将给重庆当地人的文化造成冲击。
下江人刚到重庆时,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同和欢迎。林姑娘看到洋船来了,“她拍着手,她的微笑是甜蜜。”邻居们看到洋船来了就感叹地说,“‘这就是下江人哪……,站在江边上的,无管谁,若一看到汽船来,就都一边指着一边儿喊着。”重庆本地人眼里的下江人虽是避难到重庆,但是阔气,吃得好,穿得好,钱多,他们因而也深感与“下江人”不属一个阶层,地域的差异以及经济地位的差别使得二者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不一致。林姑娘因为羡慕下江人富有,去下江人家里做工。林姑娘很珍惜这次机会,但终因工资协商无果被辞退。林姑娘的心理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被辞退之前,她對于工作永远那么热情,永远没有厌倦。……病后她完全像个大姑娘了,寂寞地去,寂寞地来,对周围的事物失去了先前的关注和好奇。”林姑娘的变化体现了在不同文化冲击下的精神状态的改变。当她知道王丫头被下江人重用,代替了她的位置以后,她脸色苍白地、凄清地、郁郁不乐地在她妈妈的旁边沉默地坐到半夜,这是文化之间的碰撞给人心灵带来影响的体现。
下江人与重庆当地人之间关系发展过程显然是一个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磨合与冲突的过程。对于两种不同文化,作者的态度并没有明显倾向于任何一方,作者既描写了下江人到重庆之前当地人安逸的生活状态,也叙述了下江人到重庆避难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者并没有把下江人塑造成“入侵者”的形象,而是以自己眼光给予关照。下江人给林姑娘送饭菜,找金鸡纳霜帮林姑娘治病,林婆婆却将这些误认为是软弱可欺,跟下江人讨价还价最后激化了矛盾。下江人和林婆婆家的矛盾,究其原因在于文化的不同,这是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冲击和磨合的表现。不同区域文化与文学的冲突、碰撞、融合成为区域文化与文学的必经之路。透过陪都重庆这一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的窗口,可以看出其主流性与代表性,显现出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主导性发展。
三、结语
地域文化特征对于萧红创作的影响是显著的,从环境与人物描写来看,萧红前期的作品几乎都与故乡有关;而1938年旅居重庆,重庆的风俗景观和社会现象给予她新的感受,战时重庆的形象也在她的挣扎和思考中得以凸现,使得这一时期萧红的创作显示出与前期不同的特征。萧红始终将生命体验融入创作之中,关注个体生命和心灵,萧红对于山城风物、人事的书写不仅构成了抗战文学中的重庆形象的一个侧面,也是对抗战文学的一种丰富。
参考文献:
[1]萧红.萧红文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2]季红真.萧红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3]葛浩文.萧红评传[M].北京: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