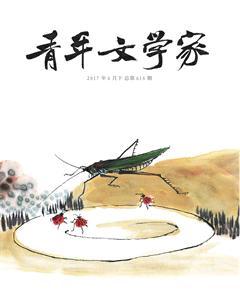从“孝”与“情”的两难看高觉新的悲剧命运
摘 要:高觉新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著名人物形象,高觉新处在时代动荡的风口浪尖和思想的更迭之处,但他却显得与新风潮格格不入,在陷于“孝”与“情”冲突的境地时,他的选择始终体现着“孝”字当头的古老准则,他的悲剧命运带有自觉地“引颈受戮”的意味。“孝”源于儒家文化中的“忠孝思想”,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遭受了“人道主义”的冲击。孝在情先,孝情矛盾,即理智与情感的分裂,成为了高觉新命运悲剧性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儒家文化;孝道;爱情;高觉新;悲剧
作者简介:李思雨(1994-),女,汉族,山东滨州人,烟台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6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8-0-02
一、儒家孝道的“卫道士”
高觉新是一个积极维护封建孝道和封建父权的典型代表,可以说他是儒家孝道的“卫道士”。儒家学说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孝是儒家精神的根本性观念,它首先呈现了父慈子爱式的天然感情。”[1][P94]
“家”在高觉新的心里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产生这种观念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古代。在中国文化中,“家族”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且男性在家族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一个集“孝顺的儿子、可敬可亲的兄长、标准的丈夫、慈爱的父亲和一个有责任心的国民”[2][P13]于一身的治家能手,是大多数男性的人生追求。尤其是长子,对于中国的传统式家庭更是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嫡长子继承制”中长子既是“臣”又是“子”,父辈的旨意与权威,不仅意味着正确,更意味着子辈的绝对服从,尤其是长子更应该对孝道这一准则俯首躬身地实践。作为长子,在古代意味着一种荣誉,而在现代,尤其是进行反封建斗争的五四时期,再以此准则要求一个青年人,更多的則是一种悲哀。“长子作为孕育于中国伦理型传统文化和宗法家庭制度这一特殊环境中的文学形象,不仅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而且作为世界上普遍出现、永久存在于人类之中的双重人格的文学概括和形象表现,也是迄今为止世界文学中较为突出的。”[3][P25]高觉新就是高家在这一房的长子,也是长房的长孙,长子这种为人臣、为人子的角色意识,是促使他自觉接受“忠孝思想”的内在动力,也是他面临高家这样的封建大家庭选择“臣服”的根源。
笔者认为,巴金对“孝道”的批判有其时代意义和一定的正确性,因为“孝道”对中国国民性的影响的确有消极的一面,但抛却封建愚昧等因素,“孝”本身具有一定的伦理价值,尊敬长辈在现代社会依然是值得弘扬和提倡的优良品德。
二、新旧冲突的“矛盾体”
进入现当代社会以后,中国文化遭受到了西方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这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以及观念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决定第二个十年文学基本面貌的,是革命文学思潮及其文学创作和人文主义美学思潮及其文学创作。这两股文学潮流中,人文主义文学思潮是传承了五四文学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人的文学”的潮流,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新兴的。[4][P130]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要“使读者得到旧社会的认识及新社会的预图”,[4][P131]这其中,“旧社会的认识”就包括对封建传统伦理中“孝道”的认识。高觉新名为“觉新”可他却是三兄弟中最固守陈规的一个。
新思想想要冲破封建观念的阻塞涌入中国的大门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的,毕竟中国的封建社会存在了长达两千多年之久,新的观念和思想是通过各种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国民的。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中国文化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有论者认为“孝的观念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和基石”,在这个时期,孝的观念这个基石也开始动摇了。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文化中的糟粕部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和以往的历次变革不同,新一代知识精英开始把思想启蒙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他们相信只有国民精神的解放才会有社会的革新进化。而当务之急,要在传统文化的劣根上动手术,打破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专制主义文化的束缚。”[5][P4]这是钱理群指出的五四文化新文化运动的本质特征。高觉新并不完全独立于新文化运动之外,相反“报纸上如火如荼的记载唤醒了他被忘却了的青春。他和他的两个兄弟一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转载的北京消息”,他折服于“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议的文句”带着的那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他对新思想是信服的,由此见得他绝对不是冥顽不化、有意害人之人,他的很多想法是“新”的,比如,他对弟妹们有的只是长兄如父般的疼爱,并没有用礼教等封建思想刻意压制与管束他们,无论自己怎样痛苦不堪,也会作为哥哥融入他们的集体。但是他无奈,他逃不脱扎根在内心深处的孝道的规约。作为长子,不仅在新的思想观念的冲击下丢失了传统家庭长子的威严形象,还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很多时候面对长辈和旧的观念他不仅是不能反抗,还是不敢反抗,更悲哀的是不想反抗。他靠着新的理论继续过旧的生活,而他“自己并不觉得矛盾”。高觉新是一个新与旧、“孝”与“情”的“矛盾体”。
三、“引颈受戮”的长子
高觉新的一生都在他信奉的“理智”和真实情感中挣扎。他的爱情悲剧带有自己心甘情愿“引颈受戮”的意味,这就决定了他的一生都将与痛苦相伴。
“高觉新是新文化运动刚刚爆发的年代里中国封建式大家族中的长子代表。”他自幼生长于、受益于封建礼教。他读的书是宣扬仁义孝道的封建传统文化的经典,在学校里他接受的却是比较先进的思想,他也有“才子佳人”的梦想,但他却在父亲的一个安排下顺从地、彻底地、温顺地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毫不抵抗的打破了自己美好的“幻梦”。胸腔中培育的“情”的种子,在刚刚萌芽、尚且嫩绿的阶段,被他自己生生掰断了。
觉新崇尚的“作揖主义”和“不抵抗”主义,换句话说,是一种对不合理的规则与命运的“隐忍”,反映了他面对权威时的软弱和面对封建礼教造成的压力时内心的恐惧。这软弱和恐惧,致使他对家中长辈的话唯唯诺诺,唯命是从;致使他在躬行孝道的过程中,他能够忍受任何痛苦、做出任何牺牲,积极维护着封建父权和封建孝道;致使他在“孝”与“情”的两难选择面前没有勇气抵抗前者而去抓住后者。在《家》中,觉新在封建礼教和孝道影响下的“软弱”体现在很多方面:
首先,父亲安排他的婚事时,他明明心中有了所爱的人,却“不说一句反抗的话,而且也没有反抗的思想。他只是点头表示愿意顺从父亲的话。”其次,觉新面对父亲和其他长辈对他的安排,无条件服从与接受,无论自己觉得有多么不合理、讲不通,或者在他的眼里长辈的做法有多么愚昧无知,觉新全部照单全收。这种软弱的顺从,给他人和觉新自己的心灵都造成了巨大的、无法弥补的伤痛,同时这种软弱的顺从也是高觉新从“受害者”向父权代理者转换的桥梁,可以说很大程度上觉新已经成了“害人者”。最后,觉新之所以能够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下去,还因为他拥有一种特殊的本领,那就是对一切痛苦感到麻木,为自己的一切牺牲找到价值,在自我麻痹中寻求安慰。在这种麻木之中,觉新渐渐把尊重长辈、孝敬长辈、遵从长辈的意愿看作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
总的来说,觉新的种种软弱是“孝道文化”隐喻的家族本位意识造成的,它导致了觉新受虐的主动性。而软弱又是觉新命运悲剧的主观原因,因此可以说觉新思想中的“孝道文化”的痼疾枯萎了觉新的青春和生命之树。然而觉新一再隐忍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呢?“隐忍”给他带来的只有满肚的委屈、一再的牺牲和无休止的哭泣。
觉新在孝与情的冲突中选择了“引颈受戮”,心甘情愿的跳入封建“孝道”的火坑,远远观望充满幸福与甜蜜的爱情的花海。当他想费尽心力爬出火坑时,火苗已然将“花海”变为“火海”。这火烧尽了这位不幸的男性对“情”的希望,也葬身了挣扎在其中的薄命红颜。毁灭了伟大的、有价值的东西,这不是悲剧,还能是什么?
参考文献:
[1]任现品.略论儒家文化的感恩意识[J].孔子研究.2005.
[2]崔国军.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中国现当代小说长子形象悲剧性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9.
[3]谢伟民.徊排于两种文化冲突之间——中国现代文学长子形象简析[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
[4]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5]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