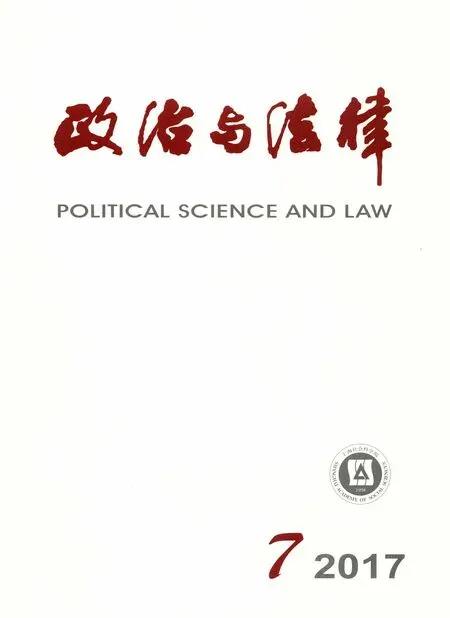我国《民法总则》的颁行 与民法典合同编的编订*
——从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看我国《合同法》相关规则的完善
石佳友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我国《民法总则》的颁行 与民法典合同编的编订*
——从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看我国《合同法》相关规则的完善
石佳友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法律行为制度是民法典总则编的关键内容之一;法律行为制度源自合同法,其规则也主要适用于合同法。民法典总则编中关于法律行为的内容对于分则中的合同编规则有着重要的影响。2017年颁行的我国《民法总则》中“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容相对于1986年颁行的我国《民法通则》中的相应内容来说,无论是在量上还是在质上均有了重大的改变。这些创新主要包括:完善了沉默适用、意思表示解释的有关规则,增加了虚假表示和隐藏行为的规定,以显失公平吸收了乘人之危,增加了第三人欺诈和第三人胁迫的规定并对二者采取了区别规定;取消了合同的变更权,增加了重大误解撤销权行使期限的规定;对合同无效的判断标准采取了新的措辞。这些修订的绝大部分内容,一方面来源于对1999年颁布的我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合理内容的总结与吸收;另一方面也源自对比较法经验的分析与归纳。这些内容都体现出立法质量的明显改善,在避免与总则冲突和简单重复的前提下,其中的部分内容应当为民法典合同编所体现。当然,我国《民法总则》关于民事法律行为部分的少部分增补,反映了中国立法者的一些独特立法政策考虑,从契约公平或契约效率的角度来看不无争议;其适用效果有待于未来的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民法总则;法律行为;合同法;意思表示;合同无效
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这也是落实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编纂民法典”这一重大战略部署的第一个步骤和成果。《民法总则》将作为未来中国民法典的开篇,统帅整个法典的分则。所谓“纲举目张”,在我国民法典中,《民法总则》就是这样的“纲”,总领民法典各个不同的“目”(分编)。因此,《民法总则》对于民法典分则部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逻辑一致性的角度来说,分则应当与总则保持逻辑一致,避免体系内的矛盾。为此,“需要妥当处理合同编与民法总则之间的关系,尽量消除二者之间的冲突”。*王利明:《民法分则合同编立法研究》,《中国法学》2017年第2期。当然,民法典分则部分可以对《民法总则》进行进一步的细化、明确和补充;这也正是民法典合同编的编订过程中所要遵循的基本工作方法。《民法总则》第六章“民事法律行为”部分与此前的我国《民法通则》和我国《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相比有不少的改动。民法典合同编相关内容的编订,必须与总则的这些创新保持一致;在避免冲突和简单重复的前提下,分则条文应尽量吸收和反映总则中的这些创新内容。
一、关于意思表示及合意瑕疵
《民法总则》对于意思表示及合意瑕疵方面的规则相对于我国《民法通则》、我国《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相应规定而言进行了比较多的修改、创新和细化,总体来说,这些修改有利于司法实践的操作。
1.关于沉默的意思表示
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66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按照这一规定,“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被视为意思表示。
1999年我国《合同法》第22条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这里,以行为作出承诺必须符合交易习惯或者要约本身有此类规定。然而,这一关于交易习惯的规定仍然存在不周延之处,交易习惯可能只是一般人之间的习惯,特定的合同当事人可能并不知晓或者并不认同。
正因为如此,《民法总则》第140条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这里,将沉默可以被视为意思表示的情形限定于以下三种: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该条明确规定,交易习惯必须为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并非一般的行业交易习惯;这一规定相对于我国《合同法》第22条而言更为严谨。
2.关于意思表示的解释
《民法总则》第142条第1款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与我国《合同法》第125条关于合同的解释的规定相比,其增加了“行为的性质”这一重要的参考指标。合同的解释仍然立足于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也就是双方所共有的缔约目的。为此,确有必要参考合同的性质,譬如,合同的有偿与无偿对于正确理解合同某些条款的关键含义来说意义重大。《民法总则》将“行为的性质”列为解释意思表示含义的一项重要参考因素,显然是有道理的。总体上,《民法总则》仍然沿袭了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强调合同解释的目的在于探求当事人的真意;在此前提下,《民法总则》强调了依据合同词句和条款、行为性质和目的、习惯和诚实信用原则等客观主义的参考要素。按照传统理论,意思主义(主观主义)主张以表意人的主观意思为解释的基准,表示主义(客观主义)主张以受领人对表示的客观理解为解释的基准。*叶金强:《合同解释理论的一元模式》,《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2期。从我国《民法总则》的这一规定来看,可以认为我国立法者采取了一种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的折中立场。
《民法总则》第142条第2款的规定同样值得注意,其内容为:“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不能完全拘泥于所使用的词句,而应当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行为人的真实意思。”该款针对的是单方法律行为,“不能完全拘泥于所使用的词句”的措辞表明,对于单方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更偏向意思主义的立场。从域外的经验来看,经2016年法国债法改革法令修订后的《法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新《法国民法典》)第1188条规定:“合同解释应根据当事人的共同意图,而不应拘泥于合同文本的字面意思。如当事人的意图无法探求,则合同应根据一个合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下所理解的含义进行。”*Ordonnance n° 2016-131 du 10 février 2016 portant réforme du droit des contrats, du régime général et de la preuve des obligations, JORF n°0035 du 11 février 2016. 笔者于本文中引用的新《法国民法典》条文均出自此法令。显然,对于这一问题法国法是以主观主义为主、客观主义为辅。《德国民法典》第133条规定:“解释意思表示应探求其真意,不得拘泥于词句的字面意义。”*陈卫佐译:《德国民法典(第4版)》,法律出版社,第48页。笔者于本文中引用的《德国民法典》的条文均出自该书。该法典第157条规定:“解释合同应按照诚实信用的原则及一般交易上的习惯解释。”可见,《德国民法典》对于这一问题采取的也是主观主义为主、客观主义为辅的立场。《民法总则》第142条第2款采取的是意思主义的立场,其合理性在于单方行为中没有相对人,不存在相对人的信赖保护问题,因此,在意思表示的解释上,应当比双方行为在更大程度上尊重表意人的真实意思。如果未来我国民法典分则部分不设置债法总则,合同编将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具备债法总则的功能。*同前注①,王利明文。在此情况下,合同编将要对单方行为(如悬赏广告)等其他债的渊源形式做出规定。如果是这样,则应遵照该款在合同编中规定单方行为的解释。
3.虚假表示与隐藏行为
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和我国《合同法》第52条均将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作为认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理由。“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一表述并不严谨。通说认为,这一规定是受到比较法上通谋虚假表示制度的启发。譬如,《德国民法典》第117条第1款规定:“对相对人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如果系通谋所作出的虚伪表示,则无效”。《日本民法典》第94条第1款规定:“与相对人通谋而为虚伪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无效。”然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与“通谋虚假表示”显然存在差别,一方面,“通谋虚假表示”适用范围更广,既可能是出于非法目的,也可能是出于合法目的;另一方面,“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中“非法目的”这一措词留给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余地,容易引发争议。此外,这一立法表述并不准确,“目的”是行为发起的主观因素,其本身并无外观形态,没有掩盖的必要,真正需要掩盖的只能是反映或实现特定目的的具体行为。正因为如此,《民法总则》第146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由此,“虚假意思表示”将涵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并且其包容性更强,包括了其他通谋虚假表示的情形。此外,该条还对隐藏行为的效力进行了规定,即表面的虚假行为无效,并不必然导致被隐藏的行为无效,后者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如果被隐藏的是合法行为(譬如名为买卖实为赠与),只要标的物合法,则被隐藏的行为有效。反之,如果被隐藏的行为违法,则无效。这是借鉴了《德国民法典》第117条第2款,即“另一法律行为被虚伪行为所隐藏的,适用关于被隐藏的法律行为的规定”。
关于隐藏行为,新《法国民法典》第1202条规定得更为具体:“若当事人定了一份表面合同用以隐藏一份隐匿合同,该隐匿合同也被称为密约,仅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其不得对抗第三人;但是第三人得主张之。”该条包含多层意思。第一,密约(阴合同),必须合法才能有效。该法典第1203条规定了密约在一些情况下无效,而且表面合同(阳合同)也无效,譬如合同的目的是为了隐瞒不动产、营业资产或者客户资源、租赁权转让价款等。第二,密约仅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不能对抗第三人。由于合同的相对性,合同只能约束双方当事人。另外,作为被隐藏的行为,其效力并不当然无效。对此,法国法与德国法和我国民法是一致的。第三,具有特色的是,该条规定,密约不能对抗第三人,但第三人可以依据密约主张自己的权利,其前提是第三人知晓其存在。在一些情况下,第三人可能主张表面合同。譬如,对于亲属之间发生的、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合同,受让人的债权人可以援引买卖合同,主张受让人是由于买卖合同而获得了一项财产,从而避免由于遗产归扣规则的适用导致受赠财产要回归到整体遗产的范围之中。不过,反过来,对于享有法定特留分的其他继承人来说,他们显然愿意主张赠与密约的存在,要求对受赠财产适用遗产归扣规则,对受赠人的继承份额做相应的扣减。同时,赠与人的债权人也可以援引赠与的存在而行使撤销权。*Muriel Fabre-Magnan, Droit des obligations, 1-Contrat et engagement unilateral, 4e edition, PUF, 2016, p.592.法国法关于隐藏行为对第三人效力的新规定,确实更为细致,值得关注。
4.关于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的合并
《民法总则》第151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这是对我国《合同法》的相关条款进行的发展。我国《合同法》第54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此条源于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后者将重大误解与显示公平并列为可变更或者可撤销合同的事由。
与我国《民法通则》与我国《合同法》的上述条款相比,《民法总则》的这一修订长处明显。
第一,将重大误解与显失公平进行分拆,二者分别在《民法总则》第147条和第151条加以规定。这一体例更为科学。尽管重大误解与显失公平都导致合意存在瑕疵,但是重大误解往往是由于误认者基于对现实情况的错误认知所得出的错误判断(但误解者并不一定对此存在过错);显失公平则多由于一方滥用了对方的某种特殊状态,譬如缺乏经验与判断力、对自己的特殊依赖关系、穷迫等。就此而言,显失公平与胁迫(而非重大误解)更为接近。新《法国民法典》将胁迫与利用依赖状态而获取明显不公平利益的情况,规定在同一个条文即第1143条中,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Christophe Lachièze, Droit des contrats, 4e édition, Ellipses, 2016, p.116.
第二,就《民法总则》第151条关于显示公平的规定而言,该条吸收了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我国《合同法》第54条规定的“乘人之危”。“民通意见”第70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利益的,可以认定为乘人之危。”“民通意见”第72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可见,乘人之危的规范重在强调利用对方处于危难之机,而显示公平则强调利用优势或对方缺乏经验;只是二者的后果都是双方利益的严重失衡,双方的权利义务出现严重的不对等。
《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第2款规定:“某人利用他人处于急迫情势、缺乏经验、欠缺判断能力或心神耗弱,以法律行为使得该人就某项给付向自己或第三人约定,或给予与该项给付明显不相当的财产利益的,该法律行为无效。”此条是所谓“暴利”条款。有学者认为,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实际上将德国法上的暴利行为一分为二:以客观要件为基础,确立了显失公平规则;以主观要件为基础,确立了乘人之危规则”。*冉克平:《显失公平与乘人之危的现实困境与立法重构》,《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5期。这种做法的后果,是在构成要件和适用范围上可能出现重叠或竞合。正是为了避免这一混乱,《民法总则》第151条对二者进行了合并,以显失公平吸收了乘人之危,将乘人之危作为一种手段,与其他手段并列,其所导致的后果是“法律行为成立时显示公平”。这一做法理顺了二者的关系,显然在逻辑上更为周延。
第三,在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方面,《民法总则》吸收了司法解释的经验。“民通意见”第70条是关于“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的规定,“民通意见”第72是关于“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的规定。在这些规定的基础上,《民法总则》第151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可构成显失公平。并且,“危困状态”和“缺乏判断能力”较之于司法解释的措辞更为严谨,“危困”比“危难”的外延要广泛,因为“危困”还包括其他的困境、困难和急迫需要。“缺乏判断能力”较之于“没有经验”也更严谨:因为“没有经验”并不必然导致当事人缺乏判断能力,从而签订显失公平的合同;“缺乏判断能力”则很容易导致当事人轻信和接受对方当事人的缔约条件。
《民法总则》第151条中“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措辞,也更接近域外法上的“经济暴力”。在法国,“经济暴力”(violence économique)制度系由判例所创立,根据法国最高法院在判例中的解释,经济暴力是“对一方经济依赖性的过分滥用,受害人由于担忧其合法利益受到威胁而产生恐惧因而接受,使得行为人获取利益”。这种情况下,合意具有瑕疵。*Cour de Cassation, 1ère Chambre civile, arrêt du 3 avril 2002.基于判例的经验,新《法国民法典》第1143条规定:“如果合同一方当事人通过滥用对方所处的依赖状态,迫使对方承受在没有强迫状态下本来不会接受的债务约束,从而使自己从中获取明显过分的利益,则此种情况同样视为胁迫。”该法的立法说明中明确提到,该条针对滥用依赖地位的一切“经济暴力”。*François Terré, La réforme du droit des obligations, Dalloz, 2016, p.23.根据学者的解释,新法上的滥用“依赖状态(état de dépendance)”,典型者如经济上具有依赖性的合同关系,譬如特许经营合同、分包合同、独家代理合同、独家供货合同等。在判断一方是否滥用对方对其的“依赖状态”时,一个重要的标准是要看是否能找到替代措施,是否能找到其他客户、其他供应商;是否能找到替代措施的评估,一般从客观角度判断;在某些情况下,法院也可以结合受害人的具体情况,从主观角度进行判断。新《法国民法典》所采用的“依赖状态”的措辞表明,如果没有相对人滥用受害人的依赖状态,受害人本不会订立合同;但相对人并不一定是导致这种依赖状态存在的人。*值得注意的是,最初法国债法改革法令的草案曾写入一方处于“脆弱状态(faiblesse)”的措辞,但最后被删除,因为立法者认为“依赖状态”的要求更为严格,譬如精神或宗教上的依赖关系导致受害人难以独立做出判断。另外,该草案中原有的“急迫(nécessité)”的措辞也被立法者删除,因为这一语词被认为过分含糊;实践中,大量的合同都是因为有急迫需要而订立的。Olivier Deshayes, Thomas Genicon & Yves-Marie Laithier, Réforme du droit des contrats, du régime général et de la preuve des obligations, Commentair article par article, op.cit., p.224.《民法总则》第151条规定的“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与新《法国民法典》第1143条所规定的“滥用依赖状态”,在含义上已经比较接近;二者的功能都在于打击所谓的“经济暴力”现象,维系契约公平。
第四,在认定和判断显失公平的时间标准上,《民法总则》第151条明确为“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这就是说,判断合同约定是否构成显失公平,应当置于合同缔结之时的情境中检视,而不应从合同履行后或者争议发生时的情况来衡量。这一规定的合理性在于:只有在合同成立时存在显失公平,才能说明合意的瑕疵自始即存在,因此,当事人可以主张撤销合同,溯及既往地消灭交易,视该交易为从来未曾发生过;而如果显失公平是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才发生的,当其非由于当事人的原因所致,则应主张适用情势变更,请求法官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而非是溯及既往地撤销合同。
二、关于第三人欺诈与胁迫的问题
关于第三人的欺诈与胁迫,域外法上有较多的经验。传统大陆法对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都采取不同的处理模式。尽管人们经常将欺诈与胁迫相提并论,二者之间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在罗马法上,欺诈之诉具有对人性特点,只针对诈欺者提出;而胁迫诉讼具有对物性特点,受胁迫而失去物品的人可针对该物品的任何占有人提起诉讼。在当代法上,立法者“通常认为, 相对于欺诈, 胁迫对受害人私人自治的侵犯更加严重。胁迫的受害人在被胁迫之下做出的意思表示, 根本不能归于他自主自愿的选择。而欺诈的受害人之所以会受到欺诈, 往往是过于轻信对方的说辞或者是贪图对方虚构出来的好处, 因此可以认为受欺诈人存在某种意义上的过失或过于轻信。这些差别导致法律对受胁迫人提供的保护更加周全, 而对受欺诈人提供的保护相对有限。另外, 从立法政策的角度看, 胁迫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更大, 也应该受到更严厉的制裁。*薛军:《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法学研究》2011年第1期。。由此,尽管欺诈与胁迫之间的差别更多是程度的而非是本质的,但是,一旦发生胁迫,“交易安全应当让位与契约正义”。*Ga⊇l Chapentepie & Mathias Latina, La réforme du droit des obligations , commentaire théorique et pratique dans l’ordre du Code civil, Dalloz, 2016, p.273.
对于第三人欺诈与胁迫,《德国民法典》是区分模式的典型立法,该法典第123条第2款规定:“如欺诈系第三方所为,则仅有在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欺诈时,表意人方可撤销其意思表示。”显然,在德国法上,对于第三人欺诈,仅在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的情况下,表意人方可撤销其意思表示;对于第三人胁迫,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要存在胁迫,无论是来自相对人还是来自第三人,表意人均可撤销其意思表示。这就是所谓区分模式,即在法律规定上对欺诈与胁迫进行区别对待。具体说来,在欺诈的情况下,如果相对人是善意的,不知也不应当知道欺诈的存在,则其合理信赖应当受到保护,表意人不得撤销其意思表示;就胁迫而言,由于是对表意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大威胁,只要存在胁迫,无论来自相对人还是来自第三人,表意人均可撤销其意思表示,此时不再考虑相对人是否为善意。因为,“在受害者与产生合理信赖的第三人之间,更为重要的应该是保护前者”。*Olivier Deshayes, Thomas Genicon & Yves-Marie Laithier, Réforme du droit des contrats, du régime général et de la preuve des obligations, Commentair article par article, LexisNexis, 2016, p.208.
新《法国民法典》也采取了这种区分模式。该法典第1138条第1款规定:“欺诈可由下列人所为:代理人、事务管理人、一方的雇员或担保人。”该条第2款规定:“欺诈还可以源自于有默契关系的任何第三人。”对于实施欺诈的第三人,该条第1款所列举的情形,均证实二者之间存在利益关联;而该条第2款上“默契(connivence)”的含义则更为广泛,这意味着并不需要相对人与第三人明示的合谋,立法者刻意避免了“通谋(complicité)”的措辞,以免给法官的认定形成过于严苛的负担而限制其适用范围。反过来,相对人对于欺诈事实的知情,足以认定“默契”的成立;如果相对人知道由于第三人欺诈了表意人,后者才与自己订立合同,这种情况下,相对人对于第三人实施诈欺的事实故意隐瞒,其实也可能符合新《法国民法典》第1137条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欺诈的适用条件。新《法国民法典》第1138条第2款实际上类似于“兜底条款”,避免该条第1款的列举挂一漏万。总之,在第三人欺诈的情况下,如果相对人对欺诈之事实并不知情,而且他对此不知情也不存在过失,那么他有理由主张其对表意人的意思表示产生了合理信赖,此种合理信赖应当予以保护。反之,如果相对人存在过失(譬如,对其引入的第三人的选任、监督方面存在疏忽),那么,相对人就不能对表意人主张的意思表示其具有合理信赖。
关于第三人胁迫,新《法国民法典》第1142条规定:“胁迫无论系合同当事人所为或第三方所为,均构成相对无效之理由。”这与对第三人欺诈的处理方法显然不同。在第三人欺诈的情况下,原则上应保护相对人的信赖,不能允许表意人撤销其意思表示,除非相对人存在过失;而在第三人胁迫的情况下,无论相对人是否有过失,表意人均可撤销其意思表示,相对人的信赖不能受到保护。*Olivier Deshayes, Thomas Genicon & Yves-Marie Laithier, ibid., p.217.这一区分模式源自法国以前的司法传统,在上世纪20年代曾受到著名法学家Louis Josserand的激烈批评,他认为这种区分并没有正当性。*Louis Josserand, Les mobiles dans les actes juridiques du droit privé, Dalloz, 1928, p.122 et s.当代法国立法机构仍维持这种传统的区分模式:第三人欺诈原则上不允许受害人撤销合同,除非相对人有过错;第三人胁迫应允许撤销合同,无论相对人是否有过错。
与区分模式相对的是所谓统一模式,即在法律规定上对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采取统一的处理方式。譬如,《欧洲合同法原则(PECL)》(2002年版本)第4:111条规定:“(一)在一方当事人对第三人的行为负责之场合,或者经一方当事人同意该第三人介入了合同的缔结,如果该第三人 1.因给出信息而造成了错误,或者知道或本应知道某一错误,2.给出了不正确的信息, 3.犯有欺诈, 4.进行了胁迫,或 5.获取过分的利益或不公平的好处, 则受害人在与恰如该方当事人自己的行为或知晓相同的条件下,可以获取本章中的救济。(二)在其他第三人从事下列行为场合:1.给出了不正确的信息,2.犯有欺诈, 3.进行了胁迫,或 4.获取了过分的利益或不公平的好处,如果该方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相关的事实,或者在合同宣告无效时尚未因信赖该合同而行事,则受害人可以获取本章的救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2010年版本)第3.2.8条也有类似规定:“(1)如果欺诈、胁迫、重大失衡或一方当事人的错误可归因于某第三人,或者该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这些情况,而该第三人的行为由另一方当事人负责,则可按照如同该另一方当事人本身之行为或知悉的相同条件,宣告该合同无效;(2)如果欺诈、胁迫或重大失衡可归因于第三人,而该第三人不由另一方当事人负责,若该另一方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此欺诈、胁迫或重大失衡,或在宣告合同无效时尚未信赖该合同而合理行事,则该合同可被宣告无效。”可以看出,这两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示范法版本采取的都是如下的模式:其一,第三人的行为由一方当事人负责的情形下,第三人的行为均归因于该合同当事人,不论其是否对第三人的行为知情;其二,在第三人行为不由合同一方当事人负责的情形,只有在该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第三人的行为时,受害人方可主张宣告合同无效。当然,一个例外的规则是:如果合同当事人虽然不知情,但在宣告合同无效时尚未信赖该合同而合理行事,没有合理依赖可言,则受害人亦可主张宣告合同无效;“这一例外的合理之处在于,在这种情形下另一方当事人不需要保护”。*张玉卿主编:《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0》,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第271页。总之,在统一模式下,如果第三人的行为不由合同当事人负责,则仅在该方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第三人行为的情况下,受害人方可主张撤销合同。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细究域外法上的各种模式之后,《民法总则》的制定者仍采取区分模式,其第149条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这里,立法要求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受害人方可主张撤销合同。其第150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这就是说,在第三人胁迫的情况下,无论合同相对人是否知情,受害人均可主张撤销合同。应当说,这一立场是有道理的,与新《法国民法典》代表的最新立法趋势相符。
三、关于撤销权的行使
《民法总则》上法律行为的撤销制度的改变,主要表现为“变更权”的取消和撤销权时效制度的改革。
1.取消合同的“变更权”
《民法总则》第136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自此,在我国法上,变更合同与解除合同一样,须依照法律规定或经对方当事人同意。
此前的相关规定并非如此。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对于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受害的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合同。我国《合同法》第54条在这两种情形之外,又增加了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受损害方均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民通意见”第73条规定:“对于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变更;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变更或者撤销。”可见,在符合上述意思表示瑕疵的情形下,如果受害方请求变更合同,法院必须予以变更;而如果其请求撤销合同,法院可以自由裁量,决定是变更还是撤销合同。赋予合同一方当事人单方请求变更合同的形成权的原因,可能在于尽可能维持交易,以较低的成本将合同的瑕疵消除,将其“转化”为一个无瑕疵的合同,从而避免通过撤销合同来消灭交易。
然而,合同变更在性质上是成立了一个新的合同。在法律上,情势变更是法定的变更事由,因为情势变更是在合同履行后终止前发生了非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客观原因,基于维系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由法官来裁定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重新安排。就缔约阶段的意思表示瑕疵而言,由于意思表示存在重大瑕疵导致双方的合意欠缺,合同本来就不成立。因此,如果受害人主张撤销合同,法院应准予撤销。但是,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受害人主张变更合同,实际上是单方发出了一个新的要约,是否接受此项要约而成立新合同,应属于对方当事人的权利。“变更权”实际上等于赋予了该方以单方变更合同的权利,对方只有接受新要约的义务,这显然违背意思自治原则。*尹田:《〈民法总则(草案)〉 中法律行为制度的创新点之评价》。在受害方仅申请撤销合同的情况下,允许法院通过自由裁量来变更合同,则更是离谱,“这就意味着, 当事人的形成意思在此等诉讼中并非决定性的,法院完全可以主动积极地通过变更等方式形成新的法律关系”,这显然是法院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不当干预。*徐涤宇:《论法律行为变更权的期间限制——基于解释论的立场》,《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由此可见,《民法总则》取消“变更权”,无疑是一个进步,更加符合私法自治的要求,防止了对当事人意志的过度干预。
2.撤销权之时效期间的规定
《民法总则》第1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较之于此前的相应立法,该条包含了一些不可忽视的变化。
“民通意见”第73条规定,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者撤销的,法院不予保护。在此基础上,我国《合同法》第5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该法第75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
与上述条文相比,《民法总则》第152条有以下变化。第一,对于胁迫,明确其除斥期间为自胁迫期间终止之日起计算。此规定显得更为公平,因为法谚有云:“时效于无法行动者不得经过(Contra non valentem agree non currit praescriptio)。”这一条文也与比较法的一般经验相吻合。例如,新《法国民法典》第1144条规定:“撤销之诉的期间,在错误或欺诈的情况下,自错误或欺诈被发现之日起开始计算;对于胁迫,自胁迫停止之日起开始计算。”第二,对于重大误解,其除斥期间为三个月,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计算。该条可能受到《德国民法典》的影响。该法典第121 条第1 款规定,错误人在知悉撤销原因后,必须在“没有过错的迟延的情况下行使撤销权”。这里所谓的不存在有过错的迟延,就是撤销权人必须尽快地撤销其意思表示,不允许存在可归责于其自身的拖延。根据一些学者的意见,在意思表示错误的情形中,仍然赋予表意人的撤销权以一年的除斥期间“显然是过于宽厚的待遇了,这无异于鼓励当事人基于一个可归因于自己的原因去利用除斥期间进一步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毫无可归责性的对方当事人却不得不忍受这一段时间处于法律上的不确定状态”,非常不利于市场交易中的善意相对方的利益的保护。*薛军:《论意思表示错误的撤销权存续期间——以中国民法典编纂为背景的分析》,《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3期。这一观点的前提是,假定重大误解的受害人通常对于误解的发生存有过错,相对人却“毫无可归责性”,因此,赋予前者以一年的除斥期间对后者明显不公。然而,这一假定并不见得符合事实,在意思表示的形成、表达、传递和受领等环节中,误解人对于误解的形成不见得必然有过错,而相对人也不见得是“毫无可归责性”的无辜者。并且,三个月的超短期间,对于重大误解的受害人显然不公;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重大误解之日起,受害人必须在三个月的期限内采取行动,保留并收集好相关证据材料,这对一些复杂合同的当事人来说,将构成一个十分严峻的挑战。
四、关于合同无效的判断标准
《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此条的入法经历可谓一波三折,系由于部分学者的呼吁而终被写入。然而,其措辞却明显偏离了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和《民法总则》之前的几次审议稿草案。由此,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立法者明显抛弃了司法解释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表述,背后蕴含什么深意?按照立法的表述,似乎是“无效为原则,有效为例外”,这样对司法实践会不会带来重大的变化?
首先,司法解释将强制性规范区分为“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和“管理性强制性规范”,笔者一直认为存在很多的可商榷之处,这大约也是立法者最终没有采纳司法解释的原因之一。实际上,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的区分,涉及公法规范的识别定性,而公法规范的识别本身是一个公法行为;由民事法官对公法规范的性质进行判断和区分,存在着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如果位居最低审级的民事法官都可以对中央立法和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进行定性,这对宪政秩序无疑是一个挑战。
其次,法律和法规中存在无以计数的强制性规范,如何能确保对这些规范的定性准确以及标准统一,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很多时候,区分效力性规范还是管理性规范,类似于一个经院哲学式的难题。一方面,“效力性规定”和“ 管理性规定”的二分不构成对与任意规范相对之强制规范的封闭式分类。*姚明斌:《“效力性”强制规范裁判之考察与检讨——以〈合同法解释二〉第14 条的实务进展为中心》,《中外法学》2016年第5期。另一方面,“效力性规定”和“管理性规定”本身均欠缺严谨的界定。按照通说,所谓效力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 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 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这一定义存在明显的同义反复和循环论证的缺陷。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针对不得已需要进行识别区分的情况,司法解释应当作出指引。一方面,应对区分标准作出规定。现有的利益识别法、对象识别法、责任识别法、原因识别法等理论,都具有一定合理性,*徐干忠:《识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方法》,《人民司法》2011年第12期。但由于缺乏具体的分类指引,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欠缺操作性的问题。这些理论之中,保护利益说相对较为合理,因为其更符合合同无效制度的宗旨。就此而言,新《法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值得借鉴。该条规定:“因违反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之规范所导致的无效为绝对无效;因为违反仅以保护私人利益为目的之规范而导致的无效为相对无效。”这被认为是吸收了现代的合同无效理论以及最新判例的成果。根据新的“保护利益”原则,如果所违反的规范仅出于保护某些特定当事人的利益(例如行为能力规范、保护性规范、保护某些出让人利益的规范等),合同一般不能认定为绝对无效。*Muriel Fabre-Magnan, Droit des obligations, I-Contrat et engagement unilateral, op.cit., pp.506-507.另一方面,还应当对识别程序作出规范,譬如,借鉴情势变更的适用程序和比较法上的“先决裁判”机理,如果法官必须对某一法律或法规的强制性规范进行定性,可考虑应当请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因为,当每个基层法官都有权自行判断规范的性质时,将加剧“同案不同判”现象,危害裁判结果的统一和法律规则的统一。
《民法总则》第153条第2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该法第8条正式确认了公序良俗原则并且,该法第143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时,强调其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公序良俗原则源于我国《民法通则》、我国《合同法》等法律中的“社会公德”、“社会经济秩序”等原则,但其外延更为广泛,可以通过法官赋予民法典对变动中的经济社会形势以更强的适应力,明确规定公序良俗原则也与比较法的经验更为吻合。
就公序良俗在合同法领域的适用而言,有几点尤其需要注意。
首先,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属于公共秩序的范围,侵害宪法基本权利的合同可视为违反公共秩序而应宣告无效。譬如,合同中侵害一方当事人的婚姻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或人格尊严。以代孕合同为例,法国民法典、魁北克民法典均依违反公共秩序的理由规定其无效。法国最高法院还曾判决:房屋租赁合同中禁止承租人在房屋内容留任何其他人包括其近亲属,侵害了承租人的私生活和家庭生活受保护的权利(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此条款无效。*Cass. Civ. 3e, 6 mars 1996, n°93-11113, RTD civ., 1996, p.580, obs. J. Hauser.
其次,合同不应构成对他人的不合理歧视,因为禁止歧视属于合同公共秩序的范畴。譬如,欧盟《共同参考框架(DCFR)》第2:101条规定:“如果一个合同或其他法律行为是关于向公众提供或供应商品及其他公众可以获得的财产或服务,在其实施过程中,任何人均有权不因性别、民族或种族而受到歧视。”其第2:102条规定:“歧视包括:(a)比起其他人正在接受、已经接受或即将接受的对待,一个人受到了不友好的对待,或者 (b)一个表面上中性的规定、标准或惯例,其实际效果会使得一群人与另一群人比较时处于特别不利的地位。”*参见克里斯蒂安、冯·巴尔、埃里克·克莱夫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高圣平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69页、第178页。
最后,在合同中应慎重适用善良风俗原则。对于民事合同,如给付原因或目的存在不法或者违反公德,构成违反善良风俗。譬如,对于存在婚外性关系的当事人之间的赠与,域外法上的普遍趋势是,仅有在赠与的目的是出于鼓励或维系婚外性关系的存在时,赠与行为方可被撤销。*Cass. Ass. Plén., 29 oct. 2004, n°03-11238.对于纯粹的商事交易合同,则应尽量排除善良风俗原则的适用。总体上,善良风俗在合同领域中逐渐隐退,其涵义逐渐出现空泛化的趋势,或逐渐为公共秩序所覆盖。2016年修订前的《法国民法典》第1133条规定:“原因如违反法律、善良风俗或者公共秩序,即为不法。”新《法国民法典》第1162条规定:“合同的条款及其目的均不得违背公共秩序,无论后者是否为各方当事人所知悉”。显然,新法的此条取消了对善良风俗的援引,仅保留了公共秩序。*Muriel Fabre-Magnan, Droit des obligations, I-Contrat et engagement unilateral, op.cit., p.480.
五、我国民法典合同编修订的相关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民法总则》以28个条文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相对于我国《民法通则》中9个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条文来说,无论是在量上还是在质上均有了重大的改变。这些修订的绝大部分内容,一方面来源于对我国《合同法》等立法和司法解释合理内容的总结与吸收,另一方面也源自对比较法经验的分析与归纳。这些内容都是在立法质量方面的明显改善,因此,它们应当被我国民法典合同编吸收。当然,《民法总则》关于民事法律行为部分的少部分增补,譬如关于重大误解撤销权的三个月超短期时效以及违反强行法的效果,反映了中国立法者的一些独特立法政策考虑,从契约公平或契约效率的角度来看不无争议,其适用效果,有待于未来的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根据《民法总则》前述相关内容,建议我国民法典合同编在整合我国《合同法》的相关条文时,既要保持民法典的内在一致性,消除总则与分则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也要避免分则对总则的简单重复,实现立法的简约。为此,建议做如下修订和调整。
第一,关于沉默的意思表示,民法典合同编在纳入我国《合同法》第22条时应将其修改为:“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第二,关于合同解释,如果在民法典合同编中继续保留我国《合同法》第125条,应在“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之间,插入“合同的性质”;另外,关于单方法律行为的解释,即便民法典合同编规定单方法律行为作为债的渊源之一,*《民法总则》第118条第2款规定:“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其中的“法律的其他规定”主要就是指单方行为的情形。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258页。也无必要另行规定其解释规则;其解释直接适用《民法总则》第142条第2款。
第三,关于虚假表示,民法典合同编中如果保留我国《合同法》第52条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则应将该条第3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改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订立的合同”。
第四,关于隐藏行为,民法典合同编中可增加一条专门的规定:“如以虚假的意思表示所订立的合同隐藏了另一合同,则被隐藏合同的效力依照有关的法律规定处理。”
第五,关于乘人之危与显示公平,建议民法典合同编毋需另行规定,避免重复。
第六,关于第三人欺诈与胁迫的问题,建议民法典合同编毋需另行规定,避免重复。
第七,关于撤销权的行使,建议民法典合同编毋需另行规定,避免重复。
第八,关于合同无效,民法典合同编中如果保留我国《合同法》第52条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则应作如下修改:首先,将该条第4款“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修改为“违反公序良俗”;其次,将该条第5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修改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合同无效的除外”。
(责任编辑:徐澜波)
石佳友,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日内瓦大学种子基金—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6XNQ021)的阶段性成果。
DF525
A
1005-9512-(2017)07-00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