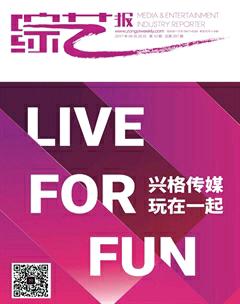名著改编不能跪着改也不能瞎改
陈丹
《综艺报》:相较原著,剧版《白鹿原》做了多大程度的改编?
申捷:在接这个活儿之前,我是犹豫的,犹豫的主要原因在于无论怎么改都会有争议;而在决定接这个剧本后,我就做好了面对这些争议的准备。我觉得作为一个职业编剧的操守,第一不能“跪”着改;第二,不能瞎改。当你深入了解这本书,把它掰碎,揉烂了化成你的血脉,你又通过这本书读了上百本书,了解了中国近现代史,了解了那些文化、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之后,你要敢于站出来,告诉他们中国传统文化该丢弃的是什么,该守住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职业编剧的操守,是我必须坚持的地方。
什么叫忠于原著?我给自己定位就是忠于原著的精神,把握住人物的命运,提炼出里面的精华,把它转化成影视作品。影视语言和小说语言完全不同。如果我们照搬小说,尤其是像这种“奇书”,把它的文学性原封不动地搬到屏幕上,我相信会有很多负面的东西。
《综艺报》:《白鹿原》播出之后,口碑不俗,但收视一直不是很高,你心里会有失落感吗?
申捷:开始有,后来想明白自己的初心就好了。我从业20年来,从《重案六组》《女人不哭》《虎妈猫爸》到前不久的《鸡毛飞上天》,收视率上还是有资本的,但只有《白鹿原》给我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说句实话,我们中国出现那么多经典电视剧的时代是不拿收视率说话的。那时收视率只是评判标准中很小的元素,电视剧的口碑、影响力、塑造的角色等,这些是主要的。开始看到收视率零点几时我也一愣,后来想明白了,可能《白鹿原》有《白鹿原》的命,现在它的收视也已经连续好几天破一。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在微博上、豆瓣上开始发声,像谢飞导演,这都是我很仰视的人。我觉得做这部作品太值了,以前做其他畅销剧的时候没有见过这些人发声。
《综艺报》:你转向正剧创作的原因是什么?
申捷:在我毕业以后碰得头破血流时,学会了讲故事,学会了适应市场——市场流行什么做什么,但我突然间有些“惶惶不可终日”。也曾投机过,曾经以为太平盛世各奔前程,也问过自己这个时代用得着大的理想和情怀吗?毕业后连续十几年都在为收视能否战胜别人,作品能否取得资本与市场,自己能否争得名利而奔波,越来越紧张、恐惧、痛苦。我不知道为什么,欲望越大越恐惧,越成功的时候越恐惧,莫名地觉得没有根。
中戏的大学四年是我特别幸福的时光,但那时关于写作的所有美好荡然无存,写作变成了我安身立命的工具。说是为了实现梦想,可梦想早已转变成一个个具体的物质目标,今天挣多少钱,我要买什么东西,所以要接这个活儿。但我发现名利不能给人幸福感——那种踏实活着的感觉,那时真的特别痛苦。我2009年的时候开始读王阳明,读了两年,想解决这个痛苦,接手《白鹿原》剧本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王阳明说唯心显现,其实这个世界所有的痛苦都是自己找的,你不进山中看野花开,野花不会为你开;同样你不做《白鹿原》,《白鹿原》也不会为你盛开。
《综艺报》:电视剧《白鹿原》对你来讲的意义是什么?
申捷: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让我能够找回写作的乐趣,而且它给我很大的信心。陈忠实先生把我的心安下來了,我始终记得老汉那个样子。我要以他为榜样,不再被世间的诸多诱惑,包括资本的诱惑所侵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