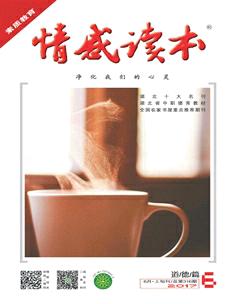生命最后的尊严
从玉华
哈姆雷特的老命题,“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如今却成了全球性的新命题。
把临终的权利还给本人
当罗点点和她的好朋友几年前成立“临终不插管”俱乐部时,完全没想到它会变成一个重大的、严肃的、要一辈子干到底的“事业”。“俱乐部”听来就不像是个正经事。
罗点点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曾经从医多年。起初,她与几个医生朋友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谈起人生最后的路,她们一致认为,要死得漂亮点儿,不那么难堪;不希望在ICU病房,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赤条条的,插满管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最后“工业化”地死去。
十几个爱说笑的人在一间简陋的老人公寓,嘻嘻哈哈地宣告俱乐部成立了。
直到有一天,罗点点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的英文文件。这是一份美国有400万人正在使用的叫作“生前预嘱”的法律文件。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的时刻通过简单易懂的问答方式,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诸如要不要心脏复苏、插气管等等。
罗点点开始意识到,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而她自己就遭遇过替别人决定生死的事。
当时,罗点点的婆婆因为糖尿病住院,翻身的时候突然被一口痰堵住,心跳呼吸骤停,医生第一时间用上了呼吸机,虽然心脏还在跳动,可是婆婆已经没有自主呼吸,而且完全丧失了神志。还要不要使用生命支持系统维持老人的生命,让老人在这种毫无生命质量的状态下“活下去”,成了困扰整个大家庭的难题。
最后,罗点点和家人一起做出了停用呼吸机的决定。后来,在整理老人遗物的时候,家人发现了老人夹在日记本里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她对临终时不进行过度抢救的要求。
但当时身为医生的罗点点仍然感到后怕。如果没有这张字条,或者字条上写着另外的意思,那怎么办?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件事不像猜谜语,不再让逝者生者两不安?这时候又传来巴金去世的消息。
巴金最后的6年时光,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先是切开气管,后来只能靠喂食管和呼吸机维持生命。周围的人对他说,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巴金不得不强打精神表示再痛苦也要配合治疗。但巨大的痛苦使巴金多次提到安乐死,还不止一次地说:“我是为你们而活。”“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2006年,罗点点和她的朋友成立了“选择与尊严”网站,提倡“尊严死”,希望人们在意识清醒时在网上签署“生前预嘱”。如今,网站累计有87万人次的浏览量。
她们设计的LOGO是一棵美丽的七彩树,一片红叶正在随风飘落,画面温馨得让人丝毫感觉不到与“死亡”相关。
罗点点说,她要用余生在全国种这棵“七彩树”,传播“生前预嘱”理念。她希望在咖啡厅、书店、银行、医院等公共场合,都能摆放关于“生前预嘱”的宣传册。
最后的日子像一面镜子
中国抗癌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军区总医院原肿瘤科主任、从医40多年的刘端祺经手了至少2000例死亡病例。
他认为罗点点她们做的事儿太重要了。这个每天把人从死亡的深井里往外拉、跟肿瘤做了几十年斗争的年过六旬的大夫说,从大三学内科起,他就知道了医学有很多“黑箱”没有被打开,此前学外科时,他还一直信心满满。
正如他的同行、武警總医院肿瘤生物治疗科主任纪小龙说:“医生永远是无奈的,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好不了,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能好,只剩下三成多是给医学和医生发挥作用的。”
可数据显示,人一生75%的医疗费用花在最后的治疗上。
在那些癌症病人最后的时刻,刘端祺听到了各种抱怨。有病人对他说:“我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现在我才琢磨过来,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为治病卖了房,现在我还是住原来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给人家交房租,我死的心都有。”
还有病人说:“就像电视连续剧,每一集演完,都告诉我们,不要走开,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后一集我们才知道,尽管主角很想活,但还是死了。”
有时候,刘端祺会直接对一些癌症晚期的病人说:“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没多久,病人卖了房来住院了。又没多久,这张病床就换上了新床单,人离世了。
刘端祺说,整个医院,他最不愿意去的就是ICU病房,尽管那里陈设着最先进的设备。在那里,他分不清“那是人,还是实验动物”。
在刘端祺经过的2000多例的死亡中,他最难忘的是一个老太太的死。这个肺癌晚期的老太太,做了3个周期的化疗,被药物的副作用折磨得不成样子。她彻底弄明白自己的病情后,和医生商量,放弃化疗。
她住院时唯一的“特殊要求”是,希望有一个单间,这个空间由她自己安排。她将这间单人病房布置得非常温馨,墙上挂满了家人的照片,还请人把自己最喜欢的一张沙发和几件小家具从家中移到病房。圣诞节、春节,她还亲手制作充满童趣的小礼物,送给来看望她的亲人朋友。
最后老人一直在镇静状态中度过,偶尔会醒来。醒来的时候,她总会费力地向每一个查房的医生、护士微笑,有力气的时候,还努力摆摆手、点点头——所有这一切,都保持了她那独有的优雅。直到最后,她再也没有醒来。
总在与死神进行拔河比赛的刘端祺说:“每一次死亡都是很个体的,死亡就像一面镜子。”
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的课堂上,他念因癌症离世的美国人崔雅的诗歌,讲海德格尔的哲学“人是向死的存在”。他还把死亡说成是“生命的秋千荡完了”。他把自己的课叫“死亡课”“优逝课”。只是,这样的课常有学生逃掉,但几乎没有人逃医学技术的“主课”。
王一方也讲温暖的绘本。他甚至很希望,有一天,和一个癌症患者依偎在一起,读《獾的礼物》。
那是个连小孩子都能读懂的故事:冬日的晚上,一只獾很老很老了。他吃完晚饭,靠近壁炉,坐在安乐椅上摇啊摇,一个美丽的梦境把他引入一条长长的隧道。他跑呀跑呀,丢掉了拐杖,到了另一个金灿灿的世界。第二天,狐狸宣布“獾死了”。冬去春来,村子里的动物们谈论得最多的是老獾。土拨鼠说,是獾教会我剪纸;青蛙说,是獾教会我滑冰;狐狸说,是獾教会我打领带;兔妈妈说,是獾把烤姜饼的秘密告诉了我……原来,獾留了这么多礼物给大家。
可王一方一直没有等到与临终病人分享《獾的礼物》的温馨时刻。他的演讲顶多是在一群病人家属中进行而已,尽管很多家属听得泪流满面,但这样的“死亡课”一直没有走进病房。
给别人让出空间,正如别人让给你一样
这样的挫败感,罗点点经历得太多了。
她去医院大厅种“七彩树”,希望传播“生前预嘱”。医院的负责人婉拒了:“我们这儿是救死扶伤的地儿,谁接受得了你们谈论死呀!”她让朋友在公园的合唱团里发调查问卷,唱歌的阿姨们不乐意了:“活得好好的,这么早让我们想到死?”结果没多久,真的有一个人去世,大家都开始思考罗点点说的事儿了。
罗点点出了一本书——《我的死亡谁做主》,她把新书发布会放在北京非常时髦的世贸天阶时尚廊举行。发布会是崔永元主持的,他笑称“这本书很难成为畅销书,还不如一个80后小孩写的书好卖”,但没办法,这是一种责任。他还念了史铁生的话:“死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春节时,罗点点把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所有的亲友。大家都说“真有你的,大过年的,说什么死不死的。”可看过书的朋友,又打电话对她说:“这是一份文明的礼物。”
她告诉别人自己在忙什么,有家境差一些的人直接反驳:“你说的问题太高端了,我们面临的不是放弃,而是没有。”也有医生说:“你们的理念挺好的,可在中国很难推行下去。”
有大夫说:“我想起我第一次抢救病人时忍不住湿润的红红的眼圈;想起我见过的最孝顺的儿子签署放弃抢救他爹的协议后,在地上磕的响头;想起患者走后家属的干号,随后在门口冷静地摊派丧葬费用;想起无耻‘医闹,不及时为逝者入殓,就开始盘点医护失误准备打官司……面对生死真是众生百态,人性毕现。”
罗点点团队里的席修明是北京复兴医院的院长,他担任ICU主任几十年。他把自己的崗位称作“生死桥头”,称ICU技术是一种“协助偷生术”。
这个从34岁就开始担任医院ICU主任的专家,23年后,却当着记者的面,泼了ICU一盆冷水。他常提醒工作人员,一个微笑胜过一片安定。他要求他的同事多给机器旁的老人梳头、擦身体,抚摸他们,哪怕病人已经没有了意识。在台湾,老师会让医学生们到一间黑屋子里,每个人躺进一个棺材,用手电筒的光,照亮遗书,慢慢地读完,体会“死亡的滋味”。
死亡在这些医生眼里,就是油尽灯灭,再自然不过。正如《阿甘正传》中阿甘的妈妈对阿甘悄悄说的:“别害怕,死是我们注定要去做的一件事。”也如哲学家蒙田所言:“给别人让出空间,正如别人让给你一样。”
生命的句号自己画
因为职业的关系,罗点点和她的朋友对“死亡是一种伟大的平等”这句高悬在北京八宝山骨灰堂门楣上的歌德的名言,有自己的理解。
王一方总讲“死亡课”,他也想好了自己怎样“下课”。他说,最后的时刻,他拒绝用机器延长生命,他会让人给自己刮胡子,用热毛巾洗把脸,再搽点儿雪花膏,干干净净地离开,要“像老獾一样,把礼物留给别人”。
ICU专家席修明说,他不会在ICU走,他要躺在一张干净的床上,一个人也没有,安静地对这个世界说会儿话,然后走,正如一只蚂蚁离开,一片树叶落地。
见惯了死亡的刘端祺,没打算把自己的死亡看作“特别的仪式”。他说,他不会浪费别人的时间,不会接受过度抢救,赶上谁来看我,就是谁;骨灰放在树下,当肥料。“我一生很充实,我给自己打80分!”
田龙华摘自“荒岛读书”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