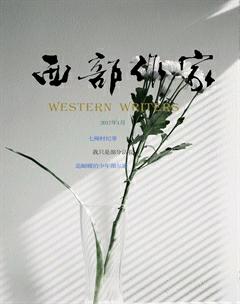我只是部分活着
皇甫卫明
我是自己爬上去的。我身子底下一块砧板,大约两米长一米宽。一阵嚎叫隐约我耳畔。小时候看父亲杀猪,它自知大限已到,叫得自然惨烈,父亲腾出左手捏紧它嘴巴,右手抄起尖刀,它张扬的长调来不及释放就被堵在口腔里,倏尔化为沉闷的呜咽,那些被切掉的频率哪里去了?一定是起伏的肚子给了最好的缓冲。猪不会自己爬上砧板,我比猪勇敢,也比猪聪明。我一个人去医院接受检查,并毫不犹豫地在协议上按上手印。
我等待宰杀。屠夫不是我爹,也不是挂着齐膝皮围身足蹬长筒胶鞋的小刀手,他们一齐白色的长衫,那种让孩子做梦都惊厥的装束。此刻他们坐在我两边吃盒饭。刚才推门进来的时候,他们的脸都绷着一块白布,表情全写在唯一暴露的眼眸。他们拉开紧绷的白布,把隐藏的脸公开,这些脸与我平时在街上碰到的没有实质性区别,他们嚼动红烧肉的时候嘴里也发出吧唧,他们自顾吧唧着,不看我一眼。他们在一个流水线上重复了六个流程,需要补充能量。我排第七,这个次序对我有些残酷,昨夜开始他们就勒令我停食,还给我灌肠,如果孙二娘把我囫囵拿到菜市,我像猪下水一样的东西,收拾起来无需花太大的功夫。
我平躺下来,把身子腿脚都使劲伸直。我上方悬着一盏灯,确切地说一组,我们家不用这种灯的,它离我那么近却一点也不热烈,像少女羞答答的眼眸。上三十以后,我基本不与少女对视,我习惯用大胆的眼神巡睃同龄少妇的三围,很少收获敌意的目光。
我为自己的镇定感到惊讶。小时候弄破一点手指都哭到绝望,流干了血会死的。三十岁时还不敢打针,护士让我把裤后腰拉下去,她用一个冰凉的棉花球擦我的腚,我蹙着眉还忍不住回头看她的手,尽力将腚往前蹶,我不在乎会载入护士口中的笑料。我用手搭下脉搏,心跳很正常,比平日还正常。这要归功于进来前他们给我戳的一针,一个小针管里的水看不出跟矿泉水有啥区别,他们凭什么知道不同的功用,他们看瓶子上的字,他们抽出水后随手把瓶子扔进垃圾筒。这些水早在我血管里窜动,流速每秒七米,它不会盘踞于我身体某一个角落,也不会在心脏里歇脚,但每次路过我心脏的时候,柔声地安慰它,轻轻地抚慰它。之前我说可不可以不打?他们的回答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都上杀场了还怕啥,我一下捡回丧失了几十年的勇气。
他們让我弓着背,最大限度地弓着。我把后背脊梁都暴露给一个麦柴管样的针管,我只从兽医那里见过这么粗的针管。牲畜也不懂配合,更不会理解你用心良苦,加快药水流速可以尽量缩短它挣扎的时间。可我配合得很好,我双手抱住腿,把脊椎的间距拉到极限,他们完全有足够的时间让药水沿着细细的针管进到我脊髓。他们作了几次尝试才让针尖得逞,说我的皮肤太老。怎么会呢,背上痒痒时稍稍挠几下就出血了,一次我踩在仰面的铁钉上,铁钉毫无阻拦穿过厚实的皮鞋底子,我反应还算快,脚底上已淌着汩汩的血。
签字时,我还不知道问题的严酷,他们说家属也要签的,我这才细细阅读上面的条文,它就是一份生死文书。过去也曾耳闻哪里有人死在手术台上,我觉得与我无关,我就是诚心让他们拿了剔刀一刀一刀地剐我,也不至于一下被弄死。他们说,签字只是必要的手续,那个情况毕竟很少,就像体育彩票的大奖。如果我不幸中奖,那第一时间我的家人该去买彩票。另外,我一签字就就认命吗,就算杨白劳甘心情愿按了手印,你黄世仁也不该糟蹋了喜儿。我是无力找你们了,我的老婆孩子还有兄弟朋友什么的,一定会到门口拉起巨大的横幅,揪着你们胸脯把吐沫喷到你们脸上。
他们作势与我攀谈,却在我背后鼓捣,一丝凉意袭进我的脊髓,还没感觉凉意的弥散,我的心连同身体瞬间从云霄跌向无底的深渊。不知过了多久,一股神奇的力量又将我托起,我漂浮在半空。我被吸入一条隧道,又糊里糊涂地上了一个飞行器,它载着我沿无尽的隧道以极速飞驰,隧道四周飞溅着漂亮的荧光,一会儿又觉得我不在飞行器里,我就一个人在飞驰。隧道弯弯曲曲,我几次就撞到边上了,我吓得闭上眼睛,一睁眼,没事。突然,我飞出隧道,飘进茫茫的星空,但此时人一下没了动力,又在黑咕隆咚的夜空中迅疾下坠,我的呼吸越来越不畅,灵魂马上要飞出身体。
“怎么醒了?”我听到说话,很真切,很遥远。我的肚子胀到极限,他们还在踩打气筒,我喊喘不过了,马上有一个东西罩到我脸上,还说,给你吸氧,这下喘得过了吧。脊梁中又是一阵凉意,我的灵魂又飞起来,这次身体却没往下跌,我甚至听清了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再推点药!他们曾问我,要不要好一点的麻醉师?我说当然。他们说,得大医院去请,要稍稍花费一点的,我们医院也配备麻醉师,就是技术差些,麻醉打不好会有后遗症,阴雨天脊椎隐隐发痛,腰也不再硬朗,打过腰麻的十有七八。我使劲点头,估计那频率与公鸡抢食啄米时差不多,并下意识去兜里摸钱包,他们说,别急,到时给就可以。
不是大医院,流水线并不每天运行。今天满负荷,一下子安排了十五个,顺利的话一个人也要一小时。里边两张砧板,他们流水作业,三个小组各自负责开膛取胆缝合,大大缩短门外的等待。工厂流水线是安装,每过一关,产品上多了一个零件,而他们拆卸了我们的零件。人到底比机器厉害,机器的零件坏了得更换新的,人的零件可以凭空拿掉。他们说,与其让它在肚子里捣鬼,不如早早割了它。乡下人常说外科医生厉害,能给人开膛破肚。我说屁话,内科大夫才是本事,他们专司修复,不搞宰杀。我说人来到地球四十万年了,造物主一直没把这个那个零件省略,说明它有用处。他们说,不见得,日本人生下来时就把阑尾割了,所以日本没有盲肠炎。我想,我哪里不好就给割了,照这样下去,我上到一定岁数我肚子里五脏六腑统统没了,再下去头和身子都没了,人家叫我名字的时候,我就叉着两条腿蹦跶过去。
回到病房的时候,我虚弱不堪。两个大男人,外加我老婆托我的腰部,我才从砧板移到床上。我身上连着五六个管子,只有右手还能动弹,我的手能勉强够到的地方只有胸部和肚子,我摸摸肚子,仿佛不是我的,局麻后他们用针尖一下下扎我肚子,问我疼吗,我说没感觉。我见他们都笑了。这个肚子是谁的?我顺着胸口一路摸下去,又从肚子一路摸上来,肚子是连着我胸部的。我的腿也能伸缩,整个人像分了两个部分,中间脱节。前年我到连云港去,发现这座城市中间有个真空地带,老城离港区有三十公里,这还能叫一座城市吗,我认识这个城里一位与我同龄的作家,他说无关地域,只要精神上一体。我跟着女儿看过《未来战警》,人都炸成一滩碎片了,这些碎片却慢慢聚拢,再站起来时一个完整的人竟毫发无损。我要小便,很明显没法去卫生间,我只有小时候在床上尿过,长大后从没当着别人的面把那劳什子架在手中。我连坐起的力气都没有,还想拖着一个别人的肚子走几步,我终于憋到晚上。
他们端着一个白色的搪瓷盆,这种方方的浅浅的盆时常放刀剪纱布体温表什么的。我身上卸下的零件,类似母鸡的产肠,他们用剪刀麻利地剪开,抖出一颗石头,用水一洗,传递左右,最后送到我眼前。它的大小和形状让我联想起小时候一直觊觎的橄榄。他们把石头留下,把那块肉端走。我问他们怎么处理,他们意味深长地笑了。壁虎逃生时自断尾巴,章鱼遇到攻击可以抛弃整个手足,它们是遇到危险。我的危险是什么,是来自我身体其他部件的排挤。一个健康躯体并不感到任何零部件的存在,它要提示我存在的时候,我会注目它,这不一定是好事。我当老师首先注目的就是问题学生,还一直担心他们把其他人搭坏了。白大褂对我说,恶变的几率是百分之三,你那东西早就丧失了功能,已达到恶变的极限。我本来没打算剔除它,也就随便看看,他们列举了一些翔实的例证,说越快越好,我说春节后可以吗,他们说量变到质变,没有人能保证,结果我举手投降。他们没有绑架我,是我自己绑架了自己,我的意志绑架了我的肉体。我一直后悔没将它要回来,浸泡在一个玻璃瓶子里,让它有朝一日物归原主。我的想法一定让人笑话,太监净身后,割下的命根由净身师父保管,太监日后得花重金赎回,百年时命根随他们下葬。大家都是肉,我那块跟太监的怎么好比呢。有人一脸坏笑让我猜个歌名,说宁可当和尚不当太监,我说把根留住,你什么智商跟我玩过家家。
老婆说我刚才脸色刷白太可怕了,我说我吹过喇叭一直看死人的脸并不感到可怕。同学聚会时老校长比划着说,黄土已经埋到他脖子上了,他今年76。我呢,我的黄土埋到哪儿了?人对死的恐惧不是因为它的可以预见,而是因为它的不可预见。这话有些暧昧,人的终极可以预见,那是必然规律,就像日出月落,四季轮回。但如果真有确切的预见,未必没有恐惧,比如判了死刑,比如身患绝症。叶广岑的《黄连厚朴》中,有位老总让龚老爷子看病,老爷子对他说,你这病啊甭治了,回去准备后事吧!老总财大气粗,只是偶感不适,哪里相信老爷子鬼话。但终究心里发虚,还背“人生自古谁无死”什么的。弘一能预见自己大限当在七日后,只写了“悲欣交集”四字,便去圆寂。悲是人之常情,欣却令人费解,我练不到弘一的境界,自然只有他明白。
那个收了我大洋的麻醉师笑眯眯地站在我床前,几个小钱让我享受了麻醉师深情的探望,她问我刚才可曾乘到飞船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啊。我曾问过其他病友是否有类似的体验,他们说睡死了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跟人家不一样呢?我有点紧张。后来才知道那是死亡体验,我看过不少有死亡体验的外国画家所默写的另一个世界,荒诞却很美。我还在旅途,没真正到达那个世界,这怪我醒得早,麻醉师说酒鬼耐药。为什么早先不跟我沟通,多推点药呢,害得我没了发言权。她说药物一旦进入大脑,你就醒不来了。我不怕我的生命在第45个年轮上定格。老人说,好死是前世修的。我在睡梦中轻而易举到达了另一个世界,省却了恐惧绝望烦躁之类诸多环节。一個未知的世界,你说它恐怖,说它幸福,有资格说这话的人已经无法跟我交流。
我其实怕死,我毫不犹豫让人将我身体的一部分处死,换来其他部件的安稳,也获得灵魂的踏实。我的身体一部分已经死了,它离开了我,谁让它搅得我吃不安稳睡不踏实。它的分量不足半斤,还不到我整个身体的百分之一,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它毕竟曾经是我的一部分,所以我只有部分活着。它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在很长一段时间它连累我的消化系统。让身体的部分进行一次死亡的演习,等到实战时我不至于猝不及防。老校长的话蛮洒脱,毫不伤感。人一生下来就冲着那个既定的目标。我们这个世界每天都减员,地球照转不误,世界依然美好。
他们让我出院,说过几天再来拆线。不是微创吗,还缝线。他们用纱布贴住我的肚子,不许我掰开看,我自己的身体还不许我看,他们在我肚子上开了四个洞,给我留下的百分比又会减去若干。我自己开车过来,回去时花了一分钟才坐进车子,位置在我非常陌生的副驾驶。他们关照我不许吃肥肉,更不能喝酒。我说你们把我害惨了,这个春节本是吃酒吃肉大显身手的美好时光,有几家还送了大礼,你们不能让我吃回点吗。
汽车起步了。我的车,开车的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