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梁四月天
○彭文斌
绿家园
浮梁四月天
○彭文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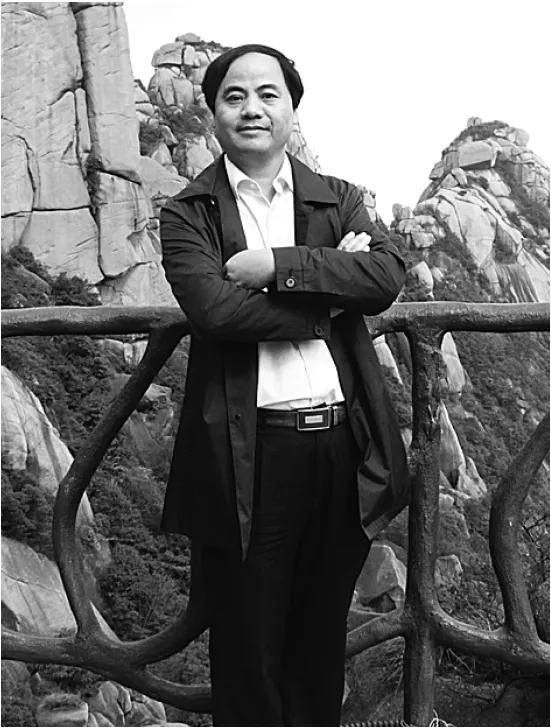
彭文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铁路作家协会理事、江西省作家协会理事。 已出版《纯粹风景》《惊尘疏影》《城市游泳》《沿着铁路散步》《一个叫彭家园的村庄》《岁月之刀原来如此锋利》《储蓄阳光》等多部散文集。 曾获全国第七届、第八届铁路文学奖。多篇作品被转载或入选文集。
几场雨连绵过后,浮梁的山色更是无穷碧了,昌江水弥漫着新鲜的气息。
我进入这座赣地边城时,夕阳正在青山与江面间徘徊,恰似白乐天笔下“半江瑟瑟半江红”的景象。正是芳菲四月,参加“中国作家看浮梁”采风活动的一干人聚集在县茶文化中心的大楼下,安静地欣赏落日熔金与一河翡翠流淌。我的脑海里反反复复翻腾着《琵琶行》里的那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除此之外,浮梁如同烟雨锁着的山峦,朦朦胧胧,不甚分明。
欢迎会上,县里的领导介绍了“浮梁”一名的来历和风土人情。我瞬间穿越到了“以溪水时泛,民多伐木为梁”的李唐岁月,瓷与茶,点燃了山乡漫漫长夜里的灯。《星火》执行主编范晓波说,这个地名很特别,携带着河流的动感和山林的气息,书写空间很大。希望作家们既有快手“榨果汁”,又有酿酒师慢工出美酒。
记得毕业那年,也是四月,我在南宁火车站实习,晨昏时最爱做的一件事是播放邓丽君的《小城故事》磁带,从不腻烦。也许,浮梁就是如此的一座小城,清丽、纯粹、透明,像一种高岭土陶瓷。我忽然惶恐起来,担忧辜负了浮梁小城的期望。会后,与《江西工人报》副刊主编王志远、鄱阳县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汪填金、小说家蔡瑛从会址徒步回宾馆,一路聊文学的话题。小城浮于花香之上,街上实在是寂静。我们好像在悠闲地品茗,茶,自然是“冠于天下,帷清帷馨”的浮梁茶,有一种出尘脱俗的气质。
同房间的浙江《交通旅游导报》副刊编辑谢宝光是个90后青年,江西南康人,文字写得行云流水,其从业过程也充满起伏。最初知道宝光,是阅读了一篇《8090:文学赣军的最新传说》,文中写道:“谢宝光、饶翠菊夫妻俩是2013年改稿会上的熟面孔。他们仍然在外省为生计奔波,但是庸常的生活被文学的光华照拂着,在他们看来就是幸福。”我们谈的更多的是情怀问题。没有想到,宝光对为人处世的把握纯澈而圆润,即便在五平方米的蜗居里过日子,他也从来没有放弃希望和快乐。树影从窗口爬进来,晚风和虫子合奏,午夜的浮梁有一种撩人的沉香之美。与宝光相遇,是浮梁给我的珍贵见面礼。
采风活动的第一站,是江村乡的严台古村。据说,东汉初期的隐士严子陵离开富春江后,一路逶迤,走进浮梁东北部的这一片山水后,再也不愿移动脚步,于是,村庄像一枚鹅嫩的新茶叶子,在严溪之畔伸展开来。严台的成长离不开袅袅茶香。民国四年(1915年),严台村江资甫的“天祥”茶号经营的“浮红茶”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
我穿过那座刻写着“严溪锁钥”四字的门楼,准备深入古村寻幽探微。本土诗人烟火蝶儿一般,先一步飞进了巷弄。这位执教鞭的80后,永远安安静静的样子,像她笔下的孔明灯,“将梦想安放 / 在浩大的夜空中/一点微光 /用以击退大地的苍凉”。故地重游,烟火依旧对那些以光阴作衣裳的老建筑充满感情,不时将白墙灰瓦的身姿收藏进手机。溪水潺潺,落满野花的芬芳,严台静得如同一滴在宣纸上洇开的墨。我和烟火一前一后默默行走。感觉自己正被明清建筑的磁场吸附,随时凝固为一具石雕。打开手机,我记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喜欢严台迷失我的感觉。喜欢猜想宅子里平凡的光阴。喜欢看阳光陪着野草翻上墙头的样子。岁月在这儿经营成一种陈茶的味道,弥漫到味蕾最敏感的部位。”
与宝光在拐角处不期而遇。那张年轻俊朗的脸上沁满汗珠,看情形,他已经在巷子间逗留已久。宝光微笑着颔首,目光却舍不得从飞檐翘壁上移开。我暗想,文字蝴蝶已经在一颗阳光的心灵里起飞。
午后,我们一行走进了勒功乡的沧溪。这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传统古村落。自唐朝伊始,朱家子孙在这处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耕读传家、经营瓷茶,培育了理学家朱宏、廉吏朱韶、大茶商朱佩泽,留下了处世良方《朱子家训》。烟火的组诗《在沧溪:重读理学经卷》作了如是表达:“一柄纸伞,走过天涯走过雨雪 /但始终走不出你布施的骨质与纹理。”内敛敦厚的沧溪,是浮梁灿烂文化的缩影。
爱美的蔡瑛跟我是江西省青年作家改稿班同学,她似乎执著地要做这些古建筑的知音,痴迷每一条巷子里的韵味,久久流连不去。来自《景德镇日报》报社的李金龙充当了“御用摄影师”的角色,以足够的耐心抓拍蔡瑛的灿烂笑容。幽深的茶商宅院、苍凉的朱家祠堂遗址、古木参天的后山、满身风霜的老墙,处处留下一位青年作家的倩影。蔡瑛后来自己用一句话调侃说:以作家的名义看浮梁,以年轻的名义多拍照。我联想起她近期发表于《鸭绿江》上的小说《风吹麦穗》,此时,蔡瑛分明就是一个极好的小说原型。也许,用不了多久,我这位秀外慧中的同学会给浮梁带来小说一般的惊喜。
赶在黄昏抛下黑袍子之前,我们抵达梅岭山庄。房间枕着山溪,流水欢腾。我和宝光倚靠着窗口,看植物生机勃勃地在谷地蔓延,看山的颜色由青变黛。宝光略有遗憾地道,如果把窗台设计成小露台,夜谈、品茶,该是多么的惬意。我很有同感,不过,能如此亲近大自然,心已满足。似乎心有灵犀,晓波在朋友圈发了一则感叹:“浮梁四月天。那些令人心醉的,都是日常视野里业已消失的。今晚,必须用瑶里水田中一千只雄蛙的合唱安眠。”
我与宝光相约,明日起早,去看梅岭古村。或许乐极生悲,我一失手,那台照相机骨碌碌从床头滚到了木地板上,眨眼间,惨不忍睹,我顿时一阵天旋地转。宝光忙劝慰说:千万别破坏了好心情,还有手机呢。其实,我悲的不是钱,难过的是无法用相机拍摄瓷源茶乡、诗画浮梁啊。餐桌上,得知消息的蔡瑛仗义地道:拿我的相机去用。一阵温暖顷刻间包裹了我的身体。
事情很快峰回路转,当我再次察看照相机的受损情况时,意外发现它竟然还能正常工作,只是要特别提防镜头部分发生脱落。心情彻底放晴。趁着宝光外出散步之机,我屏息敛气,抓紧时间用手机创作散文《严台茶香》。正用功时,王志远来串门,他偷拍了一张照片,发到群里,留言道:“正在现场‘榨果汁’,香甜、可口、暖心。”
窗外溪流的雷鸣声忽然变得愈来愈响,仿佛从天庭兜头倾泻。下雨了。银河决堤一般的雨。黑夜正在演奏磅礴的《黄河大合唱》。晓波到走廊上探看了几次,显然,他担忧明天的行程受阻。我宽慰他道:放心,晚上雨越猛,明天越可能是晴天。大雨挡不住作家们对浮梁的爱慕。蔡瑛在朋友圈发了一组美图,有严台的灯笼,有沧溪的牌坊,有阳春河的篁竹,有梅岭山庄的黄昏,而留言也充满诗意:“极简或繁复 / 从容与跳跃 / 都是浮梁的打开方式。”
次日5时便醒来,耳际轰鸣依然,辨不清是暴雨还是溪流,惦记着看梅岭古村的事,便打开房门,豆大的雨溅在水泥地上,像朵焰火,片刻即逝。无奈,又蜷回被窝。辗转反侧。煎熬了一个小时,无意发现婺源县作家协会主席洪忠佩在朋友圈晒出了一组观云亭的照片,一激灵,冲出门,探手一试,果然,云收雨霁。轻轻唤了几声宝光,见他依旧酣然梦中,不忍心,便独自悄悄出了梅岭山庄。
田野张着双臂,迎对云朵,泥土的芬芳如醇酒,瞬间醉了我。不远处,观云亭飞凌于涧水之上,缄默似禅。自从拍摄了电影《闪闪的红星》后,人们喜欢称之为“红军桥”。我小心翼翼地端着“残疾”照相机,选择角度拍摄风景照。之后,站在桥边,静静凝视着这当年“饶徽古道”的组成部分,想起岁月深处的重重身影。我忽然情绪奔涌,难以自已,即兴在微信朋友圈里创作诗歌《在梅岭古村遇见一座桥》。不知何时,浮梁县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高岭文化研究:景德镇陶瓷文化渊源探微》一书的作者冯云龙出现在桥头,尽管走遍浮梁的山山水水,他对故乡还是保持着初心,像一炉不熄的窑火。浏览了一遍我的“打油诗”,冯云龙感慨不已,希望我能投递给他主编的《浮梁历史文化》杂志。他说:参加作家采风活动和学术会议风格完全不一样,前者轻松,相互欣赏,后者严肃,相互争论不休,还是当作家好。我哈哈一笑,其实我还想告诉他,真想化用陈毅称赞桂林的一句诗表述我此刻的心情——愿作浮梁人,不愿作神仙。
晓波已将我那首诗歌的截图发到群里,注释道:“彭文斌早晨刚榨的果汁。”烟火跟帖说,感觉更像醇香浓郁的酒啊。群里热闹起来。蔡瑛称,她“莫名觉得这古桥像一个痴汉。坚韧、执拗、沧桑”。汪填金则献上《瑶里一夜》:“文如榨汁诗如酒,雷似击鼓水似歌。”素来擅长对联的他兴致未尽,晒出新撰的数联,一是写冯云龙、烟火叙谈情景,道是“人间烟火,天上云龙”,一是写汪德胜、王伊同座,道是“得意风光之胜者,忘情艺术之伊人”。浮梁县文联主席王小勇深受鼓舞,也亮出一首《作家浮梁行》:“名家采风觅浮梁,盛世风景勿能藏。笔墨写赞因太美,敢叫君临叹服还。”
临出发前,大家被满天空的纯蓝惊住了。是透明的蓝。是瓷一般的蓝。蔡瑛说,一夜暴雨后,这瑶里的天空像孩子哭过后的眼睛。宝光则说,这种蓝是蓝生出来的蓝。调侃间,山重水复,大巴车进入汪湖原始森林腹地。一匹飞瀑向春天大胆吐露鲜美的情语。古驿道隐没于苍莽之中。汪湖仿佛一本巨大的教科书,帮助我重新认识植物。汪填金这些年潜心研究植物学,收获颇丰。他走在队伍的后面,一边认真拍摄各种乔木、灌木、野花,一边向我介绍,这是甜槠,那是檫树,绿的是雀舌黄杨,瘦的是马银花。电视连续剧《牟氏庄园》《母仪天下》的编剧王伊伫立于涧水边,神情专注,坚持用手机拍摄天河谷的视频,积极向朋友们推介浮梁的山水。天河谷的确是一道无与伦比的大菜。我们不约而同暂停了交流,将目光和灵魂全部交给了流水。
重游绕南古制瓷遗址,我估计自己可能黔驴技穷,写不出新的文字。正好王志远上前交流散文写作的心得,我乐意奉陪到底。可是,当他站在宋代龙窑遗址前点燃香烟时,我的思绪忽地豁然开朗,即兴写完一首诗,结尾这样写道:“同伴在龙窑前点燃一支香烟 /燃着了千年窑火。”更有意思的是,在瑶里古镇的程氏宗祠里,我巧遇单位的两位同事,她们是利用双休日前来领略浮梁风光。三个人像孩子一般欢呼,直嚷着要合影。感觉心胸忽然被阳光打开一扇门,鲜花怒放,快马轻裘,只有在浮梁,我才找到了如此的感觉。
东埠是此行的最后一站。作为地地道道的高岭人,冯云龙难以抑制内心的澎湃,他音调高亢、绘声绘色地讲述记忆中的古村轶闻,曾经的东埠似乎复活了。高岭土、独轮车、瓷土船、瓷茶商一众元素走出历史的烟尘,在东河之上点起一盏盏渔火。冯云龙特意引我们去古村的上街头观看一块清代禁碑。清代乾隆年间,浮梁、婺源两地船户为争夺瓷土运输资源发生纠纷,最后由饶州府、浮梁县出面,裁决,明确规定由瓷土客商选择,“不得妄自分清界限”。眼前的东埠早已恢复平静,几声棒槌,化为水语言的一部分。
作家们在浮桥边的香樟下歇脚,静听东河绵绵不休的倾诉。停下来就舍不得起身了。我们即将像那些运输高岭土的船工走向浮梁外的世界,这一别,千山万水,红尘遮蔽,不知何时再能握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