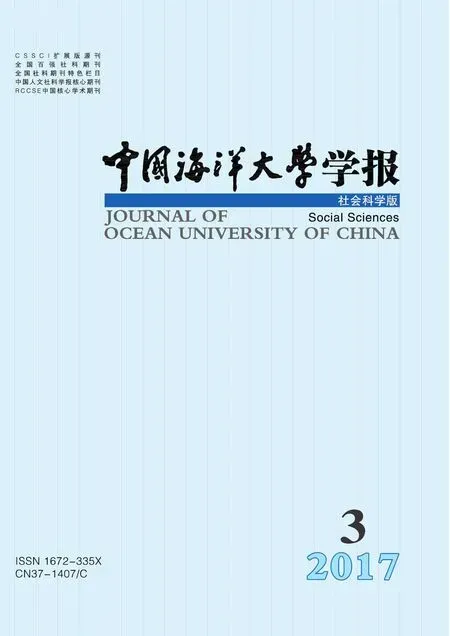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宪政的国际法路径设计
刘学文
(西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2)
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宪政的国际法路径设计
刘学文
(西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2)
农业生产的弱质性和粮食安全的战略性使得国际农产品贸易充斥着保护主义因素。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实际上加剧了贸易扭曲和不公平。具体形态表现为与农产品有关的多边贸易关系的不公平、国际贸易规则的不公平、相关主体的不公平和国际贸易行为的不公平。因此,农产品公平贸易须置于由宪政的国际法所推动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之中予以推进。最根本的是要实现程序公平和实质公平之统合。程序公平的实现须完成治理体系的正当性论证。而实质公平则有赖于构建多元主体民主参与和公民本位的贸易民主化治理机制,强化国际法与国内法在宪政的国际法框架中的联动,以及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争议解决机制对农产品贸易规则的司法造法功能。
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宪政的国际法;程序公平;实质公平;正当性
当前的国际体系是一个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建构于民族国家(nation-state)之上的“现代国家体系”(modern state system)。*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一个法学概念,具体所指的是对内对外都代表着主权的国家权力,而空间上则拥有明确的领土范围,即国土,社会层面上指的是所有从属者的结合,即全体国民。国家统治建立在成文法形式上,而国民是在一定的国土范围内通行的法律秩序的承载者”。(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包容他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该体系强调民族国家主权的至上性和绝对性,容易引起国家之间的疏离或者对抗。二战以来,无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在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南北之争”时期,该体系均被西方国家所掌控,这使得国经济法及其规则呈现出较强的地缘性。[1]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几乎所有产品从其原料采购、生产、交易到消费的整个环节均被纳入全球产业链之中。因此,全球化这种当今世界各国更加紧密的“一体化”已经引出了对更多共同行动的需要。[2](P309-323)共同行动则是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的基础,而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的重要手段则是国际法。*美国天普大学比斯利法学院教授杰夫瑞·唐纳福(Jeffrey L. Dunoff)和塔夫斯大学弗莱彻法学院教授乔尔·荃齐曼(Joel P. Trachtman)认为,全球化与国际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一方面是因为与全球化相关联的跨国活动引发了对包括国际经济法在内的传统国际法中众多规范的更大需求;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国际经济法促进了与全球化有关的商品、资本、人员和思潮的跨国流动。See Jeffrey L. Dunoff, Joel P. Trachtman,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Constitutionalization”, in Jeffrey L. Dunoff, Joel P. Trachtman, eds., Ruling the World? Co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Law, and Global Govern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36.未来国际农产品公平贸易的实现务必在自由贸易和公平正义理念指导下,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通过适用国际法的原则和强行法予以推进。最根本的是,应坚持宪政的国际法治理路径。宪政的国际法在规范层面确立了个人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在功能层面厘定了个人基本权利与国家主权权力二元关系的法律边界;在价值层面将个人的价值与人类共通的价值作为本源性和终极性价值置于重要地位。[3]但如何在宪政的国际法范式下完成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的构建,则值得深入探讨。
一、农产品不公平贸易亟需公平的全球贸易治理法律机制
(一)农产品不公平贸易的具体形态
“公平”(fairness)和“正义”(justice)所解决的是个人和国家社会生活的根本性问题,当无疑义。[4](P26)公平贸易有着复杂的概念分歧,在实践中也是被任意使用的。公平贸易本身内含公平性、互惠性与对等性等价值属性。[5](P21)因此,公平贸易是一种具有价值偏向性的贸易形态。而关于公平贸易内涵的基本界定,笔者赞成黄进教授的观点,即公平贸易至少应包括多边贸易关系的公平性、国际贸易规则的公平性、国际贸易主体的公平性,以及国际贸易行为的公平性几个方面。[6]而考查其不公平,也应从这几个方面着眼。结合黄进教授的观点,笔者认为,农产品国际贸易领域的不公平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农产品多边贸易关系的不公平。如前所述,建构在民族国家这一体系之上的多边贸易体系是“权力导向型”(power-oriented)的结构,故该体系从一开始就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多边贸易规则的公平性推进。在这一体系下,“个人—国家”体系受到国内法的规制,而“国家—国际社会”则又受到国际法的规制,中间隔着难以逾越的主权屏障。因此,农产品多边贸易关系的推进总体上受到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不公平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从关贸总协定阶段开始直至今日的多哈回合谈判,农业谈判的艰难旅程再次证明了这种多边贸易关系的不公平性。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巨大的贫富鸿沟所引发的对不同利益主张的核心关切,使得多边贸易谈判变成讨价还价的商场,共识性的成果难以达成。而横亘其间的主要是国家利益。
其二,农产品国际贸易规则的不公平。这种公平性不足在程序公平和实质公平两个方面均有所体现。*偏好稳定和秩序的正当性(程序性的恰当的过程)与注重变动的分配正义(实质性的)是“公平”(fairness)的两个方面。据此,她将国际法和国际机制中的公平划分为“作为程序公平的正当性”(legitimacy as procedural fairness)和“作为公平的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 as fairness)两种类型。正当性是公平的关键要素,表达出对秩序的偏好,它提供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即一个公平的规则体系应牢牢地扎根于这些规则如何被制定、解释和应用的形式化框架之中。与正当性不同之处在于,分配正义作为评价法律的后果性影响,其根植于法律体系赖以运作的共同体的道德价值。笔者立基于托马斯·弗兰克的理论,并结合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人的学说,为"正当性"(legitimacy)设定了透明度、权威性、安全性、确定性、一致性、形式有效性和可责性七个核心要素。为确保“分配正义”的“衡平”(equity)则设定了罗尔斯“复数正义”、哈贝马斯商谈正义、“公民本位”下多元主体参与的贸易民主、WTO“司法宪法化”、特殊与差别待遇、对等原则、反向协商一致原则等核心要素。See Thomas M. Franck, Fairness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stitu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7-9.概括起来,主要公平性缺陷表现在:第一,在程序公平方面的缺陷。很多现有的多边贸易规则由于谈判时备受争议而采取了较为模糊的措辞,或者回避对一些关键术语作出清晰界定(如对“农业补贴”、“农业生产者”未作定义),一些条款的设定缺乏可操作性。这导致很多规则难以符合程序公平之正当性的各项要素。第二,在实质公平方面的缺陷。一些多边规则的设置从实施结果来看显然更有利于部分成员。如“肮脏的关税化”仅满足了程序公平的要求,从削减的效果来看,仅有一些无关紧要的产品关税得以削减,重要产品依然保留高关税,从本质来看并不符合实质公平;再比如农产品特殊保障措施设置严苛的触发程序,实际上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援引。此外,世贸组织成员方目前尚存在着广泛的信息和权利的不对称状态,在争端解决机制中也存在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不均等的问题。[7](P81-83)这都是对实质公平的背反。
其三,农产品贸易相关主体的不公平。国际贸易主体一般在狭义上被理解为国际贸易中的交易主体,实际上还包括国际贸易的管理主体。自1990年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国际贸易已不再是仅由公司这一单一主体相互竞争的格局,而是出现主体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有230多个国家与地区介入国际贸易的竞争之中,因此主体不仅包括国家、经济一体化组织、特别关税区政府和大量的跨国公司。[8](P226)因此,以全球视野观之,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存在的主体之间的不公平至少可以概括为国家与国家间的不公平、国家与区域一体化组织之间的不公平、交易对象相互之间的不公平、农业生产者与贸易商之间的不公平、不同国家的消费者之间的不公平。以国家之间的不公平而言,由于发达国家的科技与政策优势,高度保护的农业补贴和支持体系使得其农产品对外出口极具竞争力,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出口式微。一些国家的农业与农产品贸易在融入区域一体化的多边体制中走向崩溃,这以“墨西哥农业危机”最为典型,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没有解决好制度安排中的公平问题。高度保护的农产品贸易无论是在各国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都引起严重的分配正义问题。我们发现,全球产业分工以及产业链的积聚正在重塑国际分工。而旧有的治理模式则对农产品贸易形成扭曲,这一扭曲进一步加剧了农产品贸易及其上下游诸多主体利益分配上的不平衡,进而从根本上引发了对公平价值的拷问。最后,农产品具有品种集中特性,而这些品种集中的农产品贸易极易被跨国公司所控制,而跨国公司通过对食用农产品的垄断与控制,对发展中国家形成十分明显的侵夺态势。总之,当前的农产品国际贸易在多边框架安排中趋于保守、形成的成果不多,而与农产品有关的诸多贸易规则由于公平价值的缺乏,很可能会加剧贸易主体之间的不公平,因此亟待通过公平价值导向下的宪政的国际法改变这一现状。
其四,农产品国际贸易行为的不公平。这可能引发不公平的农产品贸易行为主要包括农产品的倾销行为、补贴行为、技术性贸易壁垒行为、社会壁垒行为、不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行为等,当然这与发达经济体普遍实施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紧密关联。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对农业实施一定程度的保护。农业发展水平、科技与法律发达程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国的农业保护水平,这就决定了发达经济体一方面实施高水平的农产品补贴与国内支持以提高本国农产品对外竞争力,另一方面高筑贸易壁垒以限制外国农产品进口。这便引起了农产品贸易的扭曲和不公平。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因农产品贸易扭曲引发的农产品贸易摩擦呈现出加剧之势。农产品国际贸易中集合了众多贸易手段,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也极易与农产品贸易发生结合。
(二)农产品公平贸易须置于公平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之中
全球化趋势加快所造成的挑战远非经济结构受到冲击那么简单,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治理结构亦受到重大挑战。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促使我们静下心来思考哈贝马斯所称“全球公共领域”的治理问题,[9](P1-5)国际农产品贸易问题亦需被置于这一背景中进行考量。经济全球化已然对新时期的全球贸易治理提出要求。为此,有人主张当前讨论全球化应该讨论更为重要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问题,而全球治理的法律体制安排则要受到一定的价值指引,这又进一步涉及“全球正义”(global justice)和“国际公正”(international justice)问题。*See Amartya Sen, “Global Justice: Beyond International Equity”, in Inga Kaul, I. Grunberg and M. A. Stern, eds.,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And see Amartya Sen, “Justice across Borders”, in Pablo De Greiff, Ciaran Cronin (eds.), Global Justice and Transnational Politics, MIT Press, 2002.
因此,农业全球化在未来应分别被纳入国内治理机制与国际治理机制共同组成的双重治理框架之中。当前,与农产品贸易相关的诸多私人主体在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利益冲突,最后集中表现为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全球化时代传统的“二元分立”法律控制模式受到了挑战,“个人—国家”和“国家—国际社会”的双层分立式组织结构出现分化。在国内层面,传统国内法体制仅规制国内私人经济事务,而对于跨国私人经济事务仅表现为“消极的禁止权或限制权,而不具有积极的扩展和保障权”;在国际层面,传统国际法致力于对国家等国际公法主体权益的保护,而疏于顾及非国家主体,即个人、法人等私人主体之权益的保护。[10](P208-230)这一“二元分立”的状况已无法适应农业全球化对国际分工与合作的治理需要。正如杰克逊所言,全球化引起的核心问题需要发展出一套与之相配套的国际制度。近年来围绕WTO宪政化发展出制度管理主义的宪政、以权利为基础的宪政和司法造法的宪政三大理论流派,目的在于通过贸易民主合法性,设定一系列关系的元规则,以保障贸易民主化,并在全球福利分配的过程中更多地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进而满足全球治理的实际需要。[11]但是,在国际贸易治理过程中,突破贸易自由化、贸易保护主义的博弈,探索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贸易则十分重要。
公平贸易是一种具有价值偏向性的贸易形态。而价值则又是十分抽象、深奥、玄妙和模糊的哲学术语,如果不为其确立标准,则这种贸易形态注定是凌乱的,因而也是容易被随意解释和滥用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公平贸易被发达国家滥用,一度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挂在嘴边的“陈词滥调”的原因。*李春林博士总结了公平贸易三个方面的鲜明特征:(1)体现出明显的单边主义性质;(2)体现出强烈的国家战略性;(3)体现出标准的双重性。参见李春林著:《贸易与劳工标准联结的国际政治经济与法律分析》,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38-140页。因此,笔者认为,农产品公平贸易应被置于全球贸易治理的框架中予以评定。而全球贸易治理最根本的是依赖国际法,因此,农产品公平贸易中的“公平”即是要体现国际法的公平价值。而托马斯·弗兰克则为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确立了基本的公平标准,即程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二分法。故农产品公平贸易与托马斯·弗兰克关于程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二分法具有内在的关联,或者说这种二分法能够作为农产品公平贸易是否体现全球分配正义的重要标准。
二、农产品公平贸易“五层楼”治理层次论及其正当性论证
(一)农产品全球贸易之“五层楼”治理层次论
黛博拉·凯斯(Deborah Z. Cass)总结了内尔·沃克(Neil Walker)提出的将国际贸易宪法化理念转换成一个渐进式过程、拟定国家、地区和国际治理的相互作用和边界、进而完成从治理层次的渐进式设计的观点,随之提出了WTO宪法化的“五层楼”(five-storey house)的层叠式治理模型,每一个楼层代表了一个治理的层次,即从“亚地方的”(sub-local)治理层次开始,通过“地方的”(local)治理层次、“国家的”(national)治理层次、“区域的”(regional)治理层次,最后到“国际的”(international)治理层次。[12](P240)而对于这“五层楼”模型的具体设计,黛博拉·凯斯则是语焉不详。针对黛博拉·凯斯所倡导的有关国际贸易组织宪法化“五层楼”的层叠式治理模型,笔者运用该理论,就农产品国际贸易治理的宪法化进路作出如下图所示的设计。

图1 农产品全球贸易“五层楼”治理层次示意图
上图是笔者对黛博拉·凯斯有关WTO宪法化进程“五层楼”层叠式治理模型在农产品领域的演绎与应用。详言之,关于农产品全球治理的“五层楼”层叠式治理模型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一楼”:亚地方的治理层次。主要指的是在国家内部地方以下的局部范围内形成的以利布曼(Liebmann)所倡导的社区协会(community associations)[13](P174-175)等实体为基础的治理体系,属于最基础的治理层次。于农产品贸易治理而言,某一地方的农产品行业协会或某一自治性共同体基于不同的市场、组织形式、企业集团、农业生产单位(如农场、农业生产基地、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等形成的自治性农产品贸易治理机制。在这一治理层次中,通常会形成一个组织严密、生产经营高度一体化、对外具有统一议价能力和开展对外合作与交往能力的经济实体或者法律实体,内部具有统一的标准和自治性规范,对外有统一、一致的话语权和行动。亚地方的治理层次实为未来全球农产品贸易治理层级中最基础的单元,也是农产品民主治理的重要权源;亚地方的治理层次其治理能力也是未来判别一国农产品贸易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其二,“二楼”:地方的治理层次。指一国内部地方一级的以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规范为核心内容的制度建构。此处地方的治理层次指的是“新地方主义”(New Localism)的治理层次。地方的治理层次作为多层治理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立基于地方,但又不局限于地方的传统边界;它强调分权化主导下的地方权力使用效能与自主管理能力,也提倡各个层次的政府之间、政府与市民社会之间、政府与民营企业以及公共机构之间、政府与农户之间形成广泛的合作互助关系。[14](P384-386)对农产品贸易治理而言,地方的治理层次强调的是地方政府、农产品行业组织、农业自治团体、农场主、牧场主、农户、消费者等多元主体相互之间的,以规范化、有序、民主协商为主要方式的管理、互动和合作关系。
其三,“三楼”:国家的治理层次。指的是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在国家立法层面围绕农业生产、价格支持、农产品市场准入、农产品质量安全等进行的对农产品治理所作的制度安排,表现为宪法性规范、法令、条例、指令(在中国表现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不同类型的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同时也体现为国家对外通过参与谈判、缔结条约、解决贸易争端等外交、缔约、司法等活动。美国、日本等国家有关农产品贸易规则的国家立法、法令、规章制度以及技术标准、技术评定程序等,均是国家治理层次的重要法律渊源;区域贸易协定、双边贸易协定中有关农产品制度安排也属于国家层面的治理。而国家农产品治理层次的主体是国内包括国家、公共机构、企业、个人。这些多元主体平等、民主地参与全球农产品治理的过程,公平地分配资源,是符合全球分配正义的农产品公平贸易法律治理的核心路径。
其四,“四楼”:区域的治理层次。指的是超越国家层次的一些区域一体化实体所确立的有关农产品的治理路径,该层次是“多边形式”全球贸易治理的另一种形式。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从欧共体到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简称CAP),这一农业一体化治理路径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参与缔结了区域合作协定,很多区域合作协定都有关于农产品的安排,世界范围内的区域合作协定相互交叉重叠进而形成“意大利面碗”效应(Spaghetti bowl effect)。*“意大利面碗”效应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于1995年在其出版的《美国贸易政策》一书中提出的,由于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所设定的差别性原产地规则和优惠待遇犹如意大利面条,盘根错节地纠缠在饭碗里,其复杂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系形成负面侵蚀。参见于津平:“国际贸易新格局与全球贸易治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74页;同时参见程大为:“全球贸易治理中多边主义、诸边主义和大区域主义的比较与选择”,《经济纵横》,2014年第4期,第97页。但是,区域合作的负面效应亦十分明显,其改变了国家之间在国际贸易领域合作与竞争关系的格局,代之以区域集团的关系。因此一方面具有很强的歧视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贸易扭曲;另一方面,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向整个区域范围扩散;最后,区域合作还可能进一步削弱成员国在全球多边贸易合作中的积极性。[15]因此,区域治理层次与其它治理层次的协调与互补十分重要,区域农产品的治理尤其要强调其对国际治理层次形成有益补充。
其五,“五楼”:国际的治理层次。国际的治理层次是全球贸易治理的最高一级的“多边形式”,主要指的是从关贸总协定到世贸组织的多边贸易治理体系,这是农产品贸易治理的最高治理层次。其理想状态是立足于“全球市民社会”的治理背景,包括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私人、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简称NGO)等诸多主体广泛参与的、以农产品国际法规范为主要内容的治理层次。规范的内容表现为条约国际法、习惯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等,对于促进在全面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贸易的共同治理具有重大作用。国际农产品公平贸易的最终实现也主要寄希望于在WTO框架下多哈回合谈判中取得更多的一致成果,越是广阔的自由化市场,越有利于孕育农产品的公平贸易。
综上,高水平的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形成势必要依赖以上“五层楼”层叠式模型所确立的五种治理路径的携手并进,任何一个层次都不可偏废。它们是彼此补益、互相促进的递进式关系。由于治理的实现主要依靠法律,而国际的治理层次和区域的治理层次主要依靠国际法规范,地方的治理层次和亚地方的治理层次则主要依靠国内法规范。而居于中间的国家的治理层次最为重要,其既依赖国际法规范也依赖国内法规范。而且这一治理层次还承担着农产品贸易治理国际法与国内法联结与互动的重要使命。当然,这一联动是通过宪政的国际法实现的。从根本上来讲,主要依赖国家层面农产品治理能力的强化,同时也要依赖农产品多边贸易规则跨越国界的“国家间”次序的有效构建。该“五层楼”治理层次的构建正如楼层的建设,是从最底层的亚地方治理层次开始并最终达致最高的治理层次,这种“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治理路径则为全球农产品贸易治理搭建了民主的基石。各个治理层次的形成和构建均对下一层级的治理产生依赖。
(二)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中公平价值的正当性论证
“正当性”(legitimacy)一词在我国通常被译作“合法性”,与“合法律性”(legality)相区别。陈征楠认为,正当性属于实践哲学的“基石概念”,也是贯穿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三者的媒介概念。其大致意思是指“对人类实践活动具有指导力的某种规范的合理效力或价值属性,该种效力或属性通常以此种规范事实上所获得的认同为现实表现。”因此,正当性也被用来描述实践主体和可能对主体行为产生影响的规范标准之间的关系,特别用以指称某种规范准则所拥有的被尊重与服从的应然属性。[16](P21-25)托马斯·弗兰克基于正当性和分配正义两个独立变量构建起公平价值的二分法,认为国际法和国际制度中的公平其实就是如上两个变量的混合体。她据此将这一公平分划为程序公平和实质公平,[17](P26-27)这也是本文的基本分类标准。
置身于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世界各国对公平贸易的强调无不将一些劳工权益、动物福利、环境保护、公共健康、知识产权、公平贸易标识等问题与农产品贸易本身的公平进行联结,使得农产品的贸易规则越来越多地体现各种类型的价值考量。因此,农业全球化已将农业产业链以及农产品贸易置于全球市民社会中。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高筑贸易壁垒的农业治理模式已然式微,这也是农产品领域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农产品贸易摩擦大量出现的根本原因。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的路径从根本上讲应以法律为核心,或者说未来的农产品公平贸易的实现亟需置于国际贸易宪法化的框架中考量,而公平贸易的起点是解决农业相关规则的正当性问题。具体来讲,即要考量国际农产品贸易规则在多大程度上依照参与者认为的权利义务关系和满意的程序制定和实施。而农产品贸易治理所依赖的法律应当包括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两个层面。从国际法层面讲,主要指的是不断完善WTO框架中的农产品公平贸易纪律,包括完善以《农业协定》以及与农产品贸易相关的诸如《1994年反倾销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保障措施协定》、《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技术贸易类协定》为主要内容的实体法规范,也要同时完善以《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贸易政策审议》为代表的程序性规范。从国内法层面来讲,主要指的是各国在多大程度上实施了国际贸易规则,以及实施的效果如何。当然,法律的正当性并不太关注其适用的结果,它仅仅设想法律被一致地应用到每一个相似的情形中,而不考虑这种普遍适用可能导致的不公平的结果。[18](P174-175)因此,法律正当性只是初级的公平性要求。笔者认为,具体要做到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正当性的要素主要包括透明度、稳定性、权威性、形式有效性、可责性等。透明度指的是缔约方实施的各类与贸易有关的行为、法律、条例、司法行动,以及可能影响缔约方之间国际贸易政策现有规定,须及时公布。作为基本原则,应贯穿于农产品贸易治理的法律体系中。如《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第19.10条为落实缔约方的合作,设定了“透明化与公众参与”原则。权威性指的是规则的制定符合法的正当程序,规则的施行公平公正,规则的效力能够平衡各方的利益。稳定性强调农产品贸易规则要前后统一、具有可持续性,这能最大化地确保当事人获得对其行为的可预期性。而形式有效性和可责性则强调规则体系对法律事实的调整应做到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个人等行为应服从于规则的形式效力,不得逾越规则的禁止性规定;行为一旦违法,行为人则要受到法律的谴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其二,国际农产品公平贸易的全球治理体系要确保在规则的制定、应用和解释,以及裁决的执行等方面均在法治的框架之中进行,特别是倡导司法宪法化路径的重要性。一方面,只有在民主的法律程序之中,各类双边的、多边的贸易机制的构建过程才能真正有助于消弭贸易分歧、达成共识,避免和消解国际层面的农产品贸易规则以及国内层面的农业法律与政策中的单边主义、“碎片化”、扭曲性等特征。另一方面,只有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深刻体现哈贝马斯所倡导的商谈正义,即通过交流对话、确保多元主体的参与、保障程序公平,才能使劳工权益、动物福利、环境保护、公共健康、知识产权、公平贸易标识等与农产品贸易相联结时体现全球分配正义的要求。
总之,只有以具体明确的实体规则、民主透明的程序、衡平的价值、宪政的国际法制度演进策略搭建的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才能真正经得起正当性的叩问。
三、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的民主参与和公民本位之塑造
(一)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民主参与的理论框架
农产品全球贸易已经深受国际与国内贸易治理体系之外传统因素的影响,而且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环境保护、劳工权益、公共健康、动物福利等因素都已开始深入人心。因此,未来的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亦应考虑贸易民主化的价值诉求。正如瓦伦丁·莫加丹(Valentine M. Moghadam)所言,当前的全球化进程催生和塑造了跨国集体行动,全球化因此也遭受批评和怨怼。但全球化创造了集体行动的机会,特别是它创造了构建跨国合作和动员框架的机会。[19](P34)其实,为WTO所构建的多边贸易体系在跨国合作框架的建设方面是素有成就的。正如黛博拉·凯斯所言,WTO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扮演一个开放市场或者协助抑制“特殊利益”的立法者角色,它的重要性在于成功地推动全球化向跨国参与的新形式即全球民主形式的转型。[12](P241)但是,WTO由于多边谈判的举步维艰,当前正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而WTO多哈回合艰难推进的最大原因在于各方在农产品议题中分歧严重,难以达成一致。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贸易汇集了太多的利益诉求,博弈难度甚大。在这一情形下,全球贸易民主更应提上日程。
哈贝马斯对此诉诸其商谈理论与程序民主模式,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国际法规则的安排既要充分尊重民族国家的文化独立性,更要保障民主和基本人权。因此他主张通过民主的程序进行国内法律的合法性论证,而在国际法领域则有必要构建一个民主、协调一致的国际公共领域,在该公共领域中通过民主的程序构建规范意义上的治理机制和秩序。[20](P137)如果讨论将哈贝马斯的思想运用于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之中,与此相关的则是哈贝马斯民主结构的思想。笔者具体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阐释:
第一,基于民族国家的传统农产品治理模式存在落后性。如前文所述,当前无论是农产品有关的多边贸易规则抑或是各国的国内农业与贸易立法,均是建构在传统的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为了国家利益最大化,国家在国内对农业提供多类型的政策支持和补贴,或者对外一方面高树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另一方面极力促进农产品出口领域的自由贸易。这种双重标准的确立很明显地映射出各国在农产品贸易政策安排上的单边主义倾向,这正是为哈贝马斯所批判的,因为它从根本上动摇了为他所建构的商谈理论的根基,也与罗尔斯复数正义论中第二个原则的第一部分“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不一致。
第二,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应进入程序化的民主商谈路径。如果将农产品的贸易治理体系扩而广之到国际层面,按照罗尔斯的正义标准,则要寻找虚幻的世界政府,在当前来看是这一想法是不合时宜的。哈贝马斯为此着眼于商谈理论与程序民主模式这一程序正义的路径。依据该理论,农产品公平贸易的实现无论是农业规则的谈判、农业协定的签订、农产品贸易争端的解决、对现有多边贸易规则的解释与适用,都应被纳入严格的理论基础和程序之中,各种意识、话语和价值的交锋、碰撞均应体现主体性、主体间性、语言性、开放性、可理解性、真实性、正确性等。[20](P98-99)总之,应置于商谈理论与程序民主模式之中。
当前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过于倡导经济效益的优先价值问题,而对于从自由贸易推衍而出的普遍价值和社会问题则置若罔闻。且缺乏从国内到国际两个层面的民主参与和民主问责机制,因此WTO的制度设计运行中未能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内涵。[21]民主与正义一样,不仅适用于国内社会的各群体之间,同样适用于功能各异的国际社会群体之间。现实情况是,单纯依靠一国的国内法难以有效保障公民的利益,这就产生了创制新的国际规则为国际公共物品的治理提供符合民主、法治、正义理念的制度供给。
实际上,治理的正当性首先来自于民主的制度安排。欧盟内部为了有效解决治理的正当性问题,通过在欧盟法中体现参与性、协商性和国家间民主等要素,不断补充和完善欧盟成员国内部的“代议制民主”。[22]这一贸易民主的实现须依赖“五层楼”层叠式治理体系的搭建,而这一过程则又要在现有的多边贸易体系的基础上进行构建。对于主权林立、利益诉求多元化的国际社会而言,在哈贝马斯商谈理论指导下,内含协商、博弈与妥协等要素的程序化的民主商谈过程则十分重要。或者说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农产品国际贸易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二)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中多元主体的民主参与和公民本位
1、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应基于多元主体的民主参与
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看,贸易摩擦所涉主体最为广泛,不单纯表现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贸争端。农产品贸易摩擦的主体除国家之外,涉及诸多国际经济组织,同时涉及国际和国内的诸多主体。任何农产品贸易摩擦的解决都涉及对各方利益主体的利益再分配,如WTO反补贴调查的裁决很可能影响出口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国际农产品公平贸易的治理体系首先要依赖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多元主体的民主参与。当前的全球贸易治理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民主参与缺陷”问题,引起人们对WTO等贸易治理平台的民主正当性拷问。[10](P17)只有从多元主体的角度广泛思考和关照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中各方的利益需求,才能真正做到保护动植物卫生以及人类健康、生态环境和基本人权。这就要求未来农产品贸易规则的制定、解释、执行要综合考量民主参与性和价值,深刻体现程序公平的正当性价值,也要体现实质公平的衡平性价值,最终实现农产品领域的全球分配正义。
然而,制度的需求与供给之间总是充满沟壑。当前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的最大缺陷在于民主参与的主体不足。主体参与的缺失,一方面使得贸易政策缺乏公平性或公信力,另一方面可能引起无参与权的法外主体为贸易繁荣带来的反作用力。如2003年9月WTO部长级会议在坎昆召开时,发生数千人规模的反对全球化的游行示威事件;再比如2015年12月,在WTO第十届部长级会议主会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对美国废止多哈回合谈判、以新机制取而代之的表态掀起强烈抗议。尽管抗议者的观点并不总是明智的、甚至可能会无理取闹,但是其中为数不少的人所提出的一些思考和关切的确为公共理性的发展做出了建设性的贡献。[23](P409)总之,多元主体民主参与的制度安排的缺失容易引起正当性程序之外的法外诉求。
关于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的多元主体,应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进行通盘考虑。既要考虑作为传统国际法主体的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包括全球性的和区域性),还包括国际公共机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实体基于各自的利益进行的民主参与;在国内层面也要考虑农产品产业链中的诸如农业生产者(包括农场主、牧场主、普通农户,以及家庭联营实体)、农产品进出口商、农业与农产品行业协会,甚至消费者等多元主体的民主参与。其中,关于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概念应该进一步明确,如果不予以明确,将无法保证农产品公平贸易的全球治理需求。就我国而言,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概念应当包括农产品产前、产中和产后整个过程中的相关主体,既包括普通的农户,也包括具有法人资格的农场、农业专业经济合作社、农业生产加工企业等。[24](P291)这意味着农产品贸易谈判的推进、多贸易规则的创制、贸易争端的解决应基于法治化的民主参与程序,使得与案件有关的利益相关主体公开透明地了解和参与案件的有关过程,明确表达利益诉求,决定、裁决的作出均符合正当性的法律程序。
在对透明度、权威性、稳定性、形式有效性、可责性等要素进行正当性论证的前提下,贸易中的诸多价值联结并不总是失当的,只要规则的制定基于民主的国际缔约程序以民主商谈的谈判模式达成,而非基于一国的单边行动。包括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等诸多主体在“多层全球治理”框架之中开展的单边行动、双边与多边(包括全球性与区域性)协作,或者在“全球市民社会”中采取的国际行动,均是基于与国际法发生直接或间接联系的诸多全球治理手段。如趋同化的单边法律与政策、双边与多边(包括全球性与区域性)的多层次国际法之深度拓展。[25]这是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走向公平的核心要义。
2、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主体应坚持公民本位
全球贸易治理中的主体问题十分重要,王贵贤博士在其合著作品中对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全球正义理论进行了对比考证。认为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在论述全球正义的主体问题时保持了理论上的一致,均遵循了康德的传统,两人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理论扩展至国际层面。罗尔斯走得较远,他所寻求的全球正义基本上全然否定了国家的主体地位,认为只有自由民主的人民才是国际“社会的行动者”。而哈贝马斯则试图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进行调和,认为当前的“权宜之计”是尊重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和自觉性,但要形成“世界公民的意识”,故他认为公民与公民行动应先于政府做出自我调适。最后,王贵贤认为,全球正义所谋求的目标不仅仅是国家之间在政治地位上的平等,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则应称为核心关切。因此其结论是:全球正义所保障的主体,更多应面向个人而不是国家。[20](P103-104)在该意义上说,个人是全球正义的真正受益者。因此,在全球治理环境中倡导个人主体的公民本位十分重要。实际上,随着以个人为代表的私人主体在国际社会基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反思而掀起的风起云涌的跨国社会运动,使得“全球市民社会”这一独立的社会和政治空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悄然兴起。“全球市民社会”指的是在全球思潮与人类共通价值为基本导向,以实现全球公共利益为主要内容,各类非国家实体和私人广泛参与的非政府性国际公共空间。[26]“全球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跨国力量的出现,反过来又从功能、概念等方面对国际政治和国际法产生影响,不受约束的传统单一民族国家的主权权力被注入更多的权利要素。[27](P1)因此,国际公共空间的存在提出了全球治理之需求。安德鲁·哈雷尔(Andrew Hurrell)认为,一个合法有序的国际社会要应对三重挑战,分别是:第一,寻找共同利益;第二,规制不平等权力;第三,调和差异与应对价值冲突。[28](P287)而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作为一种程序主义的民主理念,则有助于担负调和差异、沟通和达成一致,进而构建行之有效的治理机制。
完成从传统的主权国家的统治模式向全球治理模式的转换,其实质就是由多元化的权威场域所引发的治理主体的民主化,全球市场渠道与全球市民社会的决策过程融入了诸多价值诉求。因此,全球正义不只是实现国家间正义,其终极目标应当是在全球层面有效实现个人正义。[29]无独有偶,著名国际经济法学家也持大体类似的观点,如彼得斯曼认为,由杰克逊推崇的国际经济法宪法化理论使用了一种“公民导向”(citizen-oriented)的宪法化方法,深入考量了全球产业链中利益相关主体的切身需求,同时兼顾国际规则和组织的民主正当性以及权力制衡的必要性。[30]
总之,从国际贸易规则宪法化的发展趋势来看,公民本位将是未来考评农产品贸易是否公平的重要标准。公民本位意味着未来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中贸易规则的适用要超越民族国家的藩篱,在全球市民社会的视野中思考对农产品这一“国际公共物品”的治理问题。而关于农产品规则的安排首先要考虑私人主体的切身利益,如反倾销制度中引入公共利益的问题就着重体现出了这一点。总之,基于民主协商、正当程序、公民本位的农产品贸易治理体系,便获得了正当性的法律基础,也赢得了贸易民主的程序考量。
四、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联动策略及DSB司法造法功能之发挥
(一)宪政的国际法背景下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联动策略
国际法与国内法两者的联动,需要的是法律全球化特别是宪政的国际法的助力。刘志云教授立足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全球化理论,结合当前世界范围内法律变革的现状和趋势,认为法律全球化“是从广度、深度、速度、影响等角度对不同地域、不同领域以及不同层次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的交流、重叠、竞争、秩序化乃至一体化的进程或趋势的描述”。它在各国国内层面上体现出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的相互融汇,以及不同国家国内立法上的趋同。在国际层面表现为对所涉领域范围的扩展、层次的加深、影响力的加大等演进趋势;而在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上形成的“国际条约之效力优先于国内原则”,有效地保证了两者之间的逐步统一。[31](P477)因此,全球贸易治理需要法律全球化的推动,而要考虑的最根本性问题便是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联动,仅仅研究国际法或者仅仅研究国内法均不能透彻解析全球贸易治理的核心问题。
而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联动,其策略是复杂的。具体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符合民主商谈理念的农产品贸易体系的宪政的国际法推进,使得与农产品有关的各类国际、国内法主体广泛参与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促进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全面融合。主要表现为,多边贸易规则应开放和扩大利益相关的私人主体对于规则运行过程的参与度;各国国内贸易法规也出于保障公共利益和私权的需要,扩大私人参与贸易政策制定、贸易纠纷解决的权利。第二,将自由贸易理念、公民本位的价值理念深刻植入农产品国内与国际治理体系之中,推动国际农产品贸易规则对于私人主体权利的保障,以及国内法对农产品全球治理责任的制度化回应。第三,确立多边主义框架下共同治理机制的农产品贸易价值体系的引进与推行,以及符合程序公平之正当性与实质公平之衡平性相结合的公平理念的指引。第四,通过法律移植、转化,使得国际法规范融入国内法体系之中,同时国内法也通过授权、审查、裁决国际案件,以达到促进国际法完善之目的。第五,通过国内农业立法对国际农业贸易谈判、缔约、司法的施加影响,以此推动国际法规范的完善。
(二)发挥DSB的司法造法功能,以衡平的方式实现实质公平
WTO争端解决机制构建的以规则为基础、准司法的争端解决体系,推动了多边贸易体系向守法主义的转向。[32](P424)从其二十多年来的发展实践来看,该体系对于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平衡、消除发达经济体的单边主义行动带来的负面影响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根本原因就在于该机制所具有的法律解释与司法造法功能。约翰·H.巴顿等斯坦福大学的几位教授认为,WTO的司法造法行为有着两个方面的重要功能:一是填补法律漏洞,二是澄清法律规则之模糊性。填补法律漏洞主要是指就法律直接规定中缺失的事项进行法律续造,而澄清法律规则之模糊性则表现为就法律规定的某些不明确的事项进行法律解释。这两种造法功能进一步促进了WTO体制的整体性、完备性和连贯性。[33](P78)
以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的视角观之,发挥WTO司法造法的功能对于促进农产品多边法律治理的稳定性,确保国际公平与正义十分重要。这也是实现托马斯·弗兰克所设定的程序公平与实质公平相统合的重要方式。事实上,在GATT/WTO争端解决机构裁决历史上,受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农产品贸易案件的影响,国际法与GATT/WTO多边规则之间产生了微妙的互动,并最终影响了贸易与环境问题的法律融合。1991年和1994年相继爆发的“金枪鱼案”和“汽车税案”,使得人们开始争论一国环境法在国际贸易中的域外效力以及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Processes and Production Methods,简称PPMs)问题。这随后引起了WTO争端解决机构在裁决案件时适用的法律向WTO涵盖协定以外的国际法领域的扩张。也就意味着WTO争端解决机制可能适用的法律规范隐含了《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所列明的规范类型,而且包括GATT/WTO专家组报告和上诉机构报告。[34]WTO裁决争端适用法律上的扩张为其司法造法功能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当前世贸组织规则不完善、公平价值缺陷的情形下,充分利用DSU中的解释功能,发挥法官在案件争端解决中的司法造法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衡平法的作用。使得世贸组织相关规则得到补正和补强,进一步促进了世贸组织多边贸易规则体系内的实质公平。WTO司法造法宪政主义也是实现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的重要路径。
五、结语
农产品公平贸易中的“公平”即是要体现国际法中的公平价值,而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的公平进程最终要在国际法的“良法善治”保障下整体推进。托马斯·弗兰克为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确立了基本的公平标准,即程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二分法。故农产品公平贸易与托马斯·弗兰克关于程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二分法具有内在的关联。当前农产品贸易治理体系中的不公平集中体现在农产品多边贸易关系的不公平、农产品国际贸易规则的不公平、农产品贸易相关主体的不公平和农产品国际贸易行为的不公平四个方面。因此,一方面现有的农产品国际治理体系存在着众多的不公平,另一方面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成为总体趋势。故农产品贸易的全球治理应顺应贸易自由化的总体趋势,在“公平价值导向”下以动态化的制度演进策略作出新的制度安排。在1950年在国际法学界掀起GATT/WTO宪政化研究风潮的代表性人物凯斯将宪法化理念视为一个渐进式过程,拟定了国家、地区和国际治理的相互作用与边界,进而提出国际经济宪法化的“五层楼”(five-storey house)的层叠式治理模型。作为对凯斯理论的演化与应用,笔者为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量身打造了“五层楼”的治理层次。分别是亚地方的治理层次、地方的治理层次、国家的治理层次、区域的治理层次和国际的治理层次。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公平路径依赖以上“五层楼”层叠式模型所确立的五种治理路径突进。五个层次互相补益、彼此融合、不得偏废,呈现出一种递进式的逻辑序列。其中国际的治理层次和区域的治理层次依照国际法规范,地方的治理层次和亚地方的治理层次则依照国内法规范,而居于中间的国家的治理层次最为重要,它的治理既依照国际法规范也依照国内法规范。因此,国家的治理层次需要通过宪政的国际法推动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二者的联动。
农产品全球贸易治理宪政的国际法公平贸易路径首先要求完成正当性论证,这符合托马斯·弗兰克关于公平的二分法中的程序公平之要求,同时也为进一步满足实质公平做好准备。而全球农产品公平贸易的治理体系首先要依赖“全球市民社会”中多元主体的民主参与。既要考虑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包括全球性的和区域性)、国际公共机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实体基于各自的利益进行的民主参与,也要推动与农产品有关的全产业链中的诸如农业生产者(包括农场主、牧场主、普通农户和家庭联营实体)、农产品出口商、农产品进口商、国内公共机构、农业和农产品行业协会,甚至消费者等主体的民主参与。最后,保障WTO争议解决机构在农产品贸易规则的适用中充分发挥法律解释、法律续造,通过司法宪法化路径进行利益衡平,也是推进农产品公平贸易的重要路径。
[1] 何力.国际经济法的地缘新格局[J].政法论丛,2016,(3):11-16.
[2] Narcís Serra, Joseph E. Stiglitz.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considered: Towards A New Global Governanc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8.
[3] 陈喜峰.宪政的国际法:全球治理的宪政转向[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59-162.
[4] Americo Beviglia Zampetti. Fairness in the World Economy: US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Relations[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6.
[5] 王世春.论公平贸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6] 黄进.公平贸易公平吗[J].大经贸,2001,(6):20-22.
[7] Joseph E. Stiglitz, Andrew Charlton. Fair Trade for All: How Trade Can Promote Development[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8] 张汉林.强国之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战略及政策选择[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9]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M]. Translated by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The First MIT Press Paperback edition, 1991.
[10] 陈辉庭.世界贸易体制的变革: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联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1] 左海聪,范笑迎.WTO宪政化:从“司法宪法论”到“贸易民主论”[J].当代法学,2012,(4):148-157.
[12] Deborah Z. Cass. The 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egitimacy, Democracy, and Commun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 Eric H. Monkkonen. The Little Platoons: Sub-Local Governments in Modern History, by George W. Liebmann[J].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26, No. 2 (Mar., 1997).
[14] Richard C. Box. Citizen Governance: Leading American Communities into the 21st Century[J]. Administrative Theory & Praxis, Vol. 21, No. 3 (Sep., 1999).
[15] 于津平.国际贸易新格局与全球贸易治理[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72.
[16] 陈征楠.法正当性问题的道德面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17] Thomas M. Franck. Fairness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stitution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8] Nam-Ake Lekfuangfu. Rethinking the WTO Anti-Dumping Agreement from a Fairness Perspective[J]. Cambridge Student Law Review, Vol.4, 2008.
[19] Valentine M. Moghadam.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Islamism, Feminism, and the Global Justice Movement[M]. Plymouth: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8.
[20] 艾四林,王贵贤,马超.民主、正义与全球化: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1] 范笑迎.WTO宪法化理论之正当性建构:在自由与民主之间[J].武陵学刊,2015,(4):67-75.
[22] (德)E·U·Petersmann 著,王朝恩译.国际贸易中多层司法治理的法治与正义理念[J].东方法学,2013,(5):105.
[23] 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M].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4] 吴喜梅.WTO框架下我国农业补贴立法的建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25] 刘志云.论全球治理与国际法[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87-94.
[26] 蔡拓,刘贞晔.全球市民社会与当代国际关系(上)[J].现代国际关系,2002,(12):1-7.
[27] Veronica Raffo, Chandra Lekha Sriram, Peter Spiro and Thomas Biersteker.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ld Divides, New Developments[M]//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dging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28] Andrew Hurrell. On Global Order: Power, Value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87.
[29] 姚璐,徐立恒,张国桐.论全球正义——关于正义问题及实现路径的分析[J].太平洋学报,2015,(3):7.
[30] Ernst-Ulrich Petersmann. On the Constitution of JOHN H. JACKSON[J].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winter, 1999, 20.
[31] 刘志云.当代国际法的发展:一种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的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32] Hannes L. Schloemann, Stefan Ohlhoff, "'Constitutionalization' and Dispute Settlement in the WTO: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Issue of Competenc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93, No.2 (Apr., 1999), p.424.
[33] (美)约翰·H.巴顿,朱迪斯·L.戈尔斯坦,蒂莫西·E.乔思林,理查德·R.斯坦伯格著,廖诗评译,贸易体制的演进:GATT与WTO体制中的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4] 李威.论WTO/DSB贸易与环境争端的新发展[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12,(4):68.
责任编辑:周延云
The Path Designing of International Law of Constitutionalismon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Liu Xuewe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 710122, China)
The weak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strategic feature of food security fill international tra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 protectionism. In fact, free tra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ggravates the unfairness and distortion of trade.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of trad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can be concluded in four aspects: (1) The multilateral trade rela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re not fair; (2)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are not fair; (3) The related participan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re not fair; (4)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behavior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re not fair. Therefore, the fair tra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hould be assessed under the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framework advanced by international law of constitutionalism.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rocedural aspect of fairness and the substantive aspect of fairness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mean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rocedural aspect of fairness needs to complete argumentation of the legitimacy of governance system.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ubstantive aspect of fairness relies on constructing trade democratic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and citizen-orientation, strengthening the combination of the domestic law and international law under the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law of constitutionalism,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judicial law-making function through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agricultural products;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nstitutionalism; the procedural aspect of fairness; the substantive aspect of fairness; legitimacy
2016-11-07
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科青年学术创新团队科研成果
刘学文(1982- ),男,甘肃白银人,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中国(陕西)自由贸易区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国际经济法、国际法哲学、全球治理研究。
D996.1
A
1672-335X(2017)03-009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