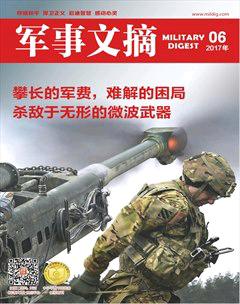叙利亚局势再生变数:化武、空袭与无法到来的和平
巴沙尔意图扩大在北方战线优势的冒险,引发了美国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强度最大的军事报复。而刚刚在第四轮日内瓦谈判中初现雏形的和平进程,极有可能再度全功尽弃。
特朗普终究无法避免走上前任奥巴马的老路,在他不愿投入资源却无法放弃责任的中东展开军事行动。自1月20日他正式就职以来,已经发起了两波大规模空袭,第一次在也门,第二次在叙利亚。
美军空袭汗谢洪
当地时间2017年4月7日凌晨,就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开启访美之旅之际,巡弋于地中海东部的美军“宙斯盾”导弹驱逐舰“罗斯”号和“波特”号向伊德利卜省政府军控制下的汗谢洪空军基地发射了59枚“战斧”巡航导弹,摧毁了这个驻扎有2个中队苏-22型攻击机的机场的大部分机库、储油罐和1个防空导弹阵地。
美国军方宣称,此举是为了报复3天前发生在当地的疑似化学武器袭击事件,以削弱政府军继续动用空中力量投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能力。行动开始前,美方曾向巴沙尔政权的最重要盟友俄罗斯当局做了消息通报,保证空袭不会伤及仍在叙境内活动的俄罗斯军事人员。不过普京对此显然并不领情—空袭发生之后,他公开谴责美方的行动“违反国际法,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犯”,“对国际联盟打击恐怖主义的进程构成了阻碍”。
引发此次空袭的疑似化武袭击事件,发生在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黎凡特解放组织”激烈争夺中的伊德利卜省南部前线。自2016年12月底政府军收复北方重镇阿勒颇,并与若干稳健派反政府团体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军事反攻重点就转移到了中、北两个方向上。在帕尔米拉战线,击退“伊斯兰国”对中部能源走廊的攻势,使其在短期内无法恢复野战能力;在伊德利卜省,继续压缩激进派武装“解放组织”的控制区,重点摧毁这支目前尚有2-4万名战斗人员的主要反政府武装的战斗力。
脱胎于“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黎凡特人民胜利阵线”的“解放组织”,由自阿勒颇地区撤出的资深战斗人员组成,在3月11日已经被美国政府界定为恐怖组织,并未参与2017年初进行的和平谈判以及停火协议。他们不仅与政府军交战,还对稳健派反政府武装“自由叙利亚军”“黎凡特自由人民伊斯兰运动”,甚至同为恐怖组织的“伊斯兰国”的控制区进行蚕食。在2017年2月的伊德利卜省战事中,“解放组织”接连从“自由叙利亚军”和“伊斯兰國”手中夺取了多处城镇。位于伊德利卜省南方外围的政府军则乘机对“解放组织”控制区的后方进行攻击。汗谢洪事件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
谁是化武投毒人?
据《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报道,4月4日上午7时,在政府军对两军控制区交界地带的重要城镇汗谢洪(战前约有5.3万人口)发起空袭之后不久,大批当地平民注意到空气中出现异味,同时不断有人出现四肢瘫软、心率和血压下降、瞳孔放大等中毒现象。半小时之内,已经有100余名中毒者被送往当地的野战医院。截至4月5日中午,当地救援人员已经确认有74人在袭击中死亡,超过600人受伤。而法国驻联合国大使在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死亡的平民人数已经超过100人,包括数十位儿童。4月6日,土耳其卫生部在对伤员和当地土壤样本进行化验后,确认了大部分伤亡是源自沙林毒气袭击。由于确认病因较早,大部分伤者目前已得到有效治疗和救护,但伊德利卜省的战事仍在继续进行当中。
化武袭击的消息传出之后,巴沙尔当局官员在第一时间告知路透社记者:政府军从未在作战中动用化学武器,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稍后,亲政府新闻网站“源头消息”承认4月4日上午政府军曾出动苏-22型攻击机轰炸汗谢洪的叛军目标,但仅仅投掷了常规炸弹。俄罗斯国防部随后确认了这一消息,并给出了一个看上去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政府军飞机投下的炸弹命中了“解放组织”在汗谢洪的一处军火库,导致其中储存的毒气弹泄漏,酿成了此次悲剧。
但俄方公布的空袭时间是4日中午11点半到12点半之间,与第一批伤亡者出现中毒症状的时间并不吻合。而内含沙林毒剂的化学炮弹或炸弹一旦被常规炸弹诱爆,有毒气体在火焰燃烧形成的高温中会迅速分解(沙林的分解温度为150℃,尚不及普通打火机的焰温),无法再对人体造成危害。故“空袭造成沙林毒气泄漏”的情形,只有在军火库并未被彻底摧毁,且其中的炮弹或炸弹外壳出现破损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在汗谢洪地区驻扎的温和派反政府武装“自由伊德利卜军”的指挥官则明确宣称:以反政府军的技术能力,根本不可能在缺少大型化工设备的汗谢洪自行生产或储存化学武器,所有毒气都是来自苏-22型攻击机投下的炸弹。
叙利亚政府被指控生产和保有WMD,历史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为对抗以色列的核项目,哈菲兹·阿萨德政权曾经在苏联和埃及的技术援助下,进行过芥子气、沙林和VX神经毒气的生产。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在回忆录中也记载,叙利亚在朝鲜的技术援助下,在代尔祖尔地区进行过铀浓缩活动和核反应堆的试安装。叙利亚内战爆发后,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派出的调查团在2013年确认政府军至少在3处战场使用过沙林毒气,特别是2013年8月21日反政府武装进攻大马士革郊外的乌塔地区时,曾经遭到多枚携带沙林弹头的苏制“月亮”M短程战术导弹的攻击,造成上千名平民和武装人员丧生。另外,在伊德利卜省和哈马省发现了8处使用氯气炮弹的痕迹。俄罗斯调查团给出的解释是:毒气弹系反政府军用土制火箭发射。
自始至终,叙利亚政府从未承认曾经制造或储存过化学武器。不过在乌塔事件之后,由于美国的外交压力,巴沙尔政权最终在2013年9月正式宣布批准《化学武器公约》,由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和联合国成立的特别代表团,对其已经生产出的化学武器进行核查和销毁。根据OPCW公布的信息,截至2013年10月,叙利亚政府军手中保存的芥子气、沙林和VX神经毒剂总量约为1300吨,特别代表团将在美俄两国的配合下,用1年时间将这些WMD彻底销毁。不过随着销毁进程的推进,更多秘密暴露了出来。叙利亚军方承认,至少有4处曾经的化学武器工厂的信息未被披露给OPCW,并且东部有1处储存有蓖麻毒素武器的工厂已被反政府军占领,一批化学炮弹和炸弹下落不明。以色列情报机关认为,即使是在销毁了大部分有记录可查的WMD之后,叙利亚政府军手中至少仍藏匿有数十吨神经性毒剂,随时可以发动战役级规模的化武攻击。而OPCW在叙利亚境内的调查活动,至今仍未中止。
从二战后化学武器使用的发展和使用轨迹看,除去1995年的东京地铁沙林袭击事件系由少数邪教信徒实施(使用的是纯度不高的自制沙林毒剂)外,要造成百人级规模的伤亡,无一例外是由正规军使用专业生产和储存的化学炮弹或炸弹来完成。2004年,伊拉克反政府武装曾经引爆1枚萨达姆时期遗留的155毫米化学炮弹来袭击美军巡逻队,但由于操作不得法,仅造成2名美军士兵受轻伤。换言之,类似乌塔事件和汗谢洪袭击这样的大规模化武使用,要么须由正规军完成,要么证明已经有一个库存惊人的化学武器库落入了反政府武装手中,并且由专业技术人员实施了引爆和发射。无论如何,这已经足以证实叙利亚政府军并未按照2013年时的承诺销毁全部库存化学武器,隐藏的威胁依然存在。
和平何时到来?
2016年底,阿勒颇战事尘埃落定且政府军与主要反政府武装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叙利亚局势在世人看来似乎进入了相对平稳的阶段。2月底第四轮日内瓦谈判期间,一度传出了由俄罗斯等国作为担保人,在2021年下一届总统大选之前完成巴沙尔的和平下野,以及由反对派联合委员会和部分现任政府官员共同组成过渡政府的和平方案。但随后的发展显示,事情并没有那么顺理成章。由于日渐坐大的“解放组织”并未参加本轮会谈,政府军依然在伊德利卜省周边采取全面攻势,其余反政府武装和“解放组织”的交战也未中止。而在南方战场,反政府武装利用政府军和“伊斯兰国”在帕尔米拉交战的机会,重新扩大了控制范围,部分扭转了2016年秋天以来的不利战况。在这一背景下,所有反政府武装派别一致缺席了由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发起的3月阿斯塔纳对话,交战各方再度进入了寻求以军事优势换取发言权的阶段。
在此背景下,一度在2016年转危为安的巴沙尔再度处在了尴尬的位置上。尽管政府军依然占据西部地区,但其主要盟友俄罗斯已经撤回了部署在地中海东部的航母编队,并且做好了在必要时接受政权更迭的準备;另一盟友伊朗也无意继续投入人员到损伤惨重的正面攻势,而将北方战线的行动交由政府军自己来完成。为了避免被过早抛弃,采取坚决的攻势似乎成为必然。只是当这种攻势再度导致有数百位平民伤亡的恶性事件之后,乐于向盟友兑现安保承诺确实性的特朗普不愿再置身事外,立即发动了反应激烈的军事回应。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也公开表示:已经将迫使巴沙尔下台作为其中东政策中的重点任务。
然而,仅仅空袭汗谢洪机场却不打击周边防空导弹阵地的做法明确显示:美军无意扩大在叙利亚领空的军事行动,更无意全面定点清除政府军的主要军事目标(当以色列在1982年进攻黎巴嫩境内的叙利亚正规军时,第一步措施便是消灭后者部署在贝卡谷地的防空设施),从而深度卷入当地局势。特朗普政府的回应虽然相较奥巴马时期略显强硬,但本质上仍是坐观局势变化,等待叙利亚战局朝美国期盼的方向发展。当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在伊德利卜省境内打作一团,且悬而未决的和平进程随时可能前功尽弃之时,所有人仿佛都忘记了:在叙利亚境内控制最多领土的,依然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伊斯兰国”。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意愿承担起成本高昂的军事介入和经济重建责任时,叙利亚漫长的“新三十年战争”只能无限期地延长下去,直至将一代人的鲜血流尽。
摘编自《三联生活周刊》
责任编辑:葛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