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怪诞”的悲喜剧
胡越
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 Friedrich Dürrenmatt, 1921—1990)是瑞士当代重要的戏剧家、小说家。他的生平既少坎坷又无奇特之处,寥寥数行便写尽其一生。迪伦马特1921年1月5日生于伯尔尼州科尔丰根的一个牧师家庭,父亲是基督教牧师,祖父是政治家兼诗人。父辈对迪伦马特日后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讽刺才能不无影响。1935年他随家庭迁往伯尔尼市,在那读完中学。随后在苏黎世度过一个学期,又返回伯尔尼城攻读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这期间他研究了基尔克郭尔、尼采、卡尔·巴特、阿尔贝特·史怀泽等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著作,在文学方面受到阿里斯托芬、奈斯特伊、拉伯雷、毕希纳、魏德金德、卡夫卡等作家的影响,阿里斯托芬讽刺现实的喜剧尤其受到他的推崇;同时他也对绘画颇感兴趣,创作了许多具有“怪诞”特征的美术作品。毕业后他曾在苏黎世《世界周报》任美术和戏剧编辑,这时期也写了一些尝试性的剧作和小说。迪伦马特的主要成就在戏剧,其中代表作有《老妇还乡》(1956)、《物理学家》(1962)、《罗慕路斯大帝》(1949)、《天使来到巴比伦》(1953)和《弗兰克王世》(1959)等。
作为艺术上的“叛逆者”,迪伦马特不愿意因袭传统,或步他人后尘,而是标新立异,另辟蹊径,经过创作实践和舞台试验,建立起“一套自己的理论”,从而形成其以“怪诞”为特征的悲喜剧风格。综观迪伦马特的所有剧作,它们在整体上都呈现出一种悲喜交融的怪诞风格,这一特征在其经典剧作之一《 老妇还乡》中表现得尤为鲜明。
《老妇还乡》的故事并不新颖,“复仇”是古今中外作家笔下最常见的题材,但迪伦马特运用了不同寻常的表现手法,使《老妇还乡》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复仇剧。这个不同寻常的表现手法就是用喜剧的形式来表现悲剧的主题。而就喜剧表现手段本身而言,迪伦马特采用的表现手法又有别于传统喜剧中常用的夸张与戏谑,而是“怪诞”,“即把现实中的普遍性事物加以变形,使之怪异、荒唐,以造成和现实之间的某种距离(即失去真实感或舞台幻觉),换一句通俗的说法就是:给描写对象戴上一种假面具”。
具体到《老妇还乡》,剧本的中心情节围绕着老妇复仇和伊尔的死展开,但对于老妇买凶杀人和居伦人集体谋杀这一令人发指的可怕死亡事件,作者却运用喜剧手段加以描述,从而产生了幽默、讽刺的效果,带来整体风格上的怪诞。

除了表现手法的怪诞,剧本中的诸多人物形象也具有怪诞色彩。女主人公克莱尔一出场就给人以怪诞的感觉,“……红色的头发,戴着珍珠项链和巨大的金镯子,她一方面看来是那样凶恶,一方面尽管神情古怪,却仍然具有交际场中贵妇人少有的风度”。珠光宝气的装扮,凶恶的神情再加上贵妇人的风度,集种种因素于一身的克莱尔从视觉上给人以既可笑又可怕的怪诞色彩。在迪伦马特的笔下,克莱尔“等于是已用一个石头模子铸定”,“代表一个石头偶像”。她的性格是固定、僵化的,她的复仇计划更是贯彻始终、从未动摇。她的富可敌国使她能够专横跋扈、不顾一切,但最让人心生畏惧的是她能够用金钱支配他人命运,似乎任何事情都在她的掌控之中。为了报复伊尔,她早已做好了周密的准备。克莱尔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将那两个被伊尔收买,谎称与她睡过觉的假证人找回,派人割去他们的生殖器,弄瞎他们的眼睛;昔日错判克莱尔之子父权案的法官现在也受雇于克莱尔做总管;如今她带着复仇所需要的证人、总管重返故乡,一步一步地实施她的复仇计划。这些都展示出老妇那可怕的无所不能的力量,她太清楚金钱的力量多么巨大,居伦人的正义、善良和人道主义在金钱面前完全不堪一击。
然而如果把克莱尔刻画为一个纯粹的恶棍——尽管“那个老太太的确是個恶棍”——这个人物形象就称不上怪诞。迪伦马特在后记中也强调,“在表演时决不能让她露出一副恶人相,而要尽可能让她合乎人情,要让她在观众中引起的情绪,不是愤怒,而是悲伤和幽默”。因此,“石头偶像”式的克莱尔也具有人性化的一面,当她再度与旧情人伊尔在康德拉村的树林里聆听布谷鸟的叫声和风吹树叶的声音,对于往昔恋情的追忆和留恋依然使她心中充满惆怅和感伤:
克莱尔:我已经对你谈过了关于咱们的小女儿的事。现在你谈谈我的事。
伊尔:关于你·
克莱尔:谈谈我的过去,谈谈我17岁的时候你爱我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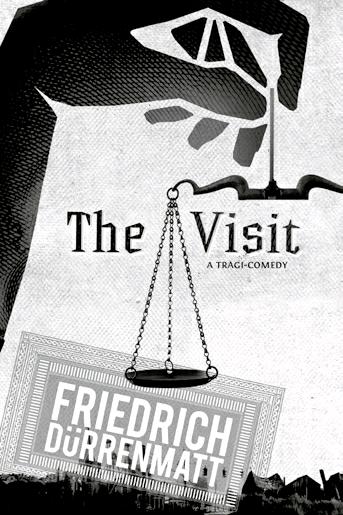
此时克莱尔更像是一个因为失去爱情而悲伤不已的普通的女人。尽管她富可敌国,却无论如何也买不回逝去的爱情了。
由于迪伦马特在刻画老妇克莱尔这个人物形象时,一方面充分突出了她性格中的骄横、邪恶、残忍,进而使她成为可怕的“复仇女神”的象征,令观众毛骨悚然;另一方面却将悲伤和滑稽等种种本不相容的因素集合在她一人身上,从而塑造出一个典型的怪诞形象,更加深了全剧的怪诞色彩。
另一个充满喜剧怪诞色彩的角色是克莱尔带来居伦的一对盲人小老头。他们因为被伊尔收买作伪证而遭到克莱尔的残酷报复,被阉割并且弄瞎双眼。克莱尔供给他们考究的衣服和牛排火腿,而他们也就安然接受了这样的生活。在重返居伦城完成了作证任务之后,他们被克莱尔派人装运到香港的鸦片馆里抽鸦片去了。这对小老头总是成对出现,每说一句话都要重复一遍,因此塑造这样的人物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完全像凭空幻想出来的神话中的人物”。
此外,剧本中还出现了许多怪诞的场景。第一幕的欢迎仪式上,欢呼的居伦人在看到那具非常精致的黑棺材时,“一个个都不自觉地停住了喊叫”,而这时“那尚未抵押出去的火警钟毫无畏惧地开始响起来”。本应隆重热烈的欢迎仪式上出现一口棺材已经让人心惊肉跳,用火警钟欢迎贵客来表现居伦的贫困则有极强的讽刺意味。这样—个不伦不类的欢迎仪式不能不说极具怪诞色彩。又如第一幕中伊尔在树林里幽会他的旧情人克莱尔。当克莱尔暗示她将对故乡有所帮助时,伊尔一时激动,禁不住在她左肩上拍了一下,但马上又痛苦地把手抽回来,原来他恰好打在克莱尔假腿的一个链条上。克莱尔告诉他:“这是一次飞机坠毁劫后余生后装的假腿!”接着伊尔又碰到她的胳膊,同样又冷又硬,克莱尔干脆说:“是的,我的全身都是用象牙装配起来的!”这一典型的怪诞场景中,迪伦马特塑造的老妇克莱尔已然是一个浑身装满假肢的摔不死的傀儡,她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滑稽而又可怖的。
迪伦马特独具特色的悲喜剧,正是用这种偏离生活形式的怪诞方法,突破了模仿和表现真实生活的限制,充分发挥了戏剧艺术的假定性、象征性特征。为了达到表现思想内涵的目的,他进行了大胆的想象和虚构,从而形成了以外在形式的“假”表现内在本质上的“真”的突出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