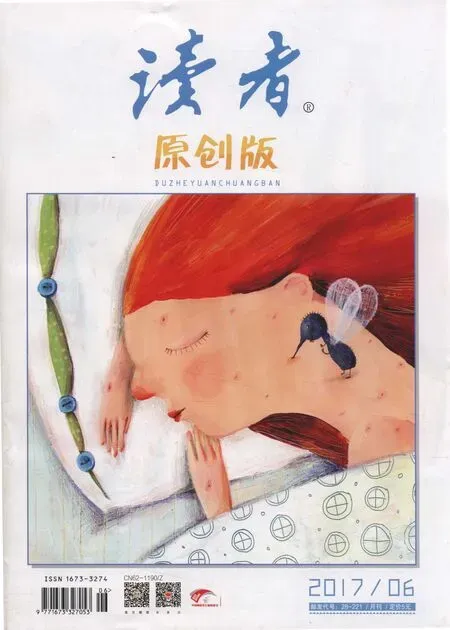她的羊
文|韩昌盛
她的羊
文|韩昌盛

母亲打电话说:“回家来,要杀羊了。”
我不信。母亲说:“真的,不喂了,都卖了,留一只杀了。正在找人杀,收拾好你们回来拿肉。”我打电话给大妹妹,她也不信。
但羊确实杀了。我们吃了羊肉,还带走了羊腿,兄妹四人,一人一条羊腿。母亲说:“都带走吧,吃了就没有了。”父亲说:“不喂了,草不好割。”
草其实不少,不过种庄稼的地都打了除草剂,附近的草不敢割,只好上沟边地头、抛荒地,或者学校的操场割草。我没见过母亲割草。大夏天,我在空调屋里上班,星期天回家时,母亲已经回来,一手擦着汗,一手拿着矿泉水瓶猛灌。矿泉水是在街上批发的,五角钱一瓶。她说这个好,带上两瓶,渴了就能喝。我问:“不会中暑?”她说:“不怕,有水。”然后,她去做饭。吃饭时,她兴高采烈地跟我说她到中学操场割草了,草有半人高,一刀下去,倒一大片。我还没吃完,她说得喂羊了。羊在另一个院子,曾经的老屋,荒凉、破旧,有两间西屋,泥墙,快倒了;有三间正屋,墙有点歪。院子里有一棵枣树,很空旷,养了13只羊,看见母亲进来,一齐奔过来,争着抢着,一抱草就分开了。母亲抢过来一把,扔给一只抢不到草的羊。羊就埋头吃草,母亲在那儿看着,也不理我。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那年大年三十,母亲做好饭,炒了菜,然后就走了,说一只羊要生了。母亲已经准备好一簸箕麦秸,还有干干净净的锅灰。她说:“你们先吃吧,我去看着。”孩子过去喊了几次,她也不过来。我过去,母亲有些紧张,自言自语道:“最好能生四只。”我笑了:“也许只生一只。”母亲瞪我,说我是乌鸦嘴。还说在我小时候,有一次,就是我在老宅里看着羊生产,结果真的生了四只。母亲还是有些紧张,说:“上次这头羊就生了一只,这次肯定不会。”
这次也是一只。母亲一边将小羊羔放在麦秸上让母羊去舔,一边愤愤地说:“得把它卖了,不能喂了。”然后来这边院子烧豆芽汤,一大盆。我说:“先吃饭吧,你还没吃饭呢!”母亲不理我,端着汤就走。她有些生气:“怎么就生了一只?”母亲说前几天还死了一只羊,拉肚子。她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有关羊的事情,才吃了一点儿饭。
大多数时候,提到羊,母亲都是很高兴的。她说她割的草干净,因为她比别人跑得远;她说我们家的羊长得快,吃的都是“绿色生态环保菜”—这些广告词,她用得很顺溜。说着说着,我们就去看羊。一开门,母亲就提醒我赶紧关门。几只大一点儿的羊飞奔而来,母亲大声呵斥着,用脚踢着,羊就回去了。母亲站在院子中间,点着羊,告诉我哪只快下小羊了,哪只已经下了,哪只是这头羊的孩子。我说我记不住,母亲说:“你当然记不住,我全部能记住。”母亲叫我牵羊到地里去,这个季节的麦苗可以吃。我就牵着两只,后面跟着四只,往麦地里走去。母亲也牵了两只,羊往前挣,她快要跌倒了。母亲说:“没事,我不会跌倒,我这么胖呢。”
嫁到附近的小妹说:“她撒谎,有一次跌倒在地上,她很长时间都没起来。”母亲说:“那是血压高,感觉头晕,然后一点儿劲儿也没有,想起来就是起不来。”我说:“那不能起来。”母亲说:“知道。听到羊叫唤,感觉声音跑到天边了。”我问:“然后呢?”小妹说:“后来自己慢慢坐起来了。”我说:“这样不行,你得吃药。”母亲辩解说:“吃啊,一直都吃,一顿不少。”我说:“这羊不能喂了,再喂要出事。”母亲说:“与羊有什么关系?喂羊心情好。”“可是喂羊你身体不好。”“哪儿不好?下地割草,空气多好。”“反正我们要你身体好,不要羊了。”母亲生气了,不理我们;我们也生气,但是还得理她。
我抱草给羊吃。我看着羊争先恐后挤过来,就将草抛向空中,草像网一样散下来,羊就抬头往上迎着。母亲在后面说:“怎么这样喂?”我说:“和羊开玩笑呢。”
但是生活也和我们开玩笑。2013年,父亲吃不下饭,检查说是肿瘤。我带他到南京做检查,各种各样的检查,等结果,一个又一个片子的结果。我说:“没事,就是个肿瘤,割掉就好了。”父亲说:“知道,就是个肿瘤,割掉就好。”晚上我们去散步,我说:“给家里打个电话吧。”我拨通电话,和母亲说医院楼很高,病人很多,护士很好,食堂不错,检查结果还没完全出来,但是估计没事,这个医院水平很好……母亲就说:“没事的,肯定没事的,心里一点儿都不慌,家里没事,什么都好,人好鸡好羊也好。”我把电话给了父亲。来了几天,父亲还没和母亲说上话。父亲问:“家里都好吧,麦子该出穗了吧?”又说,“在这儿很好,到了就有病床,检查结果快出来了。”路上有路灯,有行人,有穿梭的车流和喧闹的声音。父亲突然说:“我要是不行了,把我葬在北湖那块地上。”“你说这干吗!”我使大劲儿在旁边喊,“那羊不喂了行不行,到南京来!”
母亲和其他家人就都到了南京。我们都沉默着在手术室外等结果。幸运的是,手术成功了,母亲高兴,我们每个人都高兴。我问她:“家里的羊怎么办?”小妹笑话我:“要你问,三舅在咱家帮着喂羊。”我说:“别喂了,回家得照顾病人,你没时间喂。”
她还是要喂羊。父亲在县医院化疗,我看着。母亲自己坐车来,穿过人流从车站跑到医院。我问:“谁看着羊?”她说:“不看,大秫秸放好了,它们自己吃。”我说:“别喂了,你血压高,你不能再出事了。”母亲不说话,在那儿坐着。父亲也不说话。晚上,父亲和我在走廊里溜达,父亲说:“再喂一段日子吧,羊值钱,家里人情重,能打发不少用处。”我说:“我们给啊!”父亲摇摇头,说:“你们也不容易,现在我和你妈还能干活。”
父亲的胃癌奇迹般地好了。他还能种庄稼,还能开三轮车拉庄稼。母亲却说不喂羊了,真的不喂了。她得了白内障,两个眼都有。她使劲揉眼睛,还是看不清楚。医生说暂时还不能做手术,母亲只好一边揉眼睛,一边抱草给羊吃。
母亲站在门口送我们,说:“羊肉不要送人,自己吃,好羊肉,绿色生态环保的。”母亲一边揉眼睛一边说,“以后就没有羊了。”父亲笑眯眯的,不说话,坐在椅子上晒太阳,椅子依在墙根。母亲说:“他病好了比什么都好,不喂就不喂了。”
然后,母亲扯起围裙擦了擦眼睛,向我们挥挥手。父亲看着她笑,坐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就走了,穿过一大片田野,一大片青草,一大片树林,一大片池塘,一大片云朵,一大片麻雀。然后我无来由地想起,母亲曾在这儿割过草,回家喂她的羊,伺候她的病人,想念她的孩子,打扫她的房子。然后,我突然想起,我们其实都是母亲的羔羊。然后,我满脸是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