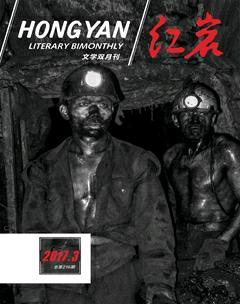林先生和房子
周洁茹
一到黄梅季,大华弄就淹掉了。
每年的防汛防涝新闻都要提到大华弄,全城人也都知道,一下雨,大华弄就会淹掉。
大华弄是兰陵城最后的一条老弄堂,早先家家书香门第,弄堂中央还有一条河,碧清的水,柳色青青。江北的船开过来,船上人上岸走走,春光明媚,令人沉醉,就移民來了。河填掉了,多出了地皮盖房子,大华弄就不全是书香门第了。即使没有新移民,大华弄也不会一直书香门第下去,时代都不同了,哪里还有什么书香门第。
如今的大华弄处处危房陋房,小弄堂纵横交错,多数不通,尽头也是人家,院里种的一式一样的茉莉玉兰小月季,门牌号码都没有。外头的人常常在大华弄迷路,找不到方向。
一下雨,雨大些,整个大华弄就淹在水里面了,有关部门就要派出三轮车,装好方便面矿泉水蹚水过来,报纸电视台也过来拍,一式一样的报道。
大华弄虽然地势低,位置倒好,市中心,一出去就是市政府,市民广场,江南商城。只是这条老弄堂实在是太老了,好像一个破衣烂裳的穷苦女人,总要混在穿金戴银的名媛群里,不合宜,不和谐。而且动不动就被水淹了。
林家是个例外。林家地基打得高,水再高,就是大前年的那次特大洪涝,大华弄几乎家家户户都进了水,那水也只漫到林家的门坎下面,再也不往上面涨了。隔壁吴家在旁边毒毒地看,眼珠子都妒得发绿了,林先生也不理会,心底里暗自高兴,还是当年翻房子打的底好,有远见。
吴家进了水,簸箕铲勺子舀都没用,一觉醒来,床腿都浸在水里面,脚一伸去,鞋都不见了,踩了一脚的黄泥水。水下去了以后,吴家就在门口筑了一道十分高的门槛,工程很有些浩大,又是拌水泥,又是砌红砖,过后水倒再也没有来过,只是坚硬的高门槛绊倒了自家人好几回,只好再把水泥门槛敲掉了。
吴家和林家是对头,梁子结了好几年了。林先生结婚那年,天天在外面跑,跑得胡子拉碴,跑全了建筑材料翻房手续回来,隔壁邻舍都打过了招呼,要把林老先生传下来的老房子推了翻盖一座新式楼房,吴家脸色不好,林先生来打招呼倒也客客气气地应了。林先生正要动工,吴家跳了出来,死活不让盖。林先生差点没气昏过去,工人已经坐在地盘等着,拖多一天就多一天的损失,连夜找了中人去吴家谈判,赔付了一笔钱才算放过门。
盖了没两天,居委会主任王婆走过来说检查团要来查卫生,上头都有文件的,你们黄沙砖头建筑垃圾都堆在外面,查卫生要是查到我们这个居委会不及格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硬是让林先生每天早上把砖头搬回房间里去,晚上才搬出来,这么搬了两个多星期。家里只有林先生林太太一对年轻夫妻,也没什么办法,两个人每天上下班前后就忙进忙出搬砖头,林太太长得娇小,搬砖头搬得背弓了,像只小虾米,林先生心疼老婆,一个大男人,差一点掉眼泪。
房盖到一半,吴家又跳出来不让盖了,理由是你们家房高了我们家可就太阳也照不着了。林先生已经被房子的事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该有多烦,阁楼草草结了个束,半年不到,一下雨,屋顶就成了个蓄水池,漏得不成样子,林先生又找人来修,前前后后忙了四五回。
改造大华弄的提案提了好几年了,一直没有具体落实下来,终于到了年初,政府有明确的承诺下来,今年实事办理头件大事就是改造大华弄。而且很快地,消息见报是九号,十号林先生和林太太下班回家,就发现自家墙上已经写了“拆”字,墨汁淋漓,一直淌到了墙根底下,到十一号一张薄纸就塞进门缝里来了,通知十二号有专人上门测量建筑面积使用面积,十三号就收到了正式的房屋拆迁通知,附了厚厚一份拆迁政策宣传文件。通知列明了原使用面积大于五十平米的可安置到旁边的青云小区或返回安置,未满五十平米的则一律安置到市郊新村;十天内搬出,腾出空房者奖励一千元,二十天内搬出奖励二佰元,一月内搬出奖励一佰元,逾期不搬者诉诸有关法律规定强制拆除。
通知一下来,林先生就大大地吃亏了,前些年大华弄一直说要拆却一直没有个准头,一直这么等着,林太太就叫苦了,老房子里当然是没有抽水马桶和垃圾房的,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拎着痰盂去倒,垃圾箱也有些远,满满一桶的垃圾端着去倒,苍蝇蚊子都围着端垃圾桶的人乱舞,大水一来,垃圾箱公共厕所里的东西都漫出来了,黄的红的臭的烂的漫到各家各户。林先生实在捱不过了就去居委会问,问了几次,王婆主任说要拆的要拆的,大概什么日子拆她可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林先生想想刚结婚那年吃的苦头,一咬牙掏钱出来,洗手间换了玛瑙浴缸,厨房安了抽油烟机,门窗全换铝合金,地板全换花岗岩。装修是件烦琐事情,日日夜夜赶进度也赶了一个多星期才好,房子装修后林先生安慰自己说,将来要拆,即使只一年就要拆,就当是我为这房子付了一天一百五的租金。
没想到装修了不到一个月就要来拆,这扔进去的钱可是一丁点儿也收不回来了,林先生懊恼不己,这苦也只能往心里面去,又说不出来。这天林先生下班,正在门口停车,王婆主任凑上来满面孔的关心,“我说要拆的吧,不是,白装修了不是?”林先生气得话都讲不出来。
测量面积那天林先生是请了假等在家里的,一早就坐在桌旁,认真阅读了一遍托人复印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的办法》,读完,从抽屉里拿了包烟放在桌子上,想想,又拿了一包出来。直到中午了,听见外面喧闹,开了门看,几个人拿着卷尺计算器正往这边来,王婆主任也一本正经地跟在后面,还有几个闲人,个个伸长着脖子张望,量到哪家就跟到哪家。轮到林先生家,林先生迎上去满脸堆笑,递烟过去,一个看去像是领头的胖子,客气地摆手,说:“不抽,不抽。”又递给其他人,也一概摇头摆手:“不抽,不抽。”林先生就把烟放下了,看着那几个人手脚麻利地摆开架式,一会儿功夫楼上楼下都量完了,林先生也略懂些,在旁边看着他们往纸上写数字,说:“师傅,三楼的面积好像不大对吧。”胖子说:“我们公事公办,你这阁楼只能算一半的面积,高度不够,差也就只差一块砖头的高度。”
林先生听了不说话,心里想当年如果不是吴家过来闹,这一块砖一定是上去了,叹了口气,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
第二天通知和估价单就来了,林先生一看估价单大吃一惊,一整套房子居然只值一万块钱,铝合金门窗花岗岩地板也只折算了几百块,但是如果不折价自己拆下来又有什么用,想想一个月前投进来的四五万,真真是打了个水漂儿不见了,连个响声也没有。
估价单下面还另注了一条,对公布的面积如有异议,可在三日内提出申请复量。这天是星期天,林先生无事,也去看看,还没到地方已经人山人海,都是大华弄的邻舍,个个面孔潮红,挤在一起。林先生挤进去,小小的一间屋子,也挤满了人,墙上贴着一份市长令和一份建委关于调整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助费标准的文件通知,每个人都带了纸笔,贴在墙上抄写,一字一点,生怕错过重要的内容。一个精瘦的中年男子,坐在外面的条凳上,眯着眼睛,抽着烟,林先生不去轧闹猛,也在外面站了会儿,听见有人管那精瘦男子叫主任,就在那男子的旁边站定,递了根烟过去,男子笑笑,接了,也不说话,林先生就说了:“挺忙啊。”主任又笑了一笑,说:“怎么?要复量?”林先生摆手:“不不,只是过来看看,看看。”就往远处看,仍然很多人,不厌其烦地抄写、盘问。林先生看了会儿,觉着热了,就回去了。
已经有几户拿了搬家补助和提前搬家奖励早早搬到新村房里去了,一家老小眉开眼笑,挑了黄道吉日作乔迁之喜,搬家公司的大卡车也往来得频繁,有回忆的老家具旧被褥全部扛上车去,要不是早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文件发下来,每天都要响好几回鞭炮。这户人家早上走,到下午拆迁办就来拆房子,几个民工在那里砰砰砰敲了一阵子,发一声喊,墙就倒了,轰起一大片陈年的土,断墙破壁地竖在那里。剩下的人走来走去就看得到残败的废墟,触目惊心,慢慢地都主动去找危积陋改造安置办公室谈话,安置到各大新村里去了。
大华弄越来越冷清了,该搬的都搬了,不搬的也只守着自己家,盯牢着别人的去向不敢乱说乱动,各家各户都动员起来了,有熟人的去找熟人,打听到远亲在有关部门供职,也拐弯抹角地去认亲,就算是几十年不往来的小学同学也从旮里旯落里跳了出来,叙旧过后就是拆迁的具体情况。
林先生家,吴家,王婆主任家都算是钉子户,林先生有林先生的主意,其他几户是眼睛巴巴地望着林先生家。剩下的人因为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常在一起讨论,但是牵扯到分配安置又会万分小心,生怕流露了自家私下里做的手脚,气氛是越来越紧张了。路已经拆得不大好走了,原先是路的地方堆满了砖块水泥板,原先通畅的弄堂也堵住了好几条,要走出去就要绕大半个大华弄,捡垃圾卖旧货的也拖着各自的三轮车来凑热闹,一路过去满目疮痍,晚上回家,窗格家具上都落了厚厚一层白石灰。林先生看着这一切在身边发生,就像神话一样,说拆就拆了,林先生生在这儿,长在这儿,也有三十多年了,住久了就对这地方这房子有了感情,现在要搬,心里只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这天一大清早,王婆主任搬了一张竹靠背椅坐在自家门口,先是絮絮叨叨自言自语,见没什么人理就号啕起来:“这是什么世道啊,骗我们说女儿三楼,我们老俩口可以分在一楼了,现在可好,女儿分了个六楼,把我们老头老太婆分到三楼去了,我真是命苦啊命苦,苦啊苦啊。”王婆主任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围观的人听了冷笑:“十几平米的破房子,倒要求分到青云小区,实在达不到目的了,才去了新村,要了两套房子,女儿一套四十平米的,六楼,她分在了三楼,也有四五十平米,她倒在这里哭拆迁办给她当上。”
林先生在旁边看,心底里好笑。王婆主任见围着的人多起来了,又哭:“我们家没门没道,又没钱,不像有的人,晓得去走路,我们是老实人,欺负我们呐。”
林先生听得烦心,一甩手回去了。
旁边是有个青云小区,林先生特意去看过,走过去十五分钟,绿化很好,只是楼层都卖得差不多了,也没有多的房子可供选择。住房面积过五十平米的才有资格去,林先生想想,自己家是有资格的,但这大华弄的房子是父母手里传下来的家产,人总是恋旧的,一个住惯了住久了的地方怎么再忍心离开它另寻去处?大华弄将来也是造小区房,只是要在外面过渡两年,自己又没有房子过渡,过渡费和返回安置的楼面都要去和拆迁办谈,林先生想想这些事情就觉得头疼。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许多钉子户也悄悄搬了,前夜里还见着人,第二天早上已经是人去楼空,鬼鬼祟祟招呼不打一个就走。前脚走,后脚就有贼上门来,趁着钥匙交出来了,拆迁办还没来得及拆这个空档,把那些铁的钢的撬下来锯下来,月黑风高夜扛了走。
吴家还硬着,对外宣称:连个说法都没有,就要把我们赶走了?我们大华弄虽然破烂,可是个黄金地段,他们是决不会再让你搬回来的!他们倒会耍手段,过渡费没有,新小区的设计图没有,返回安置的楼层朝向不好定,只有面积能够定,超过的部分倒要先交钱,这种协议有什么好签的?你们看好了,大华弄一千多户返回安置的一半都不会有。我们就是不搬,我们就是要一个说法!
王婆主任搬了,拖了个把月,拆迁办天天来人做工作,王婆主任只是铁青着脸拿捏作态,后来却不来了,什么动静也没有,王婆主任就有些心慌了,报上也有报道说某处配合市政建设要拆迁,某钉子户对屡次通知置之若罔,其房已于某月某日被强制拆除,拆除费用还要由这家钉子户承担。王婆主任搬了。
吴家不搬,左邻右舍都搬得差不多了,吴家仍然不搬,誓与拆迁办共存亡。这天吴家女人小孩睡在楼上,男人一个人睡在楼下面,一个贼进来,打着手电明目张胆翻了半天,吴家男人才听见声音,忙从门后面抽了根棍子,赤著脚上楼去。贼是从隔壁拆了一半的旧台翻进来的,手脚麻利又从原路翻走了,第二天过来吴家仔细查对东西,发现手表被偷了,到派出所到报案,派出所说大华弄拆都拆得差不多了,这些贼都是外面来的流动人员,这案子一时半会是破不了了,吴家男人回来指天划地骂了一通。
林先生和林太太商量好了去住青云小区,林先生就去和拆迁办谈,要一套看好了的二楼的房,拆迁办却不给,说是已经订出去了,交涉了一通,拆迁办就火了:“你们大华弄的工作最难做,个个削尖了脑袋要好房,都是不讲理的。”林先生心平气和:“我是最讲理了,要什么房子不是我的权利吗,我打听过了,那套房空了一两年了,多大的领导干部是可以订住套房一直空着的?我家也够条件,国家政策都允许,你们不给是你们的不对。”拆迁办就诉苦:“都来问我们要好房子,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啊,那套房确实就是不能给你。”
林先生最后要了四楼的房,按一平米三千的公差价,又贴了好几万块钱,楼层不讨巧,却要补楼层费,然后就是装修,拆迁办催着搬,急匆匆搬了出来,又没有地方过渡,新房草草装修了事,钱是花了不少,总算是住进去了。林先生松了口气。
青云小区的物业管理却一直没能跟上,一条中央大道两头通,由着重型卡车开来开去,黑灰满天飞。林先生这幢楼的旁边又是街道开办的卡拉OK,夜夜唱不停,只有楼下面的一个小花园算是好的了,种了几棵枫树桂树,还有海棠花,鲜红的一片,站在窗口望下去,倒也赏心悦目。
这天林先生正站在窗口,一个老太太,挎了个竹篮摸到园子里,先是若无其事草地上走走,左顾右盼没什么人,就掏出把小锄头,飞快地挖了海棠花放进篮子里去,挖的时候很是心急,弄得一地枝叶,林先生吃惊,看那张脸,是一张大华弄的熟面孔。林先生第一次为着大华弄感到了羞愧。
其实大华弄的邻舍们都是不见了,也找不到了,林先生后来听闻,王婆主任在新地方没有争取到居委会的职务,很是忧愁,只好时常回来,走走看看,追忆过往。吴家后来怎么样了,没有人知道。
林先生一直想要回大华弄去看看,却一直没能去成,大概也是怕见了心里难过,林先生就一直没有去,直到大华弄围了一圈墙开始造新小区了,林先生才回去了一次,空旷的一片地,也分不清楚哪儿是哪儿,估摸着自家房子的一片平地上停着一辆大卡车,一点老房子的痕迹都没有了。
责任编辑 吴佳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