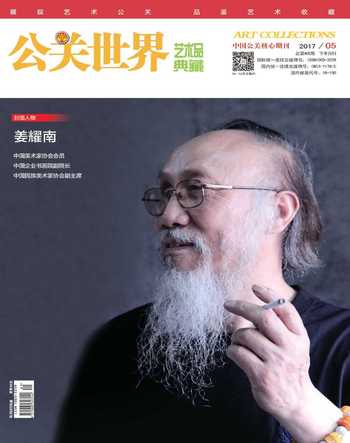那些鲜为人知的海派画家逸闻有多少
谈到海派,我们想起的总是那几个代表性画家:任伯年、虚谷、吴昌硕、蒲华、黄宾虹、吴湖帆、张大千、刘海粟、唐云、林风眠、程十发、谢稚柳、陆俨少等。但从上海书画出版社近期推出的重磅新书《海派绘画大系》中可知,这些大家只是冰山一角。此书收入画家一千六百余人,其中八百六十多人均有作品收入。那么,鲜为人知的这些画家到底有谁?他们的艺术成就如何?本文选取三块为读者略作介绍。
被淹没的画家
黄宾虹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沪上名流之画”,开篇便言:“画士游踪,初多萃聚通都。互市以来,橐笔载砚者,恒纷集于春申江上。”这里的名流便有冯金伯、蒋宝龄、秦炳文、改琦、费丹旭、沈焯、胡公寿、杨伯润、虚谷、任熊、任薰、任预、任颐、顾沄、陈允升、张熊、吴榖祥、蒲华。
在黄宾虹列出的名单中,除却虚谷、任颐、蒲华,其他人多不为一般读者所熟悉,可翻开历史,他们在当时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如改琦、费丹旭开启了海派人物画的先流,其后的人物画家沙馥、钱慧安等无不受他们影响。无锡秦炳文,曾为沪上画会蘋花社社长,而此社成员有王礼、钱慧安、周闲等名扬沪上的画家。吴江沈焯,字竹宾,他是胡公寿、杨伯润的老师,而胡、杨二人均因其高超的画艺、书艺为时人所敬佩。
既然黄宾虹称他们为沪上名流一定有其道理。当时沈焯、蒋宝龄往来密切,《盛湖志》载沈焯学画便是与蒋宝龄交游之后。而蒋宝龄又与程庭鹭、费丹旭等人为诗画友。沈焯的学生胡公寿、杨伯润又与任颐、陈允升、蒋确等人交往密切。可以说这些人当年组成了沪上书画的名流交往圈,这个圈子是黄宾虹等人所仰视的。
除此,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宦游之远,见闻既广”而成为沪上名流。黄宾虹列举出吴云、吴大澂二人。吴云,字少甫,号平斋,晚号退楼,又号愉庭,官苏州知府。吴云不但善画山水及枯木竹石,其所收藏的青铜器和碑帖拓本也十分惊人,曾因得两吉金大器命名其室为“两罍轩”。吴大澂更是如此,他是吴湖帆的曾祖父,到吴湖帆时仍有很多藏品是吴大澂遗留的。而吴云、吴大澂更是金石之友,仅凭此,也令黄宾虹等人仅能望其项背。
还有一些人是“不必尽寓沪江,而画事流播,名著近远”者,他们是陈崇光、姜筠、沈翰、郑珊。他们虽未至上海,但画艺远播,为黄宾虹所遥瞻。例如陈崇光,黄宾虹在著作中就多次提到他,言其“画山水花鸟人物俱工,沉着古厚,力追宋元”、“双钩花卉,极合古法,人物山水,各各精妙”、“此近古中之佼佼者也”。可能正因此,很多人认为黄宾虹跟陈崇光学习过,实则更多的是“心赏”吧。
画家的子孙们
在这一千六百余人中,有一部分人的先辈是大画家,他们一方面得先辈画家亲授,却也一辈子待在祖辈的阴影下,虽如此,他们却是将海派传承下来的一个重要脉络。
清末画家戴熙画名极显,他擅山水,工诗,书画造诣皆深,与汤贻汾齐名,人称“汤戴”。山水取法王石谷,创“蝉翼皴”,笔墨雄健,入神品,为世推重。所写竹石,停匀妥帖,颇有雅致。间作花草人物。与张之万论画学最为相契,时称“南戴北张”。戴家可谓书画界的名门望族,其弟戴煦,长子戴有恒,侄子戴以恒、戴之恒、戴其恒、戴尔恒,均擅画,所作山水无不出自戴熙。
任伯年的子女任霞、任堇、任天池也同样善画。任伯年晚年因长期嗜食烟酒,肺疾日重,却又欠下许多画债,便由任霞代笔作画。因此,观任霞本款的作品,与任伯年晚年的风格十分相似。任霞之弟任堇却截然不同,因任伯年去世时尚年幼,受其父影响较小,但却继承了父亲的艺术天赋,在书法上造诣较深,初学李北海,中年后学钟繇,书风朴秀高古。任伯年去世时任堇刚满十五岁,其弟任天池便更加年幼,他的画名也较兄姊不显,仅是在《申报》等处见其卖画启示。
吴昌硕的两个儿子吴涵、吴东迈在书画印上均继承其父,绘画笔墨饱满、老辣,书法苍古,篆刻厚重。吴涵为吴昌硕第二个儿子,长子吴育在十六岁时不幸夭折,因此多是次子吴涵侍奉在其左右。传言当年吴昌硕名噪东瀛,登门求画者应付不来时即由吴涵及其弟子赵子云代为作画。成立西泠印社时,吴涵也得以成为第一批社员。可惜吴涵在五十二岁时突然去世,吴昌硕又一次经历了丧子之痛。吴东迈是吴昌硕的小儿子,十分受疼爱,《海派绘画大系》中收录了一张俞礼所绘的《苏苏小影》,画的即是吴东迈幼年时。他手提一篮枇杷,面露喜色,吴昌硕题跋言:“苏儿苏州生,头角颇岐嶷。两岁呱呱啼,随父适海国。今岁才六龄,之无未渠识。渠父酸寒尉,束肚弄不律。吃墨分所宜,余者力不及。光福枇杷熟,卖趁端阳节,尉也腰无泉,全家戒弗食。达夫俞兄来,曰‘苏尔无泣,西山黄金果,昨日吾手摘,破筐盛累累,慰尔经年忆。,苏儿见之嬉,踊跃来绕膝。达夫为写照,真意笔端出。儿有食肉相,愿为万夫帅,弗学耶读书,齑盐困卑秩。”言语中多是对贫苦现状的无奈和对小儿的憐爱。
他们也是画家
除上述之外,还有一些人也善画,却因为在各自领域成就极高而将画名掩盖。如演员赵丹、摄影家郎静山、翻译家林纾等。
在电影艺术上成就杰出的赵丹,其实早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师从黄宾虹、刘海粟、潘天寿等人,与李苦禅也为莫逆之交。1977年,赵丹曾与陆俨少相遇在井冈山,陆俨少去给革命纪念馆作画,赵丹去井冈山体验生活。赵丹便常常到陆俨少屋中串门,借他的笔墨作画,陆俨少对他的绘画评价很高,称“零纸整幅,杂置案头,乱抽一帙,随手涂抹,笔墨狼藉,顷刻而成。看似极不经意,而图成之后,奇趣横生,章法谨严,似有宿构者,通幅真气流转,不可羁勒,放浪恣肆,时或明有,皆各自具一种天机灵变之致,非人所及”。赵丹也对陆俨少倾诉心事,称演员的职业很辛苦,感觉精力不济,打算不久之后“退休”,一心从事绘画,“模山范水”。他这样讲,或许也是出于无奈。赵丹晚年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戏可拍,当时他打发时间的方法就是伏在案头作画。据去过赵丹家的人说,去拜访的人无不夸赞其画艺,然而赵丹却怒吼道:“我是演员,我是演员!”说时眼泪流了下来。
我们常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摄影大师郎静山却做到了“影中有画,画中有影”。他被称作中国摄影第一人。1931年,他的摄影作品《柳阴轻舟》入选日本国际摄影沙龙,其后他便成为国际摄影沙龙中的常客。据统计,他一生累计入选国际摄影沙龙的次数多达三百余次,作品在千幅以上。
郎静山的作品如此受青睐,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创作了一种颇具中国风的摄影技法,即将中国画的六法与摄影结合在一起。谢赫“六法”为: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六点构成了中国画创作的基本准则,而将此六法运用到摄影则是一种被称为“集锦”的手法,即在暗房中“集合各种物景,配合成章,舍画面之所忌,而取画面之所宜者”。
因此,郎静山的摄影作品更像一幅中国画,他不在意光影的变化,却在章法结构上极其讲究,也会落款及钤印。他还会仿照古画进行集锦摄影,而古画中那坐在松荫下或听风或观瀑或抚琴的高士则由他的最佳男主角———张大千扮演。张大千与郎静山十分亲密,郎静山的夫人曾拜张为师,而张大千的许多照片也多由郎静山拍摄。除了张大千,借着摄影之名,郎静山与齐白石、徐悲鸿等人也为至交。与众大师的交往以及对中国画与摄影的钻研,他作画也是手到擒来,此书中收录的《云山小景图》即是其代表作。
胡适曾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的小说。古文里很少有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和狄更斯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和《迦因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林纾在翻译家中绝对称得上“奇葩”,他不通外文,全凭“意译”,所以增删、错讹时有存在,并以古文翻译西方文学,捡取《巴黎茶花女遗事》中的一段便可知其风格:“君往日书来,祈我释憾君心,马克安有不知?盖君蓄难诉之情,怀不释之疑,急而见诋,吾愈知君笃念之深,实有激而为此也。”尽管如此,他所译小说仍影响到后来很多大作家,如鲁迅、周作人、钱锺书等。
可能就是这样“守古”的思想让林纾的绘画更加师法传统。他的画作早年以花鸟画为主,其后旅居京城,见识了大量的古代繪画名迹,也使其晚年绘画更偏向传统文人画。这段时间也是其画艺的高峰,再加上他深厚的古文功底,在题画诗上就体现出了不同于他人的高度。在京期间,他同严复、郑振铎等名士交往,绘画上与齐白石、金城等人切磋,这也为其画艺提高奠定了基础。
海派绘画风云变幻百年,而这一百年也是中国变化革新,不断有新事物涌现的百年,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使得海派绘画不同于其他画派,它新潮、丰富、包容。除了上述的种种,更多精彩还有一一掀开面纱。
——从任伯年到徐悲鸿”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