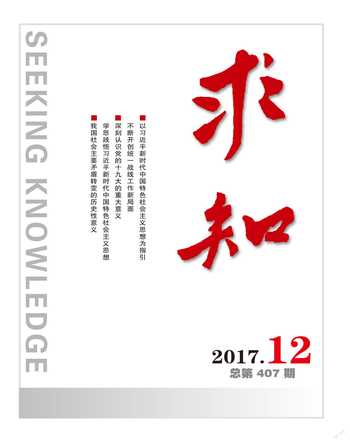国外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与我国的创新思路
陈杨
乡村治理是现代治理的一种基本类型,是指政府及其他治理主体、依托制度设计分工,领导、调控、服务乡村社会发展的行为及过程,其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的长期健康发展。
一、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1.从治理的主体角度看,乡村社会组织发育程度低,是当前乡村治理的突出短板。长期以来,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被定位为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乡村社会组织的主体性、自治性、自主性并未得到充分彰显。乡村社会组织发育程度低、发展不健全,直接影响了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事实上,各类乡村社会组织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表,能将力量分散、组织化程度低的单个农民有机聚合成有力的整体,为个体化的农民参与政治生活、表达利益诉求等提供制度化的参与平台和渠道。
2.从治理的内容角度看,突出体现在公共服务供给和核心资源分配不均等带来的一系列治理难题。一是乡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有限。一方面,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另一方面,环境保护等新型公共服务供给滞后。同时,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政策、规划以及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重视不够,对农村环保治理的投入严重不足。二是土地等乡村核心资源分配不均带来一系列治理难题,对现代农业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都形成了一种障碍。
3.从治理的方式看,德治、法治等多样化方式尚未得到娴熟运用。一方面,德治缺乏厚实基础,另一方面,法治化治理在乡村尚未形成常态。
二、国外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创新
1.法国的“权力让与”治理模式。法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和基层自治传统。从总体上看,法国的农村基层治理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权下的地方有限自治的体制。法国的城市和农村都实行市镇制,市镇的人口和规模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行政村或自然村。据统计,法国全国85%的市镇是农村市镇。在法国,市镇是地方自治性质的基层政权,主要职能是发展公益事业,兴办和维修公共工程,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等。为了进一步增强市镇的自治活力,20世纪80年代初,法国通过了《有关市镇、省和大区的权力和自由法案》,即“权力下放法案”。其核心是层层下放权力,扩大基层自治范圍。在农村基层市镇方面,该法案扩大了市镇的权力,加强了市议会的地位。市镇财政主要由市镇自主处理。同时,注重培植农村基层经济合作组织的自主性,农民可以参加一个或多个合作社组织,合作社内部实行民主管理,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由社员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市镇充分尊重合作社的独立地位和自主性,不干预其内部事务。法国对基层市镇进行的这种“权力让与”对于增加基层自我治理的责任心和自主性的效果都比较明显。
2.日本的现代乡村治理体制建设。二战结束后,日本制定的新宪法第八章明确规定,日本实施地方自治制度。据此,1947年日本制定并公布了《地方自治法》,日本农村开始建立起一整套现代自治管理制度。一是在政治上推行民主政治选举。法律明确规定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均为普通地方公共团体,必须设立各级地方议会并且由居民直接选举首长。总理府内设立地方自治厅(后升格为自治省)管理地方选举和财政支援等事务。二是实现自然村行政村的有机统一。在合并町村的过程中,传统的自然村依然得以保存,形成了行政村和自然村的双轨制格局。三是农协和行政系统相互合作。日本在农村地区建立农协组织,农户100%参加农协。农协以行政村为基本单位,向下深入自然村并形成联谊组织,向上建立县级联合会和全国联合会。农协通过村级组织扩大了农民的经营规模,通过县级组织垄断了农村商业市场,还通过全国中央组织建立了农协银行等。四是合并农村行政单位以提升行政效率。21世纪初,日本农村开始第三轮行政单位大合并。由1999年的3232个市町村自治体减少到2013年的1719个,其中行政市为789个,行政町为746个,行政村184个。这次合并扩大了地方自治体的规模,节约了行政费用,有利于地方分权,实现和中央的对等平权关系,也有利于确立适度规模的城乡结合和功能完备的居民生活圈。
3.韩国新村运动中的乡村治理举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韩国新村运动,在乡村治理创新方面,有两个举措值得关注。一是关注农民的精神启蒙。针对农民文化素质较低、缺乏创新精神的现实,韩国将农民的思想启蒙贯穿整个新村运动并将其作为全面振兴农村和农业的一个关键环节,以培育农民“勤勉、自助、协同”精神为新村运动的价值导向,培养农民勤奋向上的精神,凝聚农民共识,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二是构建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协作供给模式”。为解决农村贫困落后的问题,韩国新村运动开展初期,由财政出资给全国所有3.3万个村庄和居民区修建农村道路,完善农业生产设施,改善农村居住环境等,由各村庄居民根据实际需要民主决定具体的建设计划。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重点提高农村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水平,增加农民福利,缩小城乡差距,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韩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投资来源有各级财政投入、民间企业投资和农村合作组织筹资。通过构建政府、企业、民间团体多元协作供给的模式,韩国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得到快速提升,基本上实现了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
三、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创新的总体思路
1.树立乡村治理的新理念。在城镇化进程中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是我国乡村治理创新的基本方向。为此,在乡村治理创新过程中,应当依据城乡一体化原则,树立起一些新的理念。一是要重新认识乡村价值。自现代化进程开启以来,城市优越、农村落后,城市优于农村的理念就非常流行。事实上,城市与乡村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必须正确对待两种文明的关系,不能以一种文明驾驭在另外一种文明之上,而是要择其善者而用之,促其相互融合。二是重新认识城镇化的基本途径。历史上,发达国家的城镇化都走过了人口向城镇聚集、郊区化、远郊区,甚至是乡村化等不同阶段。在我国过去的城镇化进程中,受工业化浪潮的冲击,城乡差距拉大,现代都市生活具有强大吸引力,农民流向城市不可阻挡。但随着乡村的不断发展,新农村建设持续推进,部分乡村开始具备城市般的生活舒适度,也有部分乡村发展乡村旅游、规模种植、乡村服务等新经济,吸纳了更多就业人口。因而,农民市民化也可以通过农民的职业非农化、流动自由化、乡村美丽化、村镇生活城市化等来实现。三是以真正的治理意识引领推进城乡一体化。考虑到过去城镇化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乡村治理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以适应社会需求。在未来的乡村治理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突出“治理”的色彩,探索政府与农民及社会组织的对话、协商与合作,在乡村事务治理中构建出政府、社会组织和农民共同参与的格局。
2.乡村治理制度创新的主要着力点。一是大力发展乡村经济,奠定良性治理的经济基础。在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应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的总体开发。着力发展乡镇企业,充分发挥乡镇企业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助推作用,进而增加农村就业机会,引导精英回流。在经济方面,未来要重点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组织、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和组织制度创新上下功夫,发展更加强大的农业产业。还应进一步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强农业科研,实现产学研一体化,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实用农技推广,积极扶持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和农民自主创业,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同时,在城镇化进程中,应该注重提升文化软实力,保持乡村原有特色,开发特色资源,发展生态旅游,促进农村文化消费。二是改革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实现政治治理的良性发展。改革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实现政治治理的良性发展重点是要重新定位各治理主体的功能。在完善治理制度方面,应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完善农村民主选举制度。在规范民主管理方面,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是目前农村地区普遍采用的民主管理制度,是农民参与民主管理的重要依托,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的相关规定,保证村务的民主管理。在加强民主监督方面,应完善村务公开、财务公开、村民评议制度,将农民享有的监督权落到实处。还应进一步明确乡村治理主体的职责与功能,防止各治理主体职责的交叉、重叠,完善以村民自我治理为主导的乡村治理模式。三是推进农村土地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完善核心利益的公平分配机制。要进一步明确土地权属,加快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权益,推动土地规范流转,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同时,还要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逐步构筑和完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基础性工程。四是增强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形成乡村治理的外部保障机制。要树立正确的施政理念,为社会提供系統性、制度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公共服务。要保障公共服务的财政支持,加强对公共服务的监管,健全公共服务体系。要逐步扩大公共服务覆盖面,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支出、消费、增长、供给及管理模式。要重塑政府与企业、基层自治组织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服务投入方面的合作互动关系,建立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公共物品决策体系,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五是扶持农村社会组织建设,为乡村治理发展提供组织和法律保障。积极引导和扶持农村社会组织的建立、改革与完善,规范其内部管理制度,进而使其充分发挥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改善乡村文化环境,将法治观念融人农民的基本观念之中,作为农村社会组织行为的基本准则,继而提高乡村治理主体的法律素养,保证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合法性,为乡村治理的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责任编辑:双艳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