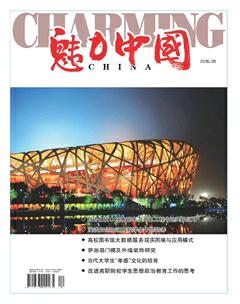清代方志《藏纪概》的整理和研究
胡江花
【摘要】中华民族具有5000年的灿烂文化,历史文明一直延续,文字的记载和文献典籍起着重要的维系作用。地方志是我国古代文献中的一个类别,历朝历代发展到盛世无不修志,到了清代,方志学的编纂句读的一个整理并从文献学角度对它进行探究。它是清代成书的最早著作,是了解十八世纪初叶西藏政治、风俗等很珍贵的资料,也是清代研究藏族史的一手资料,因此,本文对《藏纪概 》进行阐述、研究进行阐述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清代方志;《藏纪概》;整理与研究
一、清代首批方志产生的原因
(1)康熙末年,清政府加大力度治理西藏是首批藏志产生的根本原因
清初,清政府对西藏一直奉行羁糜政策。随着三藩的平乱、恢复台湾、击败沙俄。到康熙末年,清政府开始调整治理西藏的策略,由羁糜抚绥转为直接治理。当时,西藏政局动荡频频发生战乱,康熙五十六年,长期与清对抗的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到策妄阿喇布坦时期派策零敦多布起兵入藏,导致西藏社会动乱加剧。康熙五十七年,清政府第一次用兵西藏,兵败未果。康熙五十九年,第二次用兵西藏,驱除策妄势力,藏局暂稳。雍正元年,青海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清政府第三次用兵青藏,平定其乱。雍正五年,爆发了“卫藏战争”,清政府再次派兵入藏平乱,并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同颇罗湘共理藏政。乾隆十五年,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谋叛,清政府第五次用兵西藏,至此西藏长期混乱的局面才逐渐稳定下来。随着藏乱被平定下来和清中央政府加强治藏力度,内地与西藏的往来日益频繁,因此,从各方面了解西藏成为必然。从编撰《皇舆全览图》,清政府就开始了对西藏山川地理的勘测调查,此图“荒远不遗,纤细必载”,是中国第一幅用近代方法测量绘制的全国地图。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上谕“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之地,皆目击详求,载入舆图。今大兵得藏,边外诸番,悉心归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图。其山川名号,番汉异同,当于时考证明核,庶可传信于后……尔等将山川地名详细考正具奏。”这份上谕正发布于清政府第二次用兵西藏平定策妄乱藏之后,要求前方将士将藏甘川滇大西南一带诸水水源、西藏山川地名考求明核,是清政府了解藏情的一份重要指示,推动了大规模调查记录藏情的活动,进一步促成和加速了我国首批藏志的产生。
(2)清政府重视修志是产生的重要条件
我国历朝历代,盛世无不修志。发展到清代,方志编撰达到鼎盛。清代方志之所以能达到我国古代方志的全盛时期,与清政府重视地方志和一统志的编修密切相关。清政府重视方志编撰,也是我国首批藏志产生的重要条件,“编纂《一统志》和各地方志,正是清政府维持对全国各地有效的统治,维护大一统局面的重要举措和手段,也为反映清朝的大一统状况和清政府的功绩提供了一个载体”。在重视修志的大背景下,雍正诏谕“著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葺,务期…以成完善之书”,此份修志诏谕“适奉檄修直省通志”则为我国首批藏志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更进一步助推了西藏方志的继续发展。
(3)参与修志个人努力也是另一重要条件
清政府五次用兵西藏平乱,1727年设置驻藏大臣,一来一往就使得交流更加频繁,在人们心中留下了大量的所见所闻,于是就将这些都记录下来,成为纪略,或者志书,最后它就成为首批藏志产生的资料来源。例如《藏纪概》的作者李凤彩,江西建昌人,康熙五十三年(1714)中武举,也是清军首次进藏的一员,康熙五十八年随从山东登州总兵李麟护送达赖喇嘛进藏,撰写《西藏行军纪略》两卷。第二次用兵进藏,在拉萨停留6个月,“见其人老成达事者,询其建置沿革”未果,“姑就目击耳受者叙之”“留心风土,采访夷情”“咨访老练,记注殊异”。为何会如此?“中外悉归皇舆,纪载宜补未备”等。总之,一部方志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而成,是偶然中的必然。
二、《藏纪概》的编纂过程及内容
方志《藏纪概》在书《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与《中国地方志综录》均作方志著录,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方志大辞典》也有词条作专门介绍。一般来讲,一部方志的内容及特点,尤其是其中那些不见于他书的记载,与著者的经历,特别是著者在搜集材料与编撰时所处环境及具有的条件密切相关。《藏纪概》也应是如此。因此,非常有必要对此书的编撰情况、内容及特点先作探讨与分析。
此书作者李风彩,江西建昌人,康熙五十三年(1714)中武举,也是清军首次进藏的一员,康熙五十八年随从山东登州总兵李麟护送达赖喇嘛进藏,撰写了《西藏行军纪略》两卷。《藏纪概》是不是在此基础上编写而成,还缺乏有力证据,但是两者肯定具有一定的联系,现存于世的《藏纪概》共有三卷,卷首有唐肇序,唐肇其人生平不详,序文末标署撰写时间为“雍正五年夏至前”,可知《藏纪概》编写当在康熙六十年至雍正五年间。有关它的作者,书中每一卷前都有铁船居士(李风彩)吴丰培先生有考证和奎峰山人,此人生平不详,通过阅读,可略知奎峰山人在当时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儒学者,评论中提到“余恒览天官书”,可知他熟读古书是一位传统的儒学者,对藏族文化了解甚少。在编写过程中奎峰山人称:“铁船本孝廉效力,行间进履其地,不但降氛安藏,功绩居多,而且留心风土,采访番情,以备一朝之纪载,供纬划之考稽,归来述其见闻如此。”可以得知李凤彩在西藏留心考察,编有著述。李风彩从藏地归来后向奎峰山人述其经历,编成《藏纪概》。因此可知《藏纪概》不是李风彩所著《西藏行军纪略》也并非奎峰山人在原书籍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评论,而是两人集体完成的有一部书籍,此书中不同的篇幅,编写的方式也不同,书卷初署名“修江铁船居士纪次,吴陵奎峰山人读辑”,卷之次署名“修江铁船居士辑编,吴陵奎峰山人辑订”,卷之尾署名“修江铁船居士叙编,吴菱奎峰山人辑订”不同卷数标注的方式也不同,从这个信息可以看出两人在成书过程中分工不同。而在摘抄的史志材料涉及的方面,与可能对西藏的认识不仅缺乏系统性,所以其书《风俗》、《物产》目中真正反映西藏地区的材料并不多,风俗习惯、衣食住行及物产等,书中多为零散的的记载,有的方面还有所欠缺,因此它只可以看做是方志的一个雏形。卷之初:康熙皇帝论地理水源,详细叙述了李风彩入藏经历。卷之次:记录四川成都至乌斯藏路程,李凤彩随军从西宁出发,从青海入藏,在由川藏返回。卷之尾:記录了西藏的风俗习惯,这也是最能体现出它具有西藏方志特点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可以推测《藏纪概》创作过程:李风彩随军进藏,留心考察西藏的风俗物产并记录去西藏的行程路线,将在西藏的见闻一起共同对比,有奎峰山人执笔,对李风彩原稿进行整理和辑订,并加以个人评论,最后成书,命名为《藏纪概》。
三、《藏纪概》的编纂特点及价值(文献价值、史料价值)
(1)很好地保存了18世纪初叶有关西藏的历史大事。展现了十八世纪初叶西藏西藏风云骤变的政治军事,又因为其记载具有亲历性和最初性,可性感度比较高,不仅为后期一些藏志极其相关著述所采用,也是今日藏学界不得不参考的重要文献正如学者评价的:《藏纪概》“是西藏方志乘之首”(2)对西藏的地情、民俗、民生并举记载。记录西藏的山川,地理,交通,风俗,宗教,礼仪等,尽管有些门类的内容不是很具体,但是大多都抓住了藏族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为后期西藏地方志的撰写打下了一定的基础。(3)开创了具有西藏特点的西藏方志体例。方志是全面记载一个地方,并且凸显某个地方特点的一种体裁。《藏纪概》首次全面记录西藏的方志雏形,写作模式较为成功,书中除了记载随军进藏的路线之外,还记载了西藏的种类,物产,招迹等条目,涵盖了西藏的气候,物产,地理和风俗等各个方面,后来雍正朝《四川通志·西域志》中的内容基本上是在《藏纪概》体例基础上撰写的。(4)文化色彩浓厚,汉藏文化对比较为明显。文中的叙述着眼于汉藏文化的对比,唐肇在序中说,《藏纪概》对“彼中所无,中华所有,中华所不足道,彼中习以为宜然者,略加忝论”因此,文中对于文化的对比色彩显得非常的浓厚,譬如对西藏天气就有这样的描述:“总似中华二八月也”,奎峰山人论曰:“云南省夏多雨,则年丰,故昼无酷暑气,东多晴,故不甚寒,今乌斯藏四时昼夜亦然”在比较的过程中,缺乏理性的思考,将异族文化与本土文化想联系,缺乏进一步的理性和深入思考。另外,传统文人会有很强的优越感,所以很容易形成对异文化的歧视,不能够更加客观的认识文化的本质。因为这部方志的的作者是李风彩,奎山峰人都是儒家人士,由于对藏文化了解的不够深入,所以在比较过程中会出现贬低藏文化,抬高汉族文化的现象,这也是一大特点。(5)弘扬大一统观念贯穿其中。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王朝在政治上实现统一后,思想文化上的统一观念也很快提升。《藏纪概》虽然不是官方著作,但作者是食官俸之士,奎峰山人也是饱读诗书的儒家学者,其思想深处早已经打上了大一统的烙印,因此政治文化认同在《藏纪概》中表现的非常强烈。譬如在卷首序中,奎峰山人云:“声教远播,唐明两代可谓盛矣!按稽史册,皆莫能如我朝之廓大”卷前首列康熙皇帝谕旨,既是尊王权的表现,也是大一统观念的表露。(6)客观上给中原人士带来最新的西藏知识,促进了西藏文化在内地的传播。书中提到西藏的山川、河流、藏族服饰等,以前几乎闻所未闻。李凤彩归来像友人叙述西藏的所见所闻,这是清军首次入藏后,西藏文化在内地传播之一例,《藏纪概》刊印入室,极大地促进了西藏文化在内地的传播。
总而言之,作为西藏方志书的第一部《藏纪概》具有一定的价值:对于康熙59年清军由西宁进兵至拉萨平定策零敦多布乱一事,对青藏路上所发生的所见所闻记述的最为详细。保留了早期川藏、滇藏的路程记载。该书还有唐“叙”、自述“原由”和“奎峰曰”之论,可以帮助阅读者把握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作者对所经历之事的一个感情态度和倾向,理清历史的真相。收集了当地民俗地情的相关资料,虽然无法与后起得《后藏志》相比,但比起同期的《藏程纪略》有关服饰,气候等记载的就比较详细。
但由于所处时代背景的限制也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作为西藏方志书的第一部,编纂工作完成于雍正初年,无论从体裁体例上,还是书中内容,其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书中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1)书中的内容过于简单。之所以说是西藏方志的雏形,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方志书,主要是因为内容过于简单。一部成熟的方志应该包括所记地区的历史、地理、风俗、人物等各个方面,《藏纪概》在内容上显然是不符合方志严格要求的,主要原因因为是当时人们对西藏缺乏了解,作者虽然入藏有半年的时间,但是因为公务在身,无法亲身游历做进一步考察,多是听别人说的,亲自感受少,而参与《藏纪概》的辑订者,奎峰山人似乎并没有去过西藏,这必然会导致内容上有些过于简单,,由于属于私人修书,虽然两人协作,但是官方档案难以查阅。《藏纪概》对西藏历史叙述涉及很少,仅仅云:“大宝法王等已经《明史》列入列传,其文字繁多,不复补载”对清代的历史从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军进藏开始谈起,因此说《藏纪概》仅仅是西藏方志的雏形,为后人进一步了解西藏,编纂西藏志书奠定了基础。(2)体例不纯首次创新西藏方志体例,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时代的局限,分类过于粗略,例如:农事和医卜都混为一体,这些缺陷可能与该书大编写方式有关。另外,因为编写方式是两人合辑而成的,一部分是李凤彩述编,奎峰山人辑订。(3)书中大民族文化偏见比较严重。传统文人对异域文化有很大的偏见,不去从内在挖掘异国文化,风情内涵,而是以天朝大国自居,从儒家文化角度去评判一切,这种思维方式几乎是传统文人的共同特征。
四、清代藏族方志史上的地位
《藏纪概》是清代西藏方志的雏形,长期以抄本的形式流传,20世纪70年代末才以油印本广为流传,应当说,近几十年来方志学界对这部方志著作还是比较重视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清代西藏方志史上,这部方志尽管相对简略,体例上也与内地常见的方志著作不大相同,但对后来的西藏方志编纂却产生了值得注意的影响。此书在编撰及资料上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反映了清代西藏方志的发展,也使此书在清代西藏方志中具有重要地位。部分材料为编撰者亲历及耳闻目睹所得,在西藏研究及川滇藏区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 刘凤强 《清代藏学历史文献研究》北京[M],人民出版社,2005年
[2]李凤彩 《藏纪概》,转引自吴丰培 中国民族史地资料丛刊,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1978年,第7一 8页
[3] 巴兆祥《方志学新论》 北京 学林出版社,2004 年, 第111 页
[4] 曹抡彬、曹抡翰 《雅州府志》·西域 [M],转 引自张羽新 《中国西藏及甘杳川滇藏區方志汇编》 [Z] 第37 册,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3年 第 3页
[5] 吴丰培《藏纪概·跋》,载《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第1函,第58页正面,彭升红的《清代民国西藏方志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对李凤彩生平及著述亦有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