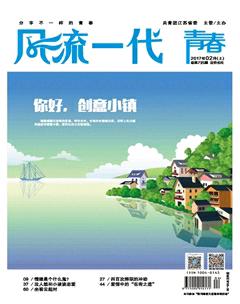耐烦
耿艳菊
起初,我以为“耐烦”只属于豫东,是方言乡语。奶奶喜欢菊花,喜欢田里的庄稼植物,喜欢喝粥,喜欢穿旧式的棉布斜襟的衣裳,喜欢我们这些孩子的热闹。可是,她不说喜欢,她总是笑眯眯的,一脸慈爱地说,我耐烦菊花,耐烦孩子们……
母亲也是这样说,我的那些亲戚邻居们也是这样说。
他们对喜欢的人和事,都说“耐烦什么什么,耐烦谁谁”,讲起不喜欢的,就说“不耐烦什么什么,不耐烦谁谁”。仿佛“耐烦”就和田里的庄稼和泥土一样,是属于他们的质朴和亲厚。
而“喜欢”这个词对于乡人们来说,就有点书面化了,像城里人的词汇。若由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说出来,总觉得不妥当。有点矫情了,听者别扭,说者也疙疙瘩瘩地心虚。
记得青春韶华,悄悄喜欢一个人,给远方的朋友写信,信里用的是中意二字,而向身边的朋友说起那人,用的是耐烦。中意和耐烦,它们都有古意,比“喜欢”更为曲折婉约,也最能情辞达意,不失含蓄微妙,正契合了那种悄然的情怀。
没想到,沈从文先生也說耐烦。看到一篇《听沈从文先生说话》的文章,讲到沈从文先生生前演讲的录音。沈先生说,一切都要经过训练……我是相当蠢笨的一个人,我就是有耐烦,耐烦改……
沈从文当年来北京时,甚至连标点符号都用不好。可是,他“有耐烦,耐烦改”,实在令人感佩动容。况我辈平平资质,更应多训练,有耐烦啊。
沈先生这里说的耐烦,有喜欢的意蕴,却不是喜欢的意思。而是有耐心,有耐性,不怕麻烦。
人活着,还真得有耐烦之心。沈先生后来从文学写作转到了文物研究,那时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工作很机械,可是他的心不机械。他有耐烦,饶有兴味地关注,从而又有了文学之外的成就,完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
耐烦的烦,很一目了然,是麻烦、烦恼。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世上哪有那么多的赏心悦目呢?怎么办呢?还是乡人们的办法好,耐烦啊!喜欢多了,烦恼可不就少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