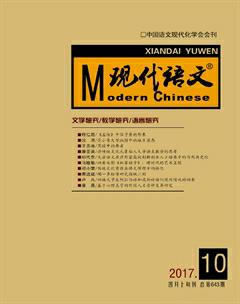从真实感的塑造审视贾樟柯的现实主义风格
摘 要:从“故乡三部曲”到《三峡好人》,贾氏影片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冷峻现实主义”风格。贾樟柯2015年上映的《山河故人》无疑也是一部艺术水准成熟的现实主义作品,他一如既往地从个人的角度切入时代,从人生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段中体察时代变迁中漂泊的情感,用记录、体验、虚构和想象完成了时空、人物、情节等多方面的真实感塑造,但也存在着符号化意象过多、主角造型失常、人物情感单薄等问题。
关键词:贾樟柯 山河故人 真实感现实主义
作为第六代导演“作者电影”的领军人物,贾樟柯的关键词与其说是“批判”“揭露”,不如说“真实”更为准确。在贾樟柯的最新一部作品《山河故人》中,“真实”仍从故乡出发,从1999年的山西汾阳,走到了2014年的上海,2025年的澳大利亚,最后回到汾阳,是一部颇具时代感和导演个人化印记的影片。90年代既是中国加速发展与变革的时代,也与导演本人的青春暗合。而故乡作为一个固定的原点,足以支撑故人从故乡离散后的情感张力。从缅怀古老情义到展现情感漂泊,不得不说,作为一个清醒的电影人,贾樟柯有种体察现实和悲悯人生的情怀,正是这种情怀让他能够保持距离看待现实,然后借由电影抒发出来。他认为,“我们跟现实的紧张关系一直存在,没法逃避,也化解不了”,而“在任何时代在情感的世界都有一些障碍”。[1]《山河故人》中的“几何问题”和“代数问题”正指向了这种紧张关系和情感障碍,年轻的主角开玩笑般抛出的疑问实际上可以概括他们在大时代下流变的人生。“几何问题”象形地勾画出沈涛、张晋生、梁建军三人的三角关系,而隐隐指向国人在时代变迁中的情感选择与情感障碍;“代数问题”比较了张晋生、梁建军二人的金钱地位,深层次上则指向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变革,以及个体在经济漩涡中受到的影响,从物质逐渐蔓延至精神。
《山河故人》无疑延续了贾樟柯一贯的现实主义风格,素材上也选取了当年的纪录片素材,与《站台》《三峡好人》《天注定》等冷峻的现实主义风格相比,因主题偏向情感而多了一些温情,人物关注面也从底层、边缘的小人物扩展到中产阶层。但贾樟柯针对这些现实困境或精神困境所创作的电影,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呈现,整体上仍保持了一种从个人角度讲述时代的,真实、平淡、隐忍的叙事基调。他的“个人印记是社会、历史、文化、家庭众多因素合力所烙下的。”[2]这种独特而相对稳定的风格有其独特的价值,正如贾樟柯在谈到《三峡好人》时所说:“我觉得生命的本质没有变化,但我会去感受每一天的生活。譬如在这部电影开场,长江里的一艘船,众生相看上去没什么痛苦,但是镜头一收,其实那是一条很孤独的小船,在长江上漂流着。”总体视角的孤独和悲情,与近距离的生命力、活力总是共生共存的,人总是在流动的时间、空间里被左右,并悄悄改变着。下文试图从影片塑造的时空真实感、人物真实感、情节真实感三个方面入手分析《山河故人》所呈现的个体情感漂泊与整体现实主义风格。
一、时空真实感
90年代正是中国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这时社会开始富足,新的生活方式也陆续出现,手机、电脑、互联网、飞机、高速公路……[3]这些事物开始对人际关系、人的情感产生强烈冲击。因此这也正是“故人”开始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时机,贾樟柯借片名“山河故人(Mountains May Depart)”的出现时机——影片开场四十分钟,故事的第一个段落之后,1999和2014之间——有意识地使观众抽离,强制性地隔开了在时间流动中分离了的故人和情感。
三次画幅变化则是导演对DV素材(未经后期处理的数字视频文件)的忠实,保留了难以复制的时代氛围,现代电影技术的进步则实现了现时拍摄与DV素材的完美融合。三种画幅不仅能够带来对不同时代的清晰辨识,还展现了人物在从青年走向中年的过程中主体性的减弱:第一个段落采用1.33:1(即4:3)的画幅比,镜头专注于人物;第二个段落采用1.85:1(即16:9,对4:3进行二次方)的画幅比,这是目前电影广泛应用的宽银幕画幅,镜头不再专注于人物,观众的视野扩大,更符合人们视觉的生理特点,因此临场真实感更强;第三个段落采用2.35:1(即对4:3进行三次方)的画幅比,横向视域继续扩大,影像画面广阔感增加,因此人物空间被压缩,人物生存的物质空间和心灵空间也微妙地呈现给观众。
除了画幅比,影像的时空塑造,即时代感和地域感的塑造非常丰富,这类真实感的创造无愧于现实主义风格的要求。贾樟柯认为:“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这种和我们擦肩而过的东西能感染我们。所以我觉得电影也应该容纳这些笔触而不是一味強调情节这种密集的推动。就像我们读《红楼梦》一样,它除了写爱情故事,还有很多闲笔。有很多笔触在写食物、在写天气,这是生活本身应该具有的美感,电影也应该容纳这些。”[1]比如沈涛在楼上看见的拿关公刀的小孩,他也是一个漂泊者,作为一个人物符号,他和主线人物的命运是一样的。还有伞头秧歌、舞狮、文艺汇演、麦穗饺子、过寿(寿桃、面条)等民间风俗;文峰塔、冰冻的黄河(黄河第九道弯)等地域标识;人们帮助翻倒的煤车、捡拾漏下的煤块,焚烧秸秆,年节时观看表演的万人广场,坠落的播种飞机和十几年后在路边祭奠的母子,为逝者超度的僧人等景观标志;钥匙、狗、枪等情感寄托;涛年轻时的旧毛衣、国际小学、苹果手机等时代标记……这些丰富了时间感与空间感的事物多次出现,作为表征的符号形成“有意味的形式”,也带来了在中国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条件下,对传统、对身份认同和人际关系的思考。
在贾樟柯的电影中,音乐是包含生命力的时代元素,它们既可以悄无声息地营造时空的真实感,又可以帮助人物塑形。比如《三峡好人》中借由流浪少年之口唱出的网络歌曲《老鼠爱大米》,这是时代变迁对拥有两千年历史痕迹的旧县城的闯入,也是生命片段的茁壮与活力,带有狂欢气息。《山河故人》使用最频繁的是迪厅舞曲Go west和叶倩文的《珍重》。Go west是90年代迪厅的青春记忆,也是沈涛人到中年孤身一人重逢青春的生命力;《珍重》则以其厚重的情感裹挟着漂泊的人们,替他们牵挂着逝去的情感。
贾樟柯的主笔和闲笔都着力于浓墨重彩地塑造时代和地域的厚重感,大量的符号和意象借助银幕画幅的形式转变在此中展现,无疑有着极强的视听冲击感,在银幕人物和观众中建构了情怀和情感的共鸣,从而完成了时间与空间的真实感塑造。
二、人物真实感
情感真实是《山河故人》塑造的核心,于是贾樟柯把人物的真实感落脚到了情感的处理上。
首先,电影人物有一个演员选择的问题,贾樟柯大多采用非职业演员或半职业演员,如《三峡好人》《站台》《山河故人》等中的韩三明、王宏伟、梁景东,以及当地的群演,复杂的或相似的阅历使演员的表达更贴近生活本色,戲剧性减弱,现实记录性增强,于是现实之“冷峻”便更为显著。但根据角色定位,贾樟柯也逐渐选用职业演员,如《天注定》《山河故人》中的王宝强、姜武、张嘉译、张译、董子健、张艾嘉等。《天注定》取材于三件真实社会案件,电影改编后的戏剧冲突性较强,更适合职业演员的爆发力和感染力;《山河故人》有多半内容脱离了汾阳小城,且部分角色因身份定位的需要要求更高的契合度,因此演员选择必定需要超出小城范围而逐渐扩大为全国乃至全球视野,这样才可以在更高程度上满足人物真实情感的塑造。
其次,电影人物的声音造型是塑造真实情感的重要方面,包括语言、声效、音乐等。在人物方言俚语的使用上,贾樟柯一直坚定地从他的故乡——山西汾阳出发,进而随着人物的漂泊逐渐扩展至四川话、上海话、普通话、英语等。《山河故人》也是贾樟柯第一次直接从全球性视野展现时代流变下的个体。正片开始之前的波涛声和开场Go west的舞曲衔接,正应和着到乐在澳大利亚的海边伴着波涛轻声呼唤母亲的名字,而涛孤身一人随着内心Go west的青春记忆无声起舞。《珍重》则裹挟着涛、米娅、到乐等人的情感,将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痛楚唤起。
再次,人物形象定位、身份定位是情感表达最直观的呈现。沈父和张到乐是电影中对立性最强的情感符号,我们以此为例来看贾樟柯对人物真实性的塑造。
沈涛的父亲是时代变迁中仍坚守情义的一个人物,在1999年和2014年这两个跨越了十五年的时间段落上,他都带着寿桃和面条坐火车为战友过寿。他的情感传统、厚重而隐忍不发,既不肯干涉女儿的情感选择,只借时机避开独自思索;又希望女儿不至于一直孤身一人,请求大姨劝女儿找个合适的对象。在车站为突然去世的沈涛父亲超度的僧人更是坚守情义的代表。在情感偏向冷漠与隔阂的社会,沈涛父亲和僧人们作为传统情感的代表令人感慨与怀念。但即使是在如此厚重的情感裹挟下,情感传达仍然有不可避免的隔膜,更不必说离散了故乡,漂泊在外,失去了情感归属的异乡人了。
与沈父扎根故乡和传统相反,张到乐最明显的特征是“失语”。他的个体身份始终是缺失的,到乐年幼时,张晋生就在上海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有一个对到乐不错的上海妈妈,但沈涛这个亲生妈妈一直处于缺席的状态,除了姥爷去世,母子再无接触。相对而言,沈涛、张晋生、梁建军的故乡身份从始至终都是被认可的,他们的汾阳方言也从不曾舍弃。到乐则不同,父母的故乡、他的出生地——山西汾阳,他几乎不曾生活过,上海也仅是暂居,澳大利亚虽已久居却毫无归属感。青春期的到乐就像一个无家的人,他的生活、精神都缺少寄托。贾樟柯其实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新移民家庭中年轻一代的失语,从母语环境(汾阳话、上海话、普通话)成长起来的张到乐,在澳洲只讲英文,与父亲的交流也只能通过谷歌翻译,与母语的链接出现了决绝的断裂。贾樟柯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他(到乐)是忘了还是不愿意说这对这个人物来说是个秘密,对于我来说这个人物的语言可能是他的一个反叛,是他切断和父亲关联的一个方法。”[1]到乐否认自己有母亲,否认记得母亲的名字,和父亲沟通艰难;但他也正在学习中文课程,一直戴着七岁时母亲给的钥匙,也记得母亲的名字“涛”是波涛的意思,甚至默默讲过山西话“能行”。相对的,漂泊在外的米娅(到乐的中文老师)也否认自己的中文名字,但又追念粤语老歌的情怀,异乡人的矛盾情感显露无疑。
沈涛他们则是处于沈父和张到乐之间的人物,涛的丈夫、儿子、挚友乃至父亲,与她的分离都不止是地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这无情地解构了涛内心仍抱有希望的物质理想,所以涛是孤独的。始终留在故乡的沈涛和离家的张晋生、梁子,同样都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情感的定点,失去了故乡的定点,不得不在时代流转下漂泊。
然而这种失去“故乡”的情形从来不是个例,现代社会的人口流动性使新时代的人越来越难被地域限定,祖籍、出生地、成长地、工作地的变迁,既有长辈迁移的被动选择,也有升学、入职的主动因素。到乐是被决定的新移民,与上一代,甚至与同辈人,都存在文化隔阂,因而缺乏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但是归属感的来源不仅仅是故乡这个地域性因素,更是身边密切的社会关系。就像沈涛一直留在故乡,她最亲密的社会关系也都已离她而去,这就是缺失。漂泊所带来的社会关系以及情感的缺失,是快速发展的社会所不可回避的真实。
三、情节真实感
故事化和情节性塑造的真实离不开逻辑的真实。首先,导演用顺时的时间线索,在26年的跨度中,截取了三个时间点——1999、2014、2025,用因果相连的三个段落,环环相扣,组成了比较完整的故事,不再是《天注定》中用网络式的人物相遇连接的独立结构。第一个段落,沈涛在与张晋生、梁建军的三角关系中,受金钱观念的影响,选择了张晋生,生下一子取名到乐(美元dollar的谐音),梁子则远走他乡。第二个段落,十五年后,梁子生活艰难,因患病选择与妻子回乡,借钱途中从韩三明口中获知沈涛离婚,张晋生在上海搞风投,家里煤矿同样难以维持,三明已决定去阿拉木图为中石油做焊工。沈涛父亲在车站离世,涛接到乐回汾阳奔丧然后送到乐回上海。张晋生与到乐也即将移居澳大利亚。第三个段落,到乐已经长大,与父亲有深刻的隔膜,与中文老师米娅产生忘年恋。到乐在海边念出母亲的名字“涛”,涛则在汾阳独自一人包饺子、遛狗,在黄河边跳起青春时的舞步。
人物的结局都与他曾经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有隐秘的因果联系。梁子的结局虽然缺席却不难想象,导演虽然展现了金钱观念对涛的影响,却从未批判,因为这些个体不是批判的矛头,这是生活,是大时代下的个体流变。
其次,故事虽有因果联系,贯穿整部电影的却不是传统戏剧故事的因果关系,而是人物,是同样处在漂泊中的主线人物:涛、晋生、梁子、到乐、米娅。贾樟柯认为:“今天我们的生活方法改变了,我们理解的世界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叙事方法也要改变。结構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方法。”[4]贾樟柯的叙事结构并不新颖,但正如《天注定》选择以上网般的感受串联起王宝强、姜武、张嘉译、赵涛的相遇,《山河故人》选择以个体人物承载时代发展中难以磨灭的印记,因为这是最逼近生活真实的艺术选择。
最后,特定构图可以作为情节塑造的辅助。影片开头的人物群像利用房屋结构的便利形成了圆形构图,沈涛、张晋生、梁建军三人身处其中,形成视觉中心,因而人物没有松散感,情感也不疏离。主角人物之间的三角构图则使画面稳定,但所谓稳定的三角关系,在情感中实际上最不稳定,外在的金钱、权力,内在的尊严等许多因素都可以打破它。在青梅竹马的沈涛、张晋生、梁建军三人关系坍塌之前,梁子就已经被张晋生的金钱逼迫离开了煤矿;关系坍塌之后,更是远离家乡。在迪厅,沈涛、张晋生二人彻底打破距离,沈、张二人被置于迪厅闪烁昏暗的灯光之下,而梁子独自隐在迷离光线的暗处,三角坍塌。梁子和张晋生在煤矿矿灯管理处的交锋则利用窗框,形成了“画框中的画框”构图,窗框隔开并分别突显了张、梁两个人物,张晋生从外侧压住窗框的行动更对窗内的梁子产生了压迫感,这是一种比较强烈的视觉表达,将人物内心的某种冲突展现出来,同时与梁子、三明二人隔着窗框的温和交流形成对比。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隐喻,比如离家十五年的梁子在检查出尘肺病之后,在路边与一笼中虎对峙。笼中老虎的隐喻将底层人物内心的不甘与无奈展现出来,但梁子的性格温吞、沉默,缺少反抗与突破,就支撑笼中虎的意象而言有些无力。
《山河故人》精准提取了时代元素、地域元素,利用真实的记录、个人的体验、虚构和想象的故事,拍出了时间对情感的介入。贾樟柯的“故乡”也更直接地关注了国人的离散与漂泊,这既延续了他的现实主义风格,又突破性地将带有魔幻色彩的现实延续至未来。
影片“所带有的某种我们生活境遇的痕迹,能够唤起我们情绪上的共鸣”,[3]这就是感染力,是电影之艺术主题借助“有意味的形式”进行渲染的成功表达。但贾樟柯导演在细节处理上也有一些疏忽之处,虽然无伤《山河故人》的整体价值,但某种程度上还是拖沓了剧情,影响了真实感的塑造。第一,从导演接受采访时的自述中,我们得知导演企图利用闲笔渲染时代或地域氛围,但就实际呈现效果而言,整体符号过多,诸如扛关公刀的青年、煤车的翻倒、秸秆的燃烧等就形成了无意义的累加。第二,人物造型方面则因人物跨度26年,在视觉美感方面容易产生漏洞。首先,就赵涛、张译、梁景东三人的青年造型而言,岁月沉淀感明显,缺少年轻人的莽撞与活力,并不适合二十出头的青年人造型。但考虑到影片人物的连贯性和统一性,以及演技表达和人物本色出演的需要,主角三人的青年时代由赵、张、梁三人演绎是合理的。其次,沈涛、张晋生二人的中年妆容(五十岁)用力过度,我们大概可以明了导演意图打破视觉美感,以外形表明沈张二人的孤独疲惫和怀旧情感,但沈涛的造型既不符合她曾经的企业家身份,也不契合她的别墅住宅;张晋生则明显由中年步入了步履蹒跚的老年,不符合五十岁中年人的精气神,亦不符合他富足的身份。第三,影片的情感塑造有些单薄,情感铺垫的缺席与空白使人物的情感表达缺乏细腻感,因此青年主角与十五年乃至二十六年后的情感表达除科技手段外并无太大差异,反倒是不同时代间群体与个人的差别较为明显,这恐怕是一个硬伤。比如青年时涛可能因金钱倾向于张晋生,但涛与梁子的感情塑造明显不如张晋生更接近爱情,涛与梁子的联系最终只能具象化为两个符号——请柬和钥匙,但这两个符号承载不起时代流转之下的情感,有些生硬。如果这些细节缺陷能够得到稳妥的处理,影片在真实感方面的表达应当会更出色。
参考文献:
[1]王珍一,田惠东.心在何处安放 对话贾樟柯[J].时代人物,2016(1).
[2]史可扬.影视批评方法论[M].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3]贾樟柯,杨远婴.拍电影最重要的是“发现”——与贾樟柯导演对话[J].当代电影,2015(11).
[4]解宏乾.贾樟柯谈新片《天注定》——避免暴力,就要艺术地理解暴力[J].国家人文历史,2014(2).
(董偲 山东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27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