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个体的自我救赎
——以刘继明《人境》中的马拉为观照对象
罗晓静
孤独个体的自我救赎
——以刘继明《人境》中的马拉为观照对象
罗晓静
一、孤独的知识者
尽管在小说文本内外都有着对《人境》中的主人公马拉身份的困惑和怀疑——农民?知识分子?文人?——作家作为全知叙述者对马拉的身份其实从一开始就明确定位了:“在逯老师那儿,马拉实现了从一个懵懂少年到具有独立意识的现代青年知识者的蜕变。”作为具有独立意识的现代知识者,马垃给人留下最鲜明的印象是——孤独。
马垃的人生经历看起来有些“异样”。原乡的遗落、情爱的缺失,作家有意识地使马垃成为被“孤独”符号化了的人物。马垃真正的老家在洞庭湖边,然而父亲进湖捕鱼遇难之后,母亲不得不带着他和哥哥外出逃荒,他们在洞庭湖畔四处漂泊,几经辗转在神皇洲落住了脚。人生的无根状态和漂泊感,正是“孤独”的根源。在马垃的成长岁月中,亲情渐次消亡。他年幼时父亲去世,懂事后母亲落入水渠死于意外,十四岁时哥哥为抢救失火仓库中的稻种英勇牺牲。父母和哥哥的相继去世,使少年马垃失去了所有血缘亲人,变成一个真正的孤儿。孤儿,是作家给马垃的孤独所预设的身份前提。多年以后,精神之父逯老师的死亡,最终完成了对马垃作为孤独者的塑造。
马垃青年时期,爱情戛然而止。河口镇文化站图书管理员晏红霞,是马垃的初恋。这个俏丽妩媚、阅读广泛的姑娘,满足了马垃关于恋爱的美好想象。可是,恋爱刚刚开始,晏红霞的父亲因为诱奸女性被捕,晏红霞随之突然失踪,最后传来的消息是她嫁给了一个五十多岁的酒厂厂长。马垃独自在酒馆喝酒,用酩酊大醉祭奠了自己的这段爱情,然后变得更加沉默寡言,直到四十岁还是形单影只。
其后,经历了教书、从商、入狱等人生沉浮之后回到神皇洲,马垃的性格和命运在这片土地上得以集中展开。马垃在堤角边盖了一栋房子,从外观上就与平原乡村的水泥平顶楼房或紫瓦屋截然不同,尖而细的房顶上奇怪地耸立着一架硕大的风车,在无风有风的日子都昭示着不一样的存在。马垃在神皇洲开辟了一片猕猴桃园,猕猴桃这东西神皇洲的人之前见都没见过。马垃发起成立的同心合作社,兴师动众地把刚割完小麦的旱田改成水田,这新花样同样引得不少人啧啧称奇。同心合作社种植的生态大米,经过精心加工和包装后,更是意想不到地以比一般大米高出近两倍的价格卖到各大小超市。从穿着打扮、生活习惯到行为处事,马垃与周围的人总有些格格不入。“在很多人眼里马垃还是个客人”,“虽然马垃不愿意被村里人当做客人,每次去给人家打糍粑时,总是像出门做客一样,穿戴得整整齐齐,脖子上还系了条围巾,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衣服上看不到一点儿泥星子”。马拉的独异于众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主动的选择。
孤独,是孤独者的本质。鲁迅说:“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从肉体到精神,人与人之间总是隔膜的,因而人终究是孤独的,孤独上升为人生的处境或普遍生存状态。真正的孤独者,注定不被理解,需承担孤独;他们往往并不寻求理解,独来独往,甚至寻求孤独。刘继明在小说中引用了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的话:“呵,孤独!你是我的家。孤独啊!我在陌生的蛮人中落荒太久了,所以我不能不泪水汹涌地回到你这里。现在你只是像慈母一样抚摸我,现在你像慈母一样对我微笑,只是对我说:‘从前是谁像一阵风似的离开了我?’。”孤独,注定了是马垃的人生宿命和精神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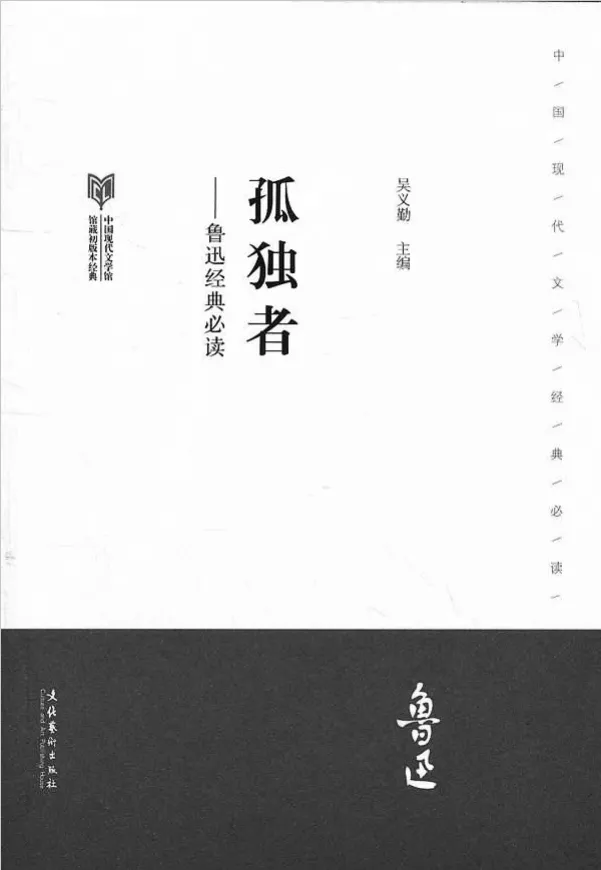
《孤独者》鲁迅经典必读
“孤独”或“孤独者”作为现代意识的表征,一再成为文学书写的主题或人物形象的范式。五四文学中,尤其是鲁迅笔下的“孤独者”,总是生存在个体性与群体性、内在性与外在性的悖论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只要他们一从众、一认同就意味着失败以至于灭亡。由此可见,寻求自我救赎,遂成为孤独者的一种生存本能和现实困境。这条救赎之路,究竟在何方?在马垃身上,我似乎看到了通往天国的一束光亮。
二、内向的自足圆满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承受被剥离殆尽后的孤独,作家也无意于让马垃负担这种空虚,而是经由替代和填补曾经消亡的故乡、亲情和爱情,首先实现了孤独个体内向的自足圆满。
小说里多次提到回到神皇洲的马垃有了一种真正回家的感觉。马垃在这里长大、读书,母亲和哥哥都葬在神皇洲,多年在外的漂泊生活使他讨厌“做客”的感觉,在内心深处他早就把神皇洲当作了自己的故乡。马垃走在神皇洲漫天大雾的外滩上,根本不担心自己走错方向,一个人在自己的家中是不会迷路的。他不仅现实上给自己安了家,在堤角边盖起一栋屋顶上耸立风车的房子;也在精神上安了家,像一棵树那样将双脚牢牢扎进土地,与这片熟悉亲近的土地融为一体。以至于神皇洲被洪水淹没,绝大多数村民离乡而去,马垃却选择留在神皇洲,即使不知道还能在这块土地上待多久……
扎根神皇洲的马垃,陆陆续续改变了离群索居的状态,仿佛一个离家出走的人再次回到人群之中。谷雨,在精神气质上与马拉最为接近,谷雨的信赖和追随是马垃实现合作社理想不可或缺的帮助和支持。小拐儿,死了父亲又被母亲遗弃,再因欠赌债被人打伤,这个孤立无助的少年攫住马拉的怜惜之情,逐渐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唐草儿,从外表到个性都是逯永嘉的继承者,她的出现延续了马垃对逯永嘉的精神依恋。“孤独是一种可怕的销蚀剂,在其中浸淫久了,心灵会渐渐生锈,变得颓废起来。所以,人总得找个伴儿,比如书,比如朋友。有了这两样,他就可能重新振作,将自己的生命与更多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彼此牵挂、休戚与共,只有亲人之间才有的情感。马垃仍旧孤独,却不再孤单。
爱情,是关乎两个人的事,它与孤独似乎有天然的敌对性,孤独者遂不可能拥有完美的爱情。如何处理马垃的爱情与孤独,作家是颇费匠心的。与晏红霞短暂的恋爱不过是一段插曲,实际上,马垃隐性而持久的恋爱对象是慕容秋。马垃十四岁时从破砖窑顶看到“慕容姐姐”湿漉漉的身体之后,别的任何女人都无法在他心里占据一席之地。但这份感情只能封存在心里,从十四岁少年时期悬置到四十岁中年人生。小说结尾写到慕容秋对“目光坚定、神情沉着,身上散发着泥土气息”的马垃产生了奇异的惶然,并决定回到曾经生活过和劳动过的神皇洲去做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差,这个开放式结局留下了意味深长的想象空间。
马垃式的孤独,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并没有构成紧张、冲突的对抗关系,而是在保持个体独立和完整提前下的和谐相融。
三、外向的启蒙理想
马垃这一孤独个体的外向救赎方式,则延续着晚清至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感时忧国精神和启蒙意识。从晚晴开始的“群治”和“新民”的政治诉求,到五四时期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思想文化变革,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统一为具有鲜明时代意义的现代乌托邦理想。现代乌托邦“能给予人以即将取得成功的感觉。它们实事求是地对待人们,并采用人所熟悉的方法。完满地实现他们的理想似乎指日可待。这是一个完全可以实现的过程,从不久以前和当今社会发展出来的过程。人们在这些乌托邦中看不到任何可以认为是不着边际、异想天开的东西”。这种现代乌托邦理想,在小说《人境》中以马拉创立的同心合作社为载体,被描绘成一幅最符合当时条件的图景,一幅可以为人们理解和可以达到的图景。
马拉回到神皇洲之后,这里就从一片自在自为的土地,演化成知识者视线中的乡土:
一切都令他如此陌生。千疮百孔、泥泞难行的道路;这儿一块、那儿一块,像补丁一样良莠不齐的庄稼,大片大片长满蒿草的撂荒的土地,臭气熏天、荒芜干涸的水渠和废弃颓败的水闸,新建的楼房和破败的土墙屋交相陪衬,显得极不协调;整个村子仿佛被刀剃过一样光秃秃的:村道边和房前屋后几乎看不到几棵树,或者即使有,也是又瘦又细,连一只鸟窝也承不住。……村里除了老人就是孩子,几乎看不到几个青壮年,一眼望去,满目荒凉,仿佛电影中遭受过战争洗劫之后的场景。……马垃越往前走越感到疑惑和不安,似乎他走错了路,到了一个他以前从未到过的地方。
在马拉的记忆中,“小时候,每逢端午节后,天气格外的晴好,神皇洲上大大小小的水田一片金黄,微风吹拂,稻菽翻滚,空气中弥漫着早谷成熟的香味儿;天不亮,社员们就下田去割谷,忙得顾不上回家,早饭还要让家人送到田里吃”。如今,这片乡土带着苦涩和隐忍的病态,回乡的知识者为眼前的陌生景象勾起满腹惆怅。具有先觉意识的马垃,由此开始在神皇洲掀起了一场现代乌托邦的建构,而这无疑可以看作是启蒙理想的当代投射。
先行者和变革者,是马垃与启蒙知识分子的共通之处。小说里提到马垃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大浪淘沙》,讲述一群经历过五四运动的青年所经历的青春、信仰、忠诚、背叛等。影片中洋溢着的理想主义气息,曾经让马垃感到热血沸腾、激动不已。马垃和逯老师那批一起下海经商的人,被称为改革开放诞生的第一代“弄潮儿”,这也就让马垃有了不同寻常的见识和勇气。马垃敏感地抓住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政策和现实契机,在神皇洲成立了第一个农业种植和销售专业合作社。这个在外面干过大事、见过世面的人,带领几家村里的困难户,走出一条互助互利的路子。
马垃对于神皇洲还有一整套规划:合作社出资在村里建多媒体文化室和老年人健身馆,购置污水和垃圾处理系统改变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现状,购买一批树苗让全村每家每户都栽各种各样的树木,请建筑设计专家将村里的房屋改造成古朴厚重、消失已久的传统民居。在马拉的憧憬中,神皇洲将变成树木成林、绿阴如盖,鸟儿们筑巢安家的“理想国”。从谷雨的眼光来看:马老师把合作社和全村的未来都规划好了,甚至他操心的不只是同心合作社和神皇洲,而是整个中国。他的心大着呢……这与老师逯永嘉曾经的愿望遥相呼应:购买一座海岛,在岛上建造自己的“理想国”。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平等享有教育、住房和医疗,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前提是不妨碍别人的生活。既不受国家的限制,也没有家庭的约束,就像摩尔在《乌有乡消息》中描写的那样……
在马拉向外的自我救赎中,“个体”与“集体”之间实现了相互生成性和一致性。现代乌托邦思想认为:“具有个人独特的‘超凡魅力’的个体所取得的成就中的新东西,只能以后被运用于集体生活,因为从一开始它就与某些当时重要的问题相关,而且从一开始它的意义就产生于集体的目的。”
四、两种精神资源的矛盾与整合
如果探究马垃这一人物性格和命运的生成路径,作家在小说中对两种精神资源的设置,是不容忽视的思考维度。读者毫无疑问都会格外关注到,马拉的成长过程中有两位价值观念截然不同的人生导师,一位是他的哥哥马坷,一位是老师逯永嘉。
马坷和逯永嘉分别代表了集体和个人两种价值观。马坷高小毕业后就回乡务农,吃苦耐劳、勇敢坚定、诚实正义、乐观积极,深受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激励和影响。仓库失火的时候,为抢救生产队的种子,马坷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刘继明借用马坷的日记,为我们再现了一个时代的青春赞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哥哥就是马垃最崇拜的人,直到遇见截然不同的逯老师。逯永嘉是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因为作风错误被发配到沿河师范教书,他风流倜傥、目空一切、我行我素、遗世独立,是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实践者和传播者。马垃被逯老师卓尔不群的风度所倾倒,追随这位“先驱”辞职下海、创业经商,投机破产以后更是代替他入狱服刑。
仔细阅读作品会发现,这两种平行相悖的精神资源,对马拉来讲并不是等同的。哥哥马坷其实是一个越来越模糊的背影,逯老师作为“启蒙导师”的形象日益高大,直至彻底取代哥哥曾经在马垃心目中的位置。“他不再是那个满脑子革命英雄情结的‘红小兵’,而是一个信奉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崇尚个人奋斗的‘八十年代新一辈’。……他觉得,这么多年来,自己如同一只被逯老师放飞的风筝,尽管貌似飞得很远很高,但始终有一个人在校正和左右着他的走向。这个人就是逯老师。”
逯老师的死,让马垃这只风筝断了线,晃晃悠悠之后,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乡。马垃来到哥哥墓前,经过二十多年的风雨剥蚀,高高的土丘低矮了许多,墓碑上的字迹也漶漫不清。马垃把逯老师的一部分骨灰葬在哥哥坟旁,让两个素不相识、完全不同的人相伴在一起。马垃觉得有点儿不踏实,他们会不会经常发生争吵呢?在马拉的大脑里,哥哥和逯老师早已发生过无数次争吵。他们之间的价值冲突曾经困扰过无数人,也反复困扰着马垃自己。但是,当步入不惑之年的马垃坐在哥哥坟头时,意识到自己真正“成熟”了,必须对后半辈子的生活做出自己的选择。马垃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身上,找到了最为契合的思想资源:“要把如此乏味、空虚、不自然的独身生活变成这种勤劳、纯洁、集体的美好生活,关键全在自己。”
马垃作为具有“自性”的孤独个体,在这一刻开始成型。
当然,小说里马垃的乌托邦试验场神皇洲,最后被汹涌如野兽一样的洪水淹没了。几年来的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转眼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全都未曾发生过一样。神皇洲以及马拉的理想被冲刷殆尽,像一座从未开垦过的亘古荒原。马垃的乌托邦理想或许注定了只能是又一场无法完成的启蒙,但显得如此崇高而悲壮。正如罗曼·罗兰所说:“力量,在孤独中默默生长,成熟……”

罗晓静,女,1978年生,湖北松滋人,文学博士,教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中文系主任。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文学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等,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