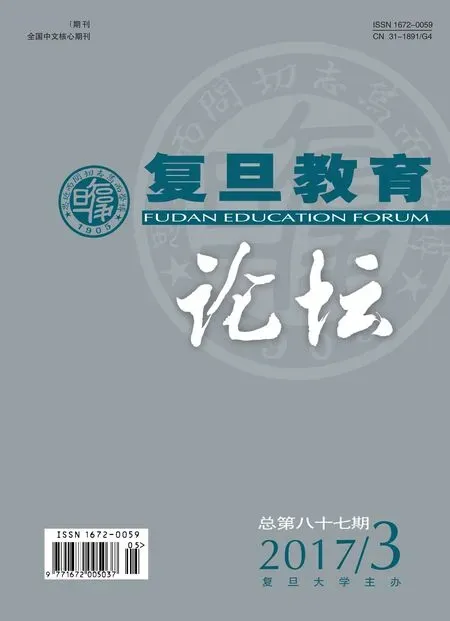论建立公私统一的高等学校法人制度
卢威(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福建厦门361005)
·专题·
论建立公私统一的高等学校法人制度
卢威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福建厦门361005)
我国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法人制度不同、改革理路殊异,这种“双轨制”倾向难以应对理论诘难与实践困境,建立公私统一的高校法人制度势在必行。公共行政范式的转变为此提供了理论依托。多中心治理的兴起,使得垄断性的国家行政转向国家与社会合作的公共行政,公法范围扩张至从事公共事务的第三部门。在国家及其创设的机构之外,从事公共事务的民间自治组织亦应纳入公法人之列。基于此,两类高校均应定位于公法人;同时,为适应其组织特性,应在公法人框架下创设专门的高等学校法人。改革路径是在建立公法人制度的基础上,由法律明确规定高校的法人属性,并据此完善相关制度安排。
公办高校;民办高校;高校法人制度;公法人
重构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完善高校法人制度,既是世界高等教育变革的重要趋势,也是深化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高校法人制度呈现出典型的“双轨制”特征:公办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民办高校①则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而从学界主流观点看,其改革理路分别是公法人化和私法人化。然而,高校无论由谁举办,都具有共同的高等教育机构本质,共性远大于差异。其法人制度的“双轨制”倾向往往过于彰显身份差别,如此不仅易在理论上抹杀它们的共性,并且也为不平等的政策实践提供了根据。那么,两类高校的法人制度有无可能实现统一?若存在这种可能,应将之共同定位于何种法人?对此展开探究,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校法人制度的“双轨制”及其省思
(一)公办高校的事业单位法人定位与公法人化改革理路
1999年施行的《高等教育法》明确了高校具有法人资格,但并未明确其法人类型。在我国,法人是民法意义上的制度,具体是指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我国民法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等类别。公办高校系由国家为社会公益目的举办的、从事高等教育服务的组织,当属民法意义上的事业单位法人。实践证明,这一法人制度的建立并未从根本上改善政校关系。所谓法人,即团体人格,以独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为根本;而“单位”则是匮缺独立性的政府延伸机构。事业单位法人的定位,使公办高校复合了“单位”和“法人”的矛盾属性,其在从事市场经济活动时是独立法人,在政府面前仍是高度依附的单位,以至于陷入了法人化不足的困境。此外,公办高校不仅从事民事活动,还行使一定的公权力。仅从民法意义上确立其法人地位,并不利于对其公权力进行规制。
对此,学界提出了若干改革思路,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公法人说”。1999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拉开了“公法人说”的序幕。在该案中,法院将高校认定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与受教育者之间存在教育行政管理关系,相关争议适用行政诉讼。[1]但由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本身并不能说明高校的法人性质,故被学界视为权宜之计。[2]在司法实践倒逼下,一些学者开始借鉴大陆法系的公法学说,主张在我国建立公法人制度,并将公办高校定位于公法人。目前,在这一理论内部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基于法国公务分权理论的“公务法人说”。所谓公务分权,便是国家将一部分不适合自己直接从事的公务活动,交由它创设的法人来承担。[3]100-101循此逻辑,该观点认为,我国公立学校是国家依法设立的公益组织,具有特定的行政上的目的,提供专门服务,属于公务法人。[2]二是基于德国间接国家行政理论的“公法人中的特别法人说”。在德国行政法中,国家行政分为直接行政和间接行政,后者是指国家通过设立分支单位执行其任务,[4]高校属于间接国家行政的范畴。[5]该观点基于上述理论,将我国公立高校定位于公法人;且考虑到高校的学术组织特性,认为将其定位于公法人中的特别法人为宜。[3]57-62
(二)民办高校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定位与私法人化改革理路
较之公办高校,民办高校的法人性质更为尴尬。众所周知,我国法人制度建立于改革开放之初,彼时商品经济刚刚起步,民间力量远未勃兴,这就使得当时确立的法人分类体系前瞻性不足,难以涵括未来涌现的多种社会组织类型。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民办高校,难以在《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分类中找到位置:作为学校,它们显然不在企业法人、机关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之列;而由非国家主体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现实,又使其与事业单位法人资格无缘。民办高校一般只能依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这一法人定位除了说明民办高校不是企业之外,并不能明晰其组织性质、组织原则和规制方式。如今,法人属性错乱已成为民办教育发展困境的源头性问题,[6]改革民办高校法人制度同样迫在眉睫。
如何对民办高校的法人类型作重新定位呢?传统上认为,公法人是一种基于国家意志创设、执行国家公务的法人制度,从事的是间接国家行政。基于这种认识,民办学校的法人类型只能在私法人框架中进行选择。有观点认为,私法人是私人团体或个人依私法而设立的法人,它可以以私人利益为目的,也可以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民办学校是由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依民法和教育法设立的教育机构,它虽然也从事公益事业,得到政府的承认或资助,但原则上受民法和教育法律的支配,应属于私法人。[7]16私法人可以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前者是“人的集合”,突出组织成员共同决策;后者是“财产的集合”,强调法人财产用于特定目的。在将民办高校定位于私法人的大框架下,对其进一步定位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主张民办高校财团法人化;[8]234二是引入分类管理视角,捐资举办的民办学校为财团法人,投资举办但不要求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为公益性社团法人,营利性的非学校民办教育机构则属于营利性社团法人的范围。[7]81
(三)公办与民办高校法人“双轨制”的缘起与现实困境
从成因看,制度层面的“双轨制”主要源于单位体制。单位体制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为适应计划经济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组织形式,其核心在于以行政整合的方式,实现政府对社会的吸收。在全盘公有制时代,个人通过被编入单位而进入体制,每个单位则通过行政隶属关系成为政府的枝节末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民间组织悄然兴起。尽管这些组织有时也被官方文件称为单位(如民办非企业单位),但它们并非真正的单位组织。经由单位体制的分隔,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二元社会结构得以形成。公办高校作为国家举办的、隶属于政府的机构,顺理成章地成为事业单位法人;而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民办高校由私人举办,与政府不存在隶属关系,无法被纳入单位体制,只能定位于其他法人类型。学理层面的“双轨制”则主要脱胎于传统的公私两分观念。这种传统观念将公域等同于国家领域。在此逻辑下,只有国家和国家衍生或创设的组织才能进入公域;只有国家创设的、执行国家行政任务的组织才有资格成为公法人。这样的界定不仅意味着公办高校只能属于公法人的范围,而且排斥了民办高校成为公法人的可能性。此外,公私两分观念过于强调国家教育权和社会教育权的区分,将公办高校作为国家教育权的行使主体,而将民办高校作为社会教育权的行使主体。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自然倾向于将两类高校划入不同的法人类型。
高校法人制度的“双轨制”倾向,很难应对理论诘难与实践困境。从现实状况看,除举办主体和经费来源外,两类高校均从事高等教育事业,均是准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职能上并无根本不同。那种认为国家教育权由公办高校行使、社会教育权由民办高校行使的理论并非无懈可击。无论在哪类高校,两种教育权均呈现混合状态。公办高校行使的不尽是国家教育权(如适应市场需要开设课程),民办高校中亦有国家教育权的成分(如思想政治课)。何况,国家教育权与社会教育权的分野本身具有相对性,前者来自人民的授予和委托。人民既可委托政府办教兴学,亦有权直接兴办教育。国家教育权是人民意志的间接体现,社会教育权是人民意志的直接表达,不能将其对立起来,进而抹杀两类高校的共同属性。从未来发展看,“双轨制”倾向的高校法人制度,不能顺应公私融合的变革趋势。“公”与“私”的划分向来都属于理想类型,两者的边界在实践中往往模糊不清。尤其是近年来,日益高涨的公私融合浪潮迅速波及了高等教育领域,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均出现公私界限模糊的趋势——高等教育供给模式走向公私合作、公立院校拓展民间经费渠道、公立高校治理模式出现私法人化特征,在此背景下,传统的公立、私立二元论划分法备受质疑,大学越来越像是混合机构。[9]这就充分说明,刻意区分两类高校法人制度将越来越没有意义。从实践效果看,法人制度的分殊破坏了两类高校的平等地位。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本无先天的优劣之分;两类高校中的师生也理应享有平等权利。然而,双轨的法人制度一方面起到了分层作用,使民办高校无法享受与公办高校同等的扶助政策,制约民办教育发展;另一方面也使民办高校被排除于公法规制范围之外,不利于保护其师生的合法权益。应该承认,“公办”与“民办”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校的身份特征,但我们应切忌将高校身份标签化和固定化,而是要立足于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把握它们均作为公共高等教育机构的本质,并基于此推进其法人制度的统一。
二、高校法人制度统一的理论基础与建构方向
(一)传统法人理论的缺憾:高校法人制度统一的瓶颈
在传统的公私两分框架中,公共领域专指国家领域,国家领域之外均被认为是私人领域的范围。长期以来,国家举办的公办高校和私人举办的民办高校被认为是分属两个领域、肩负不同职责的两类组织。尽管它们都在面向社会提供高等教育服务,但却因举办者和资金来源不同被硬生生地区隔开来。这种尴尬局面真实地反映出“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在公私两分框架下,大学作为一类组织,并没有合适的坐标”[8]9。而今,社会结构由传统的公私两分演变为三足鼎立,在国家和私人领域之外,第三部门组织悄然兴起,这就为将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分别从国家领域和私人领域中超脱出来提供了绝佳的契机。今天,将公办和民办高校定位于非政府、非营利和自治的第三部门组织已凝聚了广泛共识,这种全新的组织定位,为高校法人制度的统一奠定了重要基础。
那么,两类高校应统一定位于何种法人呢?从现成的法人分类看,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坚持公法人和私法人二元划分,且一般认为前者属于国家领域,后者属于私人领域。近来,我国有学者认为这种划分已不能适应第三部门崛起的需要,故提出了第三部门法人的概念。[10]在本文看来,首先需要排除的是“第三部门法人”这个选项。高校属于第三部门组织,并不意味着它能成为第三部门法人。这是因为,“那些既非政府也非市场的第三部门活跃其间的所谓界于公私域之间的‘第三域’,还有在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过程中产生的所谓‘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的‘社会法’,并不是超越了公法和私法区分的新领域,而是混合了公法和私法的领域,或者说,是公法和私法共同起作用的交叉地带”[11]。尽管公法与私法的界限日趋模糊,但这种二元区分仍旧存在,提出第三部门法人类型为时尚早。高校法人属性的讨论,难以超越经典的公法人/私法人二分框架。其次,可以确定,作为从事公共事务的组织,高校无论由谁举办,都与私法人制度不相契合。一方面,它们均面向社会提供高等教育服务,公共性取向鲜明;另一方面,学生无论就读于哪类高校,其受教育权是同质的,这种受教育权不能等同于私法上的权利,相应地,两类高校教育权也都具有公权力的性质,其与学生的教育法律关系不能等同于民事关系。最后,摆在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面前的,只剩下公法人一个选项。从生产公共产品、提供公共服务的角度说,两类高校与公法人制度是契合的,但传统的公法人理论也存在明显缺憾。传统上认为,公法人是基于国家意志、由国家创设、承担间接国家行政任务的主体。一方面,由于该理论主张公法人组织形成权由国家保留,使民办高校无法纳入公法人行列;另一方面,由于它过分强调国家意志,公法人化也并不尽契合高校的独立自治精神。因此,若将两类高校均归入公法人,就必须突破和调整传统公法人理论,着手理论创新乃当务之急。
(二)多中心治理、公共行政范式转变与公法人理论的革新
实际上,高校之所以面临法人定位难题,主要是缘于新兴的第三部门组织在传统的公法人与私法人中难以妥当归类。传统法人理论将“公”的范围限定于国家领域,把国家之外的领域统统视作“私”的范围,从而导致一些第三部门组织即便从事公共事务,也不被公法人理论所接纳。要破解其法人定位困惑,一条可取的路径是适应社会变革趋势,革新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公法人理论,建立以公务为中心的公法人制度。
传统公法人制度的核心特征,可概括为“国家中心主义”。从生成逻辑看,最初的公法人就是国家本身,尔后由国家陆续衍生出其他公法人。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代,国家扮演“守夜人”角色,其公共职能仅涉及国防、外交和维护社会治安等有限方面,国家行政的方式也主要限于权力行政。作为当时唯一的公共行政主体,国家是最原始形态的公法人。由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无法克服市场失灵,扩大政府公共职能、加强市场干预迫在眉睫。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作为市场失灵的治疗方案,干预主义大行其道,国家职责疆域得到空前扩张,国家行政权被高度强化,过去的许多私人事务,均被纳入政府的公共议程。此时,“政府不再是一个‘守夜’的‘局外人’,而是以‘救世主’的身份进入到资源配置的流程中,并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使人们‘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事情都在行政权的作用范围之中,这昭示着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的到来”[12]。与国家行政范围扩大相伴随的,是国家行政方式的转变。政府不仅需要继续从事过去的秩序行政,而且还要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即从事给付行政。然而,繁多的公共事务很难由政府全部包揽,也并不都适合政府亲力亲为。“在‘有限小政府’的前提下,发挥行政作用,满足多元化的社会需要,成为现代行政面临的多重目标。……这一矛盾最终的解决途径是行政分散化,即将公共行政的职能分散于多个主体,培养、扶持国家之外的其他公共服务机构。”[13]55由此,大批公法人被政府创设出来。从组织职能看,这些公法人旨在实现国家意志,担当国家行政任务。它是基于某种特定公共目的而设置的组织,是国家对公共事务进行组织和整合的法技术手段,是国家政策的产物。其特征包括:(1)目的由国家授予并以法律明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任意变更;(2)设立系基于国家意志;(3)不具有私法人所具有的自我解散的自由,若无存在必要,其解散需符合设立时的准据法规定;(4)服从国家的特别监督;(5)依法享有公权力并负担义务。[13]66可见,传统上公法人乃是政府之左膀右臂,是受控于国家旨意、行使间接国家行政职权的工具,其本质仍属于国家领域(第一部门),而非真正独立于国家的社会组织。
而今,国家中心取向的公法人制度正面临多中心治理的挑战。长期以来,公共事务治理遵循单中心模式,国家是唯一的治理主体。在此情况下,公共事务即为国家事务,公共行政即为国家行政,公共领域与国家领域彼此重合。这种“公”与“国”混淆不分的观念深深地嵌入了公法人理论,形塑了公法人制度。然而同市场失灵一样,国家包揽公共事务也无法回避政府失灵。20世纪70年代以降,随着福利国家的解体,国家行政的范围日渐退却,其卸载的部分公共职责被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所担当,多中心治理格局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形成。“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它对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权威提出挑战,它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惟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14]多中心治理打破了国家对公共事务的垄断,在未经国家授权或委托的情况下,一些没有国家渊源的第三部门组织也开始主动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国家与社会走向了合作伙伴关系,什么是公、什么是私面临重新定义,我们不能再以是否属于国家领域来划分公私界限。这一重大变化将促使公法人理论和制度走向革新。
一是参与公共事务的社会组织取得公法人地位的法理基础日益坚实。如今,公共事务早已超出了国家事务的范围;公共领域也不再是国家领域的代名词,除国家领域外,那些自发参与公共事务的第三部门组织也理应属于公共领域;行政的基本观念,则从国家行政转变为包括国家行政和社会行政在内的公共行政,非营利组织、地方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只要有利于公共目标的实现,都应该通过法定渠道进入公共事务管理领域。[15]这些从事公共事务的第三部门组织成为新的社会行政主体。从组织职能看,它们也像政府一样生产公共产品、提供公共服务。从行政方式看,它们“尽管不直接具备国家行政权力,但与第一部门组织相仿,也同时存在类秩序行政(权能行政)与服务行政(给付行政)之分,前者包含了运用权能对社会及自身成员的约束管理,后者代表了对社会公众或组织成员的服务给付”[16]。从权力来源看,它们的公共行政权来自成员让渡和自治章程。总之,“非政府主体的权利可能是‘软性的’,权威也可能是不正式的,但一旦承担公共任务,本质却是类似的。”[17]“行政主体是公法人概念的实质内核”[13]51,社会行政主体的出现意味着公法人理论和制度亟须革新。在公共领域超出国家领域、公共行政超越国家行政、社会行政主体大量涌现的今天,继续墨守公法人制度的“国家中心主义”未免落后于时代。我们有必要扬弃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公法人理论,建立以公务为中心的新型公法人制度。无论社会组织是否有国家渊源,只要从事公共行政,其公法人地位就应得到承认。
二是公法人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将进一步彰显。传统上认为,公法人乃基于国家意志、目的创设,系由国家授予、从事间接国家行政、接受国家特别监督的组织。“一个社会团体若被授予公法人地位,其组织、人事、程序、会计、运作等将被纳入国家行政体制内,这意味着该社会团体被提升、整合到国家行政组织中。”[13]108可见,公法人虽名为法人,但它仍被认为是国家的延伸,并被作为国家控制和吸纳社会组织的手段。这种与国家暧昧不清的关系定位产生于社会结构的公私两分(国家-私人两分)时代,彼时公法人仍寄身于国家领域。而今时过境迁,上述局面已大为改观:公私两分的社会结构已演变为“国家-第三部门-私人”的三分社会结构;而在国家创设的公法人之外,因自发从事公务而取得公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也大量涌现。这些转变都为重构公法人与国家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国家虽然可以创设公法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法人必然要镶嵌于国家体制之内。国家设立的公法人应同社会自发从事公务的公法人一样,转变为真正独立自治的社会组织,归入非政府的第三部门。我们应根据公法人属于第三部门这个新的定位来重构它与国家的关系:一方面,公法人从事公共事务、生产公共产品、行使公共权力,须接受公法规制;另一方面,公法人不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而是高度独立于政府并依据章程充分自治的组织。
(三)公法人理论革新视野下高校法人制度统一的建构方向
公法人理论的革新,能够有力地破解高校法人制度统一的难题。一方面,民办高校同公办高校一样,均应定位于公法人。当公法人制度从“以国家为中心”转向“以公务为中心”时,是否由国家创设、是否秉持国家意志、是否从事国家行政之类均不再是成为公法人的必要条件。只要一个社会组织立足于公共使命,致力于提供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行使的是公共权力,就理应被纳入公法人的行列。民办高校虽不是国家利用财政资金举办,但其从事的仍为公共高等教育活动,依据组织章程行使公共教育权力,在这一点上它与公办高校别无二致。作为社会行政主体,将民办高校定位于公法人既符合理论逻辑,也顺应实践变革趋势。另一方面,公法人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高校屈从国家意志、有损独立自主。在传统理论视野中,公法人无非是一种具有法人地位的政府分支机构,国家的规制作用被过分强调。“高等学校公法人独立处理的教育事务从根本上来说是国家公务,自主行使的权力也是国家根据行使公务需要而授予的国家权力,其所具有的自主性实质上是一种国家意志主导下的自主。”[10]而新的公法人理论认为,高校虽具有公法人地位,但其从事的公务并不能等同于国家公务;高校的自主办学亦应理解为基于章程的自治权利,而非国家基于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专业性考虑而对高校采取的便宜之策。总之,在新的公法人理论框架下,从事公共高等教育事业的高校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都具有公法人地位;同时,这种公法人地位并不意味着高校要被纳入国家体制,顺从国家旨意。
当然,将两类高校均定位于公法人只是初步的结论,我们还需进一步讨论其具体的公法人类型。德国将公法人分为公法社团、公法财团和公营造物,这是大陆法系影响力最大的一种分类方式。相较之下,公法社团突出组织成员的作用,公法财团强调财产的目的性,公营造物则以利用人的权利和利益为中心。那么,其中哪一类更适合高校呢?从组织特性出发,现代高校是公共机构、教育机构与学术机构的复合体,除彰显公共性之外,高校运转还应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和高深知识规律,体现在高校治理层面,就是要张扬学者的学术自由权利,并强化制度化的学术权力。无论对我国的公办高校还是民办高校而言,未来都要使它们从过度科层化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回归学术本位;与此同时,还要增强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开放性和适应性。就此而论,上述三种公法人类型均非合适选项:仅将高校定位于公法社团易使之沦为高度封闭的组织,不能充分满足效率功能;仅将其定位于公法财团,则可能会将高校从以人为主的“学者共和国”转变为少数财产管理者经营的资产;而将高校定位于公营造物虽可改变其封闭状况,但又难以充分实现其自治诉求。[18]总之,将高校生搬硬套地定位于上述三种类型之一,都只能解决部分问题,还可能会带来新的困惑。
实际上,任何制度都应根植于实践需求。正如公共领域的界限、公法规制的范围和公法人的概念紧跟社会变革而产生变动一样,公法人的类型也不应永久拘泥于某种固定程式。公法人的“类型化并不是绝对的,它更多地服务于现实的行政需要,是法律技术与现实需要的政策性的结合,因此,对公法人的组织类型不能作封闭性的界定”[13]194。即便是在大陆法系其他国家,也不都遵循德国法学界对公法人类型的三元划分。很多国家都结合本土实际进行了探索。如法国就将公法人分为国家、地方团体与公务法人三类,其中公务法人又包括行政公务法人、地域公务法人、科学文化和职业公务法人、工商业公务法人。[3]63总之,我们虽有必要接受公法人与私法人二分的经典框架,但在划分公法人具体类型问题上,却不必照单全收其他国家的现成做法。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知道,日本的法人制度长期受德国影响,但在实践中却并未照抄德国的法人分类。2003年出台的《国立大学法人法》开创性地提出了“国立大学法人”的概念。从法律规定看,国立大学法人带有公法人性质,但该法并不直接把国立大学规定为公法人,而是在其下位规定为一种特别的法人类型,从而避免公法人的一般规则束缚大学改革。[19]45尽管日本的做法是针对国立大学的,但它给我们的启迪是,与其将高校套进某种现成的公法人类型,使之去接受和遵循某类公法人现成的运行规则,还不如针对高校的组织特性和公共使命,为其量身定做专属于它自己的公法人形态。我国未来的高校法人制度改革,有必要在公法人的大框架内,基于高校自身特点和发展需要,专门创设“高等学校法人”类型。这一公法人类型须兼顾公法社团的民主治理、公法财团的灵活筹资和公营造物注重利用人权益的三种价值取向,平衡高校作为教育和学术机构的自治诉求和作为公共机构的公法规制,从而真正切合高校实际。无论公办高校还是民办高校,均应定位于公法人中的高等学校法人,由此构建起“双层嵌套”的法人制度。其中,公法人这个大的定位用以实现高校的公共性;而高等学校法人这个进一步的定位,则可为高校教育性、学术性和独立自治提供制度保障。
三、高校法人制度统一的实践路径
第一,重构法人分类体系,建立公法人制度,这是改革的前提。我国法人制度肇始于1987年《民法通则》的实施。囿于特定的观念和背景,这一法人制度的鲜明特征就是将法人仅界定为民事主体,即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其根源一方面在于,我国民法学界的主流学说长期以来坚持法人概念的私法性,否认法人概念的公法意义,认为法人概念只有作为民法的概念才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20]另一方面则源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即建立法人制度主要是为了方便企事业单位等组织参与市场活动。如今,这种极具本土特色的法人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状况。将法人局限于民事主体资格,固然为一些组织参与市场经济开启了方便之门,但也导致了包括高校在内的一些行使公共职能的组织法律地位模糊不清甚至错位。未来我国法人制度的改革,首先应参照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遍做法,将法人分为公法人和私法人;其次,创造性地规定凡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从事公共行政活动、独立承担责任的社会组织,不论其是否有国家渊源,均纳入公法人范围。在这一基本分类框架下,可通过特别法对公法人和私法人的具体类型进行细分。
第二,在《高等教育法》中明确高校法人属性。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在高校法人制度方面沿袭了《民法通则》的精神。它之所以赋予高校法人资格,主要目的在于确立高校的民事主体地位、方便其参与民事活动,这一立法意图从该法进一步规定高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就不难看出。换言之,当时承认高校的法人地位并非出于实现高校自主与自治,使之独立行使公权力、承担公义务的需要。因此,未来应在建立公法人制度基础上,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均属于公法人,且系公法人中的高等学校法人。这一步改革有两条可供考虑的路径:一是专门制定新的《高等学校法》,创设高等学校法人类型并明确两类高校的法人属性;二是修改现行《高等教育法》,增加界定高校法人性质的条款。比较来看,虽然前一种方式显得改革力度更大,但在《高等教育法》已对高校组织活动作专章规定的情况下,另行制定《高等学校法》不免叠床架屋,立法难度也更大。因此,后一条路径相对可取。
第三,依据高校法人属性,完善相关制度安排。(1)在政校关系上确立院校自治原则。自治不同于办学自主权:首先,它是原发性的权利,自主则是政府授予的派生性权利;其次,自治是不受外部干涉的较宽泛的权利,政府只有监督权而不能任意施加行政规制,自主则意味着政府在较大范围内对大学行使直接管理权和监督权;最后,自治强调大学能够建立自己的管理体制,自主则使大学在管理体制上难有突破。[19]60今后《高等教育法》应从规定高校办学自主权转向明确赋予其自治权;从明确列举办学自主权的方式转向负面清单管理,即在该法中详细列举政府管理权力,法无禁止皆可为。(2)在内部治理上突出学术本位和民主参与。建立举办者、教师、学生、管理人员和校外人士等共同参与的民主化治理结构,并建立评议会等学术决策机构来专门行使学术权力。(3)在法律规制上,国家对两类高校的监督要以合法性监督为主,绩效监督则主要依靠第三方机制。另外,高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复合了给付行政与秩序行政。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法律关系不是民事关系,而是行政法律关系,相关争议适用行政救济程序。涉及学术问题的争议应遵循节制原则,充分尊重学术上的结论。
致谢
作者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注释
①随着修改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于2017年9月实施,我国民办
高校将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类。本文涉及民办高校法人制度的讨论,仅适用于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营利性民办高校的法人属性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方面,从教育的法律性质看,营利性民办高校从事的也是《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学校教育活动,与学生形成的是教育法律关系,这种教育法律关系不同于民事服务合同关系,在此意义上讲,营利性民办高校应具有公法地位、接受公法规制;但另一方面,营利性民办学校以营利为目的提供的有偿教育服务,在性质上更接近私人产品,且在实践中这类高校须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企业,这又使之具有私法人的特点。总之,营利性民办高校既具有某种公法人的性质,又具有一定的私法人特征,其法人属性应在公私法融合的视角下加以理解。
[1]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J].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4):139-143.
[2]马怀德.公务法人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00(4):40-47.
[3]申素平.高等学校的公法人地位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汉斯·J.沃尔夫,等.行政法(第一卷)[M].高家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53.
[5]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M].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570.
[6]陈长河.我市民办学校率先实行分类管理[N].温州日报,2012-05-08(9). [7]吴开华,安杨.民办学校法律地位[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1.
[8]王建华.第三部门视野中的现代大学制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9]陈涛.大学公私界限日益模糊:全球现象与动态特征[J].复旦教育论坛,2015(4):9-15.
[10]罗爽.论建立第三部门视野下的高等学校法人制度[J].教育学报, 2014(6):40-50.
[11]金自宁.“公法私法化”诸观念反思——以公共行政改革运动为背景[J].浙江学刊,2007(5):143-149.
[12]石佑启.论行政法与公共行政关系的演进[J].中国法学,2003(3): 49-58.
[13]李昕.作为组织手段的公法人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14]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
[15]张永伟.行政观念更新与行政法范式的转变[J].法律科学,2001(2):35-40.
[16]方洁.第三部门组织的“公务”诠释——行政法体系的认识角度[J].浙江学刊,2007(4):133-139.
[17]王瑞雪.治理语境下的多元行政法[J].行政法学研究,2014(4): 131-138.
[18]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10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239-242.
[19]湛中乐,主编.通过章程的大学治理[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20]屈茂辉,张彪.法人概念的私法性申辩[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5):95-105.
Analysis of Establishing a Unified Corporation System for Public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
LUWei
(Institute of Education,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China)
Different corporation systems exist for our public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 and they are facing different reform orientations.As the dual systems couldn't deal with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ilemma, establishing a unified corporation system hasbecome amust.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aradigm hasprovided a theoreticalsupport for this proposition.The popularity ofmulti-centered governance haspushed the monopolistic state administration towards a corporative public administration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and the scope of public law hasbeen extended to the third sector organizations in public affairs.In addition to the stateand its institutions,the civil organizations engaged in public affairs should also be included in the public corporation system.Therefore,both public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 should be positioned as public corporation,and to adapt to its organizational features,a specialized university corporation should be create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public corporation system.On the basisof the public corporation system,the reform is expected to clearly define the legal status ofuniversitiesby law and ameliorate the relevant institutionalarrangements accordingly.
Public University;Private University;Corporation System of University;Public Corporation
2016-12-22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单位体制变革视野中的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研究”(2016M592085)
卢威,1985年生,男,江苏沛县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