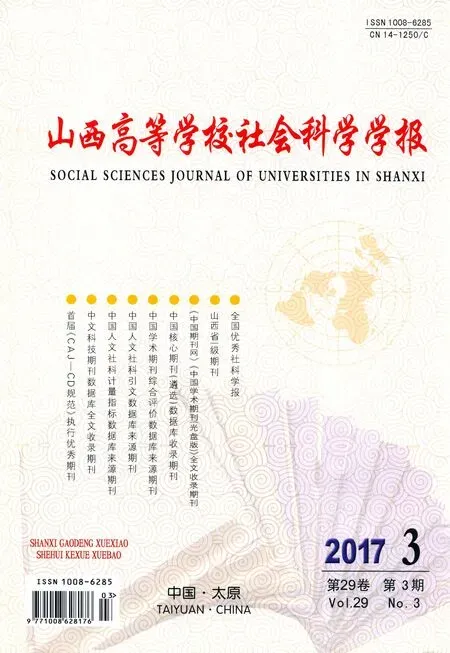朱熹《论语集注》“四论管仲”注文初探
薛勇民,范 嵘
(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朱熹《论语集注》“四论管仲”注文初探
薛勇民,范 嵘
(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朱熹《论语集注》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论语》注本。注解文本体现了朱熹对孔子仁、礼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中“四论管仲”是《论语》中孔子对人物的评价内容里所占篇幅最大的。通过研读、分析朱熹《论语集注》中关于孔子对管仲的四次评价的注文,有助于理解朱熹独特的哲学思想以及了解朱熹注解经典文本的注释方法。
朱熹;《论语集注》;“四论管仲”;仁;礼
《论语》中记载了大量的孔子臧否人物的内容,其中以孔子对自己弟子的品评和训诫为主,也有部分对同时代人物以及古人的议论。孔子在对并非是自己门下弟子的人物评价中,侧重于直接展现自己的理论主张,一方面以立场鲜明的评价表明自己的态度,另一方面以此为发端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有限的篇幅当中,孔子对其他人物的评价惜字如金,唯独对管仲例外。《论语》全篇可见孔子对管仲有四次直接评价。在这四次评价之中,既有赞扬,也有贬斥,且每一次评价,都颇具深意。朱熹《论语集注》作为《论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注本,是他“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1]穷其一生之力的心血之作,既对《论语》的经典文本有所继承,也有取众家之长以及对自己所学的阐发。朱熹《论语集注》的“四论管仲”的注文,体现了以程颐的注释为尊、增损改易古注、注重义理而不偏废训诂的特点。
一、“管仲之器小哉”与礼的多重涵义
《论语》中第一段对孔子评价管仲的记载位于《八佾》篇。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这一段是孔子以一系列管仲的非礼行为做例证,对管仲“不知礼”作出批评。整段以孔子评价管仲“器小”为开端,朱熹对本段的注文也由此开始:
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2]67。
在孔子对管仲作出“器小”的评价之后,发问人继续追问,孔子都一一予以正面回应,继而又以反问的形式,作出了管仲事实上“不俭”“不知礼”的评价。在“器小”“俭”以及“知礼”之间,从整个对话的语境中看,似乎存在着一种联系,《论语》原文并未直言这种联系,朱熹的注文中以此解释:
或人盖疑器小之为俭……或人又疑不俭为知礼[2]67。
经过注文的解释,整段对话的逻辑链条逐渐浮现并被梳理清晰:孔子做出了管仲“器小”的评价,发问人则误解管仲的“器小”实际上是“俭”,孔子继而以管仲娶了三位女性这一事实为证否认了发问人的此种误解,认定管仲“不俭”。而后则又有人认为管仲的这种“不俭”是“知礼”的表现,孔子又以管仲的种种僭越为证,认定管仲“不知礼”。朱熹于本段最后的注文则如下:
愚谓孔子讥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俭,故斥其奢以明其非俭。或又疑其知礼,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礼。盖虽不复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于此亦可见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礼,其器之小可知。盖器大,则自知礼而无此失矣。”此言当深味也。苏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于国,则其本深,其及者远,是谓大器。扬雄所谓‘大器犹规矩准绳’,先自治而后治人者是也。管仲三归反坫,桓公内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浅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复宗齐。”杨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盖非王佐之才,虽能合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称也。道学不明,而王霸之略混为一途。故闻管仲之器小,则疑其为俭,以不俭告之,则又疑其知礼。盖世方以诡遇为功,而不知为之范,则不悟其小宜矣。”[2]67-68
这一段注文则点明了孔子做出这一番评价的真实意图所在。正如注文最初所说,管仲“器小”不在于他的种种外在的行为,而在于管仲辅佐齐桓公的内在方式,是行霸道而非王道。而王霸二道混为一谈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管仲本人的学识、见闻以及修养。然而管仲种种“不俭”的明证为何还有人视作“知礼”,以及孔子为何却以管仲的种种僭越行径认定管仲“不知礼”,朱熹注文中表现出的问答双方对于“礼”的理解的偏差,揭示出了“礼”这一概念具备的多重涵义。
朱熹认为管仲之所以“器小”,是因为他助桓公行霸道而非王道。而“王道”作为一种统治秩序以及统治策略的统一,在朱熹这里形成了“礼”的第一个涵义,即以仁义的策略及秩序统治天下,即“天礼”。这是一种“跨文本解释”的方法。“王道”这一概念被广泛提出以及解释,并不是在《论语》之中,而是在《孟子》之中。朱熹以《孟子》来解《论语》,以行“王道”即“知礼”为解释,把礼纳入到了仁的范畴之内。管仲僭越,不守为臣之道,可谓违礼。朱熹引苏洵所注则进一步说明管仲僭越的内在原因。作为君的齐桓公本已极尽奢靡,而管仲为臣也不遑多让,“君淫亦淫,君奢亦奢”。管仲僭越的行径,早已违背了“臣臣”的原则,而这则来自于齐桓公先已违背了“君君”的原则。这君臣二人各自所违背的原则,就是《论语》中孔子所要表达的“礼”的涵义之二,即不同身份的人要恪守的行为规范,即“人礼”。这些规范准则的来源即朱熹所注“大学圣贤之道”,亦即“理”。管仲不知大学圣贤之道,自然也不会“知礼”。与以上两个涵义相比,朱熹注文中所体现的“礼”的第三个涵义则要显得境界小得多,即在社会生活中由于日常生活习惯而形成的成文或不成文的仪节规定,即“物礼”。由此则不难理解为何有的人会认为管仲的奢华生活是“知礼”,因为这种“礼”正是以种种看似讲究排场的形式来表现的。孔子予以否定的回答,可见孔子认为这种外在于人的“礼”的表现,是不足为管仲“知礼”的依据的,反而彰显了管仲的粗鄙。
从朱熹的注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将《论语》原文中表现得并不十分明晰的孔子关于“礼”的内涵进行精准的划分,明确了“礼”三种不同意义上不同范畴内的涵义,并结合孔子最初对管仲“器小”的评价,初步给出了他对于仁礼关系的认识。在注文中,朱熹尤为注重对“天礼”的阐发,若以他自己的话来说,即“其旨深矣”。作为百姓生活日常行为规范的仪节之礼,是会随着时代的演进而逐渐发生变化的。这种内容和形式上都变动不居的礼,不是儒家所观照的基本价值所在。而作为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场合要遵循的行为规范的礼,也同样由于其并不恒久,而没有成为朱熹关注的重点。朱熹在注文中所要表达的核心内容,在于从根本上点明管仲何以“不知礼”。一方面,管仲的行为显然与儒家重内省,重自律,由己及人以小见大的心性论背道而驰。另一方面,管仲辅佐齐桓公的治国之道,也并非儒家所主张和称许的王道治国。而王道与霸道究竟区别何在,朱熹注文中“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复宗齐”一句,虽未明言,却确实给出了答案。所谓霸道,即以国家实力以及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治国策略,其国家机器的运转,并不以人为主导,而是以具体的国家硬实力,即军事力量、物产资源、经济资本等为主导。在国际关系上则基于国家实力的优势,而对他国在事实上形成或威胁或制衡或胁迫的关系。此种国家策略之下,人并不作为行政主体而存在,相反却异化成为了以资本和武力为代表的国家硬实力的奴隶,受其宰制,丧失主体性。由于国际关系只是受这些硬实力要素主导,人在其中的作用只是工具及手段,因而才会有“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复宗齐”的结果。而王道,即以道义为核心的理想主义治国策略,正与其相反,人作为行政主体,其主体性和价值得到高扬,又以修齐治平的逻辑来对人的道德品质以及行为规范作出约束,最终则会形成一个仁君行仁政的治国模式。这种同时受“天礼”和“人礼”制约之下的君王,其无论在统治上还是个人生活上,都是不很舒服愉悦的,都与其作为动物性的人的本性相违背。吊诡的是,受到此种礼制约的君主,才不会丧失主体性以及人的尊严与高贵,始终可以作为权力的主人,处于自主自由的可进行主动选择的状态之下。而看似不受约束,可以任意违礼的“自由”的君臣,却丧失了主体性,受权力和资本的奴役而失去了自由,只能被动地被所谓各种“看不见的手”推动,蹒跚前行,却自以为得到了人世间至高享受以及绝对自由。自董仲舒以来,由“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逐渐代替了儒家自孔子以来就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关系。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以单向的义务关系替代双向的义务关系的转变,更代表了儒家政治学说的风向转变。朱熹在本段注文当中所展现出的对“礼”的界定,正是以“礼”为名,对此种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盛行的名为王道、实为霸道的背离了孔孟原意的政治伦理思想的批判。
二、“如其仁”与仁的界定
《论语》中其余三段孔子对管仲的评价都集中在《宪问》篇。这三段对话中孔子都对管仲做出了极高的正面评价,其中尤以第十六、十七两段为重。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这两段对话都是孔子面对弟子对于管仲不以死殉主而转事二主的提问予以的回答,其中都直接涉及了对管仲是否是“仁”的评价。而孔子的回答则始终结合管仲之功,最终做出了“如其仁”的评价。这是一种看上去似是而非的回答,令人费解,朱熹的注文在此也分为了对子路、子贡提问的注释与对孔子回答的注释。
如其仁,言谁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许之。盖管仲虽未得为仁人,而其利泽及人,则有仁之功矣[3]153。
在原文中孔子的回答事实上有些取巧,没有直面肯定管仲是仁,也没有断定管仲是不仁,而是在肯定了管仲的功绩是一种大仁的功绩的同时,也没有对召忽的死进行批判。朱熹的注文明确表现出了这两点,且替孔子说出了管仲算不得仁人的这一评判。朱熹审慎地并未对原文“匹夫匹妇”一句有所发明,避免了走入管仲之仁是大仁、召忽之仁是小仁的这种将仁分出层次和差等的误区。古注之中对此多有注释,有将“匹夫匹妇”训作“一夫一妇”即凡庶之人的[4]572-581,则召忽就成为了吝惜一己之名节,而弃天下于不顾的独行之士。这样,也避免了以事功来界定仁[5],从而使仁免于功利化。《管子》之中已有详细记述,以“志”代替“仁”,认为管仲志在利齐国、利社稷、济天下,召忽志在君臣之义,不在天下,因而孔子用仁来称许管仲,且认为管仲的功绩要比召忽的死节价值更大。继而得出如有管仲之功,则可以不死,若无管仲之功,且背离主君侍奉仇敌,贪生失义,则也远不如召忽。此类解释都与《论语》中孔子的原意不相吻合,朱熹在注解的时候有意留白,确保了与原意的切合。
朱熹在注文中相对于原文更加清晰的表述,在于“而其利泽及人,则有仁之功矣”一句。如果说原文此处的“如其仁”尚且给人一种模糊的感觉,让人不甚清楚孔子到底是说管仲其人还是在说管仲其功,那么朱熹注文则直接点明了此处的评价所指的对象。自荀子提出大儒、小儒的说法之后,儒家重视公共生活领域远不如重视个人品德修养以及私人生活的情况有了很大改观,儒家赞许事功,主张入世的特质也得到了高扬。朱熹此处的注文巧妙地对仁之功做出了界定,即至少有实惠和利益泽及广大民众的功绩,属于仁之功一列,还从侧面界定了仁。所谓仁之功,事实上就是孟子主张的仁政,而又与其有所不同。管仲此处之功,仅达到了仁政中满足人民群众生活富足、物质需求能被保障的重民生的最基本要求,朱熹注文中何以不直称其为仁政,而只称其为仁之功,正是由于管仲之政,是助齐桓公行霸道而非王道,而行王道治天下才是孟子仁政观点中的核心部分,才是仁政得以成为仁政的性质表述。朱熹的注文在此则与前文中注管仲“器小”一节相呼应,以思想内容的一致性而论,朱熹注仁之功而不注仁政的注文毫无疑问是优秀的。由于朱熹注文的精准,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从注文的表述中清晰地认识到,仁本身与仁之功是不同的。
对于孔子表述的评价,历来多有争议。受人非议千百年的曹操在建安十五年所写的《求贤令》,正是以此为论据的:“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6]当然《求贤令》中所谓“盗嫂受金”一节似有些偏颇,但曹操以管仲齐桓一事为据,无疑也是他对孔子这一论述的诘难。这一问题显得非常棘手,朱熹在注文中也并没有像之前对“礼”的分析那样,给出一个情感上令人满意的、逻辑上又周延的解释。这主要是受制于后人评价前人时所必然带有的后见之明,朱熹在注文中两次避免走入曲解儒家本旨的误区,已属不易。
三、“管仲非仁者与”与仁礼关系
朱熹对子路、子贡的提问所注要远远详于对孔子回答所注,这种详略有序的篇幅设置,也表明了注文所要表达的侧重点。
子贡意不死犹可,相之则已甚矣……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纠,弟也。仲私于所事,辅之以争国,非义也。桓公杀之虽过,而纠之死实当。仲始与之同谋,遂与之同死,可也;知辅之争为不义,将自免以图后功亦可也。故圣人不责其死而称其功。若使桓弟而纠兄,管仲所辅者正,桓夺其国而杀之,则管仲之与桓,不可同世之雠也。若计其后功而与其事桓,圣人之言,无乃害义之甚,启万世反复不忠之乱乎?如唐之王圭魏征,不死建成之难,而从太宗,可谓害于义矣。后虽有功,何足赎哉?”愚谓管仲有功而无罪,故圣人独称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后有功,则不以相掩可也[3]153-154。
朱熹在此处的注文引用了程颐的解释,这段解释非常特殊,并未直接评价管仲的行为,而是先对齐桓公与公子纠的身份进行了一番审视,继而又联系到初唐玄武门之变一事。朱熹对程颐花费如此规模笔墨的这段解释非常认可,引为注文,然而这段注文的前半部分存在显而易见的问题。注文明确说道:“桓公,兄也。子纠,弟也。”而事实上根据《史记》的记载,公子纠是齐襄公的弟弟,小白(即之后的齐桓公)是公子纠的弟弟,朱熹注文的兄弟关系恰与史实相反。除了《史记》之外,《庄子》《荀子》《韩非子》《越绝书》《说苑》也都是记载桓弟纠兄。《公羊传》记载桓公是篡位,《谷梁传》记载桓公不辞让,也都是认为公子纠是齐桓公的兄长[4]572-581。只有西汉文帝舅薄昭给淮南王刘长的书信中吊诡地写道:“齐桓杀其弟以反国”,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汉文帝是淮南王刘长的异母兄,刘长联络匈奴密谋叛乱,最后事发败露受辱身死,由于淮南王是弟,汉文帝是兄,他不敢斥言杀兄,所以有意颠倒了公子纠和齐桓公的兄弟地位。而朱熹注文中为管仲不随公子纠而死,转而侍奉齐桓公的行为开脱的依据就在于他颠倒了公子纠和齐桓公的兄弟地位。注文后半所举的初唐玄武门之变的例子,则因为唐太宗是弟,李建成是兄,所以王圭魏征不随建成而死已先有害于大义,其后虽然于贞观之治有功,也不足以赎前番之过,功过不能相抵,更不能以功掩盖过错。
到了朱熹的时代,中国受益于深厚的史官政治的传统,已经积累了相当规模的历史资料,其中涉及兄弟阋墙,争权夺利的著名事例已为数不少,这都为朱熹注释此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素材。之所以这种情况成为历史记载以及后世儒家关注的重点,是因为此类事件不但涉及了权力更迭,更触及了儒家的几类基本伦理关系,既涉及人与天的关系,也涉及具有血缘亲情关系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在管仲一事与注文所提及的玄武门之变一事中,还涉及了君臣之义的关系,诸多身份集于一人之身,导致了多种伦理关系交汇于一事之中的结果,这给孔子当时的评价以及后世朱熹的注释都提出了挑战。
朱熹的注文在此处已经与《论语》的原意相去甚远,子路与子贡只是想以管仲这种类似于贰臣的行径来向孔子质疑,始终并未涉及齐桓公与公子纠的身份问题,而注文则通篇在强调身份的重要性,朱熹已对《论语》的原意有自己的阐发。《论语》原文中的两段,其中只涉及一对身份之间的关系,即君臣关系,而由于齐桓公和公子纠之间的特殊关系,朱熹在注文中则又加上了第二对身份关系,即兄弟关系。这二者同为“礼”的范畴,在朱熹的注文中却都作为评价“仁”的先决条件。只有作为君的齐桓公处于正当的兄弟关系之下,符合正当的兄弟关系的秩序,作为臣的管仲的行为才有可能因为事实上的功绩而被评价为仁。朱熹还认为,如果齐桓公是弟而公子纠是兄,管仲所辅佐的公子纠是正当的继位人,齐桓公却杀了他,现在反而侍奉齐桓公,圣人还认同管仲是仁,这岂不是在给不忠不义之人助威?由于《论语》的文本无法改变,为了使孔子的理论能够自圆其说,也为了《论语》能和程颐的注释相融合,朱熹注文中有意将齐桓公与公子纠二人的兄弟关系颠倒。这样来看,朱熹的注文至少体现了他的两点认识:其一是即使礼包含于仁之中,礼的价值仍然优先于仁;其二则是在同为礼的范畴之内的两对关系,无血缘的君臣关系要次于有血缘的兄弟关系。
对于仁礼关系的把握,一定要基于仁、礼各自内涵的清晰划分才有可能做到。仁礼关系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论题,从古至今已有不少论述。造成这种现象的一大原因就是对仁与礼各自的内涵划分不清,导致了不同层次的概念相互杂糅。朱熹关于此段的注文中所表现的礼先于仁的关系,其礼的内涵为秩序,即前文所述之“天礼”。只有符合伦常秩序,即符合礼的行为,才可进一步对其作出是否为仁的评价。朱熹不惜颠倒兄弟地位,改易史实,也要表达出这一观点,可见其对伦理纲常秩序的重视。注文中表现的无血缘的君臣关系要次于有血缘的兄弟关系一节,则是对儒家基本精神的传承。儒家的血缘之亲、差等之爱,是一切伦理纲常的基本。之所以夫妻之伦为人之大伦,而非父子更非君臣,是由于夫妻乃是血缘之始,有了夫妻才有而后的父子、兄弟,君臣、长幼,朋友等则更在其后。这同样也是儒家修齐治平逻辑的体现。正如注文中程颐所抨击王圭魏征所言,连基本的基于血缘的兄弟关系都不置于前,无视建成和世民的兄弟身份,而侈谈其转事二主的君臣之义,更妄言其有功于贞观之治,其实“何足赎哉”!
四、结语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理论体系中诸如仁、礼的一系列重要范畴,发展到朱熹的时代,其内涵已经发生很大改变。朱熹在注释经典文本的时候不拘泥于古人已有的经注,将自己的思想融入注释中,以注释来阐明自己的思想。宋学自北宋中期以来形成的疑经与以己解经的学术潮流,也为如何评价学术成果的价值提出了新的疑问。严格合乎经典原文本意是否与创造建构新的理论体系之间不可调和,二者之间具有同等的价值抑或有高下之分,朱熹《论语集注》已经给予了我们明确的答案。固守经典本意的解释未必一定具有学术价值,看似离经叛道与原文大相径庭的解释也未必都没有价值。与原意是否吻合以及对理论是否有创新,这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评价体系,二者之间不必然具有联系。我们不必要在发现了新的有价值的理论之后,一定要寻求和前人理论的契合,同时也不能把所有求新求异的理论都认定其有价值。由此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朱熹注文的特点:其一,注重对原文本意的理解和继承,在关乎儒家本旨的紧要关窍处,绝不轻易自行阐发,更不必说疑经改经;其二,对于经典中语焉不详的部分,以注重分析的方法,从内容上进行划分,并加以阐释;其三,笔力通贯,逻辑严整,力求自身注文思想内容的一致性,避免抵牾。朱熹坚守经文本意的特点已与宋学前期的潮流大有不同,其注重分析的特点也给人以拨云见月之感。
对朱熹追求注文思想一致性这一点,后世给予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因朱熹所注《孟子》中有不少内容为一致性而一致性,把很多本来不相契合的内容与思想强扭在一起,有牵强附会之嫌。这固然是其不足,然亦瑕不掩瑜。
[1]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第十九·论语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6:437.
[2] 朱熹.论语集注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朱熹.论语集注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刘宝楠.论语正义卷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90.
[5] 黎翔凤.管子校注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2004:332.
[6] 曹操.曹操集·文集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2013:40-41.
A Study of ZHU Xi′s Notes about "Four Evaluations of GUAN Zhong" inCollectedAnnotationsonAnalectsofConfucius
XUE Yongmin,FAN Rong
(SchoolofPhilosophyandSociology,ShanxiUniversity,Taiyuan030006,China)
CollectedAnnotationsonAnalectsofConfuciusby ZHU Xi is the most popular and influential commentary of Analects of Confucius, because it embodie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thoughts on benevolence and etiquette (also Ren and Li) by ZHU Xi. "Four evaluations of GUAN Zhong" in the work contains the largest space about Confucius′s commentary on people in Analects of Confucius, so analyzing this commentary will help u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bout his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have a preliminary impression on his habit on commenting classical text.
ZHU Xi;CollectedAnnotationsonAnalectsofConfucius;"four evaluations of GUAN Zhong"; benevolence(or Ren);etiquette (or Li)
2016-12-28
薛勇民(1964-),男,山西万荣人,山西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副校长。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伦理学。 范 嵘(1990-),男,山西太原人,山西大学硕士生。研究方向:应用伦理学。
10.16396/j.cnki.sxgxskxb.2017.03.022
I206
A
1008-6285(2017)03-009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