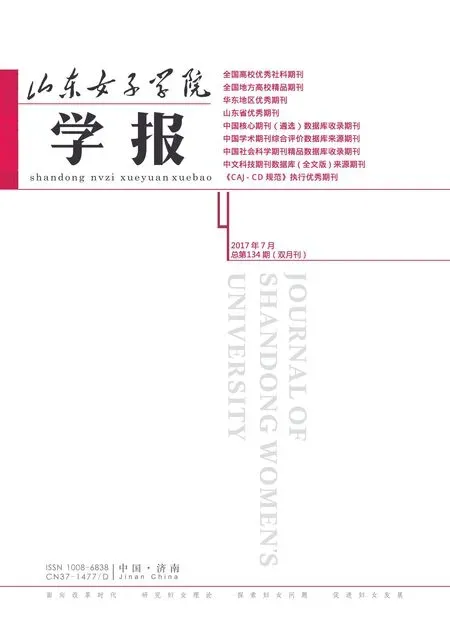以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视角解读拉祜族婚姻习惯法
杨云燕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云南临沧 677000)
·女性文化研究·
以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视角解读拉祜族婚姻习惯法
杨云燕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云南临沧 677000)
婚姻习惯法是拉祜族传统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拉祜族婚姻习惯法在规范拉祜族社会成员的行为和责任的过程中,蕴含着独特的女性关怀内涵。以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为理论支撑,对拉祜族婚姻习惯法进行解读有助于加深对拉祜族婚姻习惯法的认知,也是扩展和延伸拉祜族婚姻习惯法研究的一种有益尝试。
拉祜族;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婚姻习惯法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是16~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和情感主义理论的现代发展。女性主义伦理学并非是以女性为研究领域的伦理学分支学科,而是一种以女性主义为方法论、以性别为分析范畴进行的伦理探究[1](P17-18)。拉祜族婚姻习惯法在规范拉祜族社会成员行为和责任的过程中,蕴含着独特的女性关怀内涵。
拉祜族婚姻习惯法在继承传统恋爱自由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些维护拉祜族女性权益、尊重女性的规约。如规定青年男女谈情时不得轻佻,小伙子不得随便对姑娘动手动脚,不然就被斥为“搓别人”,要被抄家或罚款,或请全寨人吃饭,当众“洗面”[2](P209-210)。拉祜族恋爱活动俗称“串姑娘”,是以尊重女性为前提的,一旦小伙子有侮辱姑娘的不文明行为,轻则被耻笑,重则被罚款或需请寨里的人吃饭以向众人赔罪,这种约定俗成的处罚与拉祜族禁止婚前性行为的习惯法是一脉相承的。拉祜族婚姻习惯法明确规定了“串姑娘”过程中小伙子的责任,以预防玩弄女性、婚前性行为等伤害女性的事件发生。对既成事实的当事者,澜沧县糯福乡新寨的村规规定:男女青年恋爱自由,但相处一段时间后双方感情不合而告吹的,罚双方各6元,交磨巴(负责祭祀的人员)买香蜡到寨神那里谢罪。男人玩弄了女人,又不愿意娶女方为妻,女方讲出后罚男方25元,已使女方怀孕的罚男方120~150元。南段村公所南段老寨寨规:恋爱自由,婚姻自己做主张,但在农忙季节不能“串姑娘”;不调戏妇女[3]。在女性主动的地方,一寨的姐妹群到另一寨去找兄弟群,约定在某一地方歌舞,就在野外歇宿,发生性行为后结草或以棍棒为记,私为婚约。此后,男方找一媒人带一包茶到女方家中,对女方父母说明已在某处“得子”,然后择吉日过门。如男方不来说亲,女方父母便通过头人指控男方,按习俗罚半开10元或10元以上[4]。如上所述,拉祜族婚姻习惯法对青年恋爱男女的行为进行了严格的规约,在坚持男女平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突出对男方的处罚给女方最大限度的补偿。但对男性处罚的前提是必须由女性说出来才能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女性自主权,即重视女性作为受害者当事人的自愿选择权。拉祜族恋爱习惯法契合了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即在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看来,女性注重对道德问题作情境分析,强调道德话语来自具体情境也指向具体情境,强调正确的伦理学结论存在于与道德事件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及情境关系中,强调依据情感、态度、情境作为道德推理基础的重要性,强调对“抽象”的批判,以及相信女性思维(而且道德思维大体上应该)更受具体场合的影响,较少地受抽象规则的制约,也就是说更“具体”[5]。女性倾向于注意与道德事件中人的关系如何,事件发生情境的特殊性如何,并且常常不是求助于规则或原则而是注意以同情和关怀的感情去决定应该做什么[6]。
拉祜族多数村寨中男女即使定亲后,在未正式给厄莎磕头、举行传统的婚礼前,也不得发生性行为或同居。违者男女均会受到处罚。科弄拉祜族男女未婚生子女进行罚款,男罚半开百元,女罚半开60元,所生子女归母亲①。拉祜族多数村寨的婚姻习惯法对婚前性行为或有私生子的男女双方均实行处罚,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中的公正关怀。拉祜族传统观念认为,婚前生子是不洁行为,会得罪寨神,寨神怪罪,会给寨子带来灾难,因此,要进行惩罚。同时,拉祜族实行婚后从妻居,丈夫住在岳父母家。婚前生子,不管今后是否结婚,双方是否均有过错,孩子都要归女方,男女双方均要受处罚。但考虑到女方抚养孩子的生活实际,对男方的处罚更重,以对女方养育孩子给予一定的补偿。从对男女双方处罚差异的角度看,又客观上体现了寻求关怀和责任的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的特点。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倾向把自我看成一种相互关系中的存在,把道德视为对他人的责任,奉行一种重视关系和责任的关怀伦理。
拉祜族选择结婚对象注重人品及劳动能力,不计较物质和相貌等外在条件。这种摒弃物欲和功利的婚姻恋爱观,有利于双方婚后家庭的稳固和婚姻的和谐。拉祜族崇尚从妻居,老人多由幼女赡养,幼女一般继承两份财产。即使男方因特殊情况无法从妻居需女儿出嫁时,父母也要赠送女儿一把锄头、一把镰刀和一个口袋,有土地和牛的家庭还会分给土地和牛。这些约定俗成的做法在客观上有利于维护女性的主体权益,保障女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尽管拉祜族实行男女平等,但入赘女婿在拉祜族家庭中还是处于相对被动的处境,这客观上减少了婚姻家庭生活中对女方的家暴行为,有利于维护女性的权益和促进家庭的和谐稳定。
拉祜族社会男女平等、夫妻恩爱、相互扶持及没有传宗接代思想等构成了拉祜族社会理想的道德关系,为公正伦理和关怀伦理的存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拉祜族社会婚姻习惯法崇尚从妻居,女性在家中有较高的地位,很多拉祜族地区家庭是由女性掌管财务大权,妇女也积极参与各项农业生产活动,尽管反映了母系家庭的残余,但却真切地强调了女性的权利、平等和独立,体现了公正伦理的诉求。同时,拉祜族社会中夫妻双方在生产生活中分担活计和家务,即使一方有病或残疾,另一方也要不离不弃,悉心照顾。正是夫妻间的相互依赖和关心彰显着拉祜族传统的人文关怀。正如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家吉利根所说,理想的道德关系便是平等和依恋关系,这是所有人追求的目标。每个人都希望自我同他人被同等地、公平地对待,同时每个人也都希望被关怀、被反应,没有人应被忽视和受到伤害[7](P110-113)。传统拉祜族母系制大家庭的家长早期由母系担任,拉祜语称“叶协玛”,意为“女家长、女主人”,负责安排生产、生活及社会活动,传统拉祜族家庭财产由妇女继承,但拉祜族社会中女性在强调关怀的过程中也在践行着公正,如遇家中有大的开支,女性家长会召集家人在一起商量,听取大家的意见后再做定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新中国成立后拉祜族作为直过民族,受汉族等社会文化的影响,逐渐进入父权制社会,管理村寨事务的“卡些”(类似村长)多为男性,习惯法在集中村民意见的基础上由他们最后制定。从已有的婚姻习惯法的相关条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便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村规民约制定过程,也仍旧体现着对女性的关怀,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认为,公正和关怀与性别无关,即两性都可以发展关怀和公正的道德思维。女性在道德发展上以关怀为主要倾向,男性以公正为主要倾向,但两者不是绝对的,女性也可以作出公正思考,男性也可以作出关怀考虑[7](P126-127)。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的上述主张,在拉祜族婚姻习惯法中得到恰当的诠释。
妇女对于年幼孩子的养育和关怀是人类社会普遍接受的、跨文化的事实。在拉祜族传统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中,基于生产力低下及较为艰苦的生存条件,家庭中夫妻协作很普遍。拉祜族社会孕育孩子的重担也主要由妇女承担,但作为性别对立的丈夫必须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如妻子有身孕后,丈夫一般不得进山打猎,认为孕妇的丈夫若击中了猎物则会给孕妇腹中的胎儿带来伤害,导致胎儿畸形等。还有的地方禁止孕妇的丈夫进山狩猎,认为杀生会导致孕妇流产[2](P169-170)。丈夫严格遵守这些禁忌,体现出对妻子和孩子的关心和担当。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加之医疗条件落后,拉祜族妇女生孩子基本不可能去医院。一些妇女生孩子由丈夫充当接生婆,在月子里丈夫自己照顾产妇和新生儿。拉祜族没有重男轻女思想,也无传宗接代观念。跟一些地方重视男孩不同,拉祜族妇女生了女孩,家人不会嫌弃甚至比生男孩更高兴,都会尽心伺候。产妇坐月子期间,丈夫还会抽空找来当地的数十种草药,熬出滚烫的药汤给产妇蒸澡,以除湿排毒。不能生育的妇女不受歧视,领养的子女也不受歧视。
女性生理、性格等因素决定了其在家庭中要养育子女、关心配偶、照顾老人和操持家务。吉利根认为:“妇女不仅在人们关系的背景下定义自己,而且也根据关怀的能力判断自己。妇女在男性生命周期的位置一直是养育者、关怀者和帮助者,是这些她轮流依靠的关系网的编织者。”[8](P16-17)男女在生育上的两性差异“来自把社会地位和权力因素,与生殖生物学结合起来所形成的男女体验以及两性之间关系的社会背景。”[8](P1-2)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妇女的工作(如怀孕和抚育等)也是真正的工作,妇女要获得解放,就应当消除男女社会性别分工的等级制度。拉祜族婚姻习惯法中丈夫除了直接为妻子接生、精心照顾产妇和婴儿外,还会背孩子、挑柴、放牛羊及喂猪喂鸡等,妻子也在生产生活中处处与丈夫夫唱妇随,所谓的性别分工在拉祜族社会中没有明确的界限。
拉祜族人偶有离婚,离婚自由,且不受歧视。习惯法对离婚双方有相关的规约,对过错方进行惩罚,对不愿意离婚或弱势一方实行补偿,体现了男女平等且关怀女性的倾向。澜沧糯福等地的拉祜族女方可以借各种理由把男子赶走,如女方主动,女方出银3两,半两送给卡些,半两送给媒人,2两送给丈夫;如男方主动,则出银6两,半两送给卡些,半两送给媒人,5两送给女方。男女共同所有的财产实行平分,至于子女,女儿归母,儿子归父,但多归母[9]。帕良等寨夫妻双方同意离婚,男女各出半开5元,一半归寨子头人分,一半归寨子“集体”所有,如系一方提出,则出半开十五元,一半分给村寨头人,一半分给不愿意离婚的一方。分子女的原则是女儿归母,儿子归父,或由子女自行选择。夫妻共同劳动所积累的财产实行平分①。大完楼男女离婚极易,如夫妻同意,各出半开3元,一半归村寨,一半归村寨头人分。如女方主动则出银六两六钱,银归男方,反之,如男方主动则出银六两六钱,银归女方。科弄寨拉祜族男女离婚在结隆家举行仪式,男出一口猪,女方负责煮饭,招待全寨吃。财产是男归男,女归女,夫妻共同积累的平分①。金平县翁当乡拉祜族村规规定:“离婚:如系女方主动提出,则赔偿男方5元半开,一头小猪,一瓶酒;如是男方主动提出,则偿付女方30元半开,一头肥猪,若干酒;夫妻双方,如一方破坏婚约,则出解除婚约费5元半开。” 毋庸置疑,拉祜族离婚习惯法中对女性照顾和同情的规约契合了关怀伦理学中关怀弱势群体的价值向度。拉祜族经历了由狩猎采集到农耕定居的变迁,女性客观上在生产方面处于劣势地位,离婚习惯法中对离婚男女双方的处罚差异体现了习惯法对女性的关照和包容,蕴含着女性关怀的内涵,实现了从自然关怀到伦理关怀的蜕变。正如学者认为的那样,如果不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许多无过错离婚当事人尤其是女性当事人因配偶重婚、与他人同居等侵害婚姻关系的行为而受到严重身心伤害,却无法得到法律救济[10]。纵观拉祜族各地的村规,都重视维护家庭的稳固,对非正常男女关系的处罚均很严厉。1949年前,若发生不正当的性行为并被当场抓获者,被乱棒打死。后来虽废除了人身处罚,仍奉行罚款300元,或请寨人吃一餐饭,然后将全寨打扫一遍,要向寨人赔礼的习俗。同时,男方被罚款20.5元,女方被罚款19元,男方的罚款交给女方的丈夫,女方的罚款交给男方的妻子,从经济上给双方受害者补偿。另外,有婚外情的男方的舅舅代表外甥去向女方的父母、丈夫认错,请求原谅[3](P130-131)。竹塘乡老缅大寨的村规:乱搞男女关系者罚4斗米,4元钱,200市斤酒,杀一头猪供全寨人吃,但不得吊打辱骂;若头人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除给予罚款处罚外还会被立即撤职。糯福乡糯福大寨的寨规:与有夫之妇发生关系或同姓乱伦者,男的罚半开15元,女的罚10元,还要罚一头猪供全寨人杀吃。勐海县巴卡囡拉祜族村规:不准娶妾重婚,否则要罚挑带刺的扁担游寨子。澜沧县糯福乡新寨的村规:不同辈分的人通奸,事情败露后,女方有权到男方家抄家,任意拉牛拖猪,还要把当事者撵出寨子[3](P127-128)。从上述村规可以看出,拉祜族对乱搞男女关系的处罚态度很坚决,即使是头人也不能被赦免。有的地方对男女的处罚平等,有的地方对女方的处罚较轻,甚至女方即使也有过错,但男方要付出更惨重的代价,体现了对女性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拉祜族对因非正当男女关系而受到无辜伤害的当事人给予经济补偿和精神安慰,起到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作用,也可以用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的视角进行解读。正如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家诺丁斯认为的那样,关怀伦理学是关系到人们的需要、关系和反应的理论。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不是增强人们的道德推理能力和增加人们的道德知识,而是培养人们同情与体验他人痛苦的能力[11]。吉利根认为,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可以根据平等和依恋来体现,不平等和分离构成了道德关切的基础。既然每个人都可能受到压迫和被抛弃的伤害,两种道德视角,即公正和关怀就会再现于人类的体验中,不允许不公正地对待他人,不允许忽视各种不同的道德关切。
我们知道,女性主义伦理学家在理论构建层面试图通过摆脱那种由男性所确立的秩序与等级模式而重塑新的伦理自我,重写一种能够兼顾女性声音、凸显女性关怀的伦理话语[12]。在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模式的拉祜族社会中,尽管传统的从妻居习俗给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一定地位和权利,但不可否认,女性的生理条件还是决定了其仍处于弱势地位。拉祜族传统婚姻习惯法在对不正当性关系问题上的两性差异处罚彰显了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哲学智慧。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认为,关怀等道德来自日常生活产生的经验与情感。在诺丁斯的关怀伦理学中,关怀先由内圈再到外圈,内圈包括了父母、兄弟姐妹、子女、朋友等等,外圈则是与内圈相关联的人,关怀体现的是一种“由亲到疏”的内在结构方式[1](P37-38)。拉祜族以孝敬老人、善待小孩、互帮互助、家庭和睦为美德,并经常教导年轻人。在结婚仪式上有老人教导新婚夫妇的环节,在日常家庭生活中母亲也会经常这样教导孩子。拉祜族社会对老人、孕妇、产妇、小孩、无生育能力的妇女、养子女的包容及对无法正常实施从妻居的变通等都是根据实际情境的需要而实施的相应的关怀行为,这符合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理论体系中的关怀伦理的情境原则。斯特洛认为,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能够反映或表达该社会群体(或亚群体)的动机和信念。如果这些制度、法律以及社会习俗和惯例反映了那些负责制定和维护它们的人具有移情作用的关怀动机,那么它们就是正义的。依据这个逻辑,拉祜族婚姻家庭习惯法的制定者或维护该习惯法运行的人们正是具备了对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的移情关怀,才使该习惯法得以在拉祜族社会中顺利实施,并成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家庭生活正常运行的重要法规。
只有经由法律和制度上的确认和保障,女性平等权利才具备在现实中实现的制度性前提。拉祜族女性平等权利和人文关怀经由传统习惯法得以确认和保障,最终内化为现实的社会关系。传统习惯法根植于拉祜族社会,规范着每个人的行为,具有超强的影响力和威慑力。拉祜族女性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享有哪些权利及遇有其权利受到侵犯时如何给予救济和补偿,婚姻习惯法在民间层面给予保障,并成为实施静态和动态操作的依据和指南,其婚姻习惯法没有忽视女性的性别维度。因此,应制定出对她们具有补偿性的优惠政策,而不是抹煞她们的性别特征,掩盖两性的自然差异,简单地做到对男女的“一视同仁”[13]。经过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拉祜族婚姻习惯法所遵从的道德标准也在不断地变化。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也需与时俱进,要意识到关怀也受到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影响,关怀必须遵从一定的道德原则与政治规范等才能发挥力量,关怀、移情等也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体现[1](P39-40)。
因此,每一个人都在拉祜族家庭伦理所构建的关怀关系中形成了自我。正是因为拉祜族婚姻习惯法不仅体现了人与人之间情感主义的关怀,还包括了规范原则中融入的人文关怀,它才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继续显示着巨大的影响力和威慑力。
注释:
① 参见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民族组著《拉祜族佤族崩龙族傣族社会与家庭形态调查》(内部资料),1975年。
[1] 许静. 对关怀与性别二者关系的探讨——基于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的研究视角[D].合肥: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2] 杨春.中国拉祜族[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
[3] 王晓珠.拉祜族:澜沧糯福乡南段老寨[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128-129.
[4]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拉祜族社会历史调查(一)[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9-10.
[5] [美]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M].温海明,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61-162.
[6] 邱仁宗.生命伦理学——女性主义视角[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90-91.
[7] 肖巍.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8] Carol Gilligan.InaDifferentVoice[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9]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拉祜族社会历史调查(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2.
[10] 马忆南,贾雪.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实证分析——离婚损害赔偿的影响因素和审判思路[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6,(1).11-12.
[11] 胡军良.道德的“性别”之思——基于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的视角[J].云南社会科学,2011,(6):21-25.
[12] [英]帕森斯.性别伦理学[M].史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8-49.
[13] 潘萍.马克思主义公平观与性别公平[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3,(3):14-15.
(责任编辑 赵莉萍)
Interpreting Lahu Marriage Customary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Care Ethics
YANG Yun-yan
(Dian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Lincang 677000, China)
Marriage customary law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Lahu’s traditional customary laws. The marriage customary law contains rich and unique female care conno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egulating the behaviors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members of the Lahu family members. Interpreting the Lahu marriage customary law by using feminist care ethics as theoretical support helps to deepen the cognition of the Lahu marriage customary law. It is also an instructive attempt to expand and extend the research on the Lahu marriage customary law.
the Lahu ethnic group; feminist care ethics; marriage customary law
2017-04-18
杨云燕(1976— ),女,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
DF551
A
1008-6838(2017)04-007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