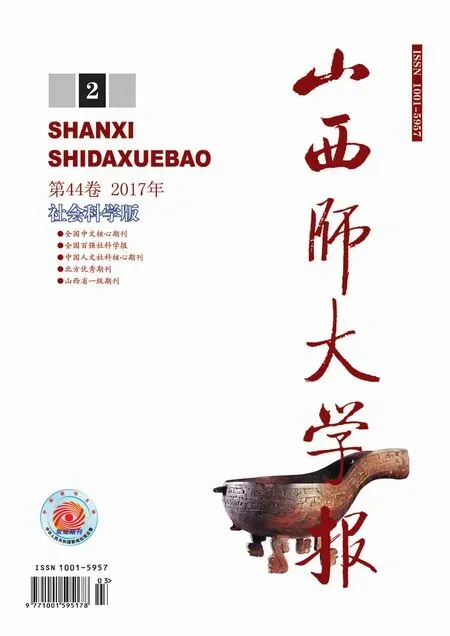中国传统词学的四大批评观念
胡建次,叶国云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南昌 330031)
我国传统词学包含着一些独特的批评观念,如尊体观念、政教观念、雅俗观念、本色观念、正变观念、南北宋之宗观念、词派之宗观念等。它们各自包含不同维面的批评内涵,亦各有发展衍化的历史过程,内在影响甚至决定着传统词学的建构及其路径走向,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与重要的批评价值。本文对我国传统词学中的四大批评观念予以论说。
一、尊体观念
尊体问题是传统词学的基本观念之一。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文学发展与自然存在角度,二是从创作之难角度,三是从诗词同源或同旨角度,四是从有补于诗歌表现角度予以论说。其中,第三个方面立足于以诗歌表现为本位而切入,第一、二、四方面立足于以词作表现为本位而展开。其共同目的在于抬升词的价值,提高其社会地位,以便人们对词这一文体有更为肯定性的认识推扬。
从文学发展与自然存在角度对词体予以推尊,大致始于元前期,主要呈现于清代,流衍于民国之时。其主要体现在刘将孙、毛先舒、陆进、谢章铤、郑文焯、谢之勃、唐圭璋等人的论说中。元前期,刘将孙在《胡以实诗词序》中对视诗词为“小技”的观念予以批评,“尝笑谈文者,鄙诗为文章小技,以词为巷陌之风流,概不知本末至此”。他持论诗词虽属音乐文学,但“发乎情性,浅深疏密,各自极其中之所欲言”。[1]236刘将孙论说诗词以性情表现为本,以性情蕴含作为艺术生发之基点,由此而主张自然地布局与结构全篇。它们与文章在体制上是无所谓优劣之分的。晚清谢章铤也从词的合理性存在角度予以推扬。其《赌棋山庄词话》持异词为“诗余”之说,认为诗词是共时出现的,“然自有诗即有长短句,特全体未备耳。后人不究其源,辄复易视,……此诚风雅之蟊贼,声律之狐鬼也”。[2]3346谢章铤认为根本上不存在所谓“衍生”之说,只不过词的发展一时没有诗之体制顺畅罢了。他批评一些人盲目轻视词体,致使词之地位不尊、发展路径不畅。民国时期,谢之勃在《论词话》中针对轻视词体之论予以驳诘。他认为,文学创作无所谓“大道”“小道”之分,其关键在入妙;“今人动言词为诗余,而不知词与诗性质同而不相属;词与诗同为吾国文学上之放异像的光芒者,又乌可以小道及附属品而屈之”。[3]898谢之勃论说诗词二体是相通而不趋同的,各有广阔的艺术空间,都在我国文学历史上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从创作之难角度展开的尊体之论大致始于宋元之交,主要呈现于清代,流衍于民国之时。沈义父、仇远、李渔、李起元、唐允甲、王隼、胡兆凤、陆奎勋、厉鹗、胡师鸿、许宝善、保培基、叶以倌、赵怀玉、邹文炳、朱绶、蒋湘南、张应昌、叶湘管、蒋如洵、谢章铤、陈庆溥、俞樾、袁翼、王柏心、汪兆镛等一大批文论家,从具体创作层面将对词体的推尊不断拓展、充实与深化、张扬开来。南宋末,沈义父较早提出词的创作难于诗,其《乐府指迷》云:“然后知词之作难于诗。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2]277沈义父认为,相对于诗而言,词的创作体现出更大的难度,它追求音律的协和、下字的雅致、用语的含蓄及意致表现的微婉合度,其在综合性艺术构造上是难于诗的。清中期,厉鹗亦把填词视为高难度之事。其《楮叶词序》认为词的创作更体现出相当的不易:一在声调择选与音律运用上更为讲究,“调叶宫商,有小令慢曲之不同”;二在意旨表现上更注重吟咏之道,“旨远辞文,一唱三叹,非别具骚姿雅骨,诚不能窥姜、史诸公堂奥也”。[4]738厉鹗认为,只有才情充蕴、格调拔俗之人,才可入乎词之至境。民国之时,汪兆镛在《题黛香馆词钞》中论说词体似难登大雅之堂,然其“义旨深微,音律幽眇,非可率尔操觚”,不是可随意为之的。他批评近人填词,“非香奁脂盝,失之于靡;即粗头乱服,失之于尨”[4]1438,都有悖于词体的雅正之求,汪兆镛之论将从创作角度对词的推尊再次张扬开来。
从诗词同源或同旨角度展开的尊体之论,主要呈现于清代,流衍于民国时期。谢良琦、查涵、王士禛、鲁超升、汤叙、陈聂恒、陈沆、王昶、李调元、王文治、汪端光、江沅、王鸿年、张维屏、汤成烈、汪宗沂、谭献、吴敏树、沈祥龙、张体刚、文廷式、郑文焯、李岳瑞、康有为、蒋兆兰等一大批词论家,从诗词作为文学体制的产生及其所发挥社会现实功用的角度,对其不断予以推尊。清初,谢良琦在《醉白堂诗余自序》中论说词作为文学形式之一,虽然体制短小,结构偏狭,自有历史渊源与内在规制,“而况诗余亡而后歌曲作,歌曲作而后诗亡,则诗余不亡,诗犹未亡也。诗余之所系,又岂渺少也哉”。[5]122谢良琦持论词上承于诗,下启于曲,是沟通诗曲之体的桥梁。在形式上,它独成一体,发展了传统诗歌创作的特点,确是需要不断学习才可有所成就的。晚清,沈祥龙在《论词随笔》中对贬抑词体之论大力驳斥,“以词为小技,此非深知词者”,批评其持论者并非深识词作之道。他对南宋词甚为推重,认为无论在豪放抑或婉约风格的创制中,其艺术路径都与风骚旨趣相合,“皆伤时感事,上与风骚同旨,可薄为小技乎”[2]4059,沈祥龙论说词体甚富于社会内涵,是不可以“末技”而轻视的。民国之时,蒋兆兰在《词说》中从“三不朽”的角度,论断“词虽小道,然极其至,何尝不是立言”。[2]4638他论断,词之艺术表现长于讽喻,寓含诗体所具兴、观、群、怨等功能,其面貌呈现温厚和平,确是甚有价值的文学形式,理应得到普遍的推重。
从有补于诗歌表现角度展开的尊体之论,也主要呈现于清代与民国之时。任绳隗、朱彝尊、屈大均、先著、王岱、吴秋、沈德潜、焦循、张云璈、刘珊、陈文述、董思诚、张曜孙、廖平、杨福臻、王闿运、程适、仇埰、夏敬观等一批词论家,主要从创作者情感表现及其细腻性呈现方面,对词体所具审美优势予以论说,并由此对词体予以推尊。清初,任绳隗较早从有补于诗歌表现角度开启对词的推尊之道。其《学文堂诗余序》云:“夫诗之为骚,骚之为乐府,乐府之为长短歌,为五七言古,为律,为绝,而至于为诗余,此正补古人之所未备也,而不得谓词劣于诗也。”[5]98任绳隗从诗体渊源演变角度论说词之由来,他强调词有补于诗体,我们不得对其持“卑体”观念。晚清,陈文述从有补于情感表现角度体现出对词之体制的推扬。其《紫鸾笙谱序》云:“词虽小道,抒写怀抱,宣导湮郁,言情最婉,感人最深,非他诗文可及也。”[5]938陈文述肯定词虽体制短小,但其在情感表现方面甚见细腻深致,也极容易入乎人心,是其他诗文之体难以比肩的。民国之时,仇埰在《蓼辛词叙》中持论词之“蓄性情,摅怀抱”,在内涵表现方面,“与诗同其用,而殊其境”,它表现人的心性情怀,抒写人之襟抱志意,更见深致委婉,在一些内容的表现上对诗体有补充拓展之效。正由此,仇埰充分肯定“故词亦本乎天,极乎人,而周乎万物也”[5]2126,亦体现出对词的充分推尊之意。
二、雅俗观念
雅俗问题是传统词学的基本观念之一。其出现于宋代,承衍于元明,繁盛于清代,延续于民国时期。它主要包括去俗崇雅、雅俗之辨与以俗为雅等方面内容,其中,去俗崇雅成为传统词学一以贯之的审美观念及批评准则。
北宋前期,词学批评中萌生雅俗之辨意识,最终促成去俗崇雅之论的昌盛。有宋一代,人们围绕对词的论评多方面呈现出去俗崇雅观念。这在对柳永的评说中有明显的体现,人们大多将柳词归入鄙俚之序列中,体现出对其过于俗化的不满之意。南宋末年,沈义父较早倡导去俗崇雅观念。其《乐府指迷》提出:“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2]277从下字用语角度论说词雅之性,认为词作用字要追求雅致,其不雅,则会使词体流于俗令时调之类。沈义父将用字雅致与音律协调及用字藏露一起,视为词的创作的基本要求。元明时期,张炎、陆行直、陈继儒、俞彦等人,主要从词作体制运用角度阐说去俗崇雅论题。如,张炎《词源》云:“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至唐人则有《尊前》、《花间》集。”[2]255张炎从词的创作源流论说其雅正之性。他认为,词在最初乃音乐性体制,其由先秦两汉至隋唐以来,都一直呈现出雅致庄整的面貌特征。
清代,张祖望、邹袛谟、朱彝尊、蒋景祁、张星耀、陈撰、厉鹗、李如金、吴锡麒、吴衡照、周济、程受易、朱绶、孙麟趾、黄曾、谢章铤、刘熙载、郭传璞、陈廷焯、陈星涵、沈祥龙、王国维等一大批词论家对去俗崇雅观念不断予以张扬。清初,张祖望《掞天词序》提出“词虽小道,第一要辨雅俗”的主张,强调词的创作从辨分雅俗入手,将雅俗之分视为词作能否入妙的关键。他界定其从内在影响着词的质性,而不论其情感取向与所用言辞技巧等,“如巧匠运斤,毫无痕迹,方为妙手”[2]605,张祖望推尚大化入妙、自然天成之作,其在实际上将自如通脱视为真正的雅化之作。厉鹗也将“雅”作为择选词的标识之一。其《群雅词集序》云:“词之为体,委曲啴缓,非纬之以雅,鲜有不与波俱靡而失其正者矣。”[5]419厉鹗强调词作面貌与风格呈现以雅致为尚,如此,才能保证词的创作始终在当行本色之道上运行。晚清,孙麟趾在《词径》中把“雅”与“清”“轻”等一起概括为“十六要诀”,将入乎雅致视为词之创作成功的关键之一。之后,陈廷焯立足去俗崇雅原则,对词人词作予以丰富多样的判析,并对去俗崇雅观念反复论说,将雅俗之论推向了高潮。《白雨斋词话》云:“入门之始,先辨雅俗;雅俗既分,归诸忠厚;既得忠厚,再求沉郁;沉郁之中,运以顿挫,方是词中最上乘。”[6]186陈廷焯将入乎雅致视为词作进入上乘之境的先决条件。他强调,只有在辨分雅俗的根基上,才能追求忠厚之旨与沉郁之气,其又云:“词家之病,首在一俗字,破除此病,非读樊榭词不可。”[6]188陈廷焯将俗化界定为词的首要禁忌,努力标树去俗崇雅的审美理想。在当代词人中,他甚为推尚厉鹗之作,界定其为引导后世之人脱却俗化的榜样。
民国之时,况周颐、赵尊岳、唐圭璋、陈运彰等人将词作追求雅致的原则与审美理想进一步倡扬开来。如,况周颐从词的创作路径上阐说去俗崇雅论题。其《蕙风词话》云:“词中求词,不如词外求词。词外求词之道,一曰多读书,二曰谨避俗。俗者,词之贼也。”[7]4况周颐强调创作主体视界拓宽,不要停留于词作之道的既有空间中。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要通过多读书以丰富情性修为,增扩识见;二要在创作中避弃俗化,以高致雅洁作为词的创作的普遍理想。
三、本色观念
本色当行问题是传统词学的基本观念之一。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对词作体性辨析角度,二是从词作风格角度加以展开,两方面相互联系与渗透,共构出传统词学本色之论的主体空间。
我国传统词体本色之论,明确出现在北宋陈师道的言说中。其《后山诗话》批评苏轼“以诗为词”,模糊了诗词二体的界限,好比雷大使之舞,以男儿之身而表现女子情态,无论如何都是难见本色的。陈师道之论,将“以诗为词”与诗词创作的是否当行相联,其论成为从词作体性角度所展开本色论之滥觞。
元明时期,张炎、仇远、杨慎、王世贞、刘凤、何良俊、毛晋、谭元春等人,进一步将词体本色之论凸显出来。如,张炎在《词源》中批评辛弃疾、刘过“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2]267。他认为,一味将豪旷之气融入词中,这有损于词的雅致之性,在不经意中将词变成只在形式上有别于诗的艺术之体,而并未显示出根本的区别。张炎之论表现出对词的独特审美质性的持守之态。杨慎在词作表现方面主张上溯六朝,其《词品》评断“大率六朝人诗,风华情致,若作长短句,即是词也”,批评“宋人长短句虽盛,而其下者,有曲诗、曲论之弊,终非词之本色”。[2]425杨慎大力批评宋代所出现的“以诗为词”及“以文为词”现象,认为这使词的创作脱却当行本色之道,与“风华情致”的审美表现要求相距甚远。
清代,黄宗羲、毛先舒、李渔、彭孙遹、王次公、聂先、丁澎、王士禄、吴宝崖、佟世南、钱芳标等人,对词体本色论题予以多样的阐说,将对词体本色观念的维护不断予以张扬。如,黄宗羲大力肯定文学之体各有本质特征,相互间是不能过于渗透与杂糅的。其《胡子藏院本序》批评“近世为诗者,窃词之妩媚;为词者,侵曲之轻佻。徒为作家之所俘剪耳”[8]61。黄宗羲认为,明末清初一些人作词流于曲体之直露与俗化,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柔婉绵丽的艺术质性。黄宗羲反对过于杂糅不清的文学样式,体现出对不同文体内在质性的坚定维护。
民国时期,卓掞、吴梅、顾宪融、蔡桢等人仍然持守传统之见。如,蔡桢通过对两种词体质性的论说,显现出其词体本色观念的传统性。他在《柯亭词论》中提出:“小令以轻、清、灵为当行。不做到此地步,即失其宛转抑扬之致,必至味同嚼蜡”,亦即以轻巧、清新、灵性为宗尚;而“慢词以重、大、拙为绝诣,不做到此境界,落于纤巧轻滑一路,亦不成大方家数”[2]4905。亦即在内涵上要体现较强的感染力,在面貌上要显示一定的堂庑气概,在笔力上要表现古致意味,似不经心而内寓周密精巧之安排。
传统词学本色之论的另一个方面,是从词作风格角度予以展开。这一线索主要呈现于明代,至清代而少有流衍。此与词学伸正绌变的贯有意识与观念是紧密相联的。张綖首开从风格角度论说本色之线索。其在《诗余图谱》“凡例”中论析婉约之作的主要特征为情感表现蕴藉含蓄,豪放之词的主要特征为气象宏大,内在充蕴着气格。他界定,“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主张词作表现以婉约之道为正途,而避免入于豪放之变径。徐师曾也从婉约与豪放风格呈现来论说词作。其《文体明辨序说》虽然肯定主体先天气质必然影响词作风格呈现,但从“词贵感人”的视点与原则出发,他仍持论词之表现“要当以婉约为正。否则虽极精工,终乖本色,非有识之所取也”[9]165。徐师曾从词之艺术表现阐说“本色”内涵,这在对以婉约词风为本色之论的标树上更见出说服力。清代徐缄在《水云集诗余序》中,通过对以周邦彦、柳永、苏轼、辛弃疾为代表之创作路径的论评,也体现出以婉约词风为本色的持论。“然学耆卿不得,不失为靡丽之音;学稼轩不得,其敝如村巫降神,里老骂坐,与本色相去万里。”[5]409徐缄认为,如果习效辛弃疾之词而不得其内在路径与神理,或者在艺术表现等方面过于俗化或议论化,都会使词作呈现出令人可怖的面目,是应该尽力避免的。
四、正变观念
正变之分是传统词学的基本观念之一。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风格呈现角度,二是从流派分属角度,三是从词人词作角度,四是从词史发展角度予以切入展开。它体现出批评者对词作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多样性观照认识。
从风格呈现角度所展开的正变之论,大致出现于明中期,张綖、徐师曾、茅暎、王骥德等人都有所阐说。张綖《诗余图谱》在承扬宋人以本色观念论词的基础上,划分“婉约”与“豪放”两大主体性风格。他认为,“婉约”之体的特征是“词情蕴藉”,“豪放”之体的特征为“气象恢宏”。张綖分别以苏轼与秦观为代表,在词作体制辨分中首次将“本色”之论转变为“正变”之辨,强调“婉约”为“正”,“豪放”为“变”,开启了词风正变之论的主流取向。之后,徐师曾将对词体正变的辨析置放于能否以情感人的视点之上。其《文体明辨序说》受本色观念影响,论断婉约词为正,“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他并提出,婉约词之所以为正,不仅在于含蓄蕴藉,更在于其触动人心的特征,“否则虽极精工,终乖本色,非有识之所取也”。[9]165徐师曾之论比张綖单纯从风格表现入手判分正变之路径更见入理。
清代,沈亿年、黄云、吴绮、李元、田同之、王鸣盛、瞿颉、郑燮、戈载、吴展成、戴廷祄、蒋师辙、谢章铤、廖平、沈祥龙、陈廷焯、俞樾等人,仍持以婉约之风为正途、豪放之风为变径的观念,但分析辨说更见入理。如,黄云《小红词集序》在肯定词作风格有婉约与豪放之别的同时,认为即使以豪放著称的苏轼也称扬秦观为词坛“大手”,此乃缘于其作“多婉约也”,他认同陈师道所评苏词非本色之论,认为豪放之风乃词体趋变的结果,其在本质上是不入正道的。清中期,吴展成《兰言萃腋》在词风呈现上持传统正变观念,“然毕竟以温柔为主,豪放为别派,犹之禅家,毕竟临济是正宗,曹洞是旁宗也”。[10]卷二吴展成以婉约之风为正、豪放之风为变,倡扬词的创作还是以婉约蕴藉为正途。廖平《冷吟仙馆诗余序》将婉约之风格呈现论说为词之正道,“词家相沿以来,体派大略有二。一婉约,一豪放。大抵以婉约为正,取其不失诗人温柔敦厚之旨也。”[5]1749廖平归结“以婉约为正”的原因,乃在其呈现温柔敦厚的特征,是合乎自古以来之审美准则的。俞樾在词风正变之论上也体现出传统观念。其《玉可庵词存序》论说苏轼与吴文英之词,虽极显才华情致,但他们在创作路径上却不见当行。“而词之正宗则贵清空,不贵饾饤;贵微婉,不贵豪放,《花间》、《尊前》,其矩矱固如是也。”[11]卷三俞樾强调词的创作以婉约为正,以豪放为变,将传统词风正变观念进一步传扬开来。民国之时,以婉约词风为正宗之论续有流衍。如,蒋兆兰《词说》云:“词家正轨,自以婉约为宗。”[2]4632仍然拘守以婉约之风为正道的观念,甚富于观照与反思之意味。
从流派分属角度所展开的正变之论,主要呈现于清代和民国时期。吴骐、周大枢、凌廷堪、吴锡麒、李调元、杨芳灿、许夔臣、谢章铤、蔡宗茂、谭献、陈廷焯、徐珂、王蕴章等人,从不同角度展开对词派孕育与衍生的观照。如,周大枢在《调香词自序》中认为,苏轼、辛弃疾等人将柔媚委婉之风衍化为豪放慷慨之词,这在文体质性上是“近于诗矣”,因而呈现出入乎变径的特点。吴锡麒在《董琴南楚香山馆词钞序》中承扬以正变辨分体派的观念,但他对正变的理解与一般人的观念明显有异。他把“幽微要渺之音”的正派与“慷慨激昂之气”的变派并列,提出“一陶并铸,双峡分流”,主张各显其长,相互间没有优劣高下之别。谭献之论亦体现出从创作路径上辨分词派正变归属的特点。其《复堂词话》肯定词有正变之别,认为不论什么人的创作,都有所受渊源流别的影响,也就必然呈现出“正”与“变”的路径差异。谭献将清前中期的词人之作,划分为“才人之词”“学人之词”与“词人之词”。他推尚项鸿祚、纳兰性德等人之作为“词人之词”,是趋入正体的;而相对的,王士禛、周济等人之词则具有变体的特点,故将其归入“旁流羽翼”。
从词人词作角度所展开的正变之论,大致出现于明中期,主要呈现于清代与民国之时。如,王世贞《艺苑卮言》认为:“词至辛稼轩而变,其源实自苏长公,至刘改之诸公极矣。”[2]391但总体来看,明代词学对正变之属的论说还不很常见。清代,刘体仁、王士禛、邹祗谟、储国钧、凌廷堪、郭麐、戈载、刘熙载、谢章铤、杜文澜、谭献、江顺诒、潘曾莹、冯煦、林象銮、俞樾、陈廷焯等一批词论家,将正变之论在不同节点上予以了落实,从一个维面显示出对词史演化发展的辨析。清前期,王士禛在《花草蒙拾》中针对前人王世贞对婉约与豪放代表性人物的判分予以辨析。他同意将苏轼、黄庭坚、辛弃疾等人之词视为“变体”,但持异将温庭筠、韦庄等人之词归为“变体”。王士禛具体以赋的衍展为譬,提出温、韦之词乃“正宗之始”,它们孕育与创生着两宋之词,与“变体”是截然有异的。王士禛之论,见出作为不同统系的“正”“变”之体,各有内在的渐变之迹。清中期,周济所编《词选》以“正”“变”加以界分,从一个视点标示出正变观念在词学批评中的鲜明呈现。周济所用“正”当为正声、正体之意,然“变”却不指变体、别调,而指“正声之次”,是指富于创新且取得一定成就的词作,并不在排斥之列,他将融通平正的批评观念落实到了具体选编之中。晚清,陈廷焯对词人词作予以广泛批评,将正变之辨推上前无古人的高度。其《白雨斋词话》对苏轼、姜夔等人之词都广为推崇,分别以“仙品”“神品、仙品”“逸品”“隽品”“豪品”予以称扬,各加标树。他认为,这些人之作虽风格各异,“然皆不离于正”,与传统词论所视为正宗、正体的温庭筠、韦庄等人一样,一同可入“大雅”之列。陈廷焯对词之“正”内涵的理解,寓示着不论什么人、什么体,只要较好地体现出词的创作特征与发展规律,便都可入乎词史之正位。
从词史发展角度所展开的正变之论,主要呈现于清代与民国时期。其主要体现在张惠言、刘熙载、杨希闵、江顺诒、陈廷焯、陈衍、郑文焯、陈洵、夏承焘等人的言论中。他们从不同视点展开了对词之历史承衍与变化创辟的正变之论。如,张惠言《词选序》持论“故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认为宋之后词均由“正”趋“变”。他对由元至清几百年间词道不畅甚为感慨,认为“皆可谓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者也”[12]卷首,体现出以时代判分正变的路径及今不如昔的感叹。其所编《词选》便祈望在对词人词作的各异标树之中,能起到引领词的创作复归于正道的功效。晚清,江顺诒具体从对词人词作的分析入手细致地加以论评,将从词之历史发展判分正变推到更为融通平正的台面。其《词学集成》对单纯以时代判分词作予以有力之批评。他以唐诗的衍化发展为譬,提出不可以时代差异而判分正变归属,先出之词也有变径,后出之词亦有正体,关键看其艺术表现如何。他将柳永、秦观等人之作视为词家之变,将姜夔、张炎等人之作视为“词家之正轨”,又将王沂孙、史达祖等人之作视为“各臻其极”,显现出对以词作历史判分正变归属的努力破解。江顺诒之论,标示出传统词学正变之论的一个更高层次,显示出从词史角度判分正变归属的更深层次思考,富于启示意义。
总结我国传统词学中批评观念的运用、演变、衍化与发展,可以看出,尊体之论、雅俗之论、本色之论与正变之论,是我国传统词学的四大批评观念。它们各自包含不同维面的批评内涵,亦各有发展衍化的历史过程,彼此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它们从主体上影响甚至决定着传统词学的关系建构及其批评展开,显示出重要的批评价值与现实意义。
[1] 陈良运.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C].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
[2] 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6.
[3] 张璋,等.历代词话续编[C].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4] 孙克强,杨传庆,裴喆.清人词话[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5] 冯乾.清词序跋汇编[C].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
[6] 陈廷焯著,杜未末校点.白雨斋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7] 况周颐著,王幼安校订.蕙风词话·王国维著,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8] 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9] 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0] 吴展成.兰言萃腋[M].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
[11] 俞樾.春在堂杂文三编[M].清同治十八年曾国藩署检本.
[12] 张惠言.词选[M].清道光十年宛邻书屋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