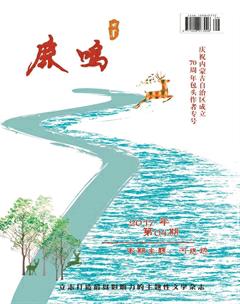坍塌
李亚强
村小学向西就是老油坊,在每年七八月份榨油的时候可以去讨要一些油渣吃;向东是老戏台,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就会有一场大戏上演;北面的牡丹山上,每到春天可以上山采野花;村小学门口的电焊铺常年四季火花飞溅,村里人常拿着破碎的铁制品来焊接。因为这些所在,学校反而成了最无趣的地方,也为了去这些地方,那时候没少被校长罚站甚至体罚。
最神秘的,还是村小学东侧、牡丹山下的纸火铺。一间低矮的小土房,门口挂着一副油腻腻的门帘,看上去年代久远。因为掉色已经看不出原来成色的小木格窗则经常禁闭着,每到放学时,窗户下的炕洞里飘着淡蓝色的烟。
村里人认为,凡是与死相关的事物,均是不吉祥的,是不被允许靠近的,例如棺材铺、纸火铺、寿衣店,甚至阴阳先生。但是那些好奇的眼光,就如三月的春风,总能找到空隙钻进那个窄小的木格窗里,尽管木格窗上的纸换了一次又一次。
冬天的时候,纸火铺的李老汉偶尔也会出来晒太阳,拿一把小凳子与村人坐着聊天。中等身材,体型微胖,头发稀疏,看上去满脸的福相,总是一副笑眯眯的眼神。打量着村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那些花花绿绿的纸火从屋子里被人提出来,跟我们身材一样大小的娃娃、闪耀着金光的金银斗、齐齐整整的四合院、展翅欲飞的白鹤。
有一年冬天,村里有老人去世订纸火,我们几个小孩跟着大人第一次走进了纸火铺。那间光线暗淡的屋子,一张土炕占了大半个屋子,坑坑洼洼的脚地上,堆放着纸扎的未成形的纸火零件,还没来得及去掉枝叶的细竹子散乱地堆在一边,竹子弯成的半成品堆在角落里。除了一张炕是空闲的,脚地上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当然,炕上也摆放着各色纸片削好的竹子。
炉子上热着水,水汽氤氲。
我们围坐在炕边。李老汉戴着老花镜,叼着一支已经熏得发黄的老烟斗,一脸的慈祥,兀自摆弄着手中的竹条,那些竹条就像他的另一只手,在空中、在我们的眼前翻飞。一盏煤油灯摆在土炕中央的方桌上,随着我们好奇的眼光忽明忽灭,也随着屋里的气流忽左忽右,黑面浆糊的味道在不大的屋子里肆意蔓延,混合着煤油的清香。这样的时刻,时光被无限拉长,那些纸火就堆在我们身边,纸人儿仿佛也要开口说话,却被这安静的气氛感染,默默站在一边,看着李老汉灵巧的双手。
一根笔直的竹子,只需在煤油灯上稍作熏烤,轻轻一弯,就能变成任意的角度,这些角度就是四合院的院墙,也能成为屋檐和台阶,还可以成为金童玉女的脸庞、手臂。纸火的骨肉成形,还要裁剪衣物、墙面,这时候的李老汉像一个熟练的裁缝,手中的纸张就是一匹匹花布,几剪刀下去,就能天衣无缝地安在纸火上。
村里人讲究,纸火烧完不能留下金属物品,否则亡人带不走那些物品,对活着的后人也不祥。那些竹子之间的结合,靠的就是炕桌上那些红红绿绿的碎纸片。我们在围观的时候也不闲着,帮着李老汉捻一些灯芯粗的纸绳,五颜六色的纸绳将各个零碎的部位结合起来,如棺材上的木楔。
村里订纸火的人交代完已经离去,小屋的光线更加暗淡了,李老汉一边做着手中的活,一边会与我们聊上几句,问是谁家的孩子,你奶奶的纸火就是我做的,或者你爷爷的纸火做得豪华。也会偶尔发几句感叹,没人学纸火了,我死了这里还不知道做啥呢,你看这房子都快塌了。年幼的我们不知道,他这些话是说给我们听,还是说给那些静默的纸火听,抑或是说给自己听。
那天晚上的梦里,我看见那些花花绿绿的纸火全部复活,在李老汉的指挥下载歌载舞,四合院也成了真的四合院,我能轻轻推开那一扇扇虚掩的院门,屋内的茶炉上热气升腾……第二天我便开始发高烧,祖母听说了我的梦境,认为我被不干净的东西沾了身,赶紧找来纸钱烧了祷告,并从此再也不让我靠近那间纸火铺。
从此纸火铺成了一种神秘的所在,似乎里面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和魂灵。
祖父曾当过村小学老师,也做过村里的阴阳先生,与李老汉交好。祖父去世时,李老汉为他做了两对童子,一座豪华四合院,两对金斗,两对银斗,在村里人的眼中,这已经是非常值得艳羡的配置。
那几年雨水充沛,漫长的雨季总不过去。村小学的教室经常漏雨,有几间教室甚至屋檐都塌了,李老汉没有招牌的纸火铺也不例外。牡丹山上的雨水顺着细小的沟沟渠渠流下来,土筑的台阶经不起雨水浸泡,也开始塌陷,屋顶上的瓦片换了一茬又一茬。李老汉的纸火越做越少,他出的纸火已经满足不了方圆几公里的村子的需求。
李老汉老了,老眼昏花,经常弓着背在村小学附近溜达,也因为经常把张三认成李四而闹笑话。但是村里人没有人笑话他,感激他为那些亡人送去的一切。我上初中的那一年冬天,李老汉去世,纸火铺在第二年春天就被拆除,变成一个小卖铺。
我不知道的是,李老汉去世的时候,是否也有那让村人艳羡的豪华配置。但我知道的是,李老汉的去世,意味着村子里再也没有一个纸火匠,在那间昏暗的屋子里孤独地扎纸火,也意味着那个时代的手工纸火的终结。
木 味
小镇西侧是一个独立而又与集市联系在一起的小市场,每三天一逢集,乡亲们背着粮食来这里粜,然后用换来的钱购买一头猪崽。小麦的味道发甜,有些陈腐的味道,那是仓里沉积的旧粮。三轮车上的猪崽吱吱啦啦哼哼个不停,车厢里的粪便混合着小麦的味道,飘荡在小镇上空。西南侧的位置,则是一台十多米长的刨床,在那个什么都靠纯手工的年代,一台如此巨大的刨床吸引了我们足够多的目光,每次跟着父母赶集,我都要在这里流连半天,合抱粗的松树,堆在一边,像待宰的羔羊,十多个工人抬上刨床,机器开动,周围的喧嚣声立即消失,只有这台刨床巨大的切割声,沉闷的、浑厚的,像隔着一层物质,但是又清晰、惊心动魄。锯条开过,木末飞溅,松木的香味也飞溅开来,那是稀有的味道,不同于漫山遍野的白杨树和柳树,有些苦,又有些清香,这味道是霸道的,可以压制一切的。
松木的味道持久而浓烈,这些被切割好的松木板,平整、宽厚度一致,各个村里的木匠都要来这里选料,这些木料,可以被打造成精美的写字桌、衣柜、板凳。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家里能有一套松木的家具,那是家境宽绰的象征。
二叔家门前堆满了这样的木头,盖着一层尼龙袋子,在阳光下曝晒,人们坐在上面聊天,谈村里唱的大戏,谈一年的收成,谈陈旧的往事,能够听到松木板开裂的声音。往往,在室外放置几个月甚至一年,这些松木有的中间拱起,有的边角开裂。难以想象那些参天的树木被伐倒然后被切割,运送到这里,制作成精美的家具,再送到镇上出售,估计木头也忘记了自己当初的模样。在一次次的切割与重组中,展现出令人胆战心惊的美。
刨床切割,推刨造型,松木里长着一个一个的节,这会成为推刨的阻力,一遍遍平推,卷曲的刨花如落叶一般落在案板下面,不一会儿就能堆积起一草篮。这些刨花是点火的好材料,休息的时候,二叔拿出亮油桶制成的茶炉熬一罐茶,点上旱烟斜眼看着案板上的那些木料,一件家具的模样已经在心中成型。
二叔抽着旱烟,眯缝着双眼,粗大的有力的双手摩挲着木头,像抚摩着柔软的皮肤。松木是好东西啊,他说白杨木容易裂缝,在潮湿或者干燥的条件中容易炸裂,影响美观及使用。松木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松木的油性可以保证对环境的适应。而且松木越是经年,越见美观。他让我从一侧拉着墨斗的线,拉定后从墨线中间一提,一条清晰的墨印出现在木头上,然后在自己的小刨床上进行分割,利刃过处,刨花纷纷扬扬,屋子里立马被那些木头的味道弥漫。那些味道是霸道的,像最后的申诉,也是柔软的,是剖开的树木的心。
在村里,树木几乎承载了人们生活的全部。
建房屋立梁柱,需要木头,家境稍好的,椽檩都是笔直的松木,推刨去皮,亮油上色,刚住进的几年,满屋都是松木的清香,晚上睡觉也是松木收缩或者扩张的声响,这样的日子是幸福的。家境较次的,则使用曲直程度不同的白杨木,白杨木性干,即便涂上亮油,也保不了色,住几年屋顶便是黑乎乎一片,而且易遭虫噬。
衣柜、床头柜、面柜,都需要木头打造。连炕头的枕木也需要用木头,形形色色的木头装点着人们质朴的生活。这让树木有了生长的机会,每户人家都要在房前屋后种上几棵白杨树或者柳树甚或梨树杏树,若干年后就可以成为家中物什的一部分。这也让每个村里都有几个像二叔一样的木匠有了营生。
二月初二村里的大戏刚唱完,二叔就开始忙活,选材料、画图形,平整板材。这时候,地里的小麦刚刚从冬天的寒冷里抽出身来,枯萎的麦苗重新返青,园子里的桃树刚刚抽出微小的花骨朵。村庄安静,人们有大把大把的光阴闲置,勤劳的人家这时候开始筹划翻新房屋,重修农具物什,添置家具用物。这时候,二叔经常要将手里的木活撂下,去其他村里做活,盖房、打家具,好烟好茶好酒招待。一张长桌可能都要做上几个月。
過年的时候,一个衣柜就能换来一个丰盛的年。小镇的供销社人来人往,窄窄的街道两边人声鼎沸,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不时烘托出祥和的节日氛围。二叔在村人羡慕的目光下,在那个小镇中央的花园边摆卖着各式各样的家具,其他村民则要么背上三五十斤麦子去粜,要么背着一两根猪腿叫卖。
后来,二叔也失业了,那些木质的家具再也卖不出去。木质家具笨重,造价高,图案单一,而经过机器打磨出来的三合板的家具,轻盈漂亮,图案多变,价格也低,这些家具逐渐代替了那些老旧的木质家具。
最后一次拿起那些落了灰尘的工具,是为祖母打寿材。在过完年的一个大雪天里,二叔和父亲搬来了堆放在门外的松木板,院子里搭起简易的工棚,叮叮咣咣动起工来。二叔一辈子不知道给别人打了多少副寿材,这次却是给自己的母亲打寿材。他嘴里叼着烟,仔细计算着尺寸,那些纷纷扬扬的木屑在地上堆起厚厚一层。“三底两盖”的配置,是村里人对寿材的最高要求,花了三天时间,二叔终于将它打造完毕,涂上鲜艳的颜料,大红的底色,两侧展翅欲飞的白鹤,含苞待放的荷花,粉里透红的仙桃,二叔勾画的每一笔,都看似自然实则艰难。成型的寿材摆在院子中央,二叔蹲在一旁抽烟,烟雾缭绕中,我看到了他眼神中的欣慰、难过和无奈。
前几年,二叔离家外出打工,忍了再忍,终于还是将那个刨床卖掉了,做工的屋子也在雨水的冲刷之后变成危房,最终轰然倒塌……
老戏台
夜戏散了,戏台下的吵闹声逐渐归于死寂。卸了妆的演员坐在连锅炕边大声喧哗,一边喝酒一边对着戏词,炉火映红了每个人的脸庞。墙壁上挂满了花花绿绿的道具戏服,像一个个站立着的人,窥视着后台的每一个人。我兀自游走,穿上龙袍,端坐在这些人身边,像戏里的人,也像戏外的人。
多少年后,在梦里出现这样一幕,我的心依然感到震颤,这种恐惧是由外而内的,像一柄长剑,直插内心。我从梦里一下被揪起,端坐在暗夜里。
那时候,庙很旧,里面供着三圣母,只有一个朱砂写就的牌位立在供桌上。没有泥塑像,这座土庙也是附近十里八乡村人的心灵寄托,求神告庙都少不得来这里烧一炷香。
那时候,土木结构的戏台也很旧,下雨的时候经常漏雨,戏台顶上的瓦片一年比一年少,村里人都在张罗着推倒老戏台再重建一座混凝土结构的戏台,但是一次次被搁浅。看戏的人少了,求神告庙的人多了,小小的土庙被翻新成了砖瓦结构的新庙,庙里的三圣母也有了具体的泥塑像,每年正月初一凌晨,村里人都要争着来这里烧一柱头香。
戏台就在土庙正对面不足20米的地方,一条原本直行的道路,到这里突然打了弯,就因为戏台的存在。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村人都要组织一场盛大的秦腔演出,名叫给神唱戏,小时候想不明白,神为什么那么爱看戏?长大了才知道,名义上是给神唱戏,实际上是给人唱戏。
其实戏之于乡亲们,只是一种载体罢了,真正懂戏看戏的人微乎极微。很多人只是为了排遣心中的空虚和农闲后的寂寞,所以大戏开场了,台下却是三三两两拉家常的。戏充当的是媒介的作用,为人们提供一个可以倾诉的场地,也正是戏,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维系着那个年代人们之间的纯朴感情。
一年农事的结束在年关,一年农事的开始是在二月初二。在没有其他娱乐方式的早年间,唱戏基本是除了社火以外唯一的娱乐形式。小时候,村里还有一支剧团,平时大家都埋身在黄土地里,是灰头土脸的张三、李四、王五,当二月初二临近的时候,这些人从黄土地抽身出来,拍拍身上的尘土,穿上华丽的戏服,成了杨宗保、成了朱春登、成了秦香莲,成了人们不认识的人。
父亲曾经也是村里的一名秦腔演员,家里堆放着厚厚的戏本。那时候除了考取公职,务农农村青年的唯一出路,也没有外流一说。一些喜欢唱戏的青年聚集在一起,组建了村剧团,最鼎盛的时候,甚至比县剧团还要辉煌,除了在本村演,还被邀请到其他村演。
后来,村里人知道新疆有煤矿、棉花,年轻人组队外流。父亲也放下了戏本,跟着村里的青年去了煤矿,日子过得比戏还苦,谁还去唱戏?村剧团散了,每年二月初二的大戏难以为继,给神唱戏成了一种应付,有时候请几个人的皮影剧团来糊弄,有时候请几个县秦剧团的演员跟原来村剧团的演员混合着唱。再后来,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手里有钱了,直接请外地的秦剧团来唱戏。
娘说,今年村里请了宁夏吴忠的秦剧团,二月初二唱夜戏的时候,戏台上的电路烧了,唱了一半的戏突然中断了,半个小时后,看戏的人已经走了一半。电路再次接通,一折戏又从头开始唱。又过不到半个小时,电路再次烧断,此时台下的观众已经所剩无几,无奈的演员又从头开始唱这折戏。都说给神唱戏呢,三圣母庙就在对面呢,唱戏中断两次,连神也管不了了。娘在电话里这样感慨。
那晚,我在梦里看见,屹立了40多年的老戏台塌了,烟雾弥漫里,我看到那些村剧团的演员,一个个身着戏袍,如皮影一般在台下张望。我知道,与纸火铺和木工一样,戏台的坍塌,其实何尝不是传统农村文化的坍塌和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