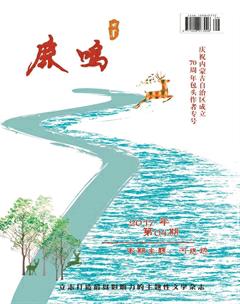师傅牛四
王存喜
牛四也算得上煤加工车间的一个名人。
他中等个,敦实、寡言,干活不惜力,一张总也洗不干净的脸上嵌着一双肉呼呼的小眼睛。眼睛微斜,很少与人对视,偶尔与你的眼光撞到一起看,转瞬便滑脱了,仿佛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林淼刚参加工作时,牛四是他的师父,跟了他半年,才晓得弄错了师傅的名字。一次安全考试,开卷,林淼龙飞凤舞地替他答完卷纸,顺手在空白处写上了牛四两个字。字很大,牛的那一竖还卖弄地拐了个弯,很像牛的尾巴。
牛四识得几个字,但写不了字。他定定地瞧着空白处的字愣了好半晌,拿起林淼丢在桌子上的笔在“四”上一笔一笔涂着。四字变成了一个黑黑的方块,牛四长长地舒了口气,在黑方块后补了三个谁也不挨着谁的牛。这三个牛加上林淼前面写的那个牛,看着倒像一头大牛带着三头小牛。
林淼眯着眼睛左看看右瞧瞧,才晓得那是一个“犇”字。
煤加工车间没啥技术活儿,师傅就是个称呼。称呼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师傅、牛师傅、四哥、老牛、牛四、闷牛。林淼嘴里的师傅变成牛四,他还在那个黑黢黢的岗位上干着,林淼已成工长。
牛四的家境不好,性格内向,找媳妇困难。浪荡到三十多岁,他老娘才从农村老家给他寻了个媳妇。结婚那天,林淼和老杨去了,让他吃惊不小的是,牛四媳妇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条有身条。喝多了的老杨大着舌头说:“这、这他妈的,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这闷牛,艳福不浅呀!”
老杨四十多岁,干瘦,五官倒也周正,唯一口大牙向外龇着。他嘴碎贪小嗜酒,好说个荤话,不论话题是什么,到了他嘴上,三绕两绕就能绕到男女床上那点事上。
两人的岗位隔条小马路,老杨岗位上有三个人。牛四闲时,喜欢蹲在老杨岗位上的一个角落里听他胡扯淡。
牛四歇完婚假,脸上多了一个大口罩,班前会后猫在自己岗位上,一整天都没出来。下班,拖到别人都快洗完澡时进来。一身肥皂沫子的老杨悄然凑过去,一把扯下了牛四的口罩,撒腿就跑。边跑还边嘎嘎地笑着喊:“牛四挂彩了,牛四在他老婆的战场上挂彩了!”
众人嬉笑,林淼见牛四左脸上几道挺深的血痕,之后“啪”的一声闷响。回头,老杨四仰八叉地倒在了浴池光洁的地面上。大家都没当回事,以为他一会儿就起来了。过了好半晌,老杨还躺在地上。
林淼正要过去,牛四慢悠悠走过去,蹲下身子,伸食指和拇指搭在一起,瞄準老杨那活儿“啪”地弹去。老杨挺尸般地坐起,浴池里爆发出一阵哄笑。
林淼在更衣箱前换完衣服,有人喊:“工长,老杨站不起来了,你快过来看看,需不需要值班车送医院?”
林淼过去,老杨脸煞白,额头上布满汗珠,看样子不是装的。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搀着老杨出来,牛四笨手笨脚地帮他穿上衣裳,值班车已经来了。
送到医院,拍完片子,牛四和另外一个同事扶着老杨向外走。林淼接过单子,上边龙飞凤舞地写着一行字,他举着单子念:“左腿明显骨折。”
话音刚落,原本还能勉强走路的老杨,一下子软在了牛四的身上。林淼过来搭了把手,架着老杨回到诊室。戴眼镜的女大夫拿起单子看了看说:“没啥事,回去休息几天吧。”
老杨磕巴着说:“不、不是骨折了吗?”
女大夫的眼睛从眼镜上翻出,横他一眼说:“谁告诉你骨折的?”老杨瞧向林淼。林淼说:“单子上不是写着吗?”女大夫剜一眼林淼:“识字吗?那是未见明显骨折!”
回去的路上,老杨说:“工长,大夫都说了,让我休息几天!”林淼没好气地说:“休个屁,你还有功了呗!你休了,活儿谁干!”
牛四喏喏地帮腔:“就让他休两天吧。”
林淼瞪了他一眼说:“还没说你呢,挠就挠了呗,戴那么个破口罩干啥,他休息可以,你明天替他干活!”
牛四说:“行呢,我替他干几天。”
老杨一把搂住牛四说:“哥们,好哥们!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你老婆为啥挠你?你昨晚霸王硬上弓来着?”牛四怒:“你要是再提这事,你的活儿自己干!”
2
牛四吝啬,婚后变本加厉,凡班内是花钱的活动,概不参加。他抽烟,从来不给别人散烟,别人给他,他也不抽。班内其他人家的婚丧嫁娶,一概不去,总的一句话,花钱的事不要找牛四。
自助餐流行那年,林淼手里攒了几千块钱的班费。年底,他张罗着聚餐,牛四去了。坐上桌子,筷子就没停过,老杨损,不让服务员撤牛四吃过的空盘子。两个小时的时限,牛四光是羊肉就吃了十八盘子。
自助餐不允许浪费,桌上或火锅里剩的东西太多,就要罚款。时间将到,牛四把桌上两盘子羊肉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一股脑倒进了锅里。锅开后,起身拿过一个汤盆,左手拎起漏勺不紧不慢地把锅里羊肉、鱼丸、蟹棒、蔬菜一勺一勺捞出,右手的筷子在漏勺里拨拉着。调料飞进了旁边的一个碗里,漏勺里的东西倒进汤盆。他捞得仔细干净,就连煮飞了的小块土豆都没有放过。锅里汤渐清,他慢慢坐下,头垂下去,嘴贴在盆沿,唏哩呼噜一阵声响,盆净。扯块餐巾纸,抹抹嘴,抬腕看看表,把胳膊杵到两眼直勾勾的服务员的眼前。
结账,老板指着门口的牌子对林淼说:“带民工进来需要加钱。”林淼怒:“哪有民工?”老板指了指拿着苹果腮帮子鼓起的牛四。林淼瞟去,颜色灰暗的夹克,沾满灰尘的皮鞋,肥肥大大的裤子挽着半截裤腿,活脱一个民工。他笑道:“你凭啥说他是民工?”老板语塞,反应却快,说:“那你怎么证明他不是民工。”
声音很大,牛四听到。慢吞吞地将啃了两口的苹果叼在嘴上,拉开夹克拉链,摸出一个包裹严实的小包,一层层打开,簇新的工作证出现了。
老板看工作证,牛四回身又抓了两个橘子。他忙不迭地把工作证递给林淼对领班说:“你给我记住,以后不许接待他们。”没过多久,自助餐馆关门了。嘴损的老杨逢人便说,弄得牛四在车间里越发有名了。
牛四成名跟老杨那张破嘴有直接关系,他却从不记恨老杨,非但不记恨,俩人的关系还很要好。
牛四有一个习惯,你多会儿在外边看到他,他都低着头像是在找东西。某次,除尘设备出问题,缺异形螺栓。林淼急,四处乱转,转到老杨岗位,老杨说:“问牛四啊,哪儿有啥东西,牛四最清楚。”
林淼以为他又在开牛四玩笑,正要骂,牛四进来。他举起螺栓问:“牛四,哪儿有这种螺栓?”牛四接过螺栓仔细端详了一阵说:“煤场的破房子里有几台拆下来的烂设备,上边有,抹着黄油呢,应该好卸。”
林淼随牛四去。门前,牛四闷声道:“当心脚底!”林淼打开手电,地上到处是塔状粪便,风干的、湿乎乎的,别提有多恶心了。牛四说:“你别进来了,我去缷几个。”
慢慢的,林淼养成了一个习惯,哪儿的设备临时处理缺了东西,马上给牛四打电话,牛四一准儿能找回来,偶尔找不回来,他也能告诉你哪里有,你去协调便可。
林淼纳闷之余,并未深想。
某天夜班,林淼拎着手电进厂房,闻到烧胶皮的糊味,以为设备出了问题。顺着糊味过去,厂房的旮旯里,有一堆快要熄灭的火。
用手电晃了晃,马上明白有人烧废旧电线,准备卖铜。他生气的是厂房内严禁烟火,自己的人应该都晓得,是哪个缺心眼的人做这没屁眼子的事。
他掩在很隐蔽的柱子后,准备抓现行。半个小时,没见人过来,失去耐心,去了操作室,打发操作工去看。没过几分钟,操作工回来说:“你说的那地方啥也没有呀!”林淼不信,下来,刚刚还着火的地方被水冲得干干净净,真就啥也没有。若不是还未散尽的胶皮味,林淼甚至觉得是自己看花眼了。
琢磨了半宿,也没弄清是哪个干的。
逢到周一早上,班里要组织安全学习。林淼坐在会议室内仅有的两张桌子前等他的兵。足足等十几分钟,人们才断断续续疲疲塌塌地进来。安全员老徐不耐烦了,说:“林淼,你的人怎么跟羊拉屎似的,现在点名,后进来的算迟到,考核!”
林淼瞥向窗外,老杨跟两个女同事追逐打闹着,后边跟着慢吞吞的牛四。他黑着脸没吱声,嗵嗵嗵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伴随着老杨嘎嘎的笑声涌进了会议室,老徐原本就很长的脸越发长了。
跌跌撞撞进来的老杨觉察气氛不对,抬头,林淼狠狠地瞪着他说:“老杨,你挺有劲啊!皮带机头那堆煤正愁没人清呢,我看你也不用开会了......”老杨苦着脸说:“工长,可不能这样呀,我上次摔了还没好利索呢。”话音未落,牛四晃到门口,老杨眼珠一转,嘿嘿地笑着说:“闷牛有勁,你还是让他去吧,省的他晚上闲溜达,万一哪个地方有个坑,再把他脚崴了,还得报工伤。”
底下的人哄然大笑,笑得牛四茫然不知所措,咔吧咔吧小肉眼睛瞧瞧这个看看那个。一股刺鼻的烧胶皮味夹杂着浓郁的汗腥气冲进了林淼的鼻腔。
林淼喊了声:“牛四,你过来。”
牛四迟疑着过来,林淼抽了抽鼻子,烧胶皮味越发刺鼻。他盯着牛四的眼睛意味深长地笑着说:“坐回去吧。”
老徐话痨,啰啰嗦嗦地讲了一大堆。大家好容易等他讲完了,林淼却讲起了防火防爆,讲就讲吧,他偏有意无意地瞟着牛四讲,讲的还挺邪乎,什么扣钱了、下岗了、坐牢了等等。牛四微垂着小眼睛,老僧入定一般。不过,他在冒汗。汗水从头顶汇集在安全帽的边沿,顺着两鬓额头淌下,那张黑脸在阳光下亮晶晶的了。
?
3
牛四被吓着了。
他弄不明白林淼怎么发现他在厂房里烧废电缆,琢磨着把几扎团好的裸线塞到裤腰带里,从厂房的旮旯里鬼鬼祟祟地出来,登上自行车上了马路。
出厂的大门有三个,一大两小,都站着穿制服戴白手套的门卫。牛四绕了个远,选了最偏僻的一个大门,那个门的检查相对松得多。好像是走霉运,老远看到大门口有三个门卫,他们正在检查一个下班工人的饭兜子。牛四慌忙勒住车闸,急速转弯。太突兀了,后面的人险些与他撞在一起。那人骂骂咧咧道:“你他妈有病!怎么说拐弯就拐弯!”牛四也不言语,落荒逃去。猛蹬了十几分钟,悬在嗓子眼的心才咕咚一声落回到肚子。
十字路口,他偏腿下车,站在路边点燃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林淼和几个同事说笑着骑车过来。正想背过脸,眼尖的老杨喊了声:“看,那不是闷牛吗,这小子躲在这儿抽烟呢。”
看到老杨那一刻,牛四忽然想起了他说过的话:“带东西出门岗,最安全的是走大门,门卫看着多,可走大门的人也多,他们查不过来。”
他掐灭手里的大半截烟,揣到兜里,跨上车子混在了其中。林淼瞧瞧他说:“身上没带不该带的东西吧?”牛四没吭声,眼神有些慌乱。看到他的眼神,林淼估摸着他身上带着昨天烧的铜线,仔细打量,却看不出他藏在哪里。
门卫的小队长是林淼的同学,他很少出来站岗,一般都坐在大门旁的房子里。房子不是很大,面向大门这边的窗子却很大。林淼因牛四的眼神,心里犯着嘀咕,抻着脖子向里看。窗子是开着的,他的同学恰好在那儿坐着。他吆喝一声:“晓光,走啊,跟我的弟兄们出去喝点。”
坐着的那人站起身推门出来说:“你他妈就没个诚心,明知道我上班,却让我跟你喝酒。”正在检查的两个门卫看到他们认识,根本就没怎么查,让他们过去了。
牛四不傻,他知道林淼刚刚帮了他,内心有些挣扎,该不该请林淼吃个早点。犹豫间便落在了后头,距离一点点拉开,萌生的念头便淹没在清晨凉爽的风中。
细细回想,林淼没少帮他。他住的房子是老娘的,房改那年,大哥、二哥都争这房子,家庭战争爆发,老婆二兰子甩下还在吃奶的牛艳跑回了娘家。老娘心疼孩子,找亲戚连着请了几回,二兰子才放出一句话:“想让我回来也行,房子必须落到牛四的名下,老太太出去租房子住。”
老娘连气带急地病倒了。大哥来了,把牛四骂了个狗血喷头,掉头走了。二哥来了,又把牛四骂了一顿,转身离去。老妹牛彩彩心疼娘,想接走她,老娘惦记着牛艳说啥也不走。
牛四忙、累、烦,干活时出了错,弄出一次事故,林淼找他谈话,要扣他全月奖金。牛四急,把家里的事儿都抖了出来。林淼不是个滋味,领着牛四找书记借车间的新客货车,准备请牛四老婆。书记说:“你们都谁去呀?”
林淼说:“我、老杨还有牛四。”书记摇摇头说:“都他妈五大三粗,能做工作吗?带上曾静。山里人好喝酒,买上一件二锅头,钱由车间出。”
书记的话让一旁的牛四心里热乎乎的。
曾静与林淼同龄,她是自学成才的楷模,读过夜大财会专业,还自修过汉语言文学,双料的“五大毕业生”。个子高,骨感,很少描眉画唇,短暂婚史,夺得过公司羽毛球比赛冠军。做事原则性强,正统,善说教,是集车间的通讯员、计生员、保管员、统计员为一身的车间大员。
山路很长,车上弄这么一个连点女人味都没有的政治教官在身旁,能做的只有一件事——睡觉。
穷山沟子里,忽然来了这么多官家的人,还有一辆气派的车,二兰子一家被唬住了。杀羊,盛情款待。老杨醉,牛四倒,林淼五迷三道,二兰子被她爹吼骂着随车回来。没隔多久又跑了,牛四找林淼,林淼找车间,二兰子回来。往往复复中,牛四老娘的房子落在了牛四的名下,小后院接盖了一个小房子,牛四的老娘被清理到那个房子里。再后来,大屋通向阳台的门也被封堵了。
牛四忆起这些,林淼仿佛感应到了,想起牛四老婆二兰子。那次封堵阳台门,他才真正领教了什么是后山女人。
封堵门需要材料,封堵后,小房子需要炉子、烟筒、水泥等等。牛四又找林淼,林淼骂:“你他妈也太过分了吧,那是你妈,你是吃她奶长大的!早知道这样,你哥哥争房子,我就不该帮着你做他们的工作,你个窝囊废!”林淼骂,牛四不吭声,再罵,还是不吭声。末了,吭吭哧哧地说:“那你再做做我老婆工作吧。”
林淼找书记,书记又派曾静跟他去了。
到了牛四家,曾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讲到了孝道,又讲到婆媳之间,滔滔不绝,密不透风。二兰子的眉毛渐渐立起来,趁着她喝水的空当,她戳点着牛四说:“你说说,你也能叫个男人?家里有那么一点事,你就弄回来一群人。咋啦,吓唬我二兰子没见过世面是不是?给我讲道理,我的道理可多着呢。”
曾静一时语塞,用手戳点着二兰子说:“你......”
二兰子嘿嘿冷笑道:“你不用戳点我,我好赖还有个老爷们儿,你呢?连个男人都拴不到裤腰带上,你还有甚资格跟我讲道理。”
曾静脸涨得通红。
林淼看不过眼,正想吃哒她几句。二兰子转过头可怜兮兮地说:“林工长,做女人也难啊,你是真不了解情况,我从进了他老牛家这个门,他们家哪个把我当人看了,你说说,就这么一个走风漏气的破房子,住到一起是真不方便!尤其是晚上。再说了,就是砌一个门,影响啥了。”
无功而返。
回去的路上,曾静说:“简直就是一个不可理喻的泼妇,我是不想再来她家做什么工作了。”
次日,书记交代给材料员,牛四需要的材料,只要车间有都给他。他又叮嘱林淼,该出人就出人,该出车就出车。林淼诧异之极,事后问曾静,女人的脸却无端红了。
那一刻,林淼忽然觉得她像个女人了。
想到这儿,林淼噗嗤笑了。他笑的时候,牛四一脚跨进了小房子。老娘嘴里叼着半截手卷旱烟,烟灰长,欲坠。手里提着家里的杆秤,眯着一只眼睛瞧着秤杆,旁边还散落着几个刚捡回来的饮料瓶。他拽出腰里别着的铜线丢到称盘上称了称,四斤四两。
老娘啰嗦:“去东边那家,他家秤上不哄人。”
牛四也不吱声,将铜线装进一个邹巴巴的黑塑料袋,提了老娘扎好的纸壳和一袋饮料瓶子,掉头出门。铜卖了八十块钱,纸壳和饮料瓶卖了八块钱。
牛四将钱分别装到两个口袋里回来,老娘已经给他热好了一碗腻乎乎的土豆和三个馒头。他把左边口袋里的八块钱掏出来递给老娘,坐到小炕上,呼噜噜几口,菜先没了,他把手里剩下的半块馒头团成一团,一圈一圈擦拭着菜碗,菜碗洁净的如同洗过一般后,三口两口吞掉馒头,站起身出了老娘的小房子。转到楼后,打开自己家的房门揭开工具箱,拽出一个劳保鞋的鞋盒,将八十块钱塞进了劳保鞋里边。塞完后似觉不妥,又掏出来,踌躇着从中抽出两张十元的票子,出门买回一盒兰州烟。
第二日,林淼本想找牛四谈谈,他怕这头闷牛捅出别的娄子来。设备的事儿太多,没顾上。刚得闲,牛四鬼鬼祟祟地进来,从烂棉袄里摸出一盒烟递过来。林淼不接烟,冷着脸说:“啥意思?”牛四吭吭唧唧:“你、你、你抽吧。”林淼依旧板着脸说:“不跟我藏猫猫了?”牛四讪笑着说:“你是怎么发现的?”林淼接过烟打开烟盒抽出一支点燃,把剩下的又塞回到他的破棉袄里说:“你他妈的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跑到厂房里去点火!”
?
4
琐事很多,日子很快。
这年的冬天很奇怪,天总阴着,就是不下雪。立春那天却沸沸扬扬地下了起来,老天仿佛把积了一冬天的怨气一股脑宣泄下来。
漫天飞舞的雪花中,老铁厂的第三座高炉也停炉了。停炉,林淼能理解,不停怎办?炼一吨赔一吨,炼的越多赔的越多。他弄不明白这钢铁行业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要是都停了,他们这些工人怎么办?
前两座高炉停炉,林淼庆幸自己三年前来了新铁厂,这边生产正常,工资依旧,用不着惶惶不可终日。对于那边的动荡,显得很淡漠,甚至还有一种隔岸观火的窃喜。偶尔提及,也如同谈论东海的钓鱼岛、南海菲律宾那条破船那般举重若轻。
新老铁厂相距不远,以一条大坝一样的铁路线为界,站在高处,两边泾渭分明。东边挤挤插插的厂房、通廊因常年的日晒雨淋、粉尘侵蚀,颜色陈旧不说,且闹腾;西边则灰是灰、蓝是蓝,规规矩矩,十分安静。新铁厂的工人多是从老铁厂过来,照理说那边发生了什么,这边很快应该知道才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就说停炉这件大事吧,若不是在一个婚礼上碰到曾静,他根本就不会那么快知晓。
曾静变化很大,身材丰腴了许多,眉眼弯弯、嘴唇红红,长发披肩,身上散发着甜丝丝的气息。林淼的眼睛发直,曾静笑嘻嘻地过来拍了他一把,顺势坐在旁边说:“怎么了,不认识了?”林淼呵呵地笑着说:“大街上肯定不敢认,你是越活越年轻了,还在车间干万能员呢?”曾静感慨:“早就被人家精简下去倒班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如今领导都喜欢娇滴滴的女人在身边。我们他妈就像是块破抹布,用过就扔。不过也挺好,要不是被减下去,我也不可能在外边弄个羽毛球班,哪能活得这么滋润呢。”
林淼惊异。
曾静又说:“你还记得牛四吗?”
林淼说:“那是我刚入厂的师傅,他怎么了?”
曾静说:“他现在跟我一个岗位,好人,你要是能帮就帮他一下吧。”林淼问:“他又捅什么娄子了?”
曾静愤愤:“高炉停炉,车间老系统全停了,闲人太多,整出一个竞聘上岗,让大家考试。如果公公正正地考也说得过去,关键是让老系统的工人去考新系统的实操,工艺虽然相同,设备却不一样,你说那能考过吗?更让人气愤的是,新系统缺的几个名额早就内定了,简直就是他妈哄鬼呢,绑着人家强奸还说你自愿。”
林淼揉揉眼睛,细细打量着曾静,他都不敢相信这番话出自她的口中。曾静举起杯说:“来,干一个,吓着你了吧。”林淼说:“你还没说牛四到底怎么了。”
曾静说:“考试那天,卷纸刚发下来,牛四倒提着卷纸砸到了讲桌上。新来的书记觉得牛四在示威,挡在门口,问他为啥交白卷,牛四一膀子把人家拱了个趔趄,还骂了一句,滚你妈的吧!然后扬长而去。他这么一带头,老系统的人全交了白卷。”
林淼说:“你们车间怎么处理的?”
曾静说:“前天才发生的事,还没处理呢,听说要扣三个月的绩效工资。”林淼低头思谋了一阵心里道:牛四一根筋,这事肯定是老杨扇乎的,这头闷牛!曾静让他帮忙,他又能帮上什么,如今的领导和以前的领导不同了,如今的厂子和以前的厂子也不同了,冷冰冰的沒有人情味,他林淼又算是个干啥的。
席散,林淼和曾静相互加了微信好友。
次日,林淼给安全员老徐打了个电话。老徐说:“挺麻烦,风头浪尖,他的这件事影响太坏,书记又不依不饶,已经报厂里处理,你别跟着瞎掺和。”
林淼虽想帮他,却爱莫能助,叹息了一声作罢。
这日,一个陌生电话连续打到他的手机上,最后一次,他犹豫着接起来,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传了过来:“工长,我是牛四。”林淼笑着说:“我可不是你的工长?别瞎称呼,找我干啥?不是找野鸡又被人讹住了吧。”话一出口,有点后悔,他来新铁厂前,牛四在棉纺路找站街女被人家讹住了,大半夜给他打电话,他带着三百块钱把他弄了回来。
那件事让林淼的眼珠子差点掉在地上,这么一个老实人居然干那么不老实的事。更让林淼诧异的是,他们回来后,牛四坐在一个超市门口的台阶上脱了一只鞋,抠出鞋垫,变戏法似的变出好几张百元钞票。林淼生气:你他妈有钱半夜给我打什么电话!牛四的小肉眼睛死盯着自己的脚面。林淼又说:你老婆远比你找的那个野鸡漂亮,你图个啥?也不怕得病!牛四还是不说话,林淼越发生气:“你要是给我讲不出个所以来,我就把这事告诉你老婆,再汇报车间处理你!”
牛四低着头,用脚搓着地上的一根树枝,树枝的皮都叫搓没了,还是不说话。“不说是不是!那你就想好怎么跟你老婆说,等着车间处理!”林淼作势欲走。牛四慌,结结巴巴地说:“跟、跟我老婆也、也要钱。”
林淼险些晕倒:“他们说你的工资本都是你老婆把着呢,你哪还有什么钱?”牛四说:“奖金”。
头一遭听到这么奇葩的事,林淼简直都无语。
出神间,牛四的声音从电话里挤过来:“我交白卷的事你知道吧,车间要扣我一个月绩效工资,我这两天在爬到厂房顶上想踅摸点废电线卖......”林淼打断他的话头说:“叫人家抓住了?你个愣货,我以前就说过你,别贪那点小便宜,叫人闹住工作都得丢,你就是不长记性!”
牛四连声说:“不是、不是,老杨用手机拍了我站在厂房檐的照片传到微信里了,说我要跳楼。厂里来人要跟我谈话,你说我说啥呀?”一个念头在林淼的脑海中闪过,他快速说:“他们跟你说啥都不要接茬,眼睛死盯着一个地方装傻,装得越像越好,一直装下去,跟谁也别说。”末了又加了一句:“包括曾静。”
牛四闷声嗯了一声挂掉了电话。
几天后,曾静打来电话说:“牛四装傻的主意是不是你出的?你的馊主意可真损,我现在有活干了,天天上班看着他。”
林淼嘿嘿地笑。
曾静说:“你还笑,我现在都弄不清楚他是不是真傻了。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别让他在我跟前装了,我瘆得慌。”
林淼说:“厂里怎么处理的他?”
曾静笑着说:“你是真有一套,厂里不仅没处理他,还带着东西去他家慰问了。我们老系统的人也跟着他沾了光,考试作废,都到新系统干活,一个人的岗位三个人干,大家现在幸福得跟花儿一样。”
牛四的事儿渐渐淡忘时,公司召开了职代会,林淼是正式代表。与历届职代会不同的是,这次职代会的报告上假大空的东西少了,提出的全部是触目惊心的问题。什么负债上千亿,什么每天一睁眼都要面对一千多万的利息,什么四万员工,有一万人不干活,什么今年必须减亏几十亿等等。
林淼的思想在溜号,他想起家里厨房角落里的一个放置了很久的苹果,看着很光鲜,硬挣。某天好奇,拿起它用菜刀剖开,才发现那果子内里早就烂了,只剩了薄薄的一层皮。
林淼的心里哇凉。
这一年春天,北钢的动作前所未有,合并厂矿、由上至下精简机构、压缩机关人员,无论工人还是干部,全部从原来的位置起立,逐级竞聘上岗。所谓竞聘上岗是公司领导聘厂矿一把手,厂矿领导再聘副手以及车间、科室的一把手,车间一把手选出班组长,班组长再选工人。没有竞聘到岗位的工人干部或内部退休,或分流到以前民工顶替的艰苦岗位。由于减员幅度非常大,民工顶替的岗位有限,容不下那么多的人,工人的精简政策出台:以年龄为界采取“一刀切。”
牛四的年龄虽然还差一年,却因他们车间书记成功竞聘为主任,他被定为脑子有病,无法胜任本职工作,提前内退回家。这日,林淼意外地接到了二兰子的电话,问他牛四还能不能留在厂里了。林淼叹了一声说:“我连我自己留到哪儿都不知道了。”
因为这事,林淼内疚了很久。再次见到牛四,他混迹在一群站桥头的民工当中,背微驼,头发花白,脸又脏又黑,目光呆滞。林淼叹息了一声,掉转头,迎着渐渐沉下去的太阳,默默地过了桥。再次抬头,暮色已经模糊了北钢那高高低低的烟筒和厂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