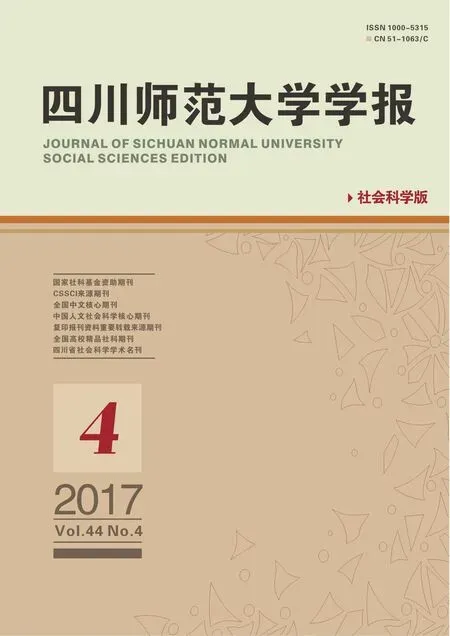宋育仁“封建论”中的“地方”与“天下”
陈 阳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241)
宋育仁“封建论”中的“地方”与“天下”
陈 阳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241)
中国读书人具有超越地方的“天下”政治关怀,宋育仁在清末民国之际坚持的封建论是这一天下思维的具体呈现。在清末维新运动时期,宋育仁和蜀学会师生的封建论带有明显的“外向”性质,通过“自分”的构想去抵御西洋外患的冲击;民国建立之后,宋育仁的“天下”政治失去了根本的制度依托,从而回到封建的“内向”维度,以此表达对民国政体的批评,并通过倡议乡礼复古来构建一个家国一体的“天下”蓝图。
宋育仁;政治思想;封建论;地方;天下
一般说来,随着清末权力重心的下移,以乡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获得了更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张力形塑了近代中国的权势结构。地方精英在清末民国时期不断以“自治”为口号,在挑战中央权威的同时亦扩充了自身的政治话语权,这一思潮直至“联省自治”的提出达到高峰。不过,正如罗志田教授所言,在近代中国参与构建乡里权力空间的地方精英未必都是“乡曲之士”,他们虽身处乡里却依然保持着“天下士”的自我定位[1]26。在中国读书人的思维里,“地方”和“天下”是同在一个依次递进的纵向结构中的,而地方知识精英的思想中始终存在超越性的维度[2]7-10。在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的思潮下,“地方”是制度建设的载体,而以“天下”的视角来看,其制度化的体现则当属“封建”①。尤其在清代中后期,受到今文经学复兴潮流影响的一部分读书人,发挥“天下”和“封建”的制度想像,希望形成一套新的政治秩序②。同时,地方主义的发展不断在现实层面给传统精英提出新的问题,如何转化传统的“天下”话语以应对这些新问题,成为徘徊于新旧之间的读书人思考的重点,这一困窘一直延续到民国时代。这也意味着,要深入理解这一时期所谓“旧派”知识人,不仅仅要关注他们的文化表现,亦不能忽视其思想中的政治性和制度性③。宋育仁(1858—1931)正是这类读书人中颇有特点的人物④。本文无意对宋育仁的思想作一整体介绍,而是仅从其中与政治联系紧密的“封建论”入手,讨论宋育仁政治思想在清末民国时期的变与不变,以此折射近代中国读书人多元的政治关怀。
一 封建乃救时急务
光绪二十三年(1897),宋育仁从驻欧参赞官任上卸职,随后经由张百熙举荐,回到四川办理商务。在这一时期,他接连在重庆、成都两地创办了《渝报》和《蜀学报》。维新潮流蓬勃之际,时人对新式报刊抱有极大的期望:“究新学也,达下情也,振陋风也,存公议也,动众耻也,凡所论说,皆天下之大务,救时之良言。”[3]11宋育仁则对报刊有更丰富的认识,他认为,西方报刊多与“教会、议院、学会、商会相辅而别行”,实际上代表了某一组织的思想言论,因此蜀地办报,就“不能专门而别居,要以宏问学之路,则以学为名”,要“论撰博采,而必反之于经”,最后“归重以卫教为主,明政为要”[4]8。基于此,《蜀学报》成为了成都尊经书院“蜀学会”的机关报。宋育仁提出,蜀学会的宗旨应“期以通经致用为主,以扶圣教而济时艰”,强调:“此会以经训为主,与祖尚西人专门西学者有别,至格物穷理,无分中外,临讲务求折衷至当,不得是彼非彼,率相诋諆,致长轻浮。”[5]1
“蜀学”本就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学术名词,尤其在近代,“蜀学”的提出隐然有与四川之外的学术主流相较量的意味[6]。这无疑是四川学人寻求自身主体性的表现。尊经书院都讲吴之英曾给蜀学的宗旨下一定义:“蜀何学,曰学周孔耳。乡之学者,肤寸而合,其于周孔,分络之筋脉,坚实之精髓,未或抉也。”同时在吴之英看来,蜀学以周孔之学为根基,并不妨碍其引进新学知识,“何以购西书报,何以采西说”,归根结底仍是“尊周孔也”,其逻辑则是“窥鸠巢者,非欲化鸠,怒其夺他巢而据之也,探虎穴者,非欲化虎,将欲得其子而缚之归也,勾践不履吴王之庭,不能老之甬东,康成不入何君之室,不能操其戈以伐之也”[7]6。原本和东南学界相比不那么“进步”的蜀学,在中西之间找到了独有的地位,宋育仁将这一思路总结为“复古即维新”:“欲兴其国,先修其政,欲修其政,先论其治,论治之纲在治官,治官之实在用贤,用贤之源在造士,造士之枢在讲学,学术晦盲久矣,举古今中外民于天地,必有与立,其依在教,我欲不易教而治,讲学必依教为根。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岂仅富强而乐利。反经即复古,复古即维新。”[8]9正因为蜀学能严守周孔原典的精髓,所以能够在剧变之际担负起同西学分庭抗礼的责任,原本异于主流学界的一隅之学,通过在“复古”与“维新”之间独特的转换,跻身于中西对抗的前沿,俨然占据了超越地方性的“天下”之学的位置。
正是在此语境中,宋育仁展开有关“封建”的讨论。宋育仁在蜀学会会讲时提出:“封建井田,乃救时急务,非矫语高远也。画井分沟,既阻车马,不得径达,是平原亦可设险也。又人人皆有田,既便寓兵于农,且庐墓所在,不忍委去,去亦无所得食。而学校以牗其心,圜土以纳其情,周官已纤悉俱备。约而言之,国无游民而已矣。无游民则必富强,外侮何从入哉?”在会讲一开始,宋育仁就点出“救时”和“外侮”这一时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吴之英针对这一问题,提出:“既封建,当闭港永不通商,且将清理内地洋教”;宋育仁门生之一杨赞襄则认为,尽管吴说“痛快淋漓”,不过“闭关锁港,公法所禁,恐将骈诛洋士,授彼口实,腹地犹可,贻祸海边”,因此最好是“将居华教士护送出境,海中通商,毋许上岸,既不失自主之权,而外人亦可原谅”。接下来,吴之英又提出具体的封建规划,认为“封建必如汉初”,尊经学生邓守霞亦附和其说,认为历来认为诸侯跋扈,但实际上“卒赖其拒捍吐蕃、回鹘、契丹,武宣末世,亦颐指如意,几于中兴”;宋育仁则反对封建单位过大,指出:“余意以县为一国,不必封裂太大。”杨赞襄亦赞同其师,并指出“古今异宜也”,汉唐时北方民族“但知攻掠”,所以必须“大藩广封,足以抗御”,现今则“惟患不分”,理由是:“外洋之灭人国,不尚征伐,但挟其君以制其民,以尽夺其权而后已。今若以一省为一国,则彼但尽力攻取省城,挟其君以制其民矣。若分为千百国,彼岂能尽灭哉?”杨范九亦补充道:“彼取一县,必以千万人守之,多则兵尽,少则聚歼,封小国所以穷洋人之谋也。”吴之英对此尚抱有怀疑,认为:“沿海一带,岂能支持,国小力分,唯有大去耳。”宋育仁则相当乐观,称:“纵然奔溃,仍可恢复。”杨赞襄进而提出:“广浙七省宜以总督为民主,各县为君主,仍如畴昔节制,重兵巨财,皆掌于民主,民主择贤,君主世爵,洋人纵攻虏民主,众君主仍可另戴新君,庶不忧尾大不掉及西人挟以为质之弊。”[9]18-20
宋育仁师生对“封建”的具体讨论鲜明地展现了复古眼光的“外向”维度,封建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列强的瓜分和挟持。在此次会讲之前,《蜀学报》就已经选登了四川学人有关封建的议论。川人徐昱针对清廷诏令各省大员“各保土宇”的政策,指出:“所谓权宜,各保土宇,即封建之遗意,团练以合九州,即三代之农兵也。夫中国之制,合天下以奉一人,西人即挟一人以陵天下,其势合也;封建之法,分天下以尊一人,西人不能胁一人以揽天下,其权分也”,封建制度之下,“天子恭己于上,而四方之臣民奋臂而驱除之,则西人生畏矣,西人畏我臣,畏我民,夫安得不知天子之尊也。天子既有常尊长,无西人交涉之优,则有闲暇以休养生聚,教诲于王畿之内,有何不足以制封建之诸侯,而惧其尾大不掉也”[10]1-2。成都士子邓镕亦投书《蜀学报》,提出:“我能图富强,而人亦必有先发以制我者矣。然则以四百兆之人,十八省之地,藉寇兵齑盗粮,而使外国分中国,又何如中国自分,而犹楚人失弓,楚人得之乎其分也。奈何惩孤立之弊,究众建之利,内宗室,外封重臣,予以李唐藩镇之权,酌以姬周封建之制,无事则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有事则人自为战,家自为守,而天子揆宅中土,控制群藩,准其国土之瘠腴,定其岁贡之多寡,进以剜肉补疮之说,则并兼不作,喻以舐糠及米之意,则患难与共。如此则虽十卵九叚,而得一完卵,固足以定韦彭之霸,建桓文之业矣。”[11]1-2
将“封建”作为与外敌交涉的基础,甚至为了防止列强“挟天子以令诸侯”,宁可“使外国分中国,又何如中国自分”,这一思路其实并非蜀地学人独有。1902年,浙江籍士人杜士珍亦认为,“以今之中国,而当今之世界,非封建决不足以救亡”,原因之一即“足以阻列强分割之狡谋”,中国如果实行封建,“则即有以此迫政府者,政府其有辞矣,曰此我封国之地,非我所得主也,而分封之国,亦可竭力相抗,不受政府之命,曰此我受之先祖先宗,而不容以尺土与人者也。余疆余守,无所顾虑,无所疑忌,而敌人制我之术,已失其过半矣”[12]28-29。
在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中,封建和郡县被视作一组对立的概念,尽管封建常常被用来批判郡县之弊,但历代王朝当政者从现实政治出发,并不重视封建论,围绕封建—郡县的争论,最终多归于调和。直至晚清,俞樾同样也延续着这一思路,提出:“封建必以郡县之法行之,郡县必以封建之法辅之,两者并用,然后无弊。”不过,俞樾也指出:“内地郡县而边地封建,固有天下者之长计也。”[13]415以郡县和封建分别对应内地和边地,已经隐然带有“向外”的眼光了。等到康有为作《上清帝第五书》,则更加清楚地表明,处理地方督抚的权力关系应当同抵御外敌的现实需要联系起来,其中“听任疆吏各自变法”一策就指出:“夫直省以朝廷为腹心,朝廷以行省为手足。同治以前,督抚权重,外人犹有忌我之心,近岁督抚权轻,外人之藐我益甚。”[14]196章太炎同样对地方势力的“跋扈”持积极态度,指出:“遍历九服,而观夫旌节旄纛之所建,亦苦其不能跋扈耳”[15]99;在存亡危急之际,“方镇苶弱,而四裔乘其敝,其极至于虚猲政府,使从而劫疆吏,一不得有所阻桡;割地输币,无敢有异议”[16]73。在章太炎的理想中,天下至公的制度仍然是“削藩镇以立宪政”,但若是仅为私利削藩,“私之至者,不行媚白人,使脍中国以至于尽不已”,则不可不驳,因为“藩镇虽离于至公,而犹未合于至私”[15]102。
康、章二人并未明确提出“封建”,但其言论中的“疆吏”“藩镇”确实有着与诸侯封建相仿佛的作用。以“藩镇”之分立去应对外患压力,就是与前述“何如中国自分”相同的思路。与此相比较,宋育仁的封建论又有其自身更加特殊的要求,他倡议的“复古即维新”论,实不以藩镇为然。在宋育仁看来,“封建”之益,不在于“势”,而在于“道”。这是宋育仁同康、章等人南辕北辙之处。黄宗羲曾提出:“封建之弊,强弱吞并,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县之弊,疆场之害,苦无已时,欲去两者之弊,使其并行不悖,则沿边之方镇乎。”[17]21尽管宋育仁对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颇为推崇,但在这一点上,他并不认可黄氏对方镇的看法。宋育仁认为,“方镇”不是圣王真意,如果处在真正的封建之世,即便有周厉王这般暴虐人民、“上失其道”的君主,不久以后仍可轻易“中兴”,因为“制度未废,王师所在,诸侯各以方伯连帅卒正庶长之职,出师以从,此采薇治外之一效也”;而封建的崩溃,要到周幽王时,“自破坏其军政,申后宜臼又召戎自寇,而军制荡然乎,又弃社稷而东迁,是周已亡,而封建之流弊乃出”,故此后造成乱世,“非封建原有之弊也”⑤。前述邓镕所言“予以李唐藩镇之权,酌以姬周封建之制”,宋育仁就质疑道:“言近封建之言乎?抑犹未究公私之辨,与古今得失之源也?”宋育仁强调:“封建者,公诸天下也,使天下各保有其私,而不敢陨越,自不敢侵凌,乃古今公理,万世而不敝”,但后世政治愈来愈差,如邓镕这般有意无意间“杂以汉唐分王藩镇”之说,“是欲起死人而倍偏枯之药”[11]23-24。
宋育仁能够坚信各地自分后“纵然奔溃,仍可恢复”,正是因为他内心中有一个“天下”在。在“天下”的笼罩下,“地方”才有可凝聚的中心,这也正同于所谓“亡国亡天下”之论。在“天下”前提下,邦国和地方是一致的,而之所以藩镇受到批评,正因其更看重各地之间的权力关系,而抛弃了“天下”。宋育仁无疑受到了公羊学“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他的学生在论证封建设计时,更是直接引“素王”论,认为:“当仿教皇之意,复素王之名,奉孔子为共主,择圣智为相将及各公侯,期以教为宗旨,将相公侯有过可援经义责之,如耶稣教士之役使各国,回教佛教之能制其酋长也。合教旨者君之,否则废之。即君即师,以德为贵。各邑教士推举一邑之君,各邑之君推举牧伯,牧伯共推将相,合天下为一教,并行之外洋,可复见中庸之旨矣。”[9]18-20
宋育仁从瓜分危机中看到了恢复“封建”的必要乃至落实的可能,亦与其“复古”与“维新”之间特有的张力有关。清末西风东渐以来,西方制度成为士大夫反照自身的镜鉴。特别是像宋育仁这样有过驻外经历的士人,同西方的直接接触,无疑为其自身提供了可资比较的一手材料。如郭嵩焘曾云:“圣人以其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身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颇疑三代圣人之公天下,于此犹有歉者。”[18]627薛福成也说:“若夫夏、商、周之世,虽君位皆世及,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犹行于其间,其犹今之英、义诸国君民共主之政乎?”[19]296儒家理想的三代之制同西方制度嫁接在一起,当然会抬升西方的象征地位,而在另一方面,如宋育仁在西洋看到“三代”后所言:“昔吾从使欧洲,历观其政俗之善者,与吾意中所存三代之治象,若合符节,乃为记载,随事引证,以为如握左券而求田宅也。吾国先有三代之治象,久营于心,于其采风涉目而遇之,不觉涉笔而取以为证,初非见其政美,夫乃引经传之言而为之颂圣也。阅者不察,率以为以西政比附古制而成书,夫亦不善知识矣,急索解人不得,独且奈何哉!此亦学术不明之故也。”⑥这一声明恰是宋育仁“复古即维新”内涵的体现。在西洋那里看到的“三代”遗意,并不必然要求步武西方政制,反而可以由此增强复古的信心,西方制度成为经典中的“封建”确有实效的佐证。这样,“天下”就不只是一个虚悬的文化概念。
一旦宋育仁试图把封建这一文化理想转化为现实诉求,封建论对当下政治的批判力必然会同不甚安定的政治斗争纠缠不清。清末今文家试图通过重新阐释儒家经典来影响政治,本就意味着权力的重组和对既有政局的冲击。康梁变法的失败亦有相当程度肇因于此。《蜀学报》封建议论刊载之际,恰逢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曾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在听闻杨锐等人被捕的消息后,立即写信给曾为昔日门生的宋育仁,警告其封建论“悖谬骇闻,亟宜删毁更正”,《蜀学报》诸文“谬说尚多,不可枚举。此后立言选报,务须斟酌。否则必招大祸,切宜儆戒”[20]7657-7658。蜀学会在戊戌维新失败后解散,宋育仁在清末的封建论亦随之停滞。
二 封建即是有道之联邦
尽管宋育仁在清末以“蜀学”之名在地方活动,但他长期以翰林京官的身份出没朝堂,其“天下”士的立场实际上要压过“地方”认同。宣统三年(1911),在四川保路风潮中,他就曾因为同甘大璋等川籍京官一起反对四川保路会商办川路,与四川地方士绅矛盾重重,以至于富顺当地保路会还公电声明,开除宋育仁的乡籍⑦。而在辛亥革命后急剧的政治变动中,宋育仁忽然间失去其原有的立身之处,不得不退出“中央”政治,而回到“地方”。这一变化影响颇深。“天下”必须有一个核心,其象征就是帝位,封建论如何在一个无君的民国政治现实下展开,是宋育仁必须面临的困境。同时,民国地方主义的政治诉求愈演愈烈,原本在清末受到地方攻击的宋育仁,因其旧学功名,又被成都士民尊为“五老七贤”之一[21]。20世纪20年代,地方精英纷纷提出“自治”、“省宪”的主张。1922年8月,四川当局成立省宪筹备处,省宪筹备处主任刘成勋就专为省宪事务致电“乡贤”宋育仁征求意见[22]209。
宋育仁需要回应地方自治的诉求,但其复古理想实与近代知识精英的“地方”思想有所偏离。他在回复四川当局的信中说:“宣言以国宪勘合省宪,以自治促进统一,宗旨尤为近正,邦人认可,吾亦认可。”[23]15并未提及时人念兹在兹的“川人治川”等要义,强调的则是他所认可的“以自治促进统一”的宗旨。当然,在军阀分裂的中国,统一是许多知识精英的共同追求。各省自治与立宪,多由掌握实权的军阀直接发起并参与,但省议会和知识界在响应省宪的同时,一般又视军阀为中国乱源,是中国分裂的祸首。尽管联省自治希望加强省的独立性,看起来并不利于统一,但相当一批支持联省的知识分子,依然把“联省”视作统一的手段⑧。当时中华晨报社社长黄天石就认为:“联治为统一之手段,为组织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之基础。”[24]7署名“梦蝶”的论者也指出:“联省自治者,促成统一者也,以统一为目的者也。”[25]15直到1930年,依然有评论者提出,联省之后,政权虽分,主权不分,自治最终之目的仍是要“促成真正完全的统一”[26]7-8。
需要注意的是,宋育仁的“统一”与新知识分子的“统一”并不能等量齐观。宋育仁先是对“联省自治”这一口号是否合理提出质疑,他认为,“地方自治”在西文中的表达仅为一个单词,国人将其译作中文时,便二分为“地方”和“自治”,可随意颠倒为“自治地方”,地方成为自治的对象,而传统中国治理地方的权力和责任向来属于官员。因此,在宋育仁看来,民国人所谓争自治权者,皆不过是要争做官之权,将“地方自治”一词“离其句作地方一读”,“自治一句,则自治自属之个人涵义,脱却地方,地方不成界说”[27]1-2。宋育仁进而批评民国地方议会借此名义替人民代言自治,形成议会包办,“不明法治国之法理,所争者系本省人做本省官,仍旧是本省官管本省百姓,颠倒错乱,始而以讹传讹,因而将错就错,久而习非成是”[28]17。对于“联省”之说,宋育仁也认为大谬不然,因为“省”制属于“天下”制度的一环,“制置开府,则承制之上有君,今日民国无君,则制置何从而出,悲夫学说为天下裂,天下为学说裂矣”[29]14;民国称“联省”,实乃不伦不类,名实淆乱,“各界径言联邦制宪尚可,联省自治则非法”[23]15。宋育仁说:“省制乃帝国方域之名词,实行政中枢之分体。而地方自治,属立宪政体所应有之专条,与国体无干,更与统一无碍。地方自治,当缩小范围,何须联省。一言联省,即属中央统系,何名自治。正当由人民各就地方情形筹备自治法案,直接中央与行政官厅分权治事耳。不能指鹿为马,何劳越俎代庖。”[30]17
对比当时一些新知识分子对省制的批评,就可以看到二者的明显差异。邹明初提出“省”表示的是国家的“行政区域”(Administrative Area),不是独立的领土单位,“其本身已为国家全体之一部,无所用其联,且无可联者也”[31]24。朱希祖同样指出,“正名定分,实称之为联邦自治可矣”,省制“起于专制时代中央官署之称,决不适于联邦性质之制度”[32]。尽管表面上看,宋育仁和这些新知识分子都持反对态度,但他们所利用的思想资源和论述逻辑则大相径庭。朱希祖看到的是“省”一级制度为专制时代的官署,不符合他认可的联邦制度;而宋育仁的眼光则显然是向回看的,他解释“联邦”和“联省”的关系时称:“若言联邦,则容可为复古封建之基,亦或属止沸抽薪之计,以言联省,则实行藩镇割据之事。”[29]14宋育仁没有否定联邦的可行性,但这是因为较之联省与割据,联邦与他心中的封建稍显接近,“割据者无礼之联邦,联邦乃有礼之割据,联邦无道乃成割据,割据有道即是联邦,联邦乃有道之割据,割据即无道联邦也”,进而言之,“联邦尚属无礼之封建,封建乃成有礼之联邦,三代封建,即是有道之联邦,外域联邦,未免犹无道之封建也”,邦即是国,中国三代时的诸侯国之上是有天子存在的,宋育仁虽借用联邦一词,心中所想还是天下,“所谓先王经世之志在,因国度而建联邦,建联邦以拨乱世,即化割据为封建,乃经纶天下之大经也”,归根究底,以封建为建国基础,“知建国乃经世之大谟,即当知正名分必自建国始也”[33]18。
民国时期,中国的政治、社会毫无疑问更为西化,也正是因为西方元素渗透到民国的方方面面(“民国”本就是西方概念),宋育仁对民国的批评,可视作此前中西二元对立的延续。但毕竟民国不能等同于“外”,宋育仁在此时再提“封建”,俨然又回到了“封建—郡县”的内向维度。在宋育仁眼中,民国的混乱是同中国历代的混乱相似的,都源自封建的崩溃,“外诸侯之制已废,诸侯互相剪灭吞并,王朝不敢过问”,齐桓晋文称霸,尚且假借“王官二伯之名义,以兵力征讨不庭,禁诸侯之私相灭亡,以翊戴王室”,所以春秋五霸接踵而起,“仍用周之班制,纠合诸侯,虽属假名,而《春秋》亦与之”,等到战国时三家分晋,田氏篡齐,则纵横家之流交相煽惑,“不复有名义思想,惟有权利主义”[34]23-24。秦制之后,中央集权,以郡县治中国,“从此君与民隔绝不相通,上接于君下接于民者惟有官吏,不得不惟吏之是听,而严刑峻法之事起”,汉沿袭秦的基本政制,虽有三老、功曹、亭长等职位,与《周礼》所谓乡吏仍是“贵贱悬绝”,由此“人品悬殊,地方不能治矣,即黄黎州氏所斥后世帝王以天下为私产之孳息矣”[34]24-25。可见,郡县制实为乱世之制,“治日少而乱日多”,由于“民田之时代,豪强兼并日多,而贫民思乱者众,所以郡县民田之时代,近或数十年,远不过百年,必有一次人民造反,焚家劫舍,杀人流血,蔓延兵祸,而又易一朝,仍踵前非,在蹈覆辙”,即便是唐宋明稍安之时代,比起三代的治乱盛衰,“尚不可以道里计”,“此封建井田时代与郡县民田时代之比较,概可知者也”[34]26。
宋育仁说道:
《左传》曰:封略之内,谁非君土。其旧有之国,则因其旧爵而加封之,故春秋有唐虞之侯伯,故大传曰:君子不以无功益人之地,不以无故贬人之爵。因其原受之爵土而加以锡命,有如后世藩属,如藏卫、朝鲜、安南、缅甸、车臣、土谢图汗之属土司之比例矣。其新封之国,则大司空命其属官及匠人之属为之度地以制邑,量地以居民,是之谓建邦启宇,如此自然与王朝相联,是谓联邦制度。而且画分内五服外四服,朝觐远近之期,箸(著——引者注)为定制。近圻者每岁一见,最边远者每世一见。天子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间岁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平时礼貌优隆,享赐甚厚,情义接洽,此之谓邦交。则春官大宗伯及大行人主其官,联接待交际之政,其列邦之讼狱,则大司寇分遣其属,为之巡审,其有所诛赏,则大司马掌九伐之法,等次其罪状轻重,率王师莅境,所过之国,大国以师从,小国以旅从,至其国,宣天子命,行其赏罚,是以怀德畏威,无敢携贰,此乃真正联邦。惟德意志帝国时联邦仿佛似之,特其军国民主义则大谬相远,未脱部落之余习。其合众民主国之北美联邦、瑞士联邦,则其开国之始,形实均迥不相同。[34]17-18
宋育仁在一个中央—四裔的复古图景中,把传统儒家想像的藩属朝贡体系解释成真正的联邦体制,曾经“吐蕃”、“回鹘”、“契丹”威胁下“外向”的封建设计,在民国的政治现实下,让位于“内向”的“藏卫”、“朝鲜”、“安南”之属。中央和属国的关系可以理解成“联邦”,通过国家大礼的交际,达到“大国以师从,小国以旅从”的效果,才是符合春秋大义的“有礼之联邦”。
宋育仁强调的是一种“藩镇(割据)—联邦—封建”序列。宋育仁十分自如地将“联邦”这样的新式概念转化进他的政治图景中,依旧是其“复古即维新”论的一贯思路。联邦固然是西方学理,但因西方保留三代遗意,所以优于割据,从而又突出了封建的可行。这一过程中,民国知识分子看重的“联邦”中的中央—地方内涵,却被宋育仁有意舍弃了。二者调用了同样的政治词汇,其指向却是南辕北辙。
三 观于乡而知王道
自清末到民初,由于“天下”的崩溃,宋育仁的封建论呈现由外向内的收缩,从邦国关系降到“地方”,亦即“家”和“乡”的层面。宋育仁在民国时期的言论,一方面保持对民国制度的批判,一方面尝试从“家”“乡”的基础开始重塑这个实已不复存在的“天下”。
首先,是宋育仁对《孝经》的重视。在宋育仁的理解中,《孝经》提供了“家—国—天下”的循序渐进的上下结构,所云“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是“组织家庭国家,互为其根之鐍键关要”,所以才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之谓,由此可以得出:“有身则有家,庶人之分,及家而止,天子以至于士之分,则自家而始。”⑨更为重要的是,“家”和“国”呈现出的是一种制度层面的同构性。《孝经》诸章分别申明天子之于天下,诸侯之于国,卿大夫之于邑,士之于家,孝道自下而上推衍,均起例于家,所以说:“孝治之道,先治其家,而及于国。有国者以化行于国为限量;有天下者以化行于百姓,光于四海为限量;有家者以孝传于家,表率士民,奉天子之孝治,施于四国为限量。”⑩家国为一体,意味着父—子与君—臣之间不仅仅是简单的类比对应关系,二者是天下之道在不同范围内的同一表现。宋育仁举例说:
成立家庭,列举等位,名称有高、曾、祖、王父、王母、严君、世父、叔父、诸母、君舅、君姑、少姑、诸姑、兄公、女公、冢子、长罤、伯姊、介弟、女君、诸娣、蒙妇、介妇、庶弟、末妹、姒妇、娣妇、犹子、从子、幼子、童孙。家庭即备具君臣上下,实以名义为主,非为男统血统而设。治家治国,是同一法式,国家固由家庭起例,换言治家庭又以治天下国家为比例。
父母舅姑冠以“王父”“王母”“君舅”“君姑”的称谓,都是表明家庭与国家的比例关系。妻道即是臣道,家庭之道即是国家君臣之道,所以治家与治国才是同一法式,“经纬人伦,组织细密,丝丝入扣,鍼孔相符”。
自清末以降,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学说藉梁启超的宣传鼓吹流行中国。在梁氏译述的《国家论》中,伯伦知理提出“有机体”的假说,认为国家是“有生气之组织体”,正如聚集血肉尚不可称人类,国家亦“非徒聚民人之谓”,“非徒有制度府库之谓”,故称之为“有机体”;更直接以人体相比拟,“民人之意志,即国家之精神,宪法为其体,官府议院为其四肢五官,以成以活动体之国家也”[35]8-9。宋育仁别出心裁地将伯伦知理的“有机体”之说联系到“国体”概念上,认为:“国家为有机体,故名为国体。国体各有性质。中国国体,由家庭进为宗族,由家庭宗族演为乡党国家,故其国体,即是家庭性质。其所涵之分体,若君、若大臣、封疆大吏即是家长、族长、房长性质,小臣、百司、执事、士民即是弟男子侄性质。”[36]9宋育仁的解释显然不是伯伦知理的原意,但恰是宋从自身家国同一法式的理解中衍生出的新意。中国国家性质是由“家”“国”一体决定的,这是和西方制度绝对不同之处。外国是所谓契约国家,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由么匿(即个人)进于图腾(即部落社会),由图腾演为国家,本无家庭”[36]10。宋育仁认为,西方的“小家庭”并非真正家庭,“乃一夫一妇同居,受制于法治国家,应尽其扶养未成人儿女之义务,在尽扶养义务时期,应享有管束儿女之亲权,及子女成人及岁,即亲权丧失,是为契约结合之铁证,不容异言”[36]12。民国也同西方一样,国家乃以自然人为单位组成契约集合,“为市场公司之比,非一家一身之比,与圣人至教通国身之理,绝不相谋”[37]14。
正是因为这样的根本差异,西方社会在契约制度之下只有主仆,并无宗族关系,所以西人不理解中国宗族与家国观念,一见中国君君臣臣的言论,就妄加诋毁作“奴隶性质”[38]47。而民国学界嚼舌西方,抨击中国的“家天下”,更是不明学理的“浅见寡闻”,因为“家天下者,自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元士,凡命为爵者皆有家”[39]2,把“家天下”等同于“私天下”而大加批判,“言社会主义,言国会主义,言民政主义,言民族主义,口沫华盛顿,怀倾拿破仑,迷信于平权,归咎于专制,不惮为破坏,必欲易为民主而始快”,谬称“天下为公”,却不知所谓“家天下”之说,正是三代“天子世及,诸侯世封,大夫世官,士世采,庶人世业,能以天下为一家”的真正“公天下”,秦政以后,惟皇帝一人世及,而民田自相买卖,“天子且未尝有土”,可称作世世宰制天下,却不能称“家天下”。所以,圣人以家天下为立国根本,“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家天下者,自天子以至庶人,合为一大家,而各有其分数,分其容积,各有一家,即法天之万物一太极,物物一太极也”,尧舜能“使人各有其家,乃能以天下为一家,绝非徒袭禅让之外容,始谓天下为公也”[40]82。
其次,是对恢复地方秩序的热情。近代中国新文化人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批判声势颇大,这应当是宋育仁亟亟说明中国“家”“国”“公”“私”的直接原因。而四川自清代以来就成为一移民社会,四川地区的宗族象征难以同江南等地相比,这使得蜀地的旧派读书人对宗族形态不乏向往。在清末,《渝报》主笔潘清荫就对江南能保存义田义庄遗泽感慨万分,称:“宋范希文设施弥溥创置义田、义庄,子尧夫辈世修其法,迄于国初七百余岁,吴县子孙尚被贻泽,近世荐绅之厚伦者且希风仿效。”与宋育仁等人一同创设蜀学会的张慎仪也说:“古之宗法,即治法之最善者也。故宗法立而一族无无告之人,一族无不学之人。扩而充之,以及于乡邑,以及于州郡,以及于行省,以及于天下。于是由据乱而升平,由升平而太平,犹反手也。”宗法本寓于井田制中,现今“井田废而宗法亡,民族之鳏寡孤独废弃无以赡,婚嫁丧葬无以赠,病无以扶持,学无以勉励”,政府虽欲教民养民,“竭蹶黽皇,挂一漏万,恒苦不周”,当他听闻有人试图在乡里建设义庄义田,便赞叹:“有同志接踵而起,就义庄以维宗法,树风声而励渊尚阝,则世俗之进化也未可量矣。”
对宋育仁而言,宗族需要一步步地推衍出来,起点是“身”、“家”,而能够制度化的则在“乡”。宋育仁选择的方法是恢复古礼。宋育仁对礼的重视,应当是受王闿运的影响[41]159-170。宋育仁主持蜀学会时,就要求:“必具衣冠礼先圣,然后易服集讲”,“以三公祠为聚讲所,每月两次,朔日牌标讲目,学友各将蓄疑新义摘录送会所传阅,列入讲册,望日集讲,认题论撰者,晦日收卷”[5]2。“乡”和“地方”有着微妙的差异,乡治也不能简单等同于地方自治。乡治就是乡礼治乡,而乡礼的乡饮酒、乡射、乡相见之礼,正是“合乡为一家,各还其人身分本位”,乡饮乡射之时,“就在此时间宣讲法律,提出切近条文,说明理由,即是《周官》行政纲要所举地方自治政纲,属民读法,以正齿位”[42]8-9。乡礼重在明贵贵贤贤,贵者即是位,贤者可喻以道,贤者当贵位,即是寓道于位,“古之仕者,由选秀书升而进,则为大夫士者必国之贤也。出而长其民者,归而教其乡,其义一以贯之。所谓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宋育仁总结道:“其立根起点,特以敬养庶人之老,随地随时,表示身教言教。其最高之度,在天子养三老五更于大学,诸侯养耆老于庠。习射尚功,习乡尚齿,其低度最要之切点,在乡饮酒宾兴贤能,党正岁行乡饮以正齿位。所以明贵贵尊贤,其义一也。不但明其贵即是贤,贤即当贵,而且示以耆老即是乡党之贤,尚齿即是长长老老,长长即是贵贵尊贤。故乡饮有宾介三宾上座,示以尊贤。有遵者僎特坐,示以贵贵;有乡先生六十者坐,示以长长。故记曰:老老为其近于亲也,贵贵为其近于君也,长长为其近于兄也。”所以说,“乡”的自治,其“正式之纲领,重在贤贤”,“一篇乡饮乡射,便是提高人格,公开选举八个大字铁板注脚”,追根溯源,“将贤贤、贵贵、老老、长长,合一炉而冶之,正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此即提高人民程度,公开选举之模范也”[42]9-10。
宋育仁虽以“封建”为经国大谟,但民国毕竟已经破坏了传统的君主制度,所以真正能够直接入手操作的,就是重建礼乐节目。宋育仁提出:“礼者由博爱、德义、敬让组织而成,以为朝聘、燕飨、冠婚、丧祭、射饮、相见各篇之节文。因时际会,就事演习,而以乐纬之于其间,使人优游灌输,浸渍餍饫,而乐于行礼,又以使人情之所乐,皆归纳于礼,而引之于正。是以民用是之,故而有中和之德,睦姻任恤之行,皆以孝弟为纲领,而演成礼文,以为之节目。”中国孝悌性质,正是要通过礼演化为风俗,“全用节文以导民性,引而致之于孝敬之极点,以生其永久之和睦”,这就是“王化之成,内圣外王之道,无往非提起教孝、教弟之精神,寓之于五礼六礼节目之中”。
封建既然被视作“有礼之联邦”,复“礼”在民国时代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乡愁,更能映射宋育仁这样的旧派读书人的政治认同。宋育仁在撰写《考订四礼》时就袒露心志,称其“暮年遭妻之丧,坚意率家人由礼,以成守先待后之志”,由于民国已无服制等级之别,“士夫亦降与庶民同服”,宋育仁不得不参考大清通礼,深衣练冠,“志欲顺时变以复古先圣王之教”。与此相应的现象是,章太炎坚持以深衣入殓,以此表达反对满洲、光复汉族的愿景[43]94-107。宋育仁行冠礼服制,则恰是清遗民保存王道之象征。宋、章二人在政治认同上多有反对,但其“遗民”心态却颇有合辙之处,“乡礼”与现实相对应的政治内涵由此可见。
四 结语
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在比较“古典”和“现代”时指出,我们如今掌握的道德语言只是传统遗留的“概念构架的诸片断”,“所做和所说的一切都不再符合某些具有稳固性与融贯性的准则,而且那些使他们的所作所为具有意义所必要的语境亦已丧失,甚或无可挽回了”,因此,即使人们还在继续使用这些“关键性的语汇”,但“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们都已极大地(如果不是完全地)丧失了我们对于道德的把握力”[44]3。“封建”作为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本身就依赖于一个完整的话语体系,宋育仁能够在清末利用“封建”来回应西方列强带来的瓜分压力,这一积极的“外向”表现亦源于其天下尚存的自信。而民国代清的一个根本性断裂,就是以天子为中心的“天下”无论在象征意义还是现实制度上都不复存在。宋育仁无疑意识到了这一内在的颠覆,所以其封建论开始逐渐“向内”转变,无论是对民国制度的批评,抑或走向乡礼的复古,都是这种转变的体现。宋育仁想要做的,就是试图重新塑造“封建”背后本已崩溃的“天下”。近代中国的地方主义,无法放在一个“天下”的传统语境下去理解,而是依附于民族—国家的现代诉求。宋育仁在“地方”的复古,与现代知识分子号召的“地方自治”,尽管表面上双方均着力于同一场域,但其各自的内涵是根本不一致的。尽管不必断然否认宋育仁的“乡贤”身份,但更需强调的则是他一以贯之的“天下”政治诉求。如果忽视了这一基础,我们就难以真正理解宋育仁政治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注释:
①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认为,“封建”概念的一个基本范畴就是制度论。在制度论的话语下,明末清初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才能够将封建论作为对皇帝专制权力的一种限制,也正是“封建”的制度性批判作用,清代政府一直对其采取压制手段,封建论随之转向更为间接的地方自治论。见:沟口雄三《作为方法论的中国》,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84-116页。
②汪晖就指出,清代中后期,刘逢禄、龚自珍等公羊学家将封建论重新加以阐释,与《春秋》“大一统”的制度设计联系起来。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551-579页。
③文化层面的研究,可参见:周明之《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清遗老的精神世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罗惠缙《民初“文化遗民”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林志宏的研究则已经开始将“政治”和“文化”相结合,见: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④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宋育仁在清末维新运动中的活动,将其定位为早期维新派,而对其民国后的政治思想则关注不足,甚至过于简单地将宋育仁的后期思想视作“倒退”,未能注意到其一贯依托的思想语境。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可见:徐溥《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宋育仁》,《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5期;王尔敏《宋育仁之旅英探索新知及其富强建策》,《近代经世小儒》,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9-264页;董凌峰《宋育仁维新思想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年。
⑤宋育仁《宋评明夷待访录》,民国四川存古书局刊本,四川大学图书馆藏,第20-21页。
⑦参见:《四川京官宋育仁呈邮部请国有铁路仍接受民股文》、《富顺自流镇保路同志会致成都总会宋育仁僭称代表呈请附股请登报除其乡籍函》,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747-769页。
⑧关于地方联治的统一诉求问题,可以参看:王东杰《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46-64页。
[1]罗志田.地方的近代史:“郡县空虚”时代的礼下庶人与乡里社会[J].近代史研究,2015,(5):6-27.
[2]王东杰.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3]梅际郇.说渝报[J].渝报,1897,(1).
[4]宋育仁.学报序例[J].渝报,1897,(1).
[5]蜀学会章程[J].蜀学报,1898,(1).
[6]王东杰.地方认同与学术自觉:清末民国的“蜀学论”[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34-50.
[7]吴之英.蜀学会报初开述义[J].蜀学报,1898,(1).
[8]宋育仁.复古即维新论[J].渝报,1897,(1).
[9]五月望日学会讲义[J].蜀学报,1898,(8).
[10]徐昱.封建说[J].蜀学报,1898,(6).
[11]邓镕.封列国以保中国论(附问琴阁书后)[J].蜀学报,1898,(5).
[12]杜士珍.封建兴国篇[J].新世界学报,1902,(8).
[13]俞樾.封建郡县说[G]//郑振铎.晚清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4]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G]//杨家骆.戊戌变法文献汇编:第二册.台北:鼎文书局,1973.
[15]章太炎.藩镇论[G]//汤志均.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
[16]章太炎.訄书初刻本·分镇第三十一[G]//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7]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方镇[G]//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18]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
[19]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G]//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0]张之洞.致成都宋芸子(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亥刻发)[G]//苑书义,等.张之洞全集:第9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21]许丽梅.民国时期四川“五老七贤”述略[D].成都:四川大学,2003.
[22]省宪筹备处征求意见电(一)[G]//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军阀史料:第三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3]复庵(宋育仁).致四川制宪处概略意见书[J].国学月刊,1923,(7).
[24]黄天石.联省自治之商榷[J].孟晋杂志,1924,1(1).
[25]梦蝶.联省自治乎?割省自治乎?各省自乱乎?惟国民自择[J].丙寅杂志,1926,(2).
[26]黄葆荷.联省自治问题[J].政治旬刊,1930,(5).
[27]宋育仁.释文化:论中国古今一教三教文化源流[J].国学月刊,1923,(20).
[28]宋芸子(育仁).四川地方自治筹备会宣言[J].国学月刊,1923,(11).
[29]道复(宋育仁).箴旧砭时续前[J].国学月刊,1923,(6).
[30]道复(宋育仁).致总统意见质问书[J].国学月刊,1922,(3).
[31]邹德高.联省自治之评议[J].重庆中校旅外同学总会会报,1922,(4).
[32]朱希祖.联省自治商榷书[N].北京大学日刊(附张),1922-07-29(1).
[33]宋育仁.春秋大义上篇[J].国学月刊,1924,(23).
[34]宋育仁.政治学[J].国学月刊,1924,(24).
[35]伯伦知理.国家论[G]//新民社.清议报全编(三).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36]宋芸子(育仁).论国家性质[J].国学月刊,1923,(7).
[37]问琴(宋育仁).存伦篇补义平议[J].国学月刊,1923,(14).
[38]宋育仁.国教宣言致国民会议[J].国学月刊,1923,(22).
[39]宋育仁.礼运大同小康碻解[J].国学月刊,1923,(7).
[40]问琴阁(宋育仁).谈丛括论[J].国学月刊,1924,(23).
[41]程克雅.晚清四川经学家的三礼学研究——以宋育仁、吴之英、张慎仪为中心[C]//舒大刚.儒藏论坛:第二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42]宋育仁.礼乐萌芽·行乡饮乡射礼演说[J].国学月刊,1924,(24).
[43]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44]麦金太尔.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M].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凌兴珍]
“Local” and “Tianxia” in SONG Yu-ren’s Feudalism
CHEN Y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Chinese scholars’ political concern is about the world, i.e. Tianxia, rather than local place. At the turn of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SONG Yu-ren adhered to his feudal theory, which was a concrete presentation of Tianxia thinking. The feudalism of SONG Yu-ren and his students had a clear outward nature to resist the impact of foreign aggression when the Reform movement happened. Bu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SONG Yu-ren’s Tianxia politics had lost its fundamental system. Thus he had to turn to criticize the Republic political system with the reversed feudal theory, and tried to rebuild the world blueprint by advocating the rural ceremony.
SONG Yu-ren; political thought; feudalism; local; Tianxia
2016-11-29
陈阳(1987—),男,四川合江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的思想与文化。
D693
A
1000-5315(2017)04-015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