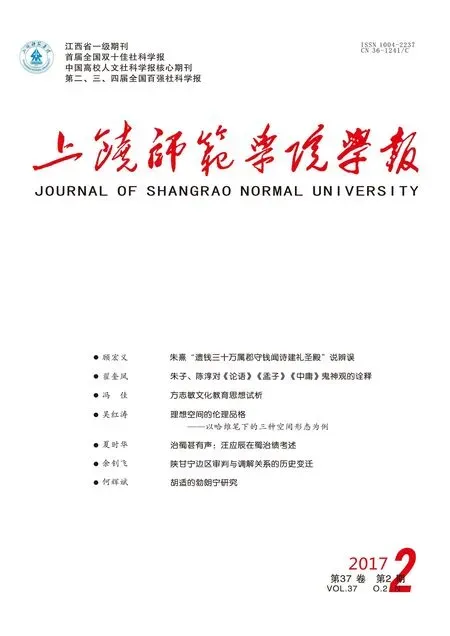陕甘宁边区审判与调解关系的历史变迁
余 钊 飞
(杭州师范大学 沈钧儒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陕甘宁边区审判与调解关系的历史变迁
余 钊 飞
(杭州师范大学 沈钧儒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司法是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的一段重要历史。与清末变法修律,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思路和实践有所差异的是,陕甘宁边区对司法制度有着其独特的理解和实践,并积极致力于探索符合自身治理思路的新型司法模式。在这过程中,调解制度成为其司法改造的重要载体。历经制度与实践的充分磨合,陕甘宁边区政权逐渐摸索出一套审判和调解高度结合的人民司法模式。
陕甘宁边区;调解;审判;司法体制
自清末变法修律以来,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法典和司法体制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司法制度。特别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基本完成了系统的法典编撰任务,形成了“六法全书”体系。另外司法体制也逐渐完成了转型,各地相继建立各级地方法院,成为受理各种案件的专职司法机关,在部分条件不是很成熟的地区也建立了承审员制度。在中国司法近代化的大背景下,作为中国经济社会最为落后的西北边缘地区也不可避免地汇入到此股司法近代化的洪流之中。尤其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并开启了全面探索新民主主义司法道路的进程,对中国司法近代化历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陕甘宁边区审判与调解关系的历史变迁进行梳理与研究。
一、国民党主导的“旧法”对抗日根据地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早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对司法工作进行了初步探索,但总体而言,由于当时较为严峻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不论是中央革命根据地还是其他根据地,都难以建立系统和稳定的司法制度。特别是在1936年以前,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围剿”,使得苏区时期的司法制度一直难以得到全面的完善和发展。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和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步伐的加快,中国共产党对边区司法问题给予了进一步的关注,但是边区司法体制和司法工作的方向还是处于摸索阶段。
(一)“旧法”体制对陕甘宁边区以外之抗日根据地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下司法体制和司法工作深受国民党司法体制“正统”思想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影响。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之下,诸多根据地政权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存在一定偏差,这导致其司法工作中对“六法全书”的依赖比较严重,其司法工作应当说与国民党主导的司法体制差异不大。以山东革命根据地为例,1941年4月山东临时参议会常驻委员会通过的《改进司法工作纲要》即明文规定,“各级司法机关办理诉讼,以中央及地方政府颁布之法令与条例为根据”,同时还规定,“各级司法机关对诉讼案件应遵守国民政府所颁民刑各法及民刑诉讼各法办理”,该纲要决定要根据国民政府颁行之法院组织法成立高等法院、地方法院等司法组织机构[1]317。可见,国民党主导的司法体制依然拥有较大影响力,反映出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司法工作上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也使得1941年山东根据地通过的各级法院组织条例,仍旧保持独立的组织系统。由于这一观念的长期存在,导致了各地司法部门的独立思想和特殊化倾向比较严重。对此,山东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总结与反省,他们认识到,“由于政治上的不敏锐和不能正确的掌握政治形势的发展、各种工作进行的深度,故不能及时的综合研究各地的具体情况,正确的转变政策,明确决定的方向,建立新民主主义司法观念和方法,明确宣布、传达、执行,以转变思想、改造工作”[1]325。所以直到1943年,在具体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特别指出处理案件须依据根据地的政策法令,不利于抗战的条文不得拘泥引用,但同时又依旧同意审判过程中继续引用旧法,这表明根据地的司法工作存在着以国民党主导的司法体制与法律体系为主要参照的倾向。尽管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合法思想”和“正统思想”浓厚。这种“合法思想”合的就是“六法全书”,“正统思想”就是“以南京国民政府确立的司法体制为正统”[1]324。由于这些观念的存在,造成了根据地司法指导思想的错误倾向,导致了司法人员不注意研究根据地政府和党的政策、法令、指示、决定,以“六法全书”为标准,并推行司法技术化、特殊化,脱离群众,而使司法工作陷于孤立。这样的司法现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施政理念存在着重大差距。
(二)“旧法”体制对陕甘宁边区的影响
实际上,上述现象在陕甘宁边区也是存在的。南京国民政府在1932年颁布了《中华民国法院组织法》,并在1935年7月1日开始实施。法院组织法规定了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三级司法组织的结构,同时对法官、检察官、书记官、司法辅助人员的职责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并对于司法语言和审判流程也做了相当细致的规定。1937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基本上参照了国民政府的法院组织法,其中的第一条就指出,条例是根据国民政府公布的法院组织法制定的[2]61-65。边区高等法院各分庭、中心县地方法院及各县司法处的架构也基本上与国民政府的法院组织类似。所以总体而言,边区的司法系统在形式上是参照国民政府的法院组织体系的。“旧法”对于陕甘宁边区最大的影响就是司法的地位和法律依据的问题。司法地位主要是关于“司法独立”的争论,法律依据主要是如何对待“六法全书”的问题。在“司法独立”的问题上,当时边区有干部认为:地方法院审判案件,不受高等法院管辖,地方政府也不得干涉,法院应当与政府分开;法院的干部地方政府不得任意调派;法院的经费独立同时不参加政府的会议①当时任高等法院秘书的朱婴同志就提出了该观点,这些观点与当时国民政府主导的司法体制是基本相同的,这一方面与其出身于朝阳大学法律系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于当时边区的特殊政治形势判断不明,毕竟边区不是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区。参见:汪世荣《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研究》(未刊稿),第229页。。这些观点实际上深受国民政府司法体制影响,不符合当时边区党和政府的政策取向。上述的一些观点尽管没有全面影响边区的司法体制,但还是融入了部分司法干部的观念之中,造成了当时边区司法理念上的一些混乱。所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工作依然受到国民党主导的法律体系和司法体制的严重影响。为此,陕甘宁边区领导人,特别是谢觉哉,高度关注边区初期司法工作中的缺陷尤其是司法工作与人民之间的隔阂问题,并开始思考新的出路和办法。
这些缺陷,归根结底,凸显了当时的司法工作与党的政治理念、人民群众的实际期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突出表明司法工作的群众观念极其薄弱。上述诸多司法工作缺陷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各级政府对于司法工作不够重视,另一方面也与当时对于司法队伍建设工作不力有关,司法工作人员在思想上尚未统一。具体而言,就是司法工作思路上存在混乱现象,方向上极其不明确。各个新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最初建立司法制度时,基本的出发点还是停留在“定纷止争”的水平上,其直接目的只是为了给民众解决纠纷,确立根据地政权的威信,尚未形成明确的司法改革理念和改革方向。
二、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司法理念的探索与实践
如何确立边区司法工作的新方向一直是困惑边区政府领导人的重大现实难题。边区司法工作朝着新民主主义司法的方向发展,这是前所未有的探索,相关经验极其匮乏,如何探索新的司法方向是一个渐进的、困难的历史过程。
(一)边区领导人对旧司法的严厉谴责和追求人民司法的愿景
实际上,早期边区政府的领导人很早就提出司法便民的认识,只是尚未明确认识到新民主主义司法的前进方向和主要载体。如林伯渠同志在193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曾经指出,边区司法工作要保证抗日民主制度及边区人民的合法利益,并强调为了人民的方便,处理案件的形式可以多样[3]。遗憾的是,林伯渠的此一认识过于原则化和粗略的方向性使其难以成为有效的政策。正因为如此,《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的“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的提法也稍显粗略。所以直到1942年左右,由于边区的司法工作受到“旧法”体制影响太大进而与人民隔阂扩大的趋势增加的时候,当时的边区政府领导人才开始认识到对于司法工作必须改进。
在整个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建设进程中,著名的“中共五老”之一谢觉哉同志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谢觉哉长期担任党的司法工作领导人,同时担任当时边区的参议会副议长,对当时边区的司法工作有着极为清晰的认知和判断。在1942年左右,谢觉哉在《边区参议会常驻会报告》中对边区司法工作进行了深入总结与剖析,他说,“对于司法工作,我们有很多缺点,没有足够的司法干部,也没有合适的司法制度,以致人民对司法有诸多的不满”,与此同时,谢老还指出,“对司法工作,我们平常注意很少,现在已不可再延了”[2]197。关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司法,谢觉哉认为它必须同群众相结合,而成为群众的东西。这是边区领导人中关于新民主主义司法的最早也是较为明确的认识。在这样的出发点之下,谢觉哉对当时陕甘宁边区司法工作的方向作出了明确的判断,那就是“边区的司法干部有旧的教条主义——国内外法律专门学校毕业的;也有新的教条主义——内战时的司法经验”[4]。其中旧教条主义的代表是李木庵等人,他们囿于法律学校所学的内容和国民政府的法律和司法体制,未能与阶级立场和群众路线相结合,不切合实际,不能实际解决问题。而新教条主义的代表是雷经天等人,他们囿于苏维埃时期的司法理念和制度传统、内战时的司法经验,虽有政治立场,但不懂得拿过去的经验到实际当中去取得新的经验。正是总结多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之后,谢觉哉同志提出和确定了新民主主义司法必须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总思路。
类似的看法在边区政府其他领导人当中也是存在的。如在1944年11月5日的《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报告中,习仲勋同志就明确指出司法工作必须坚决地站在群众一边。习仲勋认为,“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权的一项重要建设,和其他行政工作一样,是替老百姓服务的。这样,就要一心一意老老实实把屁股放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坐得端端的”。习仲勋批评道:“旧司法机关的屁股就不是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的,是坐在少数统治者的怀里”。习仲勋在严厉地谴责了旧司法机关的恶劣作风的基础上,认为司法工作的指导方针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保护人民的正当权益,他还将人民是否满意作为衡量司法工作的标准。在习仲勋看来,“越是使老百姓邻里和睦、守望相助,少打官司,不花钱,不误工,安心生产,这个司法工作就算做得好”。习仲勋还强调,司法工作人员必须深入乡村,走出“衙门”,只有这样才能把司法政策贯彻得好,才能使司法工作同人民取得密切联系,在他看来,如果不发挥人民力量,孤独地依靠司法干部去处理那就会拖延时间[5]。这些观点旗帜鲜明地要求边区的司法工作必须发挥能动性,融入人民群众之中,解决人民的实际困难。
从谢觉哉和习仲勋两位边区高层干部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党的高层干部心目中,边区所追求的司法制度应当是人民政权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应当是充分尊重群众意见、敢于调查研究为民解忧的机关,而不是充斥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司法体制,更不是原有的旧的司法体制。可见,两位领导人虽然尚未明确说明新的司法制度究竟是何种模样,但都在追求一种能使人民满意的新型司法体制,这种司法体制实际上就是新民主主义司法体制。
(二)破除旧司法的缺陷与全面树立司法的群众路线
当然,谢觉哉和习仲勋有关司法的群众路线思想的提出应该看做是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中群众路线中边区司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可以说,边区司法工作的重心就是如何在人民群众中建立司法基础。从边区司法实践来看,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边区司法工作的群众路线也确实逐步走向深入。
尽管当时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国民党主导的司法体制和法律体系影响很大,但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也一直在不断探索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制度和工作方式,如何将司法工作与群众路线紧密结合起来无疑是其中的重点方向。而随着边区司法工作群众路线的逐步确立,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工作重点开始转向保障工农群众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至此,抗日民主根据地关于新民主主义司法工作的探索终于找到明确的方向,那就是司法工作必须全面贯彻群众路线。
实际上,早至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落实司法群众路线的进度加快,关于调解的政策法规逐渐增加,各地的调解组织纷纷建立,调解工作的群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审判工作中调解精神开始逐渐贯彻。《陕甘宁边区民刑事调解条例》正式颁发,标志着调解工作的法制化和规范工作得到全面提升。边区政府发布的《关于普及调解的指示》,边区高等法院发布的《实行调解办法、改进司法作风、减少人民讼累的指示》,标志着调解运动在边区的兴起。调解工作有助于边区政权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观念,有利于政府熟悉群众的情绪,了解群众的要求,同时也成为边区司法工作走群众路线的重要载体。
三、陕甘宁边区调解与审判关系的变化
陕甘宁边区的司法体制建设始于1937年7月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的成立,此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又于1943年3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分庭组织条例草案》与《陕甘宁边区县司法处组织条例草案》,与此同时,边区的各级司法机构也开始逐渐建成,边区的审判机关由此基本形成。这些司法机关在解决边区纠纷、稳定边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边区高等法院在其近12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保障政治稳定、解决社会纠纷、推动根据地法制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总体而言,陕甘宁边区司法机关的民事审判主要是围绕土地、债务、房屋、继承、婚姻家庭纠纷为中心的。在具体的审判过程中,各级司法机关一改以前的坐堂审案方式,开始按照纠问式的审理模式处理相关的民事和刑事案件。但是这种被动式的审判工作模式造成了司法工作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严重,既与边区党和政府为民服务的精神相背离,也导致了群众的不满和反感。1943年以后边区司法工作开始主动地融入人民群众,其中的主要举措有两个:一是走出法庭进行巡回审判,其典型为马锡五审判方式;二是全面推进调解工作,从而逐渐形成了注意实地调查研究、着重调解的司法工作新模式,开始真正走向了人民司法和全民调解。在这个格局之中边区的审判和调解的关系随着总体司法政策方向的变化也发生了一些新的转变。审判与调解作为边区最为重要的纠纷处理方式,两者之间既存在一定的差别,但也呈现了难以切割的相连关系,甚至在一定的意义上讲,出现了融合的趋向。
陕甘宁边区的审判与调解工作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出发点上的不同,这种原则的不同主要是在民事纠纷的处理上。如审判工作主要原则是:私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少数人利益服从多数人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富裕者应当提携贫困者、知识分子应当帮助文盲无知。也就是说,边区的审判工作的出发点是“公平正义,扶助弱者”,调解工作出发点则是“定纷止争、促进团结”,即消除民间纠纷,减少讼累,促进团结,维护生产。另外,审判毕竟是一项严肃的司法行为,包含着国家公权力的运行;而调解特别是民间调解更多的是诉诸当事人之间的妥协与谅解。所以用当时的边区的话讲就是:审判在法庭、调解在私下;审判带强制、调解本自愿;审判据事论法、调解含有妥协;刑事一般不许调解、民事一般提倡调解。在审判与调解的关系上,由于历史环境以及政策取向的变化,存在着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初期的“重审判轻调解”
自1937年边区的各级司法机关开始逐渐建立到1943年边区调解运动形成以前的这段时间,边区纠纷处理的主要机关是各级司法机关。陕甘宁边区各级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种类主要是土地纠纷、债务纠纷、继承纠纷、房屋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等。如全边区在1938年就审理民事案件357件,1942年则审理830件;另外边区各县在1938—1943年共审理土地纠纷达1007件[6]115。这些民事纠纷的处理一方面显示了边区的民间纠纷在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边区的司法机关在民事纠纷的处理能力上的提升。当时的法官(即推事)人数非常之少,如当时的边区高等法院到1942年只有庭长1人,推事2人,即案件最多的延安市法院在1941年也只有院长兼庭长1人,推事1人①汪世荣:《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研究》(未刊稿),第46页。。也就是说在案件的审理方面,当时的司法机构已经尽其所能了。但是,其他的纠纷化解机制始终没有得到建立和完善。由于当时国家处于战争状态,陕甘宁边区最为核心的任务是全民抗战,对于司法工作以及纠纷的处理工作,实际上当时的党的高层领导和人民群众尚未有十分深切的感受和认识,而对于调解工作,边区政府也没有足够精力来关心及推动[6]116。这样的状态一直延续到1943年。
(二)中期的“调解为主、审判为辅”
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高等法院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司法调解工作的法令与指示,边区的调解工作开始上升到相当的高度。1943年6月11 日,边区政府颁发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民刑事件调解条例》,将调解制度以法令的形式确定下来。条例规定的调解范围是:“凡民事一切纠纷均应厉行调解,以及轻微的刑事案件……均可试行调解。”调解原则是“双方自愿,不许强迫”,即“须得双方当事人之同意”,同时,调解须遵守政府政策法令和“以不违背善良风俗及涉及迷信者为限”以致“调解纷争,减少诉讼”,条例规定调解方式有民间调解、群众团体调解、政府调解、司法调解四种[7]。这就意味着调解已经成为司法干部最为重要的实际工作任务,且带有明显的强制性。这个决定将调解多少作为干部考核的标准,使得重复调解和强制调解的现象不断产生。这意味着调解工作在成为运动的同时也暴露出了急躁冒进的特点,出现了一些负面效果。1944年6月6日,谢觉哉同志在《边区政府关于普及调解、总结判例、清理监所的指示信》中进一步提出了“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的方针[8]。通过边区政府和高等法院的一系列法令,各地的司法人员开始全面检讨过去的司法工作经验和教训,开始全面执行调解政策。司法机关不仅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推行司法调解,也积极指导和帮助全边区的调解工作。调解与审判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模糊。从一些土地纠纷案件中我们可以发现,内中既有地主、佃户、租户间的复杂关系,也有贫者在弱势与强势间的迅速转化;既有法理习惯作为调解的依据,也有乡情伦理参与其中;既有政府的多层级调解,也有司法人员主动主持调解,更有依靠群众发动调解。在此,我们很难精确地区别司法调解、政府调解、民间调解,只能说在特殊的历史时代,这些调解类型的相互转化是非常模糊的。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当时司法干部的确开始深入实际、主动调解,表明了“调解为主、审判为辅”在基层已经开始贯彻。
在边区的司法工作和调解工作上,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就是马锡五审判方式。马锡五审判方式是马锡五同志在担任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专员并兼任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庭庭长期间,发挥司法工作的主动性,深入乡村进行实地调查,根据边区法律和当地习惯,将司法审判与调解工作高度结合在一起的司法工作方式。在当时边区的总体司法路线已经明确走群众路线方向的时候,马锡五处理案件的经验得到了当时边区高层的大力支持。可以说,马锡五审判方式基本上是全面贯彻了司法的群众路线,同时又十分重视调解的运用。当然,马锡五审判方式不是单纯的调解,它一改法庭内审理案件的做法,而采取深入农村、就地调查、就地审判的司法工作方式。马锡五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既使用调解,也使用审判。此处的调解既有司法人员的调解,更有发动群众进行的调解。马锡五审判方式在边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成为当时边区司法工作的标志,也成为新民主主义司法工作的一个里程碑,时至今日依旧影响巨大。所以总体而言,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产生与当时的调解运动是存在密切联系的,是审判与调节紧密相连的体现,它的产生和推广在一定意义上更加强化了“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的方针。
(三)后期“调解与审判相结合”
1943年调解运动的兴起和1944年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推广无疑使得边区的调解工作达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随之而来的相关负面作用也开始显示出来。到了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边区的部分司法工作干部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特别是1945年担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王子宜对这个问题认识得更清楚。王子宜认为,“自1943年提出调解方针和马锡五审判方式以后,边区的司法工作,曾经有了一番新气象。在这个方针下,司法工作者调查研究的依靠群众的观点逐渐加强了,广大农村中,出现了不少公平正直的调解模范,和解了许多纠纷,减少了许多诉讼,但是在执行调解方针中,我们是有缺点有偏向的,特别在提出‘调解为主、审判为辅’以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偏向就更其增多了”[9]。这种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调解范围无限扩大,严重刑事案件也被调解。如农村地区将杀人案件也调解,当时庆阳的14件命案,有11件被私下调解①参见:汪世荣《陕甘宁边区审判史》(未刊稿),2009年,第98页。。第二,强迫调解的比例上升。审判人员由于考虑到调解是重要的考核任务,千方百计想办法提高调解率,结果强迫调解、软硬兼施的调解事件不断发生。第三,调解与审判关系混乱,尤其是随着“调解为主”“调解是诉讼的必经程序”等方针提出后,调解与审判关系逐渐模糊。纠纷在各个司法机关、政府、群众之间无序地来回调解,导致了层层调解和反复调解现象的产生。
有鉴于此,边区高等法院在1945年12月召开的各分区、县、市、推事、审判员联席会议上,将司法工作的方针和调解与审判的关系着重提出来讨论。会议认为,司法工作是为了“保护人民权利、保护民主政权、保护社会秩序”②参见:王子宜《边区推事审判员联席会议总结》,陕西省档案馆,卷宗号15, 案卷号70。。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的司法工作方针已经逐步形成,司法的人民性已经逐渐体现出来了。司法工作已经从“定纷止争”的层次提升到了维护国家政权和社会秩序的高度,司法工作的意识形态建设已经得到了重视。会后,边区高等法院代院长王子宜明确指出了调解与审判之间的关系,认为“审判与调解不只是形式而且有其实质上的区别,审判是法庭依法理判决,有强制性的;而调解则是第三者依据当事人的自愿,是私下了,带有妥协性”[9]。这就明确区分了审判是强制的,调解是自愿的特征。王子宜又认为“刑事案件,一般的不许调解,民事纠纷,一般的提倡调解”,强调了调解的范围必须限制。同时,王子宜为处理审判与调解的关系,还特意提出审判与调解的几点原则:“审判的原则是:一、全面调解,虚心研究,重视证据;二、保证被告人有充分辩论机会;三、迅速处理,照顾生产;四、履行陪审制度,发扬马锡五的群众观点。调解的原则是:一、双方自愿、不许强迫;二、适合民间善良习惯、照顾政策法令;三、调解不是审判的必经程序”[9]。这些原则的设计,使得调解和审判之间既紧密协作,又得到明确的区分,使得边区的干部群众对调解与审判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入和清晰的认识,有利于边区司法工作和调解工作的正常开展。
四、结语
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制度之所以能摆脱国民党司法体制的影响而发生质的变化,可以说是边区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的必然产物。首先,边区政府早期的土地改革和后来土地政策的调整,基本消除了民间社会矛盾最为激烈的土地分配纠纷,使普通民众基本上实现了财产上的平等,为边区调解制度的全面推行奠定了较为平等的经济基础。在边区政府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方面取得了卓越的进步,使边区的社会形态和社会观念发生了一些巨大的变化,使得边区社会的纠纷类型发生了多样化的趋向。其次,边区的司法调解工作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定纷止争”,而是上升到了创造新型司法制度为人民服务的政治高度,这与边区民主政治思想与政治体制的建立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最后,群众政治组织和村级组织的完善,使边区的调解工作具备在边区全面普及的组织基础。
可以说,调解与审判关系是陕甘宁边区的司法体系中一直困扰边区广大干部群众的重要问题。在早期的陕甘宁边区,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国民党主导的“旧法”体制的影响。基于此,当时边区的党和政府逐渐确立了司法的群众路线。而调解工作由于其高度贴近群众的特点,被放置到了全面落实司法群众路线的高度,作为最为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调解与审判总是相互联系、并行发展的。在陕甘宁边区,从最初的“重审判轻调解”到中期的“调解为主、审判为辅”,都经历了诸多的曲折。经过实践磨练,1945年以后,边区的调解与审判关系才得到最终明确。概括而言,边区调解工作的开展与当时探索新民主主义司法道路密切相关,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对当下中国的司法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三辑[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2]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3] 林伯渠文集编辑组.林伯渠文集[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120.
[4]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68-469.
[5] 习仲勋.习仲勋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9-11.
[6] 侯欣一.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7] 陕西省档案院,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民刑事调解条例[M]//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北京: 档案出版社,1988: 255-258.
[8] 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178.
[9] 王子宜:调解与审判[N].解放日报,1946-01-17(2) .
[责任编辑 邱忠善]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Trial-mediation Relationship in the Sh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YU Zhaofei
(Shen Jun Ru Law School,Hangzhou Norm University,Hangzhou Zhejiang 311121,China)
The judicial system of the Sh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s an important period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aw. In contrast to the thinking and practice of the Beiyang government and the Nanjing govern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Sh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had its own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also actively explored a new judicial mode in line with its own governance thinking. In this process, the mediation system became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its judicial reform. After the full running-in of the system and practice,the Sh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gradually worked out a set of people's judicial mode with the full integration of trial and mediation.
Sh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mediation;trial;judicial system
2017-04-10
余钊飞(1981-),男,浙江诸暨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法制史。E-mail:yuzhaofei1981@163.com
D926
A
1004-2237(2017)02-0043-07
10.3969/j.issn.1004-2237.2017.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