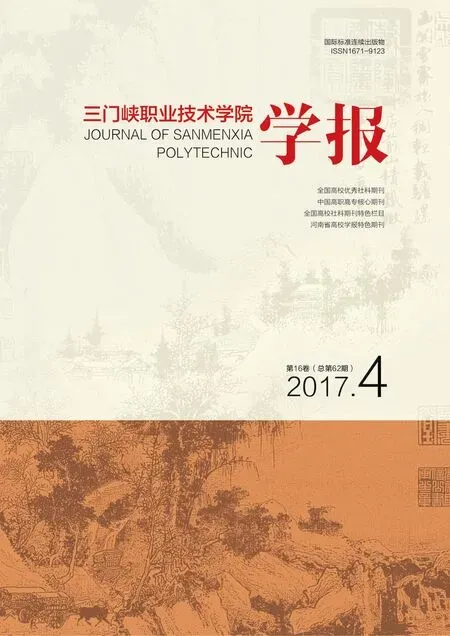论洛阳“武库”与“天下冲阨”“天下咽喉”交通形势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暨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872)
西汉洛阳居“天下之中”。①《史记》卷四《周本纪》:“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史记》卷七九《刘敬叔孙通列传》在娄敬曰:“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1]在所谓“天下”即包括帝国全境的交通格局中,曾有“天下冲阨”“天下咽喉”的军事地理与交通地理定位。体现此形势的诸多因素中,首要条件包括“武库”和“敖仓”设置。考察洛阳“武库”区域空间定位的意义,可以与东海郡武库、上郡库、姑臧库与武威库进行比较,并参考成都库的存在,理解并说明其战略位置以及洛阳因此而占据的关系全局的重要的交通地位。
一、“武库军府,甲兵所聚”
《晋书》卷二九《五行志下》:“武库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宝藏也。 ”[2]《隋书》卷二二《五行志上》:“武库者,兵器之所聚也。”[3]《宋史》卷一九七《兵志十一·器甲之制》:“天下岁课弓弩、甲胄入充武库者以千万数。”[4]据王宪《计处清军事宜》,武库还收藏军职“册籍”。①王宪《计处清军事宜》:“军之职在武库者,册籍不至于填委,故综核可精。”除了“在武库者”外,军职“册籍”还有“在有司者”“在御史者”。黄训编:《名臣经济录》卷四四《兵部·武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汉代民间社会对于“武库”作用和地位的认识,见于《焦氏易林》卷二《师之第七》:
武库军府,甲兵所聚。非里邑居,不可舍止[5]。《焦氏易林》卷十一《姤之第四十四》亦作如是。其中所谓“非里邑居,不可舍止”,《初学记》卷二四引焦赣《易林》作“非邑非里,不可以处”。[6]潘自牧《纪纂渊海》卷八《居处部·库藏》同。[7]《札迻》卷一一:“‘非里邑居,不可舍止’……翟云:一作‘非邑非里’。案:当作‘非邑居里’,此以‘府’与‘聚’为韵,‘里’与‘止’为韵,文例正同。若作‘非里邑居’,则下二句失韵矣。《周礼·载师》郑注云:‘廛里者,若今云邑居里。’是‘邑居里’为汉人常语。”[8]徐元太《喻林》卷一〇九《政治门·丧乱》引作“井里邑居,不可舍止”。[7]
武库为“帝王威御之器所宝藏也”的情形,见于《晋书》卷四《惠帝纪》:“(元康五年)冬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②《晋书》卷二七《五行志上》:“惠帝元康五年闰月庚寅,武库火。张华疑有乱,先命固守,然后救火。是以累代异宝,王莽头,孔子屐,汉高祖斩白蛇剑及二百万人器械,一时荡尽。”[2]《晋书》卷二五《舆服志》:“斩白蛇剑至惠帝时武库火烧之,遂亡。”[2]《晋书》卷三六《张华列传》:“武库火,华惧因此变作,列兵固守,然后救之,故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屐等尽焚焉。”[2]又《晋书》卷四六《刘颂列传》:“武库火,彪建计断屋,得出诸宝器。”[2]武库收存军职“册籍”事,未见具体记载。而“武库军府,甲兵所聚”情形,实例颇多。如《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熹平六年二月)武库东垣屋自坏。”李贤注引蔡邕曰:“武库,禁兵所藏。”[9]《后汉书》卷二二《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大战武库下。”李贤注引《洛阳记》:“建始殿东有太仓,仓东有武库,藏兵之所。”[9]《后汉书》卷二四《马援列传》:“敕严过武库,祭蚩尤。”李贤注:“武库,掌兵器,令一人,秩六百石。《前书音义》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今祭之。’见《高祖纪》也。”[9]《后汉书·五行志六》“日蚀”条:“其月十八日武库火,烧兵器也。”[9]《后汉书·百官志二》“太仆”条“本注曰: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9]《说文·广部》:“库,兵车臧也。”段玉裁注:“此‘库’之本义也。”③段玉裁还写道:“引申之,凡贮物舍皆曰‘库’。”[10]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武库“藏兵车”的实例。《续汉书·舆服志上》“轻车”条:“轻车,古之战车也。洞朱轮舆,不巾不盖,建矛戟幢麾,辄弩服。藏在武库”。《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卓既率精兵来,适值帝室大乱,得专废立,据有武库甲兵,国家珍宝,威震天下。 ”[11]《三国志》卷九《魏书·曹爽传》:“擅取……武库禁兵。 ”[11]《晋书》卷四《惠帝纪》:“(元康五年)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库,大调兵器。”[2]
我们这里对于魏晋史籍有关武库的信息予以较多关注,是因为魏晋武库很可能继承了西汉洛阳武库旧址的缘故。
二、桓将军与赵涉的建议:据洛阳武库
吴楚“七国之乱”中,战争双方分别各有重要谋略人物,都提出了抢先占领洛阳武库的战略计划。《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
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问诸老将,老将曰:“此少年推锋之计可耳,安知大虑乎!”于是王不用桓将军计。[1]
桓将军的建议被斥为“少年推锋之际”,而不被采纳。其实,弃坚城而“疾西”,快速占据“洛阳武库”,如此“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这才是具有战略眼光的“知大虑”的深刻识见。
主持平定“七国之乱”的周亚夫是通过特殊路径抵达洛阳的。抵达洛阳之后,即“直入武库”。《汉书》卷四〇《张陈王周传》记载:
亚夫既发,至霸上,赵涉遮说亚夫曰:“将军东诛吴楚,胜则宗庙安,不胜则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亚夫下车,礼而问之。涉曰:“吴王素富,怀辑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间人于殽黾阨陿之间。且兵事上神秘,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计。至洛阳,使吏搜殽黾间,果得吴伏兵。乃请涉为护军。[12]
赵涉的建议为周亚夫认可,“如其计”,于是在军事竞争中占据了上风,最终取胜,实现“宗庙安”的政治预期。
三、王夫人为刘闳求封洛阳故事
《史记》卷六○《三王世家》褚先生补述说到王夫人向汉武帝为子刘闳求封洛阳的故事:
王夫人者,赵人也,与卫夫人并幸武帝,而生子闳。闳且立为王时,其母病,武帝自临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虽然,意所欲,欲于何所王之?”王夫人曰:“愿置之洛阳。”武帝曰:“洛阳有武库、敖仓,天下冲阨,汉国之大都也。先帝以来,无子王于洛阳者。去洛阳,余尽可。”王夫人不应。武帝曰:“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菑中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王夫人以手击头,谢曰:“幸甚。”[1]
汉武帝拒绝王夫人求封洛阳的回答,体现了对洛阳战略地位的清醒认识。所谓“洛阳有武库”以及“天下冲阨”,是洛阳军事地位和交通地位的准确说明。
同样的故事,《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褚先生补述文字略有不同:“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对曰:‘愿居洛阳。’人主曰:‘不可。洛阳有武库、敖仓,当关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来,传不为置王。然关东国莫大于齐,可以为齐王。’王夫人以手击头,呼‘幸甚’。”[1]
“当关口,天下咽喉”,与“天下冲阨”,语义是接近的,而两段记载中“洛阳有武库”的表述是一致的。
四、比较研究之一:东海郡武库
《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豫州颍川郡许昌”条“汉献帝都许。魏禅,徙都洛阳,许宫室武库存焉,改为许昌”。[2]这是东汉末期曾经在许昌设置武库的史例。东汉末年文献载录,可见辽东武库的存在。《三国志》卷八《魏书·公孙度传》:“分辽东郡为辽西中辽郡,置太守。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追封父延为建义侯。立汉二祖庙,承制设坛墠于襄平城南,郊祀天地,籍田,治兵,乘鸾路,九旒,旄头羽骑。太祖表度为武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度曰:‘我王辽东,何永宁也!’藏印绶武库。”[11]孙吴都城建业也有武库。《三国志》卷六四《吴书·孙綝传》:“或有告綝怀怨侮上欲图反者,(孙)休执以付綝,綝杀之,由是愈惧,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许焉,尽敕所督中营精兵万余人,皆令装载,所取武库兵器,咸令给与。”[11]当然,割据时代的军事格局与交通形势与大一统稳固时期应当不同。
体现西汉时期武库的资料,有尹湾六号汉墓出土六号木牍,题《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者,被认为“是迄今所见有关汉代武库器物最完备的统计报告,指标项目甚多,数列明确”。最令人惊异的,是“库存量大”。以可知数量的常见兵器为例,数量超过十万的有“弩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廿六”,“弩檗廿六万三千七百九十八”,“弩弦八十四万八百五十三”,“弩矢千一百卌二万四千一百五十九”,“弩犊丸廿二万六千一百廿三”,“弩兰十一万八百卅三”,“弓矢百十九万八千八百五”,“甲十四万二千三百廿二”,“铍四十四万九千八百一”,“幡胡□□锯齿十六万四千一十六”,“羽二百三万七千五百六十八”,“□□□十九万四千一百卅一”,“刀十五万六千一百卅五”,“刃卌四万九千四百六”,“□□卌三万二千一百九十七”,“□十二万五千一十六”,“铁甲扎五十八万七千二百九十九”,“有方□钦犊十六万三千二百五十一”,“□鍭百七十万一千二百八十”。兵器中消耗量较大的“矢”“鍭”等数量巨大尚可理解,而“弩”“铍”“刀”“刃”等件数惊人,特别值得注意。李均明指出“以常见兵器为例”,“弩的总数达537707件”,“矛的总数达52555件”,“有方数达78392件。仅这几项所见,足可装备50万人以上的军队,远远超出一郡武装所需”。论者推测,“其供应范围必超出东海郡范围,亦受朝廷直接管辖,因此它有可能是汉朝设于东南地区的大武库”。他同时指出,尹湾汉简所说“武库”,应当“不属于东海郡直接管辖”。
我们推想,为什么东海郡设有如此规模的“受朝廷直接管辖”的“大武库”或“地区性大库”呢?或许是因为这里曾经是帝国的“东门”①,有重要的政治文化象征意义。可能更重要的因素,在于东海郡的位置,正大致在汉王朝控制的海岸线的中点②。
前引《晋书》卷二七《五行志上》:“惠帝元康五年闰月庚寅,武库火。……二百万人器械,一时荡尽。”[2]洛阳武库藏有“二百万人器械”,与东海郡武库所藏兵器数量比较,可知武库规模仍然是有等级区别的。
五、比较研究之二:上郡库
西汉时期上郡设武库。《汉书》卷一○《成帝纪》有关于“上郡库令”刘良继承其兄王位,被立为河间王的记载:“(建始元年春正月)立故河间王弟上郡库令良为王。”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汉官》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12]按照《汉官》的说法,此“上郡库”就是“上郡武库”。
没有迹象表明“上郡库”的规模,但是关于“上郡库令”身份的记载,体现了“上郡库”的重要地位。《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记载:“成帝建始元年,复立元帝上郡库令良,是为河间惠王。”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汉官》北边郡库,官兵之所藏,故置令。”③[13]如淳的说法,一谓“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一谓“北边郡库,官兵之所藏”,语义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都指明刘良曾经任“库令”的“上郡库”,是“北边郡”的武库。然而上郡库令刘良是河间王刘元的弟弟,后来刘元有罪被废④[12],刘良成为河间王。可知“上郡库令”身份之高。[14]陈直关注过刘良事迹透露的历史信息。他在讨论居延汉简“库令系统”官职时指出:“库令为边郡主管兵器库者,汉书河间献王传,孙良为上郡库令是也。”[15]
《汉书》卷一《高帝纪上》:“(汉王四年)八月,初为算赋。”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丘浚言:“汉高祖四年,初为算赋。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臣按此汉以后赋民治兵之始。考史,成帝建始元年立故河间王弟上郡库令良为王。注,谓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则前此边郡各有库,库有令,以掌兵器。旧矣。然《地理志》于南阳郡宛下,注有工官、铁官,则不独边郡有武库,而内地亦有之矣。”因南阳郡宛“有工官、铁官”即以为“不独边郡有武库,而内地亦有之矣”的误解,也许由自史籍或见“武库工官”并说的情形。如《史记》卷三〇《平准书》:“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于是天子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囚,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赡之。车骑马乏绝,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牸马,岁课息。”[12]显然,“南阳郡宛”武库的存在并不能得到史证。而所谓“不独边郡有武库,而内地亦有之矣”的说法,大概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六、比较研究之三:姑臧库、武威库
李均明指出,据居延汉简提供的信息可以得知,“张掖郡居延都尉属下使用的兵器有许多是从姑臧库领取的,其使用也受姑臧库的监督,则姑臧库供应武器的范围不局限于武威郡,有可能与整个河西地区有关。可见武威姑臧库是汉朝廷设于西北的地区性大库,与中央武库相呼应”。据此以为,尹湾汉简所说“武库”,也应当“不属于东海郡直接管辖”。
居延汉简可见:“●武威郡姑臧别库假戍田卒兵□留□■”(EPT58:55)。有研究者认为,“此简反映出姑臧库向居延地区提供兵器的情况。相关的记载还见居延新简EPT52:399:‘●第十七部黄龙元年六月卒假兵姑臧名籍。’此外,居延汉简7·7A‘地节二年六月辛卯朔丁巳,肩水候房谓候长光,官以姑臧所移卒被兵本籍,为行边兵丞相史王卿治卒被兵。’说明肩水地区兵器也有来源于姑臧库的情况。”[16]
又如简文“主□隧如府书」获胡烧塞所失吏卒兵器□移姑臧库”(562.12),应该是将兵器集中于“姑臧库”。
“姑臧”地在今甘肃武威[17],作为武威郡属县①《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莽曰张掖。户万七千五百八十一,口七万六千四百一十九。县十:姑臧,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九十里。”[12],“姑臧库”名号与东海郡武库及“上郡库”显然不同。不过,我们看到“武威库”简例:
元康二年五月已巳朔辛卯武威库令安世别缮治卒兵姑臧敢言之酒泉大守府移丞相府书曰大守■迎卒受兵谨掖檠持与将卒长吏相助至署所毋令卒得擅道用弩射禽兽鬬已前关书■
三居延不遣长吏逢迎卒今东郡遣利昌侯国相力白马司空佐粱将戍卒■(EPT53:63)有研究者认为:“该简记述元康时居延地区戍卒发送和迎受的情况。作为戍卒的发送方,‘将卒长吏’东郡利昌侯国相和白马县司空佐要带领戍卒赴居延。而作为戍卒的接受方,依照丞相府书,居延地区要派遣长吏‘迎卒受兵’。迎卒是迎受戍卒,受兵是接受兵器。从简文理解,受兵应是指到姑臧库迎受兵器,这些东郡戍卒的兵器应是从姑臧所得。居延汉简反映出姑臧库有为河西戍卒提供兵器的情况。此外文书要求戍卒受兵以后要对兵器爱护拿持,不要擅自在道路上用弓弩射猎禽兽和相互斗殴,反映出汉代河西戍卒的迎受制度。”[16]然而简文明确为“武威库令安世”。姑臧为武威郡治所。也许“姑臧库”“武威库”只是不同时期的称谓区别。然而前引“武威郡姑臧别库”简文也值得注意。说明“姑臧库”与“武威库”的关系及相关制度,也许还需要继续深入思考。
应当注意到,河西汉简简文中有的“库”并非武库。《释名·释宫室》:“库,舍也,物所在之舍也,故齐鲁谓库曰‘舍’也。”②任继昉纂《释名汇校》:“许克勤校……又引《礼记》:‘在库言库。’郑玄曰:‘马车兵革之藏也。’蔡雍《月令章句》:‘审五库之量,一曰车库,二曰兵库,三曰祭器库,四曰乐库,五曰宴器库。’任按:见《原本玉篇残卷》第448页,第14-16行。”齐鲁书社2006年11月版,第307页。今按:“蔡雍”应为“蔡邕”。裘锡圭指出:“库的主要任务是管理车和兵甲等作战物资……从出土的兵器和其他器物的铭文看,战国秦汉时代的库都是从事生产的。并且除了制造兵器、车器以外,也制造鼎、钟等其他器物。”“从汉代史料看,库还管理钱财”。“史书里也常提到库钱”。[18]《后汉书·百官志三》“少府”条:“(尚书)右丞假署印绶,及纸笔墨诸财用库藏。”[9]所谓“诸财用库藏”的情形,居延汉简有“金曹调库赋钱万四千三”(139.28)、“●元寿六月受库钱财物出入簿”(286.28)、“十月己亥输钱部库毕入”(507.10)等简例可以说明。而“县库”的存在也是普遍的。裘锡圭指出,“秦律《效律》提到县的都库啬夫”。“居延库嗇夫是居延县的库啬夫”。“银雀山竹书的《库法》篇讲了县库制造武器的一些规定”。③裘锡圭指出,“西汉封泥有‘成都库’半通印文,《封泥考略》以为是成都县主库掾史之印,劳榦根据居延简指出成都库应为嗇夫所主,是郑国渠的。”见《嗇夫初探》,《裘锡圭学术文集·古代历史、思想、民俗卷》,第70页。其实,“成都库”似未可排除与东海郡武库、上郡库、姑臧库及武威库地位相当的可能。此外,军队也有武库设置。《汉书》卷六〇《杜周传》:“凤深知钦能,奏请钦为大将军军武库令。”[12]《资治通鉴》言“大将军武库令杜钦”,胡三省注:“此大将军之军中武库令也。钦传,军下更有‘军’字。”[13]可知“库”和“武库”的设置,情形相当复杂。河西汉简所见“库”,不宜均读作“姑臧库”,理解为“武库”。
作为武库的“姑臧库”与“武威库”的存在,也未必可以作为“边郡有武库”“边郡各有库”的证明。而“姑臧库”与“武威库”的空间位置,对于控制西域通路的地位,是可以与东海郡武库和“上郡武库”进行对应比照的。“姑臧库”与“武威库”地处河西四郡最东,在控制河西通道的战略任务中表现出重要意义,又靠近汉帝国腹地,不至于轻易为匈奴攻击,出现前引简文所谓“胡烧塞”“失吏卒兵器”情形。
就本文讨论的主题而言,东海郡武库、上郡库、姑臧库与武威库均有重要战略地位[18],然而与洛阳武库相比,毕竟不在一个等级。东海郡武库“可装备50万人以上的军队”,而洛阳武库藏有“二百万人器械”这样具备参考意义的西晋史料,是有益于我们进行数量比较和等级区分的。洛阳有“天下冲阨”“天下咽喉”的军事地理与交通地理地位,“武库”和“敖仓”的设置,是与这一形势相关的历史存在。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焦延寿.易林汇校集注[M].徐传武,胡真,校点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6]徐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8]孙诒让.札迻[M].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
[9]范晔.后汉书[M].李贤,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10]许慎.说文解字注[O].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版.
[1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3]司马光.资治通鉴[M].长沙:岳麓书社,2009.
[14]王子今.西汉上郡武库与秦始皇直道交通[M]//秦汉研究(第十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
[15]陈直.居延汉简综论[M]//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
[16]张德芳.居延新简集释(四)[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
[17]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18]裘锡圭.嗇夫初探[M]//裘锡圭学术文集:古代历史、思想、民俗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