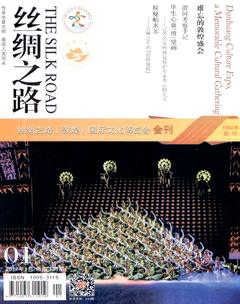张掖大地,另一种抵达
舒眉



西游遗迹觅踪
深秋的天空,蔚蓝澄澈,黑河变得安静清澈,静静地穿过张掖腹地,河两岸的树木晕染着大片大片五彩斑斓的色彩,深绿色、金黄色、橙色、大红色、深红色、酱紫色……这丰富而绚烂的美,是黑河给予张掖这片土地最丰厚的馈赠。伟大的黑河孕育了丝路古道上的古城,也孕育了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丝路文明。民间传说、历史故事、经典诗文、神话演义,就像璀璨的星辰在历史的天空里闪耀着光芒,虽然历经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兴衰,但文明的超常强韧使许多遗迹没有陨灭于草丛石堆间,数千年之后还在为后代开拓前途。在张掖大地上,《西游记》的故事不仅仅是家喻户晓,更有许多留存的遗迹和不同于书本故事的情节,引发我们的思考和探究:张掖是否就是《西游记》的发源地?
时令已至深秋,张掖市《西游记》文化研究会的20多个会员,在多红斌会长的带领下,再次沿着黑河,一路向西,从甘州到临泽,探寻《西游记》文化的踪迹。存在与想象之间,需要一条通道抵达。而我们现在的考察研究,是从既成的瑰丽奇特的想象回溯。这样的抵达,比依据现实的想象更具有挑战性。而我始终认为,寻访、捕捉、探究本身就是对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比想象更具有诗意。
最先抵达的是牛魔王洞。牛魔王的故事是《西游记》中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牛魔王也和孙悟空、猪八戒一样成为中华大地上妇孺皆知的经典形象。沿着黑河一路向西,仿佛我们也要去取经一般,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在车上,多会长告诉我们,30年前,他曾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背着水壶,从求学的张掖师范来寻访牛魔王洞。30年前,或者更早的300年前,牛魔王洞就在这里了,当时老乡告诉多会长关于牛魔王洞的许多故事,说是老一辈人代代流传下来的。多会长的一席话,让我们肃然起敬,他对文化的热爱,是来自骨子里的、发自内心的。现在,他又带着更多的热爱者来这里探寻、研究。30年的时光悄悄染白了他鬓间的发丝,却没有消磨掉他心中的激情和热忱。这份热忱和激情,更点燃了大家对《西游记》文化研究的兴趣。
牛魔王洞就在张掖通往临泽的公路旁,初看上去只是一个大土堆,下面有一个用土坯垒砌的圆形拱门,小而且残缺。走近了,才能看到拱门下面坍塌之后的洞口,也不大,已经被土掩埋了。洞上面是一个小山包,上面有几堵墙,墙上依稀有壁画的痕迹。有研究壁画的专家细细看过,说这些壁画应该是近代的,时间不会太久远。但牛魔王的故事在这里已经流传很久了,等候在这里的临泽县文联刘主席介绍,小的时候,他就听说过牛魔王洞的故事,说这个洞很深,是无底洞,人一旦进去就再也出不来。刘主席是听爷爷讲的,爷爷是听爷爷的爷爷讲的。临泽板桥这一带,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情节大同小异,人物名称却不变,关于牛魔王洞,大家都玩笑:这个洞,肯定是通往玉面狐狸的洞里去了嘛!
拍照,测量,仔细查看,专家学者们甚至拿了放大镜仔仔细细看墙上壁画的线条和色彩,似乎想从这仅存的遗留中找到西游文化的穴位、经络。深秋的风吹到脸上,带着丝丝寒意,路边的杨树上不断有叶子落下来,黑河两岸的庄稼地里,是收割过的玉米茬;远处,还有放羊的人赶着羊群。在旁边地里干活的80岁老人张凤香兴致盎然地走过来,再次给我们讲了关于牛魔王洞的故事。她说这个小小的洞口,神秘诡异,侵吞了许多牲畜和小孩的性命,许多人因为好奇探秘,进去之后就没有再出来。另有传说,这洞一直往西,出口在嘉峪关,曾有一只狗,从这洞口进去,数日之后自嘉峪关那边洞口出来,浑身狗毛全无,只剩下一身红皮。传说离奇,想象似乎也符合西游故事的思路,老人讲得认真,我们听得仔细,并不觉得这是一个笑话。老人年岁已高,但身轻体健,非常健谈,对牛魔王洞的传说深信不疑,因为这是她从小到大听了许多遍的故事。还因为,牛魔王洞的西北不远处就是火焰山,整个山体都是鲜红色,就像燃烧的火焰。她说他们这里的人都相信,这个洞就是《西游记》里面的牛魔王居住的洞穴。老人还说,当年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时,曾有人试图清理此洞,不料挖出两条大蛇来,从此谁也不敢再动这里。这些传说是和留存的遗迹互为补充、互相印证的。
看着这荒废了的遗迹,想想《西游记》故事的浪漫色彩,不能不让人感慨时间的荒芜和强大。文化的传承、发扬,不仅需要具体的实体,更需要抽象的精神力量。
接下来,去老人所说的火焰山——板桥的红沟。火焰山离牛魔王洞自然不远,不然牛魔王也不会娶了铁扇公主。沿着公路继续往西,再往北拐,大约一个小时车程就到了红沟。红沟就是红色的丹霞山,连绵起伏的群山不高,却全是红色的。猝然之间领受这壮观绮丽的气势,似在静僻之中撞见奇迹,我们不得不停下脚步来调整呼吸。如果有谁对牛魔王洞的传说还有所怀疑的话,到了红沟,一定会确信,这里的的确确就是火焰山!所有的山都是正在燃烧的火焰,赤色、深红色、橙黄色、酱紫色,深深浅浅,浓淡交错,不仅颜色像火焰,形状也像极了火焰。站在山脚下,似乎也能感受到火焰燃烧的呼呼声。惊叹中,大家跟着刘主席就近爬上一座山,到了山顶,更是令人惊叹不已——正是上午11点,红色的山体在金色阳光的照耀下,像连绵起伏的火海,一直燃烧到天边,远处的、近处的,高处的、低处的,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火苗在阳光下变幻着不同的色彩!如果没有看见过这一片连绵起伏延伸到远处的火海,怎能产生火焰山这样绮丽传奇的故事?
红沟是本地人形象质朴的叫法,任何瑰丽奇异的想象,都来自实实在在的存在。无疑,这红沟就是火焰山,就是铁扇公主、芭蕉扇这些传奇故事的真实范本。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都会如此确信。
红沟往北,是羊台山,传说是苏武牧羊的地方。汽车在茫茫戈壁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远远地看到了藍天之下的羊台山。时近正午,天空像被水洗过一样碧蓝,有几抹淡淡的云彩飘浮在上面,蓝天之下,羊台山如一座安静的城池,静默不语,山下的残砖断瓦诉说着曾经的喧嚣兴盛。羊台山下有人家,养骆驼,一群群白色的、黄色的骆驼高昂着头,在篱笆墙下的辘轳井旁等候我们的到来。这样的场景让我们感觉穿越了时空,有如隔世。张掖市文联陈洧主席和几个作家即兴创作剧本,故事曲折,情节离奇而又合乎情理。其实,任何浪漫的想象都有催生它的土壤,真正伟大的作品绝不是凭空杜撰的,《西游记》的诞生,应该也缺不了这样苍茫辽阔中的朴拙柔美场景吧!
下午,去高老庄,寻访猪八戒墩。一路上听刘主席介绍,我误以为是猪八戒洞,及至到了高庄村,遇见田边劳作的村妇,一路问过去,还是说猪八戒洞,顺着田埂七弯八拐,终于到了,却只看到一个不大的土墩。夕阳下,土墩的颜色是黄褐色的,上面夹杂着青黑的沙石。墩周围不过3米就是庄稼地,玉米已经收割完了,田野里一片空旷,不远处,就有人家,有枣园。刘主席介绍,这个猪八戒洞也是古迹了。当地流传,猪八戒洞很深,但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深,因为许多放牛的孩子都被这个洞吸走了,人不归,牛也不见了。当地人害怕,请高人做法收拾,填了洞,又在上面立了个墩,算是镇住了,从此不再有人失踪。故事里没有高小姐,也没有猪八戒,但这个墩确实就叫“猪八戒墩”,高庄村的祖祖辈辈就是这么叫的。往回走的时候,我们从一户杨姓人家的后院穿过来,老杨又给我们讲了一遍猪八戒墩的故事,和先前刘主席讲的一样。老杨还告诉我们,村名高庄,但这个村里没有一户人家姓高。大家都笑说估计是被猪八戒吓跑了吧。老杨说他也不知道,在他小时候,爷爷就是这么讲的,那个墩也一直就在那里。
任何存在自有来历,并不是每一处遗迹都能与传说那么贴切,如果是那样,我们的考察与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变成牵强附会的生拉硬套了。掩埋于荒草残垣间的遗址和依附在这些遗址上的谜一样扑朔迷离的传说和故事,都是黑河文明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蹲下身来,把心放在低处,反复寻访、探究、揣摩、学习、解读,这才是更有意味和意趣的行走。
夕阳西下时,我们结束了行程,整整一天对《西游记》文化遗迹的寻访,让我们每一个人对西游文化的产生都略有感悟。我想,无论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地方,如果忽略了文化遗迹的发掘保护,不去作实地考察,那么任何学术研究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安阳,《甘州歌》
寒冬。腊月。甘州。
出甘州城南40公里,离祁连雪山更近的安阳大地,主调不是虚张声势的苍凉感,也不是故弄玄虚的神秘感,更不是炊烟缭绕的世俗感。天蓝得澄澈,尽管整整一个冬天都没有下雪,但不远处的祁连雪山依旧巍然屹立,似乎伸手可及。清新的空气中透着白雪一样干净的清寒,让人忍不住要深深地吸一口气,再缓缓地呼出去。落光了叶子的树木并不显得萧瑟,枝干挺立,直指蓝天,更有一种别样的风骨。没有了繁茂枝叶的遮蔽和掩映,冬天的大地景物是通透的,视线可以延伸到数百米之远。站在魁星楼上向四下里看去,黄色的村庄在蓝天、雪山的映衬下,显得有点苍凉古朴,也多了些神秘。房屋、车辆、树木、结了冰的涝池、涝池里凿开的冰窟窿、从冰窟窿里担水的人,还有远处枯黄沉寂的田地、三三两两站在门口聊天的老人、居民点上追逐打闹的几个孩子、田地里静默的三两只肥牛和缓缓移动的羊群……一切都被冬日的悠然综合成一种有待挖掘的诗意,看上去那么质朴而又淡泊。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村庄像一幅巨大的默片,静谧而安详,不远处的雪山作为永恒的背景,更使这诗意变成了一种需要用心体味的空灵。
如果我们的心足够安静,一定能感受得到村庄的静美。
这是安阳的贺家城。这个小小的村庄可以算得上是离市区最远的村庄了。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足够远的距离也许是一种幸运,一种天然的保护屏障,使古老的传统得以留存。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探访古老的鼓乐演奏《甘州歌》。贺家城村有一个叫贺胜的人,他带领的鼓乐班子会演奏这一古老的民间音乐。张掖市委党校的任教授在张掖文化方面颇有研究,这次探访就是他为我们联系的。他介绍说,贺胜和他带领的鼓乐班子不仅是甘州,还是西北地区唯一流传下来的最古老、最纯粹的民间鼓乐演奏班子。在别处,再也听不到这样传统的演奏了。面包车出了城一直往南走,祁连雪山仿佛就是映在车窗玻璃上的一幅水粉画,贺家城就是这幅画里的一个村庄。任教授说,出了甘州城10里之外才有真正的文化。这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也不无道理,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存在,都必定要有适合留存的环境。安阳贺家城地处城南40公里之外,离城区较远,离现代文明的浸染就远一些,民风淳朴,保留了许多古老传统的风俗习惯。
贺胜早就在自己家里等候我们的到来。这是一个典型的西北汉子,脸庞黑红,身材魁梧,方脸大眼,浓眉厚唇,脸上满是忠厚实诚的笑。他家里收藏了许多关于道教的珍贵典籍,大多是手抄本,最早的一本是明朝崇祯年间的,纸页已经泛黄了,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笔画遒劲有力。有《万神则感应矣》、《天尊说圣姥孔雀明王经卷》、《黄帝地母经》、《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等百余本,贺胜介绍说,他家是祖传道教鼓乐班子,演奏道教音乐,替人做法事、搞祭祀,到他这里已经是第五代了。也就是说,近300年来,他们鼓乐班子演奏的历史及其文化品性没有断裂过,不管王朝更换、时间摧毁,始终用一种强韧的力量将这特殊的音乐形式与这片土地相容,将他们的演奏放进了人心里和尘世间,除了“文革”期间,几乎没有间断过。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乡村葬礼越来越重视传统仪式,贺胜和他的鼓乐班子也越来越火。虽然这样的演奏仅限于丧事和祭祀活动,但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大抵是滋生于生活现场的,唯其如此,才更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要听的鼓曲是《甘州歌》。我们一行20多个人,大多数没有听过。贺胜的鼓乐班子也就四五人而已,平常各自忙活,务细庄稼,也打工挣钱,遇到哪家有事来请,才临时组合到事主家里去,演奏只是繁乱的丧事或者祭祀活动的一部分。忙乱之中,能用心来听的人并不多,其真正的作用是想通过鼓乐演奏营造一种隆重悲凉的氛围。今天,他们特意在村里的礼堂里为我们演奏。贺胜他们早已经做好了准备,几个人都穿了红色长袍,戴了黑色的方形道帽,唢呐、大鼓、铜铃等器乐一应俱全。演奏之前,任教授又作了简单介绍,《甘州歌》其实属于“西凉之声”,是西凉乐、宫廷乐、龟兹乐三种音乐的融合,“杂以秦声”,主要特色就是以锣鼓为主的梆子,加上唢呐,兼有说唱,节奏快,曲调热烈激昂,正所谓“铿锵镗镗,洪心骇耳”。任教授说,此音“可争天籁”。
果然!鼓乐气势震人肺腑,似千军万马横空腾跃,直击得人心也跟着鼓点“咚咚咚”狂跳,裂帛一样高亢悲凉的唢呐声,索性将胸腔里那颗跳跃的心一直往上提,直要冲破喉咙,不觉间我已经泪流满面,整个人都被这酣畅淋漓的演奏感染了,似通了电,通體舒畅,发烧了一般,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与痛快。
这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如同畅饮甘冽的美酒,让人醉得痛快酣畅。现在,娱乐充斥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像这样能真正打动人心,使人震撼的演奏已经不多了。所有的人都被鼓乐声牵动着,带领着,进入了一种微醉微醺的状态。
比我们更陶醉其中的,是演奏中的贺胜本人。自演奏开始,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完全沉浸在音乐之中,无论是吹唢呐,还是击鼓,他都微微闭着眼睛,陶然忘我,似乎对周围的世界已经浑然不觉。他不是在表演,更不是在演奏,而是在享受,享受已经融入他生活和生命中的这份挚爱。这份爱,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五辈人近300年代代相传的文化,已经深深扎根、流淌在他的血液之中,使得他身上散发着有别于其他演奏者的一种特殊精神气质。也许,感染了我们的正是这种精神气质,而并非他精湛的演奏技巧。这个世界上,真正让人感动、触及我们内心深处的,是执着,是坚守,更是全身心的投入和热爱。缺少了热爱,任何优秀的文化传承都不会有恒久持续的生命力。有这种精神气质打底的演奏,不仅打动人心,更让人肃然起敬。
从第一场《西番赞》开始,到《哭长城》、《千里渡行》,不觉间,两个小时过去了,正午的阳光透过窗户射进来,小小的礼堂里已经挤满了闻声而至的村民,先前还有点阴冷的礼堂变得暖洋洋的,似有热气在沸腾,演奏者和听众都意犹未尽,这酣畅淋漓的鼓乐演奏仿佛把现场的所有人——无论是听者还是演奏者都带到了远离现实却又是最世俗的生活现场。这样说似乎是矛盾的,但现实是全民物质化、功利化、表面化的,我们的内心,其实期待着能回到一种有文化传统和精神归属的俗世。
也许,某一刻,地处偏远的安阳贺家城,因为有了像贺胜这样的民间艺人和《甘州歌》这样的文化传承,可以算得上一个理想的俗世吧!音乐,或者任何文化的真正传承,甚至创新发扬,不在曲高和寡的高档演奏厅里,而在民间。
我们心有期待。期待,会成为一种文化传承和延续的生命线,“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只要愿意听,一切都能延续;只要能够延续,一切都有改观。就像张掖的《西游记》文化研究一样,我们期待文化的传承,更期待文化的拓展、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