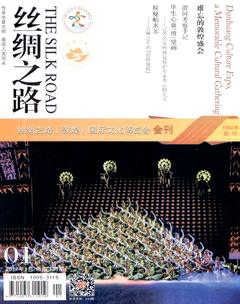探秘帕米尔
孟昭毅

天津《今晚报》副刊2016年4月2日登载了一篇李忆莙写的小文《美丽的旅程》,我读后产生了一定要去南疆帕米尔高原红其拉甫口岸的冲动。帕米尔当地语为“U型河谷”,帕米尔高原古称“葱岭”,是五条山脉扭结之处,号称“山结”。它是古代联系东西方世界的枢纽,也是古代东西方主要经济、宗教、文化的交汇处。至今,它依然蕴藏着无尽的奥秘,如丝绸之路穿越帕米尔的具体路线、唐代高僧玄奘去天竺取经归国的路线等,这些都使人产生不尽的遐想。带着这些诱惑,2016年7月中旬暑假期间,我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准备,终于如愿以偿地踏上了被诸多亲友称为古稀之年的“危险旅程”。
下午从天津机场出发,傍晚到达乌鲁木齐转飞喀什。由于当地与北京有两个小时的时差,所以到达目的地时,虽已是晚上8点多钟,但天还亮着。出租车穿过喀什旧市区,一路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派歌舞升平的安定景象。第二天清晨,我和同去红其拉甫口岸的幾位年轻朋友,坐上越野车在喀什疏附县乌帕尔附近的快餐店吃了早饭,买好路上的食物和水,顺着平坦开阔的314国道(又名中巴友谊公路)直奔目的地而去。
可是好景不长,过了乌帕尔不远,路况使我开始不那么乐观了,终于在一个有“中国邮政”标志的既卖邮品又卖土特产的店铺门前,司机告诉我们前方不远就要进入修路地段了。由于顺应“一带一路”战略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巴友谊公路重新整修,从前方不远开始有100公里左右的路段要修。本来喀什到红其拉甫只有430公里左右的路程,五个小时足以到达,但是现在这100公里左右的路程就要花费四个多小时。汽车一路颠簸,异常艰难地前行着,车内的乘客上下起伏、左摇右晃,车外尘土飞扬。到达帕米尔高原山区以后,公路进入盖孜峡谷,汽车沿着路左的盖孜河前行。首先见到的是类似于吐鲁番火焰山一样的红山矗立在公路两边。红色的庞大山体突兀在眼前,令人望而生畏。偶尔能看到一两匹孤独的骆驼无奈地站在路边的烟尘中。原来的公路有的路段需要拓宽,重新铺设;有的路段需要改道,绕开山洪冲决的地段;有的路段则是重新设计,改为高架路,所以有时要单方向行驶,有时还要下车步行,或因山坡太陡峭,或因车多路窄,总之各种情况都有。偶尔能看到高山上由洪水冲刷而形成的砂石流,犹如挂在天际的巨大瀑布,让人惊叹不已。走到整修路段一半左右的地方,在左侧盖孜河对面,隐隐约约可见到残存的栈道和几处用石块围起的低矮的方形院落,其中还有几处残破不堪的石头建筑,司机告诉我们那是驿站的遗址,传说唐玄奘东归时曾路经此地。
走出这段正在整修的公路,车速明显快了起来,前方道路的视野也逐渐变得开阔。突然在道路右侧,我们看到一片湖水,听说这是一个大水库,叫布伦湖,碧蓝蓝的天、绿泱泱的水和远处浅黄色的山峦映入眼帘。对刚刚受到艰难路况摧残的我们来说,眼前的景象犹如一副醒脑剂。定睛仔细看,更让人惊奇,原来湖对面出现的一片连绵起伏、丘陵状的黄白色山上竟然全是细沙。司机告诉我们那是白沙山,一种黄色的细沙被经过湖面的大风从山下吹向坡上,翻卷而上,就像大沙漠的沙丘一样,夹在蓝天、绿水之间,显得异常美丽,真是鬼斧神工,大自然的造化令人难以捉摸。沿途远处的公格尔山峰,云里云外,躲躲闪闪,神秘莫测。高耸入云的慕士塔格峰上雪白晶莹的冰川,曾经令19世纪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一见倾心,从此它便有了“冰川之父”的美称。它是想去红其拉甫的探险者绕不过去的障碍,汽车一直在它的陪伴下疾行。再往前就可以看到由冰山雪水融化而形成的美丽的喀拉库里湖了,倒映在水中的雪山之影让同行的旅伴心醉而流连忘返。我们走马观花式地穿行在这一路的美景之中,不知不觉已抵达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宽阔无人的大道两旁,用中、英两种文字写成并印有两国国旗的“热烈庆祝中巴建交65周年”的大红标语牌直通远方,提醒着人们已经临近国境线了。
这座口岸新城像镶嵌在帕米尔高原上的一颗明珠,海拔超过3000米,人口约有3.5万,其中近83%都是英勇的塔吉克族人,他们有着欧罗巴人种的特征,语言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帕米尔语支。生活在我国境内的塔吉克人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他们长期生活在我国的西部边陲,在广泛吸收希腊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充满了神奇美妙、绚丽多彩的迷人魅力。汽车行驶在安静、平坦、街灯高悬的马路上,一路望着天边低垂的蓝天白云,有一种心旷神怡的舒畅感。我们不敢耽搁时间,因为还要尽快去塔县边防支队管辖的红其拉甫边防检查站,办理到红其拉甫国门和参观界碑的通行证。有时通行证会因为天气原因而暂停发放。今天我们很幸运,跑了几百里路总算在接近5点钟时排上队,依次检查身份证、照相,集体办理了一行12人的通行证,可滞留三小时。在拿到通行证以后,汽车像有了护身符一样,犹如脱缰的野马在曲折蛇行、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高原公路上飞驰。
“红其拉甫”意为“血谷”,在古代它不仅是各种盗贼强人的出没之地,也是战争频发之地。在那些特殊的年代,暴力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种变异形式。红其拉甫边检站的前哨班即驻扎在国门。它位于东经75.5度,北纬37度,平均海拔5100米,是世界上最高的边境哨所之一。这里空气稀薄,含氧量仅占平原地区的48%,水的沸点不足70℃。此地的气候恶劣,瞬息万变,全年无霜期不足60天,平均气温-20℃,素有“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六月下大雪,四季穿棉袄”的“生命禁区”之称,因此吸引了众多的探险者。尽管条件如此艰苦,前哨班的官兵们还是为打造世界著名边境品牌而努力着,常年坚守国门,向世人展示了“国门第一哨”的良好形象。他们曾多次亮相春节联欢晚会,让世人感奋不已。因处于高寒地带,红其拉甫口岸一般每年只在5~9月开放,10月份关闭,期间有时还因气候变化等原因不能开放。几乎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游客淡季时四五百人左右,旺季时可近千人)不远千里甚至万里慕名而来,参观屹立在雪山怀抱之中的雄伟国门。这座新的国门是2009年国庆节前建好的,外形酷似中国古代城门,是个上窄下宽的两层高大水泥建筑,高约30米,宽约50米,中间的扁长方型门洞宽约15米,高约10米,是纪念建国60年大庆的献礼。国门外还有著名的“7号界碑”,是来访者朝思暮想的重要景观。
我们的汽车经过了上下起伏的盘山道以后,缓慢爬上了5000多米高的山顶。在车内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异常,只发现窗外雨点噼噼啪啪地打在车窗上,车里开着热风,车窗上雾气一片。当车停下来的时候,有人迫不及待地打开车门,一股冰冷的空气夹杂着雨点刮进车内。先下车的几个年轻人莫名其妙地蹲在车下,有的倚在车厢上,刚才还是欢声笑语、活蹦乱跳的年轻人突然间变得悄无声息了。因为我去过西藏,心想他们可能是因为缺氧,一会儿就适应了。于是我慢慢走下车来,从背包里拿出冲锋衣穿好,戴上帽子,缓慢地一步一步走向数百米外的国门。高大雄伟的国门,以它的气势和威严,让人从心底生出一种自豪感和敬意。我请人帮我照相时,身边不时有从中国开往克什米尔巴基斯坦控制区的载重卡车通过。我冒着冰冷的小雨缓步穿过国门来到著名的7号界碑前,看到对面有许多巴基斯坦人。他们几乎都是男性,有老人,也有青年,见到中国人就热情地握手。此情此景,让我回忆起前几年去巴基斯坦的经历: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人们的友好接待,打招呼、握手、拥抱、合影留念都是常有的事,亲身体验了巴基斯坦大街上悬挂的标语——“中国兄弟,铁哥们”的深情厚谊。在这里,我又找到了同样的感觉。7号界碑是双面的,中方一面是中文,巴方一面是巴基斯坦文和英文,上面有各自的国徽,下面写着建成的年份“1986”。我跨过一段拖在地上手指般粗的绳索,走进巴基斯坦人群,许多巴方的朋友和我合影留念,他们有尊敬老年人的习惯和传统。我请他们为我站在巴基斯坦一面的界碑前照相。由于天气的原因,山顶的光线渐渐暗下来,中方的武警也招呼人们赶快回来。我心满意足地回到国境内,完全没有了缺氧的感觉。在下山去乘返程的汽车时,大家突然惊呼起来,因为看到了雨后的彩虹,在夕阳的余晖照耀下,它像挂在天空的彩练,色泽是那么鲜明、清晰,宛如中巴两国人民心中的友谊桥梁,难能可贵。
上山艰难,下山易。我们还沉浸在顺利来到国门的喜悦中,汽车就像“轻舟已过万重山”一样开进了塔城。我们住的是“塔县旅游宾馆”。大门上方“旅游宾馆欢迎您”的霓虹灯标语,给我们一种宾至如归的幸福感。宾馆餐厅承包给了一个二十七八岁的河南小伙子,他因家境贫寒投靠亲友,已来塔县十几年了,现在已有一定的积蓄,但是还没有结婚。他说这里很安定,就是汉人少,有时感到孤独,想娶一个内地的女孩一起在这里发展。这个诚实、能干的小伙子给我做了一碗地道的面汤,炒了一盘鸡蛋西红柿,吃得我浑身发热,舒舒服服。我想如此能干的小伙子,扎根在这里一定会有美好的前途。
第二天早晨,我们一行来到塔县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入口处竖立着一块巨石,上面刻写着“丝路潮涌,深塔放歌”八个大字。可见塔县和丝绸之路的关系非常密切。这片水草丰茂之地辽阔无比,一直延伸到周围山影下的天际。湿地远方星星点点地分布着一些白色的帐篷,飘洒在绿地草滩上。一群群牛羊散落在绿毯似的草地上,犹如一幅巨大的草场油画。为了让人们能近距离地感受到湿地良好的生态环境,草滩上还铺设了木板路,水深的地方还有简易的索拉木桥。这一大片天然的原生态草滩绿地,让游人乐不思蜀、依依不舍。
远望湿地的西边,有一处像小山一样的古城堡,近看依稀可辨它矗立在蓝天白云之下逶迤雄浑的身姿,那就是著名的石头城遗址。它处于塔县的东北边缘,海拔3100米左右,是古代丝绸之路交通的必经之路。这处古城遗址与辽宁石城、南京石城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著名石头城建筑,现在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发现证明,石头城曾先后是汉朝蒲犁国、朅盘陀国,唐朝位于龟兹的安西都护府(现今新疆南疆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县,和北疆奇台地区吉木萨尔的北庭都护府齐名,都是唐朝对西域实行事实上管理与统治的重镇)管辖下的“葱岭守捉”,清朝的“色勒库尔回庄”和“蒲犁厅城”的遗址所在地。它一直是塔什库尔干叶尔羌河流域河谷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距今已有2200余年。现今的石头城遗址目测高度有50米左右,城墙有修缮的痕迹,还有新铺设的木板梯可攀登,城堡不是很大,登高远望,四周群山环绕,有的山峰顶端白雪皑皑。下面四周地上落有大量的石块,还有一些残垣断壁,似乎在向来访者述说那些古老而不平凡的岁月。苍穹之下仔细端详这座黄色的古堡,不禁让人产生一种历史的沧桑感。
塔县石头城遗址下面的大道边上修建了一组关于塔吉克族历史文化的大型浮雕群,主要分为“汉日天种”、“拜火教仪式”、“石头城”、“丝绸古道”、“张骞”、“班超”、“玄奘东归”、“马可·波罗”、“斯坦因”和“冰山上的来客”等10余个主题。这些主题主要说明了塔什库尔干和塔吉克民族在丝绸之路上的咽喉地位和丰富的历史文化。“汉日天种”讲述的是一个塔吉克族传说,相传塔吉克民族是太阳中的男神与一名汉族公主的后裔,浮雕上表现的是一位年轻俊美的异装男子骑在长着双翅的马上,脚下是朵朵祥云,从太阳里面顺着阳光的照射奔向一位汉装的美丽公主。“拜火教仪式”描绘的是塔吉克民族有崇拜火的信仰传统,这种习俗明显是受了波斯祅教的影响,是他们先民向往光明的一种心理反应。“石头城”主要介绍的是汉代史籍中关于朅盘陀国的记载。“丝绸古道”则主要表现了古代丝绸之路上往来的著名人物的事迹。如张骞凿空西域,始有丝路交通的可能;班超投笔从戎,招降西域诸国,丝路得以畅通。“玄奘东归”雕刻的是唐代高僧玄奘自天竺取经归国时,在经过塔吉克民族居住地时受到热烈欢迎。“马可·波罗”反映了700多年前马可·波罗经过塔吉克民族住地时的历史情景。“斯坦因”则是一副学者模样,穿着西服,戴着礼帽,脚下放着古代的字画文物等。100多年前,这位英国籍匈牙利裔的探险家、“文物窃贼”曾途经塔吉克民族居住的瓦罕谷地。他认为玄奘也曾从这片土地经过,引来玄奘东归路线的争议。“冰山上的来客”曾是电影的名称,浮雕主要说明了塔吉克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一员,和解放军一起军民联防驻守边疆的内容。这幅大型浮雕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塔什库尔干和塔吉克民族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可见,此地作为绿洲丝绸之路南道的重要节点是众多贸易客商、传道求法高僧和探险家等旅人的必经之地。
从塔县回喀什的公路还要路经战略要地瓦罕走廊东端,确切地说应该叫作瓦罕谷地的东端,即公主堡遗址。它是中国通向阿富汗的唯一通道,像一条横亘在帕米尔高原的“天路”,属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管辖。这个突出于中国西部边陲的狭长地带,长约400公里,东端近100公里在中国境内,西端属于阿富汗。它类似一个走廊,从北向南依次和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接壤,号称“鸡鸣三国”,是十分重要而又敏感的战略要地。塔什库尔干这种“一县邻三国”的严峻形势,使之成为中国最复杂的边境地区,堪称丝路南道的咽喉与地标。学者不仅认为马可·波罗、斯坦因等人途经这片谷地,而且还有人认为玄奘东归时也经过此地。现在有学者又根据《旧唐书·高仙芝传》考证,公元747年,唐朝边关名将高仙芝从位于龟兹(今库车)的安西都护府出发,跨越葱岭,经过长途跋涉,绕道塔什库尔干的石头城,再折向东南经瓦罕,兵分三路袭击了吐蕃人驻守的连云堡,占领了小勃律(今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地区),树立了合理利用丝路克敌制胜的成功范例。可惜的是,由于瓦罕走廊尚未开放旅游,我们这些普通游客也无缘到达中国境内走廊东端往西的尽头克克吐鲁克,这也成为我这次古稀之年“危险旅程”中最遗憾的事,但愿它不要成为我终生的憾事。
帕米尔高原的U型河谷是古代商旅和原住民出入的必选通道,徒步、驴马等行走的路线蛇形蜿蜒于其中。这些古代丝绸之路与现代公路虽然并不完全重合,但是我们的汽车在河谷纵横、山口棋布、高峰峻岭中穿行,仿佛觉得古代遍地的草场、牛羊依稀在目,古代的商旅和驴马正在蹒跚来往,伴我们同行。
跨越帕米尔,历来就被视为一种壮举,今天仍然如此。从帕米尔高原探秘归来,还有那么多的谜团尚未解开,还有那么多的遗憾存留腦际,这可能就是它无穷的魅力所在,正等待着后来者去探索、体味。
——红其拉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