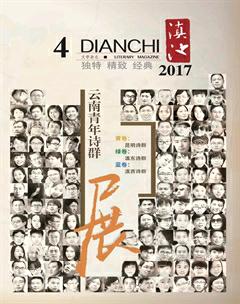诗高原:差异性树种与分层的精神现实
在这个时代我们在谈论诗人尤其是同一个生存空间的诗人群体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他们身后的地方背景和个人命运,想到一个个诗歌文本与“社会学”的千丝万缕的关联。尽管这种阅读习惯和思维定式肯定存在着问题,但是在一个愈益消解地方性知识的时代,在人人关注火热繁杂的“现实”甚至公共话题的时候,这一关乎诗人、地方和现实的传记式的阅读方法并非是无效的。除了肯定、热爱和赞颂,是否像当年的西蒙娜·薇依在 1941年夏天所吁求的那样作家需要对时代的种种不幸负责?这是否就是对作家“良知”和文学“真实度”的考验?如何把个人的现实经验转变为历史经验,如何把个体的真实通过语言的途径转化为历史的真实至关重要。“诗与真”的难题在任何时代都在考验着写作者们。
1
此次《滇池》4月号几乎用前所未有的巨大篇幅推出了“云南青年诗群”专辑,整体性地刊发近 120位青年诗人的诗作。这种力度不仅在云南,即使是在国内的刊物中都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作为创刊于 1979年的地方刊物,《滇池》在新世纪中国的诗歌版图上具有着重要意义。其对诗歌的重视程度以及所取得的成效已然成了标杆,比如影响广泛的常设诗歌栏目“诗手册”“诗歌观察”“诗展”“诗人”。尤其是近年来《滇池》不断以专辑的形式推出云南青年诗群,比如“云南新生代诗歌大展”“昆明新生代诗歌大展”“昆明青年诗群”“中国都市新生代·昆明诗群”“西南三城诗展之昆明诗页”等。
围绕着《滇池》所聚集起来的不只是一个空间整体性的诗歌气象,还在于一个刊物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共生关系。这甚至无形中形成了一个精神场域,无论是刊物、诗群,还是具体的诗人以来连带其上的性格、文化和地方背景都呈现了这座高原上差异性的诗歌树种。而这些诗歌树种自身也形成了特殊的物候,并对应于这个时代分层的精神现实。这使我想到了云南珍稀树种最少也在几百种,不要说它们的面目特性,即使是名字对于人们来说都是陌生的,比如云南拟单性木兰、丽江铁杉、大理罗汉松、滇楸、怒江落叶松、滇南风吹楠、澜沧黄杉等。这些差异性巨大的树种分布在不同的地貌、地带,对应于一个个河流、丘陵、峡谷、高原。这在精神风物学上又对位于一个个正在成长中的青年诗人(尤其是那些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诗人,当然不是全部)。如果你因为整体性而无视这种差异性,那么无异于本末倒置。《滇池》通过各种相关的地方诗人专辑的形式不断塑造起来的云南青年诗群形象使得学界一定程度上拨正了对地方性诗歌和诗歌文化地理的刻板印象。以往的空间诗学往往注重的是可规约的整体性,而恰恰忽视了即使在同一个生存空间也时时发生的写作的差异性和不可消弭的个性精神征候。从这点上来说,在一个消解地方景观的城市化时代,在同样的快速及时性的消费化阅读空间,《滇池》所建立起来的正是一种特殊的地方性知识,以及试图建立可供长久阅读的群体性的诗歌范本——尽管其难度超乎想象。
新世纪以来云南青年诗群的数量和整体水平成为令人瞠目的奇异景观。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在寻找原因——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些青年用诗歌来发声呢?高原莽莽,风声习习,时代的铁轨正在震颤。在那些城市、小城镇、乡村、河流和山野的水电站间,我闻到了粗重的气息,这些或轻松或沉重的精神面影一起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学精神。此次《滇池》推出的“云南青年诗群”分为“昆明卷”“滇东卷”“滇西卷”,以三个空间的诗歌群落立体化地支撑起一个地方的诗歌状貌。尤其是大量涌现的 85后和 90后青年诗群不仅在重新塑造甚至修正着人们对“云南诗歌”的印象,而且在不断树立起渐渐清晰的青年诗人的整体群象。平心而论,尤其是“滇东卷”所涉及的很多诗人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新鲜的。这也代表了当下快速且数量庞大的诗歌生产与滞后的诗歌阅读、评论之间的冲突。写作的有效性和阅读的有效性都成了即时性临屏阅读时代最为显豁的问题。看看当下的中国的诗歌,所谓的“好诗”或少数人标榜的“代表作”甚至公众投票选出来的“经典之作”几乎层出不穷,但是只要你结束阅读它们的生命就宣告终结了。我们的诗歌越来越缺乏的不是修辞、不是技巧,甚至也不是所谓的难度,而是一种信仰和可供认识自我的精神生活的缺失。
这是一个飞奔“向前”的时代,与此同时,那一块块钢化玻璃窗模糊了我们与窗外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时代。在一个城市化的时代,很多人正在经受着地方化命运的巨变。那么。在城市化时代的移民运动中,云南的这些青年诗人在不可避免的“时代景象”面前是否还领受到了另外一种特殊的精神和“地方命运”?在那些迥异于现代性的“老旧”事物面前,诗人感受到的不仅是时间给予的灰烬,而且更有生命与存在之间的盘诘,个体现实与历史景象之间的抵牾。其中王单单、影白、祝立根、胡正刚、尹马、芒原、老六等人的诗歌,程度不同地对现代之物充满了疑问和不解,而高原褶皱和巨大阴影里他们既是“趕路人”也是无家可归者。他们讲述这个时代的“命运之书”,他们胃中搅拌着草根,燃烧着高度酒精。显然,写作者与地方空间的关系不能是观念性和本质主义的,而应该是彼此激活的关系。甚至从语言和精神层面来说,个人和地方的关系有时候是龃龉和悖论式的。当然,也有一大部分写作者被“地方”的黑洞吸附进去,与此同时,有些来自云南的诗人其诗歌并未带有明显的“云南”烙印。写作者的“地方血统”可以获得一种发言的权利,甚至在某一个特殊的时期占得优先权,但是这种方言属性的话语权利一旦在写作中定型和无限放大,其危险性也接踵而至。
群落性的诗人必然通过语言、性格甚至道德构建起多少有些风格化的精神面影。而同一地方空间里不同诗人之间的交往不仅呈现了一段浮世绘的生活史,而且也使得彼此的诗歌获得了精进。而同类中的异类,则是我在读诗的过程中所要努力寻找和追索的。
诗人和自我、现实乃至整体空间和时代场域的关系最终只能落实在语言上。只有经过语言之根、文化之思、想象之力和命运之痛所“虚拟”和“再生”的地方景象或拟象才能够超越原型和现实表象而具有持久震撼的力量。由此我们会发现很多云南青年诗人在诗歌中构筑着一个个出生地,在不断命名和复现一个个生存空间——这是他们的精神坐标。在一个迅速拆毁的时代只有语言能够让他们在现实废墟中成为“幸存者”。也正如布罗茨基所言在某些历史时期只有诗歌有能力来处理现实并把现实压缩成某种可以被心灵保存下来的东西。而即使是同一个生存空间,不同经历的人呈现出来的感受甚至所看见的事物也是不同的。这是自我精神的一部分或者历史个人化的延伸。正如当年柏桦的诗句“而冬天也可能正是春天 /而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这是诗人的“现实”,一种语言化的、精神化的、想象性的“现实”。“地方”“空间”都是存在性体验的结果。“空间”“地方”以及附着其上的传统、伦理、秩序都使得写作者面临重重考验——如何将之个人化、历史化并且在美学上具有陌生化的效果就变得愈发重要而棘手。这甚至成为写作者的精神出处以及据守的情感和伦理底线。正像当年耿占春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和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是一种伦理和道德的关系。这不仅意味着他必须接受这个地方的秩序、传统和伦理约束,也意味着他对地方性的事物拥有许多个人传记色彩的记忆”(《自我的地理学》)。尤其是在一个“地方性知识”被清零的现代性、城市化语境之下,残山剩水也注定了失败式的写作命运——一切都是未完成的状态。处于乡土和城市夹缝或断裂带的诗人们身不由己地被某种不可知的力量推搡着去关注和描摹着现代性语境下的“消亡学”。是的,只有当一切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写作者才会缩身于写作当中,写作据此成为疗治,“只有在意识到危险在威胁我们所爱的事物时,我们才会感到时间的向度,并且在我们所看见和触碰的一切事物中感到过去一代代人的存在。”(切斯瓦夫·米沃什:《诗的见证》)
2
很大程度上我们也发现越来越多的青年诗人所呈现的恰恰是碎片化的“个体”诗学——这在拨正以往规约性、集体性的诗歌写作具有时代意义。诗人可以是冷静的旁观者,也可以是水深火热的介入者。我看到了一个个或平静或不解的面孔,还有在文字里洒落的那些碎片、酒杯、砾石、荆棘、鲜花、肋骨、灰烬。与此同时我感受到了这些诗人坚实、朴素、粗砺、深沉的气息。但是也必须注意到,当“个体”成为圭臬,成为或大或小的唯一性的精神风暴,也必然因此形成一定的危险——正如亮光必然与阴影相随。甚至我们由此还会发现,自新世纪以来“个人”几乎取代了其他言说的可能,诗歌在承担了个人趣味和内心世界的同时是否还需要承载其他的质素?这都给我们反观这一时期以来的诗歌写作提出了问题。
阅读这些青年诗人的诗作,我由衷地感触到很大程度上诗歌写作类似于一场精神事件。有的诗人是柔软、深情的,试图说出个人情感和现实境遇之“爱”;有的是修辞的高手和智性的探险者;也有一部分诗人在面对时代庞然大物时满怀狐疑甚至试图说“不”。无论你处理的是个人化的、琐碎的甚至毫无诗性可言的日常生活,还是处理一个时代的分层的现实或是企图重现一个地方的风物志和文化景观,一个诗人都应该具备更高要求的语言能力以及由己及人的扩展能力和试图说出事物和人世秘密的求真意志。而在诗歌的切入角度和题材处理上,诗人既可以虚晃一枪也可以临门一脚。无论直接还是间接,迎面撞击或者迂回闪避,诗人都需要在“要害处”说出真实不虚的语词。这建立起来的才是可靠之诗。由此,我想到了芒原的一首诗《黄昏里的果园》——“枝,叶,鸟,暮色,欲静未止 /我独自一人,坐在万千木叶下 //黄昏的果园,再也没有熟悉的脚步了 /三年前,父亲因为脑梗,没有了种地的力气 //可我还是热爱这里,爱着它的小:/小小的花香,小小的血肉,小小的人间气息 //甚至,小到风涌过果园 /我会情不自禁地站起来,看是不是//父亲。没有人——而卡在喉咙的二字 /僵直得,再也咽不回去”。鸟鸣里有世事沧桑!黄昏里的果园,病中的父亲,安静中的不安,时间光线中个人的斑驳影像,一起蒸腾出的是来自于个体又带有普世性的精神元素。一个人的世界也可能正是扇动整体精神场域风暴的翅膀,比如影白的《关于死亡的一件真事》,“我们毫不忌讳地谈论着死亡 /在时速一百公里的路上 /我溺水三次,你溺水三次 /在一个乌有之乡的 /不深不浅的堰塘里 /我们自救又互救 /一会儿你托着我爬上岸 /一会儿我擎着你爬上岸 /我们气喘吁吁,像两头鏖战之后/筋疲力尽的狮子 /看着水中的自己 /慢慢下沉而无能为力 /——这没心没肺的假死游戏 /一直到暮色笼罩四野,车驶入巧家县城 /你谈起另一件关于死亡的真事为止”。这是真实还是虚构都已经不再重要,因为经由语言的真实所建构起来的日常化和戏剧性的精神事件更具有一种持久的及物性。这是细节、场景、时间和个体存在之诗的对话与盘诘,是相互摩擦和砥砺的结果。这对于那些过于优美、顺畅、平滑的“好诗”而言是一个有力的提请。平庸意义上的“好诗”在这个时代太多了,而那些具有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诗却是乏见的——也许这些诗本身存在着缺陷——有缺陷的具有重要性的诗。
显然,一个诗人的背景、写作动因、精神出处和诗歌来路在阅读和评价的时候不是可有可无的因素,而谈论这些带有“云南血统”的诗人群体无疑具有很大的难度,因为必须将一个诗人与同一地方空间的其他众多诗人予以比较和区分。云南的青年诗人群不仅数量庞大,而且不在少数的青年诗人大多都在处理日常经验、现代性的乡愁以及写作的痛感。我看到的事实是有些渐渐风格化的诗人主动或被动地贴上了标签——地方性、地域、乡土、乡愁、民生、云南经验、痛感、反思现代性。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这种写作类型在美学和思想的双重维度下有时不是变得越来越开阔,相反是越来越狭窄和市儈化,变得有些媚俗而欺世,变得有些口舌油滑、面目可憎。多年前我就打工诗歌写作强调诗歌不能只是痛苦和眼泪,关键的是表达的有效性。这样的话,一个疑问就浮出了水面——诗人的辨识度和区别度在哪里?由此,我想到了王单单的诗句——“一滴叛逆的水。与其它水格格不入”。
在生存现场和唯现实马首是瞻的写作者中从来都不缺少“目击者”,但是将目击现场内化于写作则少之又少,而如何将日常生活中偶然性的现场有效地转化和提升为个体的精神事件则是写作者的基本道义。正像当年奥登所言的,一个焦虑的时代已经降临。在一部分的诗作中我分享到的是久违的平静,而更多则是目睹了沉痛的自省和无可奈何的叹息,看到了驯顺和僭越的博弈,看到了不安、焦躁以及试图和解、劝慰,目睹了虚无的故地以及面向远方的精神愿景。当这些交织、缠绕在一起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诗人极不轻松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既是个人的命运,也是相应的整体性的写作伦理和文化趣味。现实自身就是魔幻的、变形的、异味的——如露如电,梦幻泡影。更为残酷的还在于写作者除了承担讲述和修辞的道义,还要承受来自文字之外的现实压力或者种种真实的不幸。
3
一个普遍的写作现象是诗人往往在乡村和城市两个区域展开“作业”,而这在新世纪以来也成了聚讼纷纭的话题。在渐成流行的写作趋势中,大量关于乡土和城市的诗歌有的已经丧失了真正意义上的命名能力。在写作中重建“现实感”,承担文字的“真实”是可能的吗?尤其是在遍地犬儒主义和狗智主义横行无阻的时代——此外还有那么多的欣快症患者。齐邦媛说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那么当下的二十一世纪呢?
由云南这些青年诗人的当下之诗和日常之诗,我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一个常年打交道的当下空间重新发现、观照那些隐匿的足迹和更为幽暗的秘密。这类似于博物学家戴维·乔治·哈斯凯尔用一年的时间凝视田纳西州森林里一平方米大小的空间(坛城)所做出的微观学考察。也类似于当年的诗人史蒂文斯在田纳西州放置的那个不同于任何其他事物的修辞的“坛子”,“这灰色无花纹的坛子 /它不孳生鸟雀或树丛,/与田纳西的一切都不同。”现实之诗更多时候指向了一个人的命运感,而命运整体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再只是个人的现实,而是具有了普世性。
由“现实”写作、在场写作、细节化写作来考察,一个诗人更像是一个地方的观察者和考古工作者,他必须具备足够的耐心和足够优异的视力,以凝视的状态“保存细节”。尤其要格外留意那些一闪而逝再也不出现的事物以及携带了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事物,以便维持细节与个人、现实和历史的及物性关联——“当我坐下时,一只萤火虫用闪烁的光芒迎接我。它的绿光忽而升到好几英寸高处,随后在那里逗留一两秒。夜晚的微光仅够我看清这只小虫和它身上的灯笼。绿色的光芒黯淡下去后,这只小虫一动不动地悬在空中停留了三秒,接着俯冲下来,从坛城上空划过。随后它又重复了这一过程:打着灯笼快速上升,熄灭光芒歇息一阵,再从空中划落,一闪而过。”(哈斯凯尔《看不见的森林》)。也就是说,诗人如何延展、拓宽甚或再造一个现实边界是一个重要的工程。这些关乎个人日常性的诗歌,大体是具体化、日常化、个人化的,而这种具体化和日常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诗人应该沉溺于琐屑的日常。恰恰相反,一些诗人努力在反思、超越和拒绝这些琐屑的日常生活的惯性所制造的眩晕与茫然——天鹅绒监狱,尤其是以唐果、杨碧薇等为代表的女性诗歌。她们的诗歌气质和精神方式是冷暖交织的,可以迎向阳光,也能够在隐忍中面对阴郁和疼痛。她们把自己处于安静或者动荡的位置,有时在阁楼上自我取暖,有时又在日常情境中白日梦式的精神游荡。因此,日常生活滋生了精神事件,比如唐果的《一块胶布》:“我在地上捡到一块胶布,/一张白色的、/脸蛋干净的胶布。//我玩似的,将它贴在唇上。/刺激、狂喜、惊讶之后,/我感到恐惧。//我想喝水,可我张不开嘴,/我想说话,/声音只能在喉咙打转。//我向身强力壮的男同事求救,/他使出吃奶的力气,/才将胶布扳离。//我的唇边留下粉红的一条,/你一看就明白,/那是胶布,用纯洁的小手扇的。”
尤其是在当下“日常之诗”泛滥的情势下,一个诗人如何在日常的面前轉到背后去勘察另一个迥异的空间更为重要。物象、心象和幻象必须一起在语言中赋形。作为诗人,必须正视自我认识和体验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必须在诗歌中让更多的环节来拓展自我。“介入”与“担当”有别,“见证”与“作证”不同。“担当”和“指认”就如一个目击者或者犯案者重新被带到现场,他要重新分辨和指认。指认,是再次发现,也是对于旁观者的提请。
这些时代的诗人不仅要抒情言志,还要做一个讲故事的人。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故事的碎片和戏剧化的场景。一代诗人正在发挥着小说家和剧场的功能。布罗茨基曾经说过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笑话讲两三回并不是犯罪,然而绝对不允许在纸上这么做。那么,落实在叙述和讲故事的层面,如何能够避开布罗茨基所说的危险从而能够讲述或者复述“故事”?如果在此次的专辑中找一个与此相对应的代表性样本的话,我想到的是甫跃成的《为了在这家店里吃一碗刀削面》——冷静和节制中潜藏的却是巨大的不安和阴影。甚至当你把这些场景和偶然性事件翻转过来的时候不寒而栗会迎面而至。
为了在这家店里吃一碗刀削面,
我做足了该做的一切准备。
二十五年来,我乘坐无数汽车、
火车、飞机,没有碰上一次事故,
也没有在步行穿过斑马线时
死在车轮底下。
我路过许多城市,到过许多乡村旅游,
一次地震也没有发生,火灾
也总是躲在荧屏之后,逼真地出现在
别人的经历当中。
除此之外,我还保住了健康的身体,
没有稀里糊涂地染上肺炎或者禽流感,
也没有在爬树时摔断一条腿。
我通过了所有必须通过的考试,
顺利地上了高中和大学;
毕业后来到这个地方,有一份工作,
可以挣到养活自己的钱。
现在,我走进这家小店,坐下来,
要了一碗刀削面。二十五年来,
只要稍有差迟,我吃过的面里头
便将永远不包括这一碗。
“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诗人必须具备观照日常事物的能力,而这一观照能力还不只是留意和观察,而应该是驻足,然后蹲下身来耐心察看、抚摸、翻检,而最终呈现在文字中的物象已转换成心象——甄别、过滤、提升、变形。反之,就沦为了临摹、仿真、套用、比附、硬性的二手货色。诗人既是亲历者,见证者,是日常事物的“凝视者”,也是能够抽身离去的“旁观者”“疏离者”。正是在这种介入而又疏离的张力角度中诗人才有可能最为真实地凸现皱褶深处的本相。细节,不是刻板的镜像,而是在写作者的观照中发生了变形。“变形”是为了加深和抵达“语言真实”。里尔克说:“我们应当以最热情的理解来抓住这些事物和表象,并使它们变形。使它们变形?不错,这是我们的任务:以如此痛苦、如此热情的方式把这个脆弱而短暂的大地铭刻在我们心中”。正是“变形”能够重新让那些不可见之物得以在词语中现身。
历史必须当代化,当代也必须历史化,因为每一个写作者都是在“当下”和“历史”之间折返。这要求写作者必须具备以求真意志为前提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有别于考古学,而类似于重述。这能够让那些在历史烟云和滚沸现实中的“死难者”“失踪者”重现复活、现身、说话。由此,我看到了很多年轻诗人在那些已经消逝和即将消逝的事物那里流连、徘徊,低下头来查看。这是一种还原的工作,也是精神征候上的挽歌。那么多的年轻人有着凝重和并不轻松的面影和彳亍的行色。写作者必须经历双重的现实:经验现实和文本现实。也就是说作家们不仅要面对“生活现实”,更要通过建构“文本现实”来重新打量、提升和超越“生活现实”。而这种由生活现实向精神现实和写作现实转换的难度不仅在于语言、修辞、技艺的难度,而且更在于想象力和精神姿态以及思想性的难度。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对于现实写作往往容易分化为两个极端——愤世嫉俗的批判或大而无当的赞颂。我更认可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对现实的态度——“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我们可以确信诗人目睹了这个世界的缺口,也目睹了内心不断扩大的阴影,但是慰藉与绝望同在,赞美与残缺并肩而行。这是一种肯定,也是不断加重的疑问。“现实”从来都不是虚空无着的,这一切都最终要在语言中现身矗立。
说了这么多,诗歌最终只能是“内部的工作”——因内部的流淌而负重。如果说诗歌写作有什么胜利可言的话,那也只能是诗歌自身的胜利。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现工作于中国作协创研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台湾屏东教育大学客座教授。著有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变动、修辞与想象: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无能的右手》《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从“广场”到“地方”——微观视野下的诗歌空间》(上、下卷)《萤火时代的闪电——诗歌观察笔记或反省书》《“70后”批评家文丛 霍俊明卷》《陌生人的悬崖》《怀雪》,合著《中国诗歌通史》《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文学现场对话录》。
责任编辑 李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