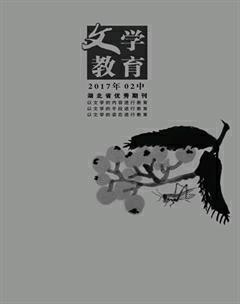清明忆母
又是一年清明,又是飘飘洒洒的细雨。在这样一个孤独的日子里,我愈发想念我的母亲。2007年元月十七日。就在那天,我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全家人的呼唤都不能将母亲唤醒。
母亲去世已经十年了,我一直想写点关于母亲的文字,却发现思绪散乱,不知从何写起。正如诗人桑恒昌所说,“每当我写到母亲,我的笔就跪着行走。”今日想起,思念的痛苦就像一块冷却的烙铁,虽然压在心头,但渐渐失去了灼痛的热度,淫雨潇潇孤独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已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眼前剩下的就只有母亲依稀的身影……
一
1921年,母亲出生在安徽的一个小山村里,排行老末。
母亲十四岁就离开家乡去合肥读书,尝尽了世间冷暖,看遍了人间百态。1946年,母亲从国立贵州大学土木工程建筑系毕业。听母亲说,当时建筑系只有她一个女生。那时的母亲水灵秀美,双眼皮,大眼睛,乌黑的长发飘逸双肩,走起路来,长发就骄傲地飘起来,飘绿了山水,飘出了万种风情,飘活了多少年轻小伙子心底蛰伏地爱情。众多的追求者向她表达爱意,最终母亲选择了憨厚却有着伟大灵魂的父亲。
父亲常常在茶饭之余,望着在厨房中忙碌的母亲的身影,很“诡秘”地对我说:“多亏了我1944年的一次踏山涉水,从重庆颠簸了三天三夜到贵州,正是那几天的春雨,才见到了这么俊俏的媳妇。”然后,他深深地吸一口气,陷入那早已逝去的岁月的回忆中。
那时父亲正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读书。大学四年级的父亲英文出色,又被调去战区给美国人当翻译。母亲和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在西南国立贵州大学。当时正是抗战,父親身穿一袭军装。清癯消瘦的面庞,两眼却炯炯有神,言语斯文,身材高大英俊,一表人才。
初次相遇,父亲激动惶惶,母亲落落大方。媒妁之言把他们牵到一起。彼此一见钟情。父亲是国立中央大学的才子,母亲是国立贵州大学端庄秀丽的大学生。见面寒暄,说不完的话语,道不完的情意。自那以后,他们就开始书信往来。父亲的每封信都情感真挚,信的开头都是“琳妹”,又充满时代激情,很有气势。母亲的每封信的最后都是写上“您的琳妹”。
爱情来得那样意外与突然。一向清高自负的父亲,在不知不觉中就坠入母亲向他张开的那张情网。热恋之后,抗战胜利,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父亲母亲结婚了。
父亲母亲一直珍藏着他们年轻时的结婚照,黑白的,浸渍了时间淡黄色的痕迹。照片上,母亲穿着洁白的婚纱,乌黑油亮长发披肩,嘴角得意地向上翘起。父亲幸福微笑,穿着正式的中山装,留着分头,憨厚而木讷地笑着。
那一段媒妁之言促成的婚姻,却有着让人羡慕的爱情。才子佳人,举案齐眉。母亲懂得父亲,超过他自己。在每一个面临抉择的十字路口,总是母亲先站起出来,替父亲选择方向。婚后,父亲无论是教书还是在部队工作,或转业到地方从事技术工作,从战火纷纷年代到和平时代,他们一路辗转南下,母亲除工作外,把自己所有的心思和精力都放在了父亲和那个家庭上,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撑起一家人的生活。此后,风雨兼程几十年,他们真的再未分开,鹣鲽情深,相濡以沫,伉俪恩爱一生。
二
母亲的一生充满了劳累与辛酸。历经的苦难难以计数,尤其是在文革中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岁月。那时父亲被关在牛棚,被拉去批斗,家中时常有些“革命青年”光顾。家也被抄了。但不管环境怎样变,母亲对父亲的爱一如既往,从没有和父亲分开过,风风雨雨、酸甜苦辣、吵吵闹闹,一起生活六十多年,已经融为一体,彼此相爱一辈子,患难夫妻六十年。
如今,母亲的离去无疑是对父亲的沉重打击。母亲弥留之际,父亲就像孩子一样扑在母亲的身上痛哭。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母亲。母亲一别,就是阴阳永隔。没能实现自己与父亲相伴到老的誓言,带着对父亲无限的牵挂,永远地离开父亲。
母亲走了,父亲的世界在顷刻间坍塌,人在一夜之间更加苍老。正如“夕阳啊,你明天落的时候,稍微快一点吧,你的残光刺得我心痛,你既不肯不去,你就快点去罢,一线的光明刺得我心痛。”这是父亲写给母亲的情诗,也是母亲珍爱一生的诗。
正是因为有了母亲的爱与信任,父亲尽管陷入自身难保的境地,但他始终坚信:党和组织会对他作正确的历史评论。父亲度过了那段最黑暗的岁月,打倒“四人帮”后,父亲平反了,并作为第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再次受到党组织的信任与重用,武汉市规划局党委授予他一支笔。凡重大建设,规划项目必须得到他的审批才可立项、建设。他当选了武汉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2002年,他被湖北省土木建筑学会授予从事土木建设工程工作五十年专家和终身会员荣誉,直到七十岁才从第一线退居二线。
父亲不管经受了多少苦难,付出了多少心血,蒙受了多少冤屈,承担了多少离别,他都毫无怨气。他只是希望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尊重。他的毅力与勇气,都来自母亲深深的爱与包容、理解。
三
今年是母亲去世十周年。这十年,我年年想、节节想、日日想。清晨,一炷香,一盂粥,一碟水果,供奉在母亲的遗像前。那天我打开一只皮箱,里面叠着整整一箱父亲和母亲相识六十多年来的来往信件。微微发黄的信纸见证着他们真挚不朽的爱情,诉说着他们动人的故事——六十年的婚姻、共同信仰、坚守信念、永不放弃。
人们常说,父爱如山,母爱似水。母亲的爱如春天里飘洒的小雨,如青石中流出的甘泉,滋润万物,细微周到。
母亲一共生了七个儿女,只留下了六个。我大姐两岁的时候因肺炎病死,这是母亲一生的痛。为了我们六个儿女,母亲操劳了一辈子,其中的苦与痛,伤与悲难以用语言表达。尤其是在文革那段最灰暗的日子里,我父亲被打倒,关在牛棚,不断地被批斗,家也被抄了。我们子女也受到影响,不能继续升学,先后上山下乡。我哥哥大学毕业去了大西北,姐姐下乡。我16岁去了蒲圻羊楼洞茶场五七干校。我胸怀壮志奔赴广阔天地,并没有太多的惆怅。那天母亲送我到火车站,火车开动那一刹那,我一下子豪情散去,泪流满面……
母亲流泪不停挥舞双手向我告别。我知道那天的火车是从母亲的心上隆隆驰过的。生活的路漫长而艰辛,在这条路上,母亲一直拉着我们的手,不屈地前行,直至走出一条属于我们兄妹自己的路。
几年过去了,她的孩子们逐渐走出了她的视线。我们兄妹六人成家立业,生男育女。她心中装着儿女这一代,还装着孙子孙女这一代。她一辈子的生活目标就是为儿女排忧解难。母亲的腰板弯了,头发几乎全白了。流年似水,我们何尝不是依靠母亲给予的力量在生活,她的单纯、善良、乐观、忧伤、淳朴时时都在影响着我们。我们兄妹六人依赖于母亲而活着,像蒜苗依赖一棵蒜。当我们到了被人估价的时候,母亲她已被我们吸收空了。
没有万贯财富,是一无所有的母亲。她奉献的是满腔满怀恒温不冷的心血供我们吮咂!
母亲,我的老妈妈!我无法宽恕我当年竟是那么不知道心痛您,体恤您。我以为母亲就应该那样任劳任怨,我以为母亲天生就是那样一个忙碌不停而又不觉得累的女人。我以为母亲是累不垮的。其实母亲累垮过很多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我们做梦的时候,几回回母亲瘫软在床上,暗暗恐惧于死神找到她的头上。但第二天她总会连她自己也不可思议地挣扎着起来,又去上班。
母亲常对我们说:“妈是不会累的,只要你们儿女平安,再苦再累,我都不会倒下,这是你们的福分。”我们不觉得什么是福分,都相信母亲是不会垮的,生活对母亲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与爱。
四
前不久我从电视中看见母鱼产子,小鱼孵出。想不到它们竟是靠噬食它们的母亲而长大的。母鱼痛楚的翻滚着,扭动着,瞪大它的眼睛,张开它的嘴和它的腮,搅得水中一片红,却不逃生。直至奄奄一息,直至狼藉残骸……
我的心当时受到极强的刺激。我瞬间联想到长大成人的我和我的母亲。联想到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一切曾在贫困之中和仍在贫困之中的坚韧顽强地抚养子女的母亲们。她们一无所有,她们平凡,普通默默无闻。最出色的品德乃是坚忍。除了她们自己的坚忍,她们无所傍靠。然而她们也许是最对得起他们儿女的母亲!因为她们奉献的是他们自己。想一想那种类乎本能的奉献真令我心酸。而在他们的生命之后不乏好儿女,这是人类最最美好的持久啊!
母爱是世界上最无怨无悔的一种爱。母爱使我的心灵常常受到震荡式的感动。母爱又是极具韧性的,它的强韧程度可以超过自然界的任何一种物质,有时甚至是无限的。
每当我想母亲,我就会不知不觉来到学校老图书馆。
很多人不知道,學校的老图书馆是母亲参与设计的,那时母亲在武汉建筑设计院任高级工程师。老图书馆的建成浸入了母亲的心血。学校新图书馆建成后,我曾拿照片给她看,并告诉她美丽大方的新馆也是武汉建筑设计院设计的,而且主要设计者之一是她曾经的学生。母亲欣慰地笑了,宛如绽开的梅花,唯一遗憾的是由于母亲长期病痛在身,没能亲自来看过去的旧馆和如今的新馆。
母亲谢世的那一夜,是我一生中最短的一夜。我做了一个梦。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母亲坐在椅子上,牵着我的手,我的眼睛寻着她指的方向辨别北斗星,一只只蝴蝶环绕在我身边,抬起我和母亲一起飞行,渐渐消失。醒来的时候,我的右眼皮重重跳了一下,姐姐的电话来了,她哭着说,母亲去世了,快点回来吧。
窗外大雪纷飞,雪花打湿了我的眼睛,寒风吹走了我的希望,等我心急如焚赶到家时,母亲已安静地闭上眼睛。送别母亲的时候,我没哭。当纸钱燃尽,墓碑立起时,我双膝跪在泥泞的土地上,久久没有动,趴在地上听着母亲的呼唤声。
我听到了,其实,我早就听到了,现在还仍然记得。她说,儿女呀,挺起腰板做人吧,母亲在远方会保佑你们的。
这么多年,我一直沿着母亲铺设的路走着,义无反顾,以慰她的在天之灵。
今夜,春雨纷纷,内心深处的思念情结一层层积聚,把我从沉睡中唤醒,让我用心灵,用生命呼唤着她,踏踏实实响响亮亮地喊一声妈,借此纪念逝去十周年的母亲,也平静自己浮躁的心。
(作者介绍:刘爱玉,湖北大学图书馆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