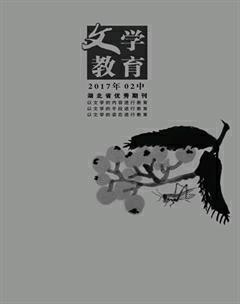女性思维中的“男权意识”
内容摘要:在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的形象不能简简单单的被解读为对男权的反抗和对话语权的争取,她的形象具有另外一层深层内涵。具体来说,李雪莲坚持二十多年的告状,她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洗刷丈夫对自己的污蔑,表面上她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不懈努力,实际上她更深深的陷入男权意识。李雪莲的形象既有对女性思维中的“男权意识”揭示,也有对女性的自我奴化现象深层剖析,以及对权利文化的整体批判和斯德哥尔摩情结现象的深层探究。
关键词:李雪莲 “男权意识” 自我奴化 权利文化 斯德哥尔摩情结
刘震云作为80年代新写实小说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他的作品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1987年创作的《塔铺》是他的成名作,之后的作品《新兵连》和《一地鸡毛》以新写实手法写出士兵人生和官场的另一面;90年代以来他的创作转向故乡系列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乡土流传》以及《温故一九四二》《手机》等故乡小说揭示了中国现当代乡村历时的面貌;新世纪以来,他的长篇小说《一腔废话》《一句顶一万句》、《我叫刘跃进》等,写出了当代人生存的悲哀与困境。
《我不是潘金蓮》出版于2012年。2016年9月改编为同名电影上映(冯小刚执导,范冰冰主演),引起强烈反响。小说从李雪连与丈夫秦玉河的假离婚说起。李雪莲意外怀了二胎,为了逃避惩罚,和丈夫假离婚,没想到弄假成真,秦玉河最终和另一个女人结婚。秦玉河不仅不答应复婚,而且还污蔑李雪莲是潘金莲,李雪莲为了洗刷屈辱,证明自己的清白,坚持了二十年告状。李雪莲最终因为秦玉河的死亡而放弃告状。
李雪莲坚持二十年上访倔强的给自己正名,她的形象既有对女性思维中的“男权意识”揭示,也有对女性的自我奴化现象深层剖析,以及对权利文化的整体批判和斯德哥尔摩情结现象的深层探究。
一.女性思维中的“男权意识”
潘金莲是中国古代极具反叛性特征的女性形象之一,她不在乎所谓的封建伦理道德(“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等),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勇于追求自己的情欲,不断挑战封建伦理纲常。在刘震云眼中,李雪莲与潘金莲具有相似性:一方面她们都是反叛者角色,另外一方面她们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不同之处在于,潘金莲所反叛的是封建伦理道德秩序,而李雪莲的叛逆是为了解脱丈夫秦玉河强加给她的冤屈,她坚持二十多年的告状的最终目的就是证明:我不是“潘金莲”,彻底清洗丈夫对他的诽谤。
李雪莲的人生价值观和潜意识里:潘金莲是淫荡、恶毒、不守妇道的代名词,潘金莲竟然毒死了自己的丈夫武大,又与西门庆风流快活,她完全没有羞耻之心,她是一个有着深重罪孽的女性。李雪莲被丈夫污蔑为潘金莲,于是她想通过告状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并不是坏女人,但是她的一系列行为却是在男权制社会认证自己的“身份”,李雪莲坚持二十年的告状源于男权社会和男权意识对她的影响和压迫,肉体上的压迫可以反抗,精神上的压迫则根深蒂固。从古至今,男性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几乎各个方面,女性都是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女性在潜移默化中不断的接受男性所规定的道德秩序与伦理准则,因此具有了女性思维中的“男权意识”。在人类主导的社会中,一切政治、经济、宗教、法律、道德等都是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而男性话语又恰恰是社会中的主流。刘震云把李雪莲放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为她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在这个过程中,李雪莲独立人格完全丧失,所有的内心欲望被深深地遗忘,她的生存状态完全受制于男权社会。她蜷缩在男权世界的阴影里,虽然经过几次痛苦的挣扎,但最终还是看不到太阳。传统文化的很多观念禁锢了她的思想,压抑了她的欲望,李雪莲一次次的状告无果,表明了传统男权文化对女性生存的强大杀伤力。李雪莲告状的最终目的是想成为男权世界观中的完美女性,她就是要维护自己的名誉,捍卫自己的清白,但她的行为不可避免的陷入了男权思维,最终还是深陷男权所设定的牢笼中,她不得不成为社会和男权意识所赋予她的女性角色,成为男人眼中的“女人”,这进而说明她更加的依附于男权。可以说,李雪莲的一生从来就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过自己的生活,因为作为一个女人,她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女性地位,从到至尾被污蔑为“荡妇潘金莲”。李雪莲其实想成为的是男人眼中的好女人,并且这种观念伴随和控制着她的一生。
二.自我奴化意识
自母系氏族社会解体后,女性主体地位逐渐下降,男性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处于主导地位,女性慢慢成为男性的从属。伴随这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女性屈服于男性权威,结果是:女性的内在主体力量持续变弱,自己的主体意识丧失,渐渐成为男性的附庸,变成男人的奴隶,家庭地位一落千丈,无法摆脱男性的强权压迫。在这部小说中,李雪莲不断受丈夫秦玉河的压迫,不断被奴化,渐渐陷入自我奴化的怪圈之中。李雪莲希冀本身有自力更生的能力,但时刻受到秦玉河与各种官员的逼迫:丈夫抛弃自己和孩子,败坏她的名誉,害的她差点自杀,孤苦无依的情况下选择告状却又受各层官员的推三阻四,无人关照。她始终不能将成为完全独立的一个人,她告状,为恢复自己的名誉不辞辛苦,但最终沦为男权与社会压迫的牺牲品,她不得不依赖与秦玉河与各级官员,完全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不断走向自我奴化的深渊。
女性自我奴化的过程其实是从内心接受了自己比男人低一等的现实。当女性行为和话语权由男人决定时,女性永远生活在男性话语权的阴影当中。女性行为的设定完全由男性控制,男性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女性,进一步泯灭女性的主体意识,使女性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女性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并在不知不觉中令女性成为了男性的奴隶。受丈夫秦玉河的影响,李雪莲的精神世界扭曲、变形,削弱了自我力量,她泯灭了自我发展的意识,完整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发展也遭到破坏,终其一生无法摆脱自我奴化。从状告丈夫秦玉河到告倒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她一生的目标为自己正名—“我不是潘金莲”,最终因丈夫的意外去世而变得无足轻重,历经痛苦挣扎、理想最终幻灭。她要求为自己正名,希望恢复自己名誉被官员无一例外地拒绝,在现实世界中挣扎、苦斗,撞得头破血流,甚至牺牲了青春。故事的最终结局是李雪莲一生都活在男性为她所设置的观念牢笼中。
父权制替代母权制以后,女性地位在家庭中的逐渐失去主导地位,财产由男性掌控,男性可以支配女性的一切,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甚至成为能男性的奴隶,长期受制于男性。自五四之始,要求女性自由解放的呼声在中国越来越高涨,时至今日,透过女主人公李雪莲的境遇,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思考当代女性的现实处境问题。为了保住丈夫的工作,李雪莲即使意外怀了二胎,想通过假离婚的方式逃避惩罚,丈夫秦玉河假戏真做,导致李雪莲被抛弃,并且的污蔑她也说是潘金莲。秦玉河当着许多朋友的面羞辱她,污蔑她是潘金莲,不遵守三从四德,没有羞耻心。这一指责的原因竟是当年成亲时,李雪莲不是处女。在男权制度依然盛行的今天,李雪莲显然是无辜而又弱小的。当男人可以不顾道义良知胡作非为时却还在要求女人的贞操与妇道,这是女性的可悲,也是现实的可憎。女性自我奴化的思维如同一条沉重的铁链拴在几千年封建社会女性的身上并延续至今,女性自身失去了个性和主体意识。
三.权利文化对女性的压迫
权力,是刘震云小说的主题之一。纵观刘震云的小说,无论是他早期的《塔铺》还是90年代末的《故乡面和花朵》,小说的主题一直没有间断对权力的探索。
刘震云的小说具有权力自觉的权力批判意识,通过人生的众生相揭露社会的黑暗,并且展现了畸形权力扭曲人性的悲剧。刘震云始终深入剖析权力给人类精神带来的灾难,展示权力对人精神的茶毒和心灵的栽害,无情地撩开权力文化的面纱。李雪莲坚持二十年的告状无果源于权力对她的无情摧残和压迫。小说中,作品中的官员说是要为人民谋利益,实际上他们只关心自身的仕途,这些人高踞社会上层,无视李雪莲的一次次状告,他们是玩弄权力、玩弄人民,以满足个人欲望的小人。这部小说无不揭示着官员对底层人民的欺压,剖露出权力对人的压迫。
主人公李雪莲为了纠正一句话,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而坚持了二十年的上访路,其实主人公李雪莲的要求并不高,只是想通过告状来证明离婚是假的,想恢复自己的名誉。她只想要一个能相信她,肯倾听她的人。但是在李雪莲告状的过程中,董宪法、荀正义、史为民、蔡富邦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极尽所能,或恐吓,或欺骗,或威胁,滥用手中的权力,极力推三阻四,不想摊上这一个“烫手的山芋”,甚至动用暴力手段,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把她关进看守所,逼得李雪莲走投无路想要自杀。到最后,李雪莲也没有摆脱权利对她的压迫,一步步被权利所掌控、迷失了人生的方向、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通过对李雪莲这一人物形象的灵魂透视,作者表现出对当下中国中国权力文化的深刻探究,在此反思的基础上,刘震云对官场和官员腐败的种种丑恶现象以及权力文化笼罩下的官员种种丑陋行为进行了揭示和批判。在对权力文化批评和反思的同时,刘震云通过这部小说向我们提出了着一个问题:中国自古就重视权力的运作,无论国家权力还是地方权力,都是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尚方宝剑。在物欲横流、价值观念错位、精神世界迷失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疯狂的追逐权利,为了权利不惜刀剑相向,不顾他人死活,最终,人们应该走样摆脱权利文化的桎梏呢?就像小说中的李雪莲,她作为生存的个体,芸芸众生的一员,终其一生都活在权利文化的阴影之下,官员对她的压迫对她生活和命运带来了痛苦和磨难。我们看到,弱小的人肉躯体在强大官场权力面前的无能为力,权力是控制人们的祛码。有了权力,便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人的身上。权力打破了李雪莲原有的平静生活,她失去了自我与自由,不再对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在这部小说中,所有的人不知不觉都被权利所掌控,所奴役。权利变成了官员作威作福的工具。
四.斯德哥尔摩情节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一词起源于瑞典,1973年8月,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突然闯入两名全副武装的劫匪。劫匪扣押了4名银行职员作人质,与警察对峙了6天之久。6天后,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3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被警方营救出来后,人质非但没有控诉绑架者,相反却为劫匪辩护,对警察的调查取证工作也采取坚决不合作的态度,致调查取证工作困难重重。这些人质之所以表现出如此怪诞的行为,是因为他们患上了一种心理疾病。从此,人们把这种心理疾病命名为“斯德哥爾摩综合征”。按照心理学分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一种病态的心理。
小说中李雪莲与丈夫秦玉河也有着这种类似的“绑架”与“被绑架”、“施虐”与“被施虐”的关系。通读小说,我们会惊讶的发现,李雪莲对秦玉河的爱,绝不是正常的男女的情感,而是一种病态、的畸形的情感。李雪莲长期经常遭受丈夫的精神暴力,被秦玉河诬陷为“潘金莲”但她没有选择彻底离开,对丈夫心存幻想并有依赖情绪,她没有选择结束这种虐待关系,陷入了“绑架者”迷恋“被绑架者”、“施虐者”迷恋“被施虐者”的怪圈中。在李雪莲和秦玉河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秦玉河是伤害李雪莲最深的人,也是对李雪莲感情践踏得最狠的人。李雪莲中途本有过放弃告状的打算,准备找秦玉河和解,但是喝酒上头的秦玉河当着众人的面说:“你是李雪莲吗,我咋觉得你是潘金莲”。“李雪莲如五雷轰顶。如果不是伸手能扶着墙,李雪莲会晕倒在地上。她万万没想到,秦玉河会说出这种话来。今天之前,她折腾的是她和秦玉河离婚真假的事情,没想到折腾来折腾去,竟折腾出她是潘金莲的事。”为什李雪莲受尽了丈夫的折磨,但在心理上对秦玉河依然有强烈的依恋?第一个原因是受封建礼俗和道德观念的影响。古代封建社会李雪莲一直处于弱者的地位,她依赖于丈夫秦玉河,对丈夫有着从一而终的依赖性。在李雪莲与秦玉河感情中,李雪莲从始至终都依恋于,秦玉河,她陷入了一种思维陷阱,找不到其它出路。在男性占有绝对话语权的时代条件下,她对爱情与婚姻的认识和理解上有某些局限,对丈夫具有一定的依赖性。第二个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对于李雪莲来说,离开自己曾经爱过或仍然爱着的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李雪莲为了这个家庭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她牺牲了自己青春,也没有尽到一个当母亲的责任,自己的儿子从小到大无人照顾,正是因为过于倾入了过多的心血,才越难做出选择离开秦玉河。因此李雪莲对压迫残害自己的丈夫不但不恨,反而对秦玉河产生了依恋的情绪和依赖的情结,李雪莲陷入疯狂与纠缠中,李雪莲面对丈夫秦玉河的污蔑和背叛,她为了自己的爱情,倔强的要给自己讨个说法,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牺牲了青春,疏忽了孩子,荒芜了天地,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到最后却换来了状告无果,孤老终生。这只能说明李雪莲患上了爱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五.结语
这部小说具有自觉的文化批判意识。刘震云一方面透过官场的众生相揭露官场的黑暗,另外一方面也展现了权利文化扭曲人性的悲剧,在《我不是潘金莲》这部小说中刘震云着力刻划了李雪莲这一犟女形象, 并赋予这个形象以较高的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他对女主人公精神世界进行发掘,展示了她的痛苦、抗争,更重要的是在女性的男权意识、女性自我奴化、权利文化的整体批判以及斯德哥尔摩情节等问题上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刘震云以人文关怀的态度关注当代社会现实,深入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对人们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①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长江文艺出版社》P64,2012年9月
②《京华时报》,《刘震云小说探讨荒诞底线》,2012年8月
③高翔.《反叛潘金莲的反叛—我不是潘金莲的解读》,《名作欣赏》2014.1月
④高芳艳.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人物形象的女性主义解读,《文本分析》,2014.4
⑤倪素平.《对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的人物形象解读》,《短篇小说》,2014.9
⑥刘震云.《潘金莲是前所未有的女性形象》,凤凰网,2012年9月
(作者介绍:郑稚丁,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研究生)